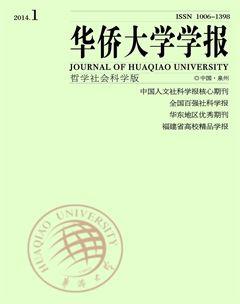走出身份建构的迷津
摘要:美国非裔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中塑造了布鲁斯特社区的黑人男性形象。通过解读几位代表性的黑人男性形象,试定义黑人男性气质,进而探讨黑人男性在种族主义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如何走出身份建构的迷津。
关键词:格罗丽亚·内勒;《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种族主义男权文化;黑人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I7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4)01-0118-08
美国非裔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1950-)曾以处女作《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1982)轰动美国文坛,该书不仅获得美国图书奖最佳处女作奖,而且被拍成电视剧,深受众人喜爱。笔者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发表论文《姐妹情谊:一个被延缓的梦——解读格罗丽亚·内勒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可供对比参考。《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出版16年之后,内勒重访该社区、再次提笔书写发生在布鲁斯特街的故事,出版了小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1998)。在该作品中,内勒重新审视布鲁斯特街这些曾经令女人伤心欲绝的黑人男性,向读者展示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痛苦、挣扎与进取。
一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是一部由若干故事构成的小说。小说中的男性人物除了布鲁斯演奏能手杰罗姆外,其他都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出现过。小说的开篇故事《黄昏》通过一位叫本的黑人男性作为社区居民的代言人向读者讲明布鲁斯特街的境况。小说的中心部分由本、
杰罗姆兄弟、巴西尔、尤金、莫兰德·伍兹、贝克以及阿布舒这些男性人物的故事组成。最后小说以《清晨》这篇故事收尾,以初升的太阳寓示布鲁斯特街的希望。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的主题以问题呈现:“何以界定美国黑人的男性气质?”美国黑人男性的“身份”话题较为敏感:奴隶制时期,大部分的黑人男性身为奴隶,受奴隶主压迫,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无从建构自己的身份。奴隶制废除后,获得自由的黑奴以为他们可以享受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部分黑人男性得以参政。然而随着大重建结束、联邦军队从南方撤走,志在以极端暴力手段维持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大肆迫害黑人,对许多黑人男性采用私刑。同时,许多南方庄园主不满黑人享有权利,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变相压榨黑人,譬如实行佃农体制。此外,南方部分州声称没有足够资金建造监狱而采用犯人租赁体制,即让犯人外出当苦力,参加修铁路、建工厂等工作。在该体制的掩盖下,许多黑人常被认为品质低下、道德败坏而被捕去当劳力。表面上法律认可了黑人,而现实中黑人的权利却未能得到保护或很好地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使很多黑人男性为自己的身份及生存感到困惑、迷惘。美国黑人的身份在吉姆·克劳主义的压制下,在白人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压迫式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美国黑人进退维谷: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并实现真正的自我?《男人们》不仅反映了布鲁斯特街社区黑人男性的身份建构,而且揭示了美国社会黑人男性在身份建构的迷津中如何寻求出路。小说的男性人物在其动态的、互动的、具体的身份建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男性气质:有些男性陷入身份建构的泥潭,比如伍兹、贝克;有些男性挣扎于身份建构之网,比如巴西尔、尤金;还有些男性人物最终走出身份建构的迷津,比如本、阿布舒。这些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过程表明:在种族主义男权文化体制的压制下,黑人男性真正自我的实现并非易事;唯有自我肯定、以坚定的精神力量抵制外在压迫及内心的迷茫,唯有彼此交心、相互帮助且团结一致,唯有牢记滋养自己的土壤、以爱奉献于自己的同胞及社区,美国黑人男性才能在与社会、家庭、他人的关系互动中不断实现自我的价值。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析《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通过本的故事揭示外在压制对身份建构的影响;通过尤金的故事展示内在身份认同所产生的身份建构危机;而来自问题家庭的巴西尔、伍兹、贝克以及阿布舒,他们的故事从正反两面揭示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迷津与出路。本文最后以布鲁斯特街理发店常客格瑞兹的故事引出结论:在种族主义歧视下的黑人男性唯有自尊自爱、相互帮助并团结一致,才能在与社会、家庭、他人的关系互动中实现自我。
二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里的主要男性人物——本的故事包括家史、成长历程以及现状。本的家史主要讲述了祖父琼斯的故事。少年琼斯因妹妹被监工暴力诱奸致死而深受打击。黑奴们为妹妹下葬时,琼斯大声抗议却被母亲甩了一巴掌:“闭嘴!孩子。听见没有?闭嘴!做一个男人。”[1]16。此后,琼斯便缄口不言,成了一个藏怒宿怨的男人。琼斯经常拿着《圣经》却又不读;每到复活节,他就去教堂,因为他认为这时的上帝是复仇之神,能够带来毁灭。
祖父琼斯的故事让读者想起《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汤姆。汤姆叔叔的形象被作者斯托夫人塑造成一个能够忍耐、以德抱怨的基督式黑奴;汤姆从《圣经》中寻求救赎,以自己的善良维持黑人的精神并以自我殉难的实际行动唤起白人的同情。白人种族主义男权文化要求黑人男性必须默默承受一切,这样才算是个男人。非裔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总结了种族主义男权文化意识形态对男性气质的定义:男性必须具备经济实力、权利、控制力并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强者,用物质标准衡量成功,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甚至以怒火或暴力掩饰自己的脆弱。然而,见证了诸多残酷行为、遭受数不清的歧视与压迫却要保持沉默、坚强承受,这样是不合理的。琼斯不愿意当汤姆叔叔,他祈求复仇之神毁灭白人的罪恶。
琼斯年少时,奴隶制盛行,黑人不被当作人;他不仅亲眼目睹妹妹的惨剧而且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是男人的话,就要忍。换言之,黑奴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唯有默默地承受才能存活。本从对祖父的回忆联想到自己的一生——实际上从奴隶制时期到现在对黑人男性的定义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本一开始就说:“我现在都快68岁了,回首自己的人生,其中一件最令我困扰的事情是不管在哪、不管遇见什么人,都没有人叫我:先生。”[1]11。
本原本在孟菲斯市一家旅馆当清洁工,后来,在妻子艾薇拉的劝说下回到农村安家,成了白人地主克莱德的佃户,即收益分成的佃农。佃农体制是美国内战后在南方发展起来的一种体制。解放后的黑奴没有资金购地,于是他们与白人地主签约、向他们租地及劳动工具,待庄稼收成时佃农按约向地主缴纳租金或农作物。从理论上讲佃农体制使地主和佃户双方皆受益,但实际上地主经常欺诈黑人农民致使他们连年欠债,身心皆受到摧残。非裔美国作家艾丽丝·沃克的代表作《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生》(1970)深刻揭露种族主义的变相剥削和压迫——南方佃农制造成小说黑人男性的悲剧。本一家三口勉强维持生活;跛脚的女儿给地主克莱德当清洁工却遭到凌辱;本意欲反抗克莱德却遭到艾薇拉的阻止与讥讽。最后,本只能无奈地看着女儿受辱、离家出走当妓女。
本的一生以及他在社会、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展示了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典型且令人心酸。处于社会中的本,由于黑皮肤而备受歧视。种族歧视使黑人无法享受与白人同等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就业权利。本所从事的大都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他清洁痰盂、擦鞋;最高理想是当搬运工,而在他看来,这样的工作已经比种田好多了——虽然得不到尊敬却不至于被累死在田地里。本知道“像我们这样的黑男人除了摘棉花之外,在外头没有多少活儿让我们干;有些人只要能够逃脱农活,叫他们干什么都愿意”[1]18。然而,处于这种境况的本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更可贵的是本拥有理想,当搬运工的理想虽看似微不足道,但本认为这个理想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实现,理想的实现就是对自己的肯定;此外,本对妻子艾薇拉能读能写的欣赏表明本对知识的渴望。奴隶制时期,黑人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而非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如果来自底层、不具备经济基础,同样也无法享受学习的权利,然而,知识、教育对一个人的认知、发展以及身份的建构却有重大意义。
不幸的是本没有及时发现妻子艾薇拉的真面目——被白化的种族主义者。比如,艾薇拉认为:“上帝赋予这个世界的:凡是白的都是好的;凡是黑的都是令人鄙视的”;艾薇拉甚至不喝黑咖啡,因为“这只会让我变得更黑”[1]22。种族歧视不仅令本无法完整建构在社会中的身份,而且由于艾薇拉的种族主义态度使得本在家庭中的身份也变得残缺不全。家庭中的本所担当的角色是丈夫和父亲,而这两个身份都让他认定:自己身为男人是不完整的。艾薇拉经常责备本:一、没有经济实力;二、性无能。这两点成了本的致命伤,因为男人必须能够养家,不让妻儿受苦;一个男人的性欲证明其男性力量,即男子汉气概。艾薇拉的指责令本深感自己男子气概的丧失;无法保护女儿的事实令本更加认为自己无能。白人地主克莱德的嘲笑不仅粉碎了本作为父亲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与位置,同时也“阉割”父亲本人,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应该是强大的、具备威望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家庭重要成员之一的艾薇拉却宁可相信压迫者克莱德也不愿意支持本的反抗:“下次克莱德先生过来时,你别死不吭声——听见没有?你要感激不尽,你这可怜的傻瓜,你要感激克莱德先生对我们的恩惠。”[1]26。来自妻子的指责使本失去最后的反抗意识,而女儿离家出走当妓女的事实可谓彻底摧毁了本——作为一名黑人男性——对自己身份的建构。最后,本以酒买醉以缓解对女儿的愧疚感。
身为底层劳动者的本在社会中难以实现自身价值,他的家庭角色也未能得到认可。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本的身份建构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年老的本成了布鲁斯特街的观察者和哲学家,带着对人生的痛彻体验,本悟到布鲁斯特街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艰难。为此,本提出自己的见解:一个男人如果得不到肯定或支持,不管他的生存环境如何,他都难以体现自我价值;不管男人的境遇如何,他对生活的态度及希望非常重要;失去自尊的男人是无望的,而一个男人唯有具备精神力量及情感基础才能抵挡来自白人的歧视,才能建构完整的真正自我。[1]7可见,颇似智叟的本在体会布鲁斯特街黑人男性的同时建构自己的身份。
男主人公本的角色——不管是社会中的佃农还是家庭中“无能”的父亲——反映了外在压制对其身份建构的影响;而布鲁斯特街的另一个黑人男性尤金,他的身份建构过程主要体现为身份内在认同的危机,即男性身份建构与性属或性取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尤金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以反面形象出现——一个意欲抛弃妻儿的懦夫;《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中的尤金则向妻子希尔解释真相,同时也让读者明了事情的缘故:尤金的同性恋倾向。
尤金的自我陈述向妻子、读者展示了他的内心,即对性取向的困惑所引起的痛苦挣扎。尤金表明他一直努力做一名称职的丈夫、父亲,然而他的性取向引发一切变故。尤金偶然间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尤金认为男同性恋者不是男人而是性变态患者,所以他一再隐瞒真相并不断在家里闹事。男性身份建构与性别认同有关吗?男同性恋者是不是男人?这些问题严重困扰尤金。一方面,他无法舍弃妻儿;另一方面,同性恋情绪又不断冲击他的内心,即唯有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才能体会到人格的完整。因此,在家庭与性取向之间彷徨的尤金不知如何建构自己的男性身份,于是对妻子恶语相向。实际上,尤金的这些消极反应表明他潜意识里所接受的是强制异性恋体制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即一个男人必须为人夫、为人父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男人。
罗伯特·康耐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把男性气质分成几类,其中一类是从属性男性气质,即同性恋男性对异性恋男性的从属。康耐尔认为:“在当今欧洲、美国社会中突出的情形是异性恋处于统治地位,同性恋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情形比起文化对同性恋或是男同性恋身份的蔑视还要严重。大量重要的实践使同性恋男性屈从于异性恋男性。”[2]107男同性恋者经常遭遇这样的事:“它们包括政治与文化上的排挤,文化上的污蔑(在美国男同性恋者现在已经变成了宗教攻击的主要象征性目标),合法的暴力(例如依照鸡奸法律条文规定的监禁),街头暴力(恐吓到谋杀),经济上的歧视以及对个人的联合抵制。”[2]107在美国,属于霸权男性气质的是异性恋白种男人,而这些白种男人宣扬:“男性气质是用来界定白种人、中产阶级、青壮年和异性恋男性的,是其他男性要效仿的。”[3]124康耐尔及金梅尔的评述表明同性恋男性在美国社会现实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身为同性恋者意味着在社会中将受到排斥、压迫。尤金无法认可自己的身份,但他认为来自社会的认可或许能挽救他,于是他不断回家扮演丈夫、父亲的角色,他需要这两个角色来证明自己是男人。但随着事情的进展,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充当一个“男人”:一、自己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二、由于被解雇,他丧失了养家的经济实力。因此,对于自己男性身份的建构,尤金陷入窘境。
故事里的配角奇诺生动地折射了尤金的困境:奇诺做过变性手术意欲让自己变成女性,之后又停止变性过程,结果变得不男不女。主流文化对性属的划分呈男女二元对立,即一个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奇诺的变性尤其是终止变性表明他抗拒主流文化对自己性别的认同、意在自我定义。深知主流文化偏见的奇诺警告尤金,建议他尽早向妻子说明真相以免悲剧发生,然而,尤金无法摆脱主流文化的桎梏,最后落得家破人亡。
男主人公本和尤金他们的身份建构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困难重重,尽管他们自我反思并继续努力实现自我,但他们的故事说明挑战并抵制种族主义男权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首先是自我的肯定,然后积极应对外在的压制。这样的挑战与抵制在现实中并不容易,需要坚持与不断探索。《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中的其他男性人物巴西尔、伍兹、贝克以及阿布舒的故事则反映了黑人男性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探索”笔者为“探索”一词加引号的意图是:“探索”一词本意是对幸福、成功等美好事物的寻找、追求,但对“幸福”、“成功”这些概念的定义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定义是被扭曲的、消极的。。这四位男性人物皆来自问题家庭:巴西尔、伍兹成长于单亲家庭;贝克的家境贫困;阿布舒则寄养他人篱下。他们四人的成长、生活经历不一样,而他们的身份建构过程从正反两面告诉读者:种族主义男权文化体制下的美国黑人不仅生存艰难,而且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奔波于社会、家庭之间的黑人男性如果无法挑战种族主义男权文化意识形态却又仿效美国式的成功,如果忘记滋养自己的土壤而不能为同胞服务,如果无法审视自己的内心同时用坚强的意志抵制种族歧视对黑人男性的偏见,那么建构真正的男性自我将更加困难。
巴西尔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同样是个反面角色——他在保释期间畏罪逃跑导致母亲玛蒂的房子被没收。内勒让巴西尔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中作为正面人物出现意在表明:一、打破对黑人男性的成见、向读者展示巴西尔是如何成为一名独立自强、懂得反思、有责任感的成熟男性;二、法律与法庭制度的不公对巴西尔的身份建构所带来的危害。
少年巴西尔沉溺于母爱而自私、不负责任。畏罪逃跑后的巴西尔学会了上进、独立;在母亲墓前忏悔的巴西尔懂得反思,发誓要成为一名负责任的父亲以求救赎。于是,巴西尔和凯莎结婚并收养了她的私生子,但凯莎却向警方告密致使巴西尔被捕。待巴西尔服刑归来,两个孩子不是进了拘留所就是自我封闭。巴西尔男性身份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他意欲担当的父亲角色,但这样的家庭角色在法律和法庭制度的干涉、制约下变得难以实现。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明显体现于司法体系中。譬如先前提到的犯人租赁体制,该体制下的犯人十有八九是黑人。他们被捕的原因一般是:大多数黑人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审判案子的司法人员一般是带有种族歧视的白人。[4]23白人在法律方面倾向于执行对黑人不利的双重标准;而警察机构则成为专门用以对付黑人的工具,而且心照不宣地假定每个白人都有权监督黑人的言行。同样法庭也施行双重系统:法庭对白人犯罪嫌疑人过度宽容,但对待黑人犯罪却充满了种族偏见,量刑过度并制造出很多不公的案例。巴西尔便是这个不公制度的受害者。早年事件纯属正当防卫,但是巴西尔仍然认定自己会被判刑而逃跑。晚期的巴西尔已经成为社会、家庭的有用之人,但他仍然没能逃脱白人法律对他的不公。实际上,法庭没有重审早期案件便对巴西尔量刑,而且一判就是六年。长期服刑使他无法抚养孩子,导致了父子之间的隔阂以及家庭机能失调。司法体系的不公制约着巴西尔的身份建构,他的努力化为乌有。值得庆幸的是一再受挫的巴西尔仍然充满责任心及意志力,他努力挽救养子杰生和艾狄的决心同时也暗示了他将继续建构真正的自我。
巴西尔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他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定位为成功的父亲,然而在法律的制约下他的身份建构并不理想。那么,如果黑人男性具备权力和地位,他的自我价值能否实现?伍兹的故事把男性身份建构的视角转向中产阶层,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黑人牧师如何变相为自己争取权力与荣耀。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伍兹在神职的伪装下玩弄女性;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里,伍兹则利用一切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伍兹同样成长于单亲家庭,母亲拼命挣钱让他就读好学校,认定伍兹终将成为一个伟人。从小被灌输这样思想的伍兹深信自己一定会成为非凡人士。为此,伍兹决定加入神职。此后,伍兹致力于自己的仕途,靠着自己的外表及谈吐获得社区内外众多信徒的崇拜。伍兹的身份建构看似成功:主教这个职位让他享有地位、权力、财力以及威望;他可以参加选举、市政会等等,在公共领域里人人爱戴、羡慕。然而,伍兹的成长历程及心理动机则表明他的身份建构实为“美国式成功”或者“美国梦”所歪曲。美国梦的一个主要理念是靠自己奋斗而成功;对男权制的男性而言,实现梦想意味着享有物质财富及政治地位。美国梦源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白手起家,发展为一名实业家而且在政界声名显赫;此后,“自我造就者(self-made man)”及美国梦成了美国人追求的神话。随着享乐物质主义及消费时代的到来,美国梦蜕化为金钱、地位及物质享受的代名词。伍兹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担任神职、为社区居民讲道的本质不是为黑人大众服务,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目的步入白人主流上层社会。伍兹为了建大教堂与执事班纳特争执这一情节便是很好的说明。伍兹建教堂的目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声誉,从而在市政选举上竞选成功;而持反对意见的班纳特深知这是对黑人财力的挥霍——建教堂的钱本可以用来成立基金为社区的孩子提供奖学金,或用来成立一个社区中心为社区青年或贫民提供服务。在班纳特看来,神职实现了黑人男性的尊严,但反过来也需要黑人男性的责任感为黑人社区服务。在与班纳特的对比之下,伍兹的虚荣、自私自利表明他并没有实现真实的自我,他外在的身份地位也许摆脱了白人种族主义的殖民,但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没能摆脱白人的殖民思想。在“美国梦”的浸染下,伍兹脱离了滋养他的黑人土壤,成了白人主流文化的代言人——伍兹当选之后决定拆毁布鲁斯特街社区,改建成中产阶级式住房,向白人靠拢。
本、尤金以及巴西尔的故事反映了大多数黑人男性属于蓝领阶层,他们不是工人就是农民、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相比之下,伍兹身为牧师,神职从某种程度上使得他避免外在的压制与剥削。然而,伍兹没有自觉抵制种族主义男权文化制度,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他而言仅仅是牟取私利,他与其他美国黑人脱离却向白人靠拢。表面上受人爱戴的伍兹实际上是白人种族主义光环下的傀儡。这样的傀儡除了伍兹外,还有街头流氓贝克。不像高高在上的伍兹,贝克没有权力和地位;他流窜于破落街道,以暴力谋利。
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贝克为了证实自己身为男人的控制力和另外几个街头流氓暴力轮奸了女同性恋者洛瑞安妮。贝克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中仍是反角:他贩毒并枪杀手足,甚至还感谢上苍给他勇气开枪,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1]129那么,作为社会的危害分子贝克何来身份建构?身为街头流氓的贝克确实无可取之处,但他堕落为恶棍的过程却向读者展示了在白人主流文化影响之下的黑人男性对男性气质的曲解,即认为只有获得金钱、权力以及威望才能成功建构身份;即使需要暴力等非法手段达到此目的也不退却。
早期影响贝克对男性气质理解的是他的父亲。在贝克看来,父亲无用、无力养家;而当贝克把偷窃、抢劫或贩毒得到的钱拿回家时,父母出于需要用了这些不义之财。贝克因此更加鄙视父亲,认为父亲一生缺少的就是金钱、权力以及威望。影响贝克的第二个人是他追随的贩毒头头、一个号称“大王”的犯罪头领。在贝克看来,“大王”是个大写的男人(“The Man”)。[1]126“大王”同时拥有金钱、地位和威望,成了贝克的偶像,贝克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大王”。因此为了表示对“大王”的忠心以及显示自己的勇气,贝克弑杀手足。
街头流氓贝克让白人种族主义者更有理由称黑人为“坏黑鬼”。种族主义歧视阻碍黑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并且威胁到黑人的生存,黑人因此遭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饿。白人对黑人的迫害必然导致黑人对白人的仇恨,致使越来越多的黑人违法者出现。白人深感来自黑人的威胁,对黑人的自然反应是“坏黑鬼”。然而,心怀仇恨的黑人却认为“坏黑鬼是一个蔑视白人的黑鬼,使人想起什么是男子气概”[5]55。但“坏黑鬼”只是蔑视白人,他们认为自己反抗不了白人,因此把怒火洒向自己的同胞并以此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贝克便是这样的坏黑鬼,他的坏不是针对白人,而是在黑人社区为非作歹。贝克没意识到父亲的贫穷是种族压迫的结果,同时他也不明白“大王”实为压迫者,施行的是变相的压迫。种族主义男权思想影响之下的贝克认为黑人男性身份的成功建构意味着物质享受及恃强凌弱,他知道自己无法像美国白人一样的成功,但他却渴望过白人一样的生活,他知道自己无法控制白人,于是便转向同胞、以压迫者的身份非法行事、以坏证明自己的存在。殊不知,这样的身份建构最终将走向自我毁灭。
回顾本、尤金、巴西尔、伍兹以及贝克的身份建构过程,他们作为男性的自我并没有得以真正的实现:本、尤金及巴西尔于失败后学会了反思,懂得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种族主义男权文化制度,他们努力挣脱身份建构之网以求实现真正的自我。相反,伍兹和贝克则深陷身份建构的泥潭,他们在种族主义男权意识形态的浸染下无法认清黑人男性身份的实质。那么在黑人男性的身份建构中何为出路?——阿布舒的故事向读者透露美国黑人男性走出身份建构迷津的希望。身为社工的阿布舒活跃于社区中心、积极帮助社区居民解决问题;他运用智慧与背叛社区的伍兹对抗;当得知布鲁斯特街社区最终还要被拆迁、自己的努力没有成效时,他仍然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决心继续服务于黑人同胞。
阿布舒同样成长于问题家庭:父亲无法忍受外界压力而回家施暴;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而找他人领养。阿布舒的养父母待人非常吝啬;阿布舒忍饥挨饿,最后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成为一名社工。尽心服务于黑人社区的阿布舒建构了真正的完整的自我。他懂得如何正确定义男性气质:“不管报酬高低,从事能够让你快乐的工作,然后让自己的家充满爱。”[1]140。在阿布舒看来,对黑人男性气质的正确定义应该自我审视、自我肯定,与此同时挑战并抵制种族主义男权文化体制及意识形态。譬如,男权文化体制认为男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养家而不是享受工作的乐趣及从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因此挣钱养家成了男子气概的衡量标准之一;另外,物质上的成功也被用以断定自我价值的实现。然而,阿布舒却选择了让自己精神上、情感上得以满足的工作,即做一名社工服务同胞,而不像伍兹终日忙于仕途。又譬如,男权文化体制认为体力、控制力以及暴力属于男性应该具备的气质,而阿布舒则懂得与社区居民相处、交流。阿布舒还尽力保护社区孩子,尤其是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不让他们流落街头变成贝克;此外,如同教堂执事班纳特,阿布舒致力于社区的福利与团结。在身份建构过程中走出迷津的阿布舒向读者表明黑人男性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积极面对现实生活、自尊自爱,以坚定的精神力量抵制种族歧视,以爱奉献于社区。
三
美国黑人男性形象经常在非裔美国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譬如,读者耳熟能详的艾丽丝·沃克的代表作《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生》和《紫颜色》、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和《所罗门之歌》。这些作品所塑造的黑人男性形象往往不完美,然而,非裔女作家们并非故意丑化黑人男性形象,她们通过揭示黑人男性的缺陷来披露种族主义歧视的残酷与危害,更重要的是她们意在向读者展示黑人男性的成长与探索。同样,格罗丽亚·内勒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这部小说中通过本、尤金、巴西尔、伍兹、贝克和阿布舒几位典型黑人男性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美国黑人男性自我界定及身份建构的历程。作者内勒在小说《理发店》这一章节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叫格瑞兹的黑人男子。格瑞兹是理发店的常客,他曾经有份好工作、有个美好的家,但如今像疯子一样流落街头,社区居民不是嘲笑他就是退避三舍。格瑞兹失败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讲,但他逢人便说三句话:“我是个男人。”“我一直努力着……”“我是个男人啊!”[1]160格瑞兹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他这三句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实际上总结了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艰难。格瑞兹最后的自杀让社区的黑人男性醒悟:他们本不该嘲笑或躲避格瑞兹,因为他是他们的兄弟,他们本该帮他克服困难。作者内勒通过这一情节向读者揭示在种族主义歧视下的黑人男性不仅要自尊自重,而且应该相互帮助并团结一致。唯有如此,黑人男性才能在与社会、家庭、他人的关系互动中不断建构真正的完整的自我。
参考文献:
[1]Naylor, Gloria. 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M]. New York: Hyperion, 1998.
[2]Cornel, R. W. Masculinities[M]. Trans. Liu Li, et al.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s Publishing House, 2003.
[3]Kimmel, Michael.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M]∥Ed.Harry Brod, Michael Kaufman.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1994.
收稿日期:2013-10-12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级课题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文学研究”(021660110007)
作者简介:林文静(1981-),女,福建漳州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小说、妇女文学、族裔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