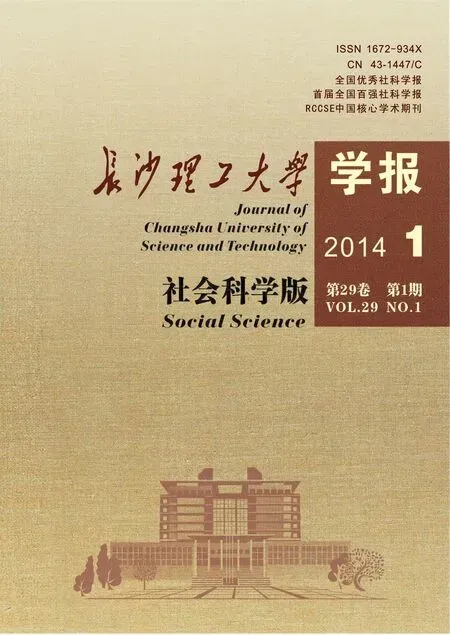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唐土红,张正一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唐土红,张正一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
善;政府公信力;伦理
所谓政府公信力系指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在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反映的是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更是构成解释和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研究政府公信力,首先要回应公信力续存的基础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将之定位于权威、观念、象征和竞争上,有学者把暴力、组织、理论视为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也有学者把公共利益视为政府公信力的基础,还有人认为,政府信任的基础在于公民“同意”。但以上有关政府公信力的基础,遵循的路径均是“政治→法律”或“法律→政治”范式。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法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基础之外,还有其存在的道德基础。这一点,也为中外理论家达成共识,即使排斥伦理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也认可非暴力的价值,他认为,暴行不能“每天重复”,“给人恩惠可以一点一点来”。也就是说,没有伦理道德作为支撑的政府是难以获得民众信任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本人认为,“善”是型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一、“善”与政府之“善”
“善”是政治伦理的核心范畴。“善”究竟为何物?从辞源意义分析,中文“善”由“羊”和“口”型构,即羊入口为善,借人之欲望类比理义之善,孟子“可欲之谓善”便具此意。孟子还从伦理规范论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熹还对儒家传统进行过注释,“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认为羞恶之心是基于道德认知基础上的一种内疚和评价。
在西方,善“good”源于拉丁文“gout”,意即“适合”、“有用”或“有益”。对善的探讨一直是西方传统伦理的聚焦点,一直吸引了众多思想家的眼球。苏格拉底将“善”视为一种秩序、和谐与理性的契合体,要求人们追求“最高的善”,柏拉图把至善厘定为“善理念”认为它是“最高善”。亚里士多德将善视为目的的存在物,激励人们追求善果,他指出:“每种记忆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是以善为目的”[1](P1-2)伊壁鸠鲁从人的感官感觉出发,把善付诸于快乐“只有当我们痛苦而无快乐时,我们才需要快乐;当我们不痛苦时,我们就不需要快乐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2]宗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则把善规定为上帝的意志善,是引向幸福生活的一种力量。如奥古斯丁认为,“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份。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3](P127),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3](P128)。阿奎则说:“人们在尘世的幸福生活,就其目的而言,是导向我们有希望在天堂中享受的幸福生活的。”[4]元伦理学家摩尔也把善视为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认为伦理学首先要探究就是“什么是善的”,但遗憾的是,他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他说:“‘善’是一单纯的概念,正像‘黄’是一单纯的概念一样:正像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的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的。”[5](P13)“如果我被问到‘什么是善’,我的回答是:善就是善,并就此了事。或者,如果我被问到‘怎样给“善”下定义’,我的回答是,不能给它下定义:并且这就是我必须说的一切。”[5](P12)
时代不同,人之理念情趣不同,对善的理解亦不同,但相异之中亦有共性的元素,即善即好的、有益的事物。即便是当前我国流行的有关“善”概念,也传承了人类这一共性元素。如罗国杰先生给定的善的定义是:善就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对社会的有价值的行为。那么,什么是善?我们认为,善说到底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范畴,即正当的、合理的,对社会、他人和自身均有正价值的事物和行为。作为“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之善,其对象并非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人民大众。因而,较之一般之善,政府之善有其更高的道德要求,它要着眼整个社会,光耀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群体。政府之善在价值层面指向了人类的生存向度,在政治层面则体现了人之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更加完善。我们说,政府是善的,意味着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增进公民福利的理念及其相应的正当行为。就政治社会而言,政府只有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采取正当行为落实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取得积极成效,才谓之善。
二、“善”作为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在政治社会,“善”是政治生活的起点,也是政治生活的终极归属,善更是获得民众认可和信任,型构其公信力的价值基础,因为:
首先,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所谓优良政府,简言之,就是值得民众信赖,能够引领民众走上优良生活的,追求终极善的政府。公共行政伦理是为“范围更广泛的‘全体居民’而不是为自我、家庭、小集团或一帮人的利益服务”[6],对“公共善”的追求是检验政府及其管理者是否合德,能否值得公众信任的根本标准。从道德本性上看,政府也应是追求“善”的共同体,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有论述。他们认为,城邦其实就是对人类的最高目的和理念——“善”的追求。柏拉图认为,个人只能在城邦生活中才能取得善的德性,城邦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德性和幸福,为人们实现善创造条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社会团体建立的目的都在于完成某种“善业”,求得某种“善果”。城邦作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最高最广的“善业”,谋求至高的“善果”。“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7](P3)“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为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7](P138)奥古斯丁从人对上帝的信仰出发,也将追求“至善”视为人类政治生活永恒的价值目标。思想家尽管对善的理解可能存有差异,但对善价值追求的意愿却高度同质。现代社会,公共行政在本质上也是政府追求“公共善”的活动,因为政府治理说到底就是通过调整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这一过程就其道德实质和价值归宿而言,即是“公共善”的实现过程。如果背离这一价值目标,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便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就此,有学者也断言:“当行政权力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时候,行政权力就是真正的公共行政权力,由此而来的行政管理就是真正的公共行政。相反,行政权力如果只为少数人或者某个行政领导者服务,那么行政权力就退化或者异化为封建腐朽、黑暗落后、专制残暴的绝对权力或者私人化权力,由此而来的行政管理就只能是恶政或暴政,根本就没有公共的实质。”[8]
其次,善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政府要获得民众信任,首先就得回应民众道德期待,被民众认可。政府只有追寻“善”的理念,为民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和产品,满足民众的需求,才能够被民众认可,赢得政府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古希腊政治理性主义者认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需要经过论证,没有经过论证的政治权力是不能得到民众信任和认可的。如何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善”知识论证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亚里士多德则将政治学和伦理学都归结为实践性的科学,他认为实践的研究,即关于人可以实践、可以获得善的研究,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科学。在他们眼里,政治本身就是追求善的,而政府之善是天下之大善。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政治之善都要满足人们以物质生产生活为基础的最基本的善,同时也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使政府之善不断发展进步。因为“在使社会政治理性化,法治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决不可忘记根本,忘记制度应有的发端,我们也许还得一次又一次地把社会政治方面的规范、把法律的规范重新带到出发点加以审视,看它们是否偏离了这一出发点,偏离了多少,并予以适当的纠正。”[9]卢梭还提出了“公意”理念,并将之视为政府最高的善,而这种善也是公民共同意志的结果。“公民有义务在共同达成的同意的基础上服从法律和管理制度,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有义务服从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共同利益而为自己规定的法律。”[10]政府之善体现了人类集体理性的结晶,对其善的拷问反映了人们对政府行为模式的共同期盼。政治生活需要最“基本的善”维系人们生活,需要正义之善来平衡发展中的冲突。以此意义而言,政府的道德使命其实也是对具体善的实施、开展和完善。善是政府存在的基础,是政府得到公民认可的前提。政治善理念通过其普遍规范性内在地型构着合法性的社会秩序和合法性的政治制度,政府只有将“善”视为政治生活的原初责任,成为人们构建优良生活的必备元素,政府才具备为民众认可的合法性。
再次,善是政府赢得民众信任的伦理基础。政府信任的伦理基础在于政府如何运用权力,是将权力指向公益还是指向私利,这其中权力就存在一个价值取向和归宿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善的理念是一切政治生活的出发点,也是其价值旨归。政府对善理念的回应和落实,涉及到政府的合法性,关系到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倘若政府在政治生活中不能捍卫善的价值,不及时回应和落实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公共行政将失去灵魂。政府公信力建设其实也是将“善”引入政府治理中,使其主动接受善价值的规导,在行政活动和行政过程中及时回应民众的价值期待,从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良性互动的桥梁,使民众在政府德治的智慧中生长出对政府信任的力量。政治善的力量,犹如罗素所言:“在漫漫的黑夜中,人们渴望一座光明灯塔的指引,这就是明确的信仰、基础牢固的希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能够超越一切险阻的沉稳的勇气。”[11]对“善”执政理念的追求,我国儒家早有阐释,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就是善政理念的结果。孟子还提出,“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可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政治“善”的意义与价值,统治者如要赢得民众信任,就须善待百姓,用“善”理念感化而非强力统治民众。致力于城邦“至善”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城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道德原则是公民有需要城邦存在的愿望和公众支持城邦的力量。“一个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2](P88)也就是说,公民信任和自愿服从是城邦存在的必要条件。而民众信任的基础则在于城邦对“善业”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追求善,并且城邦善较之于个人善更重要。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12](P7)“一种善即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13]只有城邦善才能满足“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天性,使人们过上“优良的生活”,延续城邦发展。政治之善作为政府与公众关系模式中最基本要素,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政治心理倾向。它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中,又现实化为一种应然的政府伦理准则,表征着政府对终极价值的应然追求。因而,它是民众对特定政治价值的敬仰和人们发自内心的强大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说,政治善为政府行为选择奠定了道德合理性的风向标,决定着人们对现有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正是从这种意义而言,善是政府赢得民众信任的伦理基础。
最后,善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人天生就是不断发展自己,追求优良而幸福生活的动物。何谓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理性生活,“人的幸福我们指的是灵魂的一种活动”[1](P32)。毫不忌讳地说,幸福是人追寻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我们的各个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12](P130)“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P19)那么,政治的目的又何在?这是理论家,特别是古典理论家热议的话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追求某种“善业”,完成人之本性,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既然所有的知识与选择都在追求某种善,政治学所指向的目的是什么,实践所能达到的那种善又是什么。就其名称来说,大多数人有一致意见。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那些出众的人,都会说这是幸福,并且会把它理解为生活得好或做得好。”[1](P9)“优良的立法家们对于任何城邦或种族或社会所当为之操心的真正目的必须是大家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12](P348)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天性是趋向政治生活的动物,个人品性的完善,优良生活的获得只能在城邦生活中才能得以实现。“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生活’”[12](P7)。亚里士多德将善划分两类,即具体的善(善事物)和最终的善(最高的善);将政治学视为最权威的科学,认为政治的终极目的就是追求最高的善,并把这种最高的善规定为具有自足性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是人之自然本性——追求幸福的结果,而国家的目的也是要促进人们过上优良自足的幸福生活。社会契约论也认为,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人之生命、财产和自由等自然权利不受侵犯,使人们过上安定有序的幸福生活。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从最高善思考国家目的的话,那么,社会契约论者则是从具体善来解读国家和政府构建的目的。“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段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14]人天生也是神往和追求至“善”的幸福生活的动物,政府的设置则契合了人之幸福与发展的需要,使公民与政府找到了共识性的伦理话语。
自国家和政府产生以降,善开启了人们对优良政治生活的美好向往,成为人们所期盼的古老而又弥新的理想政治管理理念。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善始终成为广大民众对优良政府的美好向往和期盼。为了将善的政治理念付诸于实践,思想家还设计了诸多善的政治管理模式,将是否以实现公民利益和掌权者的“品质”与“知识”去界定政体善恶。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至善”理念,多少带有某种“圆梦”情怀,似乎一直在重复“乌托邦”的断想。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商品拜物教与物的奴役化日益明显,在人类社会谱系日益功利化、功能化的今天,“金钱和权力逐渐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媒介,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行动的理论范式”[15],人们愈感意志的泯灭,方向的迷失,“人们越来越疏离于他们自己制度的内在原则。所以,问题是这种疏离是否能够被克服,如何克服,以及如何弥合社会文明传统的裂痕。”[16]如何拯救这个价值迷失的世界?如何调节、规范、和引导人们生活?如何重振政府“公信”?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政府“善”的回归。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103.
[3]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
[4]阿奎那.阿奎那政治学著作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86 -87.
[5]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美]特里·L库伯.行政伦理学手册[M].马塞·得克公司, 1994:1.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邱霈恩.行政权力关系的主要构成与内涵探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4):31.
[9]何怀宏.良心与正义的探求[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103.
[10][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4.
[11][英]伯特兰·罗素.自由之路[M].李国山,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381.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
[14]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133.
[15]吴琳.试论善的理念是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J].行政与法, 2006:60.
[16][美]李普曼.市场与逻辑[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30.
[责任编辑 陈浩凯]
The"Goodness"of Government:On the Ethic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ANG Tu-hong,ZHANG Zheng-yi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Government credibil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win the public trust of the masses through its own trustworthiness.In the modern society,government credibility is the barometer of the public to test the credit of the government so that it has attained the general concern and extrem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all countries.However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the academia have been bound up mainly in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In fact,apart from this viewpoint,there is also an ethical foundation,which is called the"goodness"of the government.The"goodness"of the government is the value appeal of a good government, the premis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ublic,as well as the elements for the consensu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To revitalize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the crucial thing is to appeal to the return of the"good"government in the depth of people’s heart.
goodness;government credibility;ethics
B82-051
A
1672-934X(2014)01-0046-05
2013-11-2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X069);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1YBA004);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1B009)
唐土红(1976-),男,湖南临武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学研究;张正一(1988-)男,河南郑州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