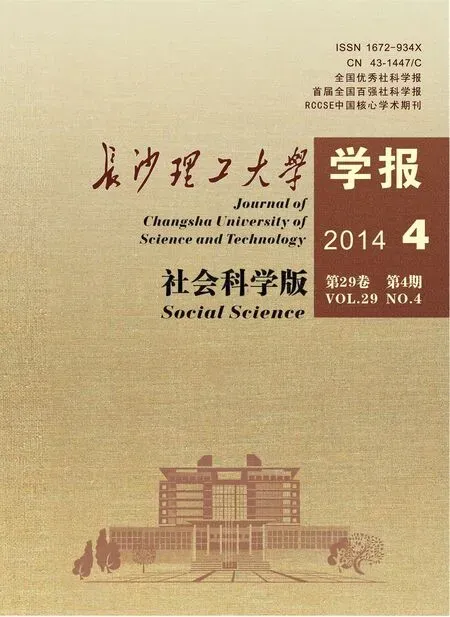互文性视野下的《苍蝇》兼及穆旦文学史形象
杨金彪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国古代“互文”指“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这种前后句意义互补的修辞手法,笔者用这个词不采用这个意思,而是借用法国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即涉及两个或以上文本之间的错综现象。这一概念是她从巴赫金理论中推演出来的,从伊哈布·哈桑对狂欢的界定来看,狂欢化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所以笔者就以众说纷纭的《苍蝇》为例,“综合”一下这两种相近的理论,在互文性的视野下观察穆旦诗歌中的狂欢性。显然,这是借助他者视角来获得关于“自我”的某种特性。这种借助是必要的,就像巴赫金所说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限度。”[1]
一、讨论的由来
穆旦广泛学习过西方诗歌,因此有很多西方的因素,前人多已论及,但是从“搞笑”而不是从严肃方面表述的,尚不曾见,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1975年的《苍蝇》。《穆旦诗文集》316页有这么一个注释,说该诗是1975年6月25日抄寄给杜运燮的,信中说:“《苍蝇》是戏作……我忽然一个上午看到苍蝇飞,便写出这篇来”。只是对“戏作”这一太简单从而不利于发掘其深刻内涵的定位,批评家们是怎么也无法认同的。易彬认为“穆旦在文革后期的诗大致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 《苍蝇》、《退稿信》、《黑笔杆颂》等讽刺意味很浓的作品,它们在语言上是直白的,与他先前的讽刺作品相类,是穆旦对生活非诗意的直接反击。”[2]在另一个地方,易先生认为“苍蝇对于世界的‘好奇’感也最终升华到意义追问的高度。”[3]程光炜认为“《苍蝇》里有波德来尔式的审丑倾向,深藏是对荒谬现实的调侃。”[4]“调侃”一词很到位,但并没提醒它包含的“有趣”的一面。显然,这与“审丑”这一前提有关。因为,对苍蝇表示关切甚至喜爱,是否一定就是“审丑”,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张宜雷以《一只并不简单的苍蝇》为题,进行了逐行分析。发现了穆旦对待苍蝇的两重性,从而理清了一些谬见,比如认为苍蝇就是指江青。他是这样提到调侃手法的:“由于文体的区别,诗歌更重形象表达而不便像散文那样直说,作者又出以调侃的笔法,这就使许多人弄不明白了。”[5]可谓一笔带过,调侃手法的唯一效果似乎只是使人不明白,似乎和“狂欢”这样“有趣”的效果扯不上联系。张先生旁征博引,不仅是在和周作人的显出对苍蝇双重态度的散文提及调侃,而且提到周先生那篇《苍蝇》、布莱克的《苍蝇》、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苍蝇诗,等等,但没有进行文本对照解读。周作人那篇《苍蝇》是对苍蝇较为纯粹的怒骂诅咒,爱惜的层面是从“流氓”变成“绅士”后才具有的,张文的“双重态度”其实是对周进行历时性的总括论说而非基于共时性的“具有”考察,表述存在令人误解的因素。小林的诗又是纯粹的爱惜。笔者只比较穆旦与布莱克。所以如此,穆旦倾心布莱克很久了,且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别人合译过他的诗,说是受其影响可谓铁板钉钉。邱景华写过一篇《读穆旦〈苍蝇〉》,提到“在我看来,穆旦的《苍蝇》与布莱克《苍蝇》有一种‘互文性’。把握‘互文性’,才能读懂穆旦的《苍蝇》。”[6]这正是笔者要做的,似乎撞车,但与他不同,笔者主要分析其中的狂欢性,而对邱先生“其实,这首诗并不是戏作,而是深意存焉”的解读策略不做恭维。相信穆旦再世,一定会很高兴终于有人遵照他对写作状态的回忆即他自己对自己诗的“有趣”的定义来解读他的作品吧。
二、“游戏”的“互文”
“游戏”是布莱克这首诗歌的关键词。
和布莱克起首呼唤苍蝇一样,穆旦也是,但接下来的叙述逻辑却大大不同了。在布莱克的第一段,是“我”占有绝对优势的,轻轻的一抹,就把苍蝇夏日的游戏给取消了,这是主客体对立的形式。用游戏来定位苍蝇的生活方式,肯定已对深爱其诗的穆旦发生了潜移默化作用。但第二节,来个令人吃惊的180度主客体倒置:“我岂不像你/是一只苍蝇?/你岂不像我/是一个人?”这里,不仅“我”的优势被倒空的具体问题,而且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玄思高度,即:我的生命本身也像苍蝇一样,不过是在进行一场游戏,而这游戏会被“命运”轻轻抹去的。这样,苍蝇乃是作为人的一个象征而存在。这样解说就为下文为什么不出现对“你岂不像我/是一个人?”进行具体阐发提供了理由。因为,作者的思维并不是对位式的。这一段的“对偶”是个枢纽与过渡。这样,主客体的换位过程中发生了生命的纽结,从而为下面的主客融合做了预备。下面三节是围绕“我岂不像你/是一只苍蝇?”展开的。“因为我跳舞,/又饮又唱”保留着人的生活形态,像苍蝇的游戏一样的生活形态。“直到一只盲手/抺掉我底的翅膀。”“直到”一词表明无知,也表明不屑和坚定。“抺掉我底的翅膀”是像我当初无心的抹去苍蝇的游戏那样随意而又偶然的,对我这一个体是残酷的毁灭,它是“一只盲手”的动作。这里不是在指责而只是表明我抹去苍蝇时也是一只盲手。“盲”似乎含有“盲目、无常、偶然、冷酷甚至无耻”等诸多模糊的意味。它表明对那只无法抗拒的命运之手或者上帝之手的隐在的不满与反抗,以及无所谓的接受。在表明我如何像苍蝇后,底下两节综合讲做怎样的苍蝇:“如果思想是生命,/呼吸和力量,/思想底缺乏/便等于死亡;”表面上看与前面的都没有关系,但我们读了末节就会恍然大悟:“那么我就是/一只快活的苍蝇/无论是死,/无论是生”这里暗含的意思是我是有着超越人生苦难的思想的,无论生死,都不能改造我的“快活”。这种思想,无疑是类似于酒神精神的,纵酒狂歌,面对苦难和毁灭也不改狂欢之态。
而穆旦这首诗,主客体关系较为“暧昧”,虽然字面上看主客似乎分得很清楚。一方面,一直是我在看,采取“梅尼普讽刺”中“交谈式演说体”在对苍蝇讲话,讲它的生活和遭遇。另一方面,讲述中却不知不觉的融进了自我,“我”的生活体验。与布莱克采取“稳重”的体式(四句一节,工整对称)不同,穆旦采取了参差体,叙述逻辑也不像布莱克那么有条理,没有从一件具体的事件出发进行玄思,而是从具体到具体,完全以“我”的观察和兴趣的顺序来叙述。叙述语气也不是布莱尔那样从对话转向独语,而是一直保持描述和问询的对话姿态,玄思的“清除”使得小诗更加亲昵无间。“苍蝇呵,小小的苍蝇,/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在阳光下飞来飞去,”一唱三叹的调子表明正如他在给杜运燮信中所说的,是“我忽然一个上午看到苍蝇飞,便写出这篇来”这样的“感物起兴”。其构思方式不是蓝棣之《论穆旦诗歌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中着重探讨的第三种方式,即以理念为出发点,通过艺术想象捕捉意象和细节,也即穆旦在分析《还原作用》时说的那种方式。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方式受西方影响最深,和中国传统拉开了距离而成为他创新最多的,也是他最在意最能表现典型的穆旦性的,所以与之不同的《苍蝇》的构思则不被他平常那么看重而大力为之,只是在闲暇偶尔为之,因此是一种言说节日,一种没有任何精神负累的话语狂欢。如果用王昌龄“诗有三思”的说法,穆旦的诗是“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的“取思”,而《苍蝇》、《退稿信》、《演出》之类可能就是“感思”,当然,这里“寻味吟讽”的不是“前言古制”而是现实生活场景。这是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的“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不是先深思熟虑了再去寻找意象,而是在现实物象(苍蝇)的启发下率尔操觚,所有的思想感情都是在写作中,即与苍蝇生活场景在笔下成形的过程中“心物互动”产生的。这样,如果非要说里面有什么深意的话,那也是无意识的内含而非着意的表现。“自我表现说”、“时代悲剧说”、“对苍蝇双重意识说”之类“并不简单”的解读都只是一种捕风捉影的过度阐释,没有进入这首诗艺术精神的核心。当我们不是用既定的概念或者深刻的解读模式而是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自身(如果我们还对自己的生命抱有信心的话)来接触这首诗歌,可能就不会非要把它往形形色色的严肃而重大的主题中去规训、套用了。
我们看到,一开始是忽然看到一只苍蝇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很好玩,于是来了兴致,提笔就在纸上“记下”自己当时兴致盎然的所见所感,思想暂时逃脱伊克希翁苦刑,甚至那以前的苦难在这一刹都变得面目和蔼充满笑意。“谁知道一日三餐/你是怎样的寻觅?/谁知道你在哪儿/躲避昨夜的风雨?”我承认这些关心是真实的,但承认也到此为止。从句式一泻千里的“畅快”而言观察言说者的态度更像是“好奇的”和“有趣的”而非凝重严肃的追问,“怜悯同情”一类的解说只能说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或表现核心。“世界是永远新鲜,/你永远这么好奇,”既承续开头被好奇打断的“飞来飞去”,也开启下面的描述。语调欢畅而毫无停滞,可以想见当时诗人绝非凝眉苦思,而是李白式的淋漓酣畅、意气洋洋。“生活着,快乐地飞翔,/半饥半饱,活跃无比”,让人想到布莱克那首诗的末节,一种酒神精神。接下来的部分更让我们领略了这种精神在生命困境中的光彩,明白了尼采在《偶像的黄昏》所作的界定,特别是当我们把他者对自己的“厌腻、掩鼻、猛烈的拍击”当成一种悲剧来理解时。“悲剧永不能替叔本华意义上的所谓希腊悲观主义证明什么,相反是对它的决定性的否定和抗议。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7]如果说寻觅三餐、躲避风雨带有作者生活经历的无意识投影,那么,苍蝇的遭厌与受击也有作者往日体验的变形映射,甚至社会状况也可以隐括进去,但所有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般的在里面隐现,不可做实,而且不是小诗精神指向的焦点,而是引发这一焦点即狂欢的因素,或曰深厚的现实与精神“背景”。“东闻一闻,西看一看”“我们掩鼻的地方/对你有香甜的蜜”“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你也来歌唱夏季”以调侃的而非严肃的笔调活画出苍蝇的活跃,那样的富有生命力,惹人“喜爱”,同时也是对把苍蝇与作者生平有意无意划等号的释读倾向的文本拒绝。“我们”与“你”的相对表述体现出“人类意识”的“觉醒”,表征着诗人自我其实是不能当成苍蝇隐喻的本体来决定此诗的表意指向的。有人不顾这里人称代词的对举,发掘其中微言大义,认为是象征穆旦五十年代的正道直行而受打击,恐怕是牵强的。“歌唱夏季”拉伸了布莱克的“又饮又唱”,在这一件事上表意更为丰富,“承受拍击”则把布莱克“无心地抺去”来个颠头倒尾,仿佛此诗是在布莱克前面写的,从而对时间的暴政进行了一次嬉笑的反动。同时,正如对艾略特以麻醉病人比黄昏那个隐喻不满而在《蛇的诱惑》用鞭子加强其力度一样,这里也对那“无心”造成的“轻轻”进行了“猛烈的”强化。这一强化里可能暗含了自我生命被压制打击的体验,尤其当用“幻觉,理想”来吸引时,很容易令人想到他五十年代初排除万难回国,“企图”大干一场,现在才发现那不过是“幻觉”。
《苍蝇》中的主客体的界限是极为模糊的,尽管在语言上还很明确。就其只是“暗含”而言,这不能证明该诗仅是自况,或主要表意倾向是自况,也不能否定这里面的调侃、戏谑意味。或许,主体(我)的生命体验和客体(苍蝇)的经验在这里被揉二为一了。诗歌在话语形式上依然保持着你和我们的主客体对照状态,从来不曾像布莱克以苍蝇自况:“直到一只盲手/抺掉我底的翅膀。”可见,主客体关系在潜意识里,或者照克里斯蒂瓦说的“生殖文本”里是若即若离、时分时合、隐约模糊的;在语言层面,即“现象文本”里,却是比较明白的对立。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作者采用的什么障眼法,那太胶着于一种深刻的解读模式了,我宁愿从文本自身说这是自然,是作者随兴所致。如果用穆旦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里提到的“血液的激荡”和“脑神经的运用”来衡量,则穆旦的偏于前者,布莱克的更重后者,倒也兼有前者。相形之下,卞之琳的《投》就是比较单纯的玄思了。卞先生曾说自己不怎么玄思,但是他的诗歌在当时是最玄思不过的了,这里所以不拿更知名的《断章》来说,是因为在结构上,《投》宛如布莱克《苍蝇》前两节的截取而去掉其中的“感情色彩”,表现为“去个性化”的主客体倒置的玄学。相较而言,穆旦这首最少玄学色彩而最多性情,生命本有的灾难与痛苦都被强大的酒神精神以活波的调侃纳入节日狂欢之中,这里,没有日常生活那第一生活的重大性严峻性紧张性,而是完全的放松和不拘形迹,连苦难和敌视都可以拿来嘲戏。学者们分析出的众多“深意”,只能说是这首诗的“潜台词”(这里只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并不意指“真实含义”)或曰背景,而非表现的核心或重点。说是“戏作”,穆旦确乎和拘泥于重大严肃考虑的学者们不同,一下子就抓住了自己那随手所写之物的灵魂。
三、解读的“游戏”、文本的“声音”及穆旦的文学史形象
萨莫瓦约就参考性提到一种“开放式的互文性”,即巴赫金所言话语的社会互动关系,即在社会话语表意实践中的参与或曰“文化参与”。在那个高大全的时代,这首诗的“参与”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像这日常生活小事(看到一只苍蝇)缺乏表现的合法性,在题材上通不过时代要求。至于表达方式的“调侃”更是与时代对庄重肃穆的绝对化要求南辕北辙。被参照的是铺天盖地的强势时代话语(而不只是某一具体文本),这注定了它只能是“地下文学”、潜在写作。在巴赫金看来,严肃是官方造成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精神架构的必然要求,是毫无自由可言的。而民间的笑则是对这种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反抗与解构,是一种维护自我与自由的生命行为。于是,在这首诗里我们读出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思考,一种别致的态度。当然,对这种特殊思考与特殊态度的表现,在这首诗中并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无意识,或者说,一种自发的流露,一种前意识的暂时失职。这种“和时代抗衡”的意义和“深意存焉”一样,更多的是由一种解读策略得到的,只是一种解读的“游戏”,不能不让人联系到穆旦的经典话趋向,而不是文本自己的精神指向。嬉戏只是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时代严重性的消解,而我们却不能据此断定此诗当然就是为了这一消解而产生。就文本而言,也许嬉戏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这嬉戏里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内容(所谓“深意”),但它们是看作使这种嬉戏更为“有力”,更为有意义(不是有用)切合文本呢,还是看成对嬉戏的否定,从而使之不必考虑更合理呢?“没有一个时代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只要我们抛开太多预设的观念,而带着尊重的态度更多的倾听一下文本也就是这首诗本身的声音,就会认识到“具有”远远不等于“只有”或“就是”。
这样,我们就从《苍蝇》中发现可以用巴赫金诗学中“狂欢化”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定位的诗质。“‘狂欢’,这个词自然是巴赫金的创造,它丰富的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等。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语言的离心力,事物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至少指游戏的颠覆包孕着甦生的因素。”[8]如果我们遍读《穆旦诗文集》的话,就会发现为数不少具有此种诗质的诗歌(笔者拙文《论穆旦诗歌的狂欢性》就此进行了详述)。穆旦的人生也表现出与之相当的诙谐、幽默等方面,①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这种诗歌素质,在其诗文中也有数次“提示”。②不过,客观的说,穆旦现存的诗中,没有一首是纯粹的搞笑,即使是《退稿信》、《九十九家争鸣记》、《时感四首》的第一和第三首、《苍蝇》这样“通篇搞笑”的诗,也都含有不可忽略的严肃性。从这个角度讲,穆旦诗歌大都是“庄谐体”了。按照诗质中严肃与“搞笑”的显在比例进行分类,一些严肃性明显占优势而狂欢性虽有而不显著的篇章不如称之为“严峻体”,如《野兽》、《蛇的诱惑》等;一些两种素质比较均衡的可以称之为“庄谐体”,这里又得区分出两个小类,一个小类是“亦庄亦谐”那种两种素质虽均衡但比较内在化、似乎混融难辨、矛盾不那么激烈突出的诗歌,如《诗八首》、《爱情》等,另一小类是两种素质都很突出,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示出一种淬火般的凝合,如《时感四首》的第一首、《伤害》等,这一类是最特别的,然而我却无法为它们命名,因为“亦庄亦谐”一词不能传达这类诗歌的那种严峻与狂欢胶着的感觉,所以笔者宁愿暂付阙如;另一些就是狂欢性占据明显优势的“狂欢体”,如《退稿信》、《苍蝇》、《九十九家争鸣记》等。还有一些诗,狂欢性几乎很难找到,这样的诗歌数量不是很多,如《冬》的第三和第四首、《友谊》、《赞美》等,笔者不把它们归入上述任何一类,认为大致不必在其中寻找什么狂欢性。这固然显示出狂欢性在描述穆旦诗歌素质方面的局限,但也表明,笔者并没有为了证明穆旦诗歌中存在大量狂欢性就非要指派每一首都存在这种诗质,同时这种局限也不能否认“狂欢化”在描述其它穆旦诗歌时的有效性。
这里强调穆旦诗歌的“狂欢”素质,并无否认其诗歌中的严肃、认真维度的意思,更不是想把穆旦诗歌定义为狂欢诗或搞笑诗,而只是揭示长期以来穆旦诗歌研究中对穆旦诗歌素质被严重掩盖、忽略的一个维面,进而反思穆旦那一副过于严肃、认真从而失真的文学史形象。
现代文学史给穆旦画了一幅面孔严峻的肖像:综观数年来的穆旦研究,无论是讨论穆旦诗歌中现代的“我”,还是探究里面的“上帝”、抑或争论其中有无宗教意识,又或为其中的西化特征或“非中国性”大动干戈,又或研究其语言革新和表现形式与技巧的新锐特别,都只是对穆旦诗歌中严重的或者说严峻的、严肃的方面进行挖掘,却没有甚或不愿“看见”那个“搞笑的”穆旦,没有对其行文的“不正经”、“不认真性”进行探究,这样,就不能平心静气的、辩证的、完整的对待穆旦的诗歌素质,不能充分看到穆旦诗歌更广层面的构成肌理和更为多样的魅力。这里的“不认真、不正经”不是指其做诗态度的马虎,而是指不遵循语言的外指性常规而另有所指、别有意趣,指一种对待世界人生的“游戏”态度,一种可与深刻的悲剧精神相互表里的“狂欢”,诚如文本分析所显示的那样,此一视点主要是就主体对其吟咏对象的精神姿态这一向度而非对待诗歌本身而言。一首《苍蝇》的文本剖析固然不足以“颠覆”这一牢固树立的文学史形象,但至少可以在促使人们对这一神圣化、教条化的形象产生怀疑方面提供微小的启示。
[注 释]
① 如他的第一篇文字《不是这样的讲》就含有诙谐、幽默成分,而不是单纯的、硬生生的讽刺。又如在他少年把杜牧《清明》读成词的样子、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所记二人在北师大参加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相遇情形都让人感到他个性中“搞笑”的一面。
② 如“要紧的是含泪强为言笑”(《诗》),再如“不可仅为了故事‘有趣’而庸俗地‘有趣’下去”(《我上了一课》)表面上是否定自己诗歌的“有趣”,但只是为了政治上蒙混过关,真实态度未必如此,反而实在的揭示了他做诗的某种一贯态度。
[1][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344.
[2]易彬.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J].书屋,2002(3):20-25.
[3]易彬.穆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22.
[4]程光炜.当代中国诗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7.
[5]张宜雷.一只并不简单的苍蝇[J].名作欣赏,2007(9):61-64.
[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47d3b01000dgi.html.2013-05-16.
[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334.
[8][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性[A].//王瑾.互文性[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