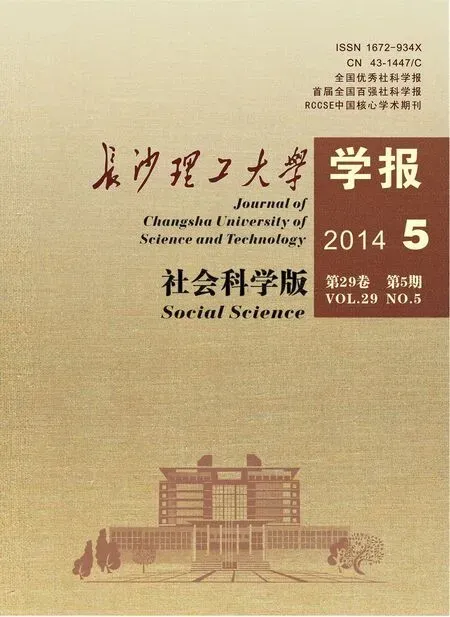论卞之琳1940年代的文体选择
陈 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论卞之琳1940年代的文体选择
陈 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1941年前后,伴随时代经验的急剧变化,卞之琳自觉诗歌写作的文体危机,并进而向小说文体转变,创作了如今只剩残篇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从诗歌到小说,虽然文体形式发生改变,但是由诗歌写作所呈现的思考方式依然贯穿于小说创作之中。一种认识论式的精神追索,必然要求作者在小说中容纳更为丰富的细节呈现,于是叙事的碎片化与场景化就不仅是一种美学原则,更与“客观性寻求”的思考原则有关。但是,当思考原则转化为行动追求时,卞之琳却遭遇更深层的思想危机,劳动以及行动的丰功伟绩似乎完全取消了沉思的意义。
卞之琳;创作;文体选择
一、引论
正如卞之琳晚年所追述,亦为研究者所探察, 1941年前后卞之琳自觉诗歌写作的文体危机,并进而向小说文体转变,创作了如今只剩残篇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
研究者努力发掘《山山水水(小说片断)》的意义,既有从政治意识与叙述主体关系入手探究小说的精神史价值,①亦有从创作者文学观念的承继角度剖析诗歌文体与小说文体的内在联系。②但是,这部长篇小说残片呈现的美学风格依然让人困惑,正如研究者所谈及的,“在叙述上,它们充满并不能推进叙述的生硬的谈话(《春回即景》《桃林:几何画》),大量的关于地理、风物、典故、文艺的枯燥讨论,以及关于风光人物的随意吟咏(《山水·人物·艺术》),或又以一个人物的几段单调的日记来作成一章的内容(《山野行记》)。”[1][P167]研究者推断,是由于“它们的作者在小说方面只‘学会朴直和笨拙’却不具备应有的‘才分’”[1][P176],所以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单薄空洞,而内容也难免零碎枯燥。亦有研究者认为《山山水水(小说片断)》中的诗意描写“显得太过刻意”,“甚至在细节上也给人以虚假感”,其原因在于卞之琳不恰当地在战争语境中引入诗意话语,而“诗意与政治的冲突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对抗”,“无疑是以个体性和诗意的失败告终”,而且这也成为其最终焚毁小说文稿的原因。③
如果我们并不以某种确定的文学经验模式“断定”卞之琳文学叙述的“失败”,而是试图去理解他的文体选择以及小说实践,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文本所彰显的一些基本问题:(1)我们该如何认识《山山水水(小说片断)》中的诗意经验?它们真的只是“在战时”这一普遍性的历史叙述中的不恰当引入吗?(2)关于战争与诗意的并置,这究竟是一次叙事的失败?还是卞之琳刻意追求的叙事风貌?(3)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创作者自焚小说文稿的行为?它仅仅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压力的理性选择吗?抑或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可以看到,关于卞之琳的政治意识、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之于精神史的认识价值,研究者大多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小说文本中大量引入的风雅谈论,研究者或只谈叙事形式上的“螺旋式结构”;④或持批评的态度,不仅认为显现出卞之琳在小说才分上的不足,而且认为表征了意识形态环境中诗体小说的必然困境。我们暂且放下研究者的观点不论,且来看看卞之琳自己如何来谈论这部小说。
卞之琳从两个方面谈及自己在写作中遭遇的危机与转变:一是他认为抒情诗文体较为“单纯”,故而“一踏上‘而立’的门槛,写诗的,可能实际上还是少不更事,往往自以为有了阅历,不满足于写诗,梦想写小说。”二是他所省察的时代因素,因为“时代不同了,现代写一篇长诗,怎样也抵不过写一部长篇小说。”[2][P267]从卞之琳引入的两个维度,一个年龄的增长,一个时代的变化,都可以看到所谓人生阅历中“经验事实”的拓展,而诗从其抒情品性来看,确实在处置“经验性”方面存在困难。事实上,1930年代末期,抒情诗的文体危机几成共识。无论是何其芳、徐迟对抒情诗的放逐,还是穆旦对“新的抒情”情境的要求,抒情诗的文体危机均缘于诗人对诗歌文体的认识以及对时代经验与意识形态压力的敏感,这是比较显豁,而为研究者注意的方面。但是,另外一面,所谓“而立”之年的成熟个体的独特经验,具体到卞之琳身上究竟是怎样的呢?虽然卞之琳在自我追述中并未言明,但是小说文本以及友人的谈论却透露卞之琳内隐而独特的个人经验:穿越于不同的文化社群的经验拓展;面向恋慕对象呈现一个更丰富、也更成熟的“我”的内在需求。
面对复杂的时代与个体经验,卞之琳确实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表现出巨大犹疑,不断增删否弃自己的诗作,以致编订《十年诗草》后的两年里(指1939 -1941年)“不曾写过甚至于想写过一首诗”;而且,卞之琳认为《十年诗草》是他到彼时为止的诗总集,而不是诗选集——这里能够被收入的,才符合他关于“诗”的最低认识——虽然他原本“也不想随随便便拿出去出版,宁愿就束诸高阁”。而他之所以还愿意在1941年把编选好之后搁置了两年之久的《十年诗草》拿出来出版,实在是为了纪念友人徐志摩的缘故,“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诚和推进技术的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以及为表现方法开了不少新门径的功绩。”[2][P9]
这里,不禁令人疑惑,这个表现出自我认同障碍的诗人在追寻什么?我们不妨首先对收入《十年诗草》中的符合卞之琳关于“诗”的最低认识的诗作做一点剖析,以便洞悉他在长达十年的诗歌写作过程中所获致的,但是在1939年之后他却认为是诗歌文体绝难表现的东西。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更为贴切地理解卞之琳在危机中的文体选择与背后的伦理关切以及内隐而较难为人理解的经验与问题视域。
二、“诗的追寻”与认识论式的现代自我
从收入《十年诗草》中的诗作来看,青年时代的卞之琳是一个对于“人之存在的时间本质”非常敏感的人。但是,有别于传统抒情经验的是,对于“时间”问题,诗人捕捉的不仅仅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怅惘慨叹,更是凝聚于一种本质性存在的形而上眩惑:“我”之存在究竟是什么?卞之琳的早期诗作《影子》(1930年),不是“对影成三人”的孤寂体验,而是孤寂当中对“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哲思疑惑——过去有个影子陪着我发呆,现在也有个影子陪着我发呆,毕竟是“你”(“昨日之我”)理解“我”(“今日之我”);“我”也想送个影子给“你”,可是“你”——这个“昨日之我”到哪里去了呢?他既在,又不在。那“我”到底是什么?
在另一首小诗《投》(1931年)里面,诗人写到“我”看见一个小孩在山坡上一边走一边唱,百无聊赖捡起一块小石头向山谷一投;“我”想到了“人”的存在,“说不定有人,/小孩儿,曾把你/(也不爱也不憎)/好玩的捡起,/像一块小石头,/向尘世一投。”“人”的生命存在来自神秘的隐形之手。可是,我们并无宗教信仰,所以,卞之琳也只是承认是“说不定有人”。而被这神秘莫测力量抛入尘世的“我们”,也由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原因,在各自有限的生命形式中表现为不同的经验形态,如《几个人》(1932年)中所呈现,“矮叫花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有些人白发上戴着一朵红花,/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面对人世经验的参差和生命存在的眩惑,卞之琳不是用“以头撞墙”的叩问去追究“人之所来为何”的终极问题——“意义”不是卞之琳的关切所在。相反,他所要得到的是“理解”。或者说,通过“理解”而建构主体的意义视域。——那诗人该如何来理解呢?
卞之琳在《对照》(1934年)中写到:“设想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见道旁烂苹果得了安慰,/地球烂了才寄生了人类,/学远塔,你独立山头对晚霞。”一种疏离,一种静观旁审的认识论式态度,不仅使卞之琳获得对人世与主体存在的哲思观照,而且使他从事关“意义”问题的主体内部经验的探索转而为对主体间关系的省察——由此,卞之琳的诗呈现一种独具个人风格的诗学效果,所谓“戏剧性处境”。
英国女学者简·艾伦·哈里森在探讨古希腊戏剧的产生时,谈到从“仪式”到“艺术”的转变,其中“距离”是形成“戏剧性处境”不可或缺的因素。所谓“仪式”即是行事,初民的祭神拜鬼,无不是为了丰收或战胜死亡的需要。而随着与原初诉求的疏离,“仪式”越来越具表演性。而一旦演变为表演性的戏剧之后,就有了“表演者”和“观众”之分——所谓“戏剧化”效果内蕴着“距离”的要求——舞台与观众席判然分隔的剧场形式即为明证[3]。卞之琳的诗里有“距离”——所谓“独立山头对晚霞”——距离,造成一种审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抒情诗写作来说,距离、审视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有了这些,才能描画出抒情主体自我审视的心理曲线。然而,卞之琳诗的戏剧化效果,却和这“距离”之宏阔远大极有关系。他的旁观与自审,其距离之远大,宏阔到不再是有限时空中的“内部对话”,而是以“无限”的宇宙意识来审视人之存在。这就好像有了一个舞台和观众席:观众席上升到“宇宙”之高而远,舞台则凝聚着全部世界的色相,可以微观为一声叹息、一滴雨珠。于是,才出现了《圆宝盒》(1935年)这样以古典意象构建而极具现代哲学意味的诗句。
在这首诗中,卞之琳有意识地以宇宙无限来与人之存在的有限时空进行对照,“我幻想在哪儿(在天河里?)/捞到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诗人在天河里捞到的“圆宝盒”仿佛魔法世界的水晶球,既是至大之物,也是至小之物,凝聚一切,也折射一切。有意思的是,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没看读懂这首诗,认为诗中“桥”的意象是“结连过去与未来的现时”,卞之琳写了长长的信去解释:既然时光是河流,则过去与未来当为河流本身;既然如此,人又怎么能把混成为一体的东西分为上/下、前/后、左/右呢?[2][P120]
诗人在这里用形象构建呈现一种世界观,“圆宝盒”即是这世界观的形象化,它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宇宙意识。在层层的回转返观之中,诗人让我们看到:这种世界观不仅审视他人,也内蕴着自我审视,主体自我所体认的“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观念被涵纳于“圆宝盒”的观照之下——“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人类感情的结合与沟通方式也被涵纳于“圆宝盒”的观照之下——“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同时,主体对自我经验限度的认知也被涵纳于“圆宝盒”的观照之下——“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也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圆宝盒》对主体意识自足性与相对性的体认呈现出一种观念的圆融与溶解,抒情诗写作不再具有单一、确定的叙述角心,由此意象与意象间的连结与流转,就不仅是一种自觉的美学风格,其背后还有对“思考”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自觉,卞之琳自解为“beautyofintelligence”(笔者译:“智性之美”)。
关于“思考”,阿伦特谈到,“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思考的总是那些直接的感官知觉中没有的或从直接的感官知觉中抽出的东西。所思的总是一个再现,即实际上不存在而只能呈现给心灵的事物或人,心灵通过想象能够使它以形象的形式呈现。”[4][P134]“思考”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具有其独特的指涉对象,所谓“实际上不存在而只能呈现给心灵的事物或人”。既然“所思的总是一个再现”,既然思考活动总是以回忆与想象为基础,那么思考活动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呈现为如此状态,也即“在思考时我就离开显象的世界,即使我思考的只是被给予感官的普通对象,而非形而上学思考的传统领地里的那些不可解的概念或观念。”[4][P135]由此,可以引而伸之的是,“思考”并非哲学家的专长,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思考,只要人能够不时离开“显象的世界”而只“与自己为伴”——一个思考的人,“他们不仅与别人对话,也与自己对话”——独处,对于“思考”活动的运行和发生是必须的,《距离的组织》(1935)正是这样一出对“不可见”的思考过程的戏剧化呈现,它具有“思考”的所有要件:独处,心灵活动(即“想象”),所思对象(即所谓“思考”的质料)
由于对人类经验相对性与自足性的错综认识,《距离的组织》是对过去与现在、实体与表象、存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微观与宏观的组构交织。在这首短诗中,由主体经验所划定的观念边界似乎消隐了——诗人用了一句引语“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来表明一个与“我”相对的主体意识世界;诗人并未对此主体的意识世界进行深描,但是由此呈现的是——与主体“我”相对的并非一个陌生的他者与客体,而是暗含一个同样具有自我意识,需要“我”去洞察理解的主体。至于主体“我”的意识世界,诗人则进行相当清晰的描画——当“我”从清醒而进入梦境时,梦境中的无意识与报纸上的他者经验相对接,并构成无意识梦境中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而当梦境被梦境外的现实所唤醒时,以致主体产生似梦非梦的奇幻感;当“我”终于清醒意识到“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时,时间正在流逝,时间已然流逝。两个主体之间由于友人的来访建立了交互关系,但是友人并未意识到主体“我”的内部世界所产生的那一切奇妙丰富的意识与变化——由主体经验所划定的观念边界依然存在——这一边界通过主体“我”的写作行为能够消失吗?这首富于智趣的诗作极为典型地呈现出卞之琳对人之存在与主体关系的哲学性体认:距离的组织。因此,“写作”就具有沟通与理解的功能;但是,《距离的组织》的副文本——注释,恰恰表明诗人对自己的写作与认知的疑虑:怕人读不懂,以致用自注自解的方式努力让人读懂。
从上述对《十年诗草》中诗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卞之琳始终在诗歌写作中追求一种“心得”,或者说“道”、“知”、“悟”,探寻一种符合智性的思考方式与写作方式,在文本中呈现对不同主体的客观性理解,而非呈现一种主体自我经验的抒情性表达。因此,在卞之琳的思考方式中就呈现出鲜明的认识论特征,而非一种本体论式的形而上眩惑。他对主体关系的理解,认为“距离”缘于主体存在的本质差异,只要“我”能够找到恰当的表达手段,对情绪、感觉进行智性的转化,而把细微复杂的经验呈现出来,理解与沟通就是可能的。因此,在1938年秋冬之际获具“西北大后方”的新经验后,1939年回到“西南大后方”,卞之琳用同样的思考方式与写作方式写“慰劳信”,“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写人及其事,率多从侧面发挥其一点,不及其余(面),也许正可以辉耀其余,引发绵延不绝的感情,鼓舞人心。”[2][P4]
但是,时代在变,由于阅历与认识的深广,抒情诗文体完全不能够容纳复杂庞大的经验体量,“诗的形式再也装不进小说所能包括的内容,而小说,不一定要花花草草,却能装得进诗。”[2][P4]
三、现代危机与小说文体的“客观性寻求”
在卞之琳看来,狭窄单一是诗歌文体的天然缺陷,无法承载广阔复杂的时代经验。而出于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信靠,“中西”“古今”“左右”之间的种种冲突,只要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隔膜与误解就是可以消除的——“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和痴心,我在1941年,妄图以生活实际中‘悟’得的‘大道理’(借用故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当时在昆明常对我说的一句口头禅),写一部‘大作’,用形象表现,在精神上,文化上,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参见《雕虫纪历》自序)。当时妄以为知识分子是社会、民族的神经末梢,我就着手主要写知识分子,自命得计。”[2][P267]
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友人沈从文看来,卞之琳构思《山山水水》的主要动力源于私人性的情感经验,并非仅仅出于如小说家本人事后追认、公开张扬的出于“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的宏大愿望;而且,恰恰是在此由友人所披露的微妙而内隐的个人意识层面,“写作”显现了它的“沟通”与“理解”功能的失效:
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以宏愿,用个五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扩大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慎重的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就因为他还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5](《绿魇》,1943年)
沈从文的叙述饶有意味,他认为卞之琳从诗歌到小说文体的选择是出于一种“表现自己、扩大自己”的内在需要;但是,旁观者与知情人沈从文清楚洞察,卞之琳并未设想自己根本不能获得倾诉对象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卞之琳并不了解那个“他所爱慕的女孩子”亦有其内在曲折多变的主体经验,在时间与空间阻隔变迁中,“对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个人能有所取舍。”(《绿魇》)面对主体意识的曲折流变,沈从文对“文字”的表意与沟通功能具有一种近乎后现代式的怀疑。
如果说面对时代危机与个人情感意识,卞之琳心念关切的是“沟通了解”,沈从文却比他更深一层的逼近问题的本质:现代认同形成所凭靠的“自我”实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寻其根源,如此我们才能重获奠定现代伦理的人性基础。面对此问题,沈从文踏入对人之存在的本体论式的审察,并在1940年代的哲思化时期,将“爱欲”确立为现代自我的根源,以此来构建现代认同;这样,沈从文就寻获了他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人性支点。但是,卞之琳的思考方式并不倾向于对“本体自我”问题的追索;相反,他似乎更接近那一类现代哲学家,“现代哲学的内省发现了作为内在感官的意识,借此,他可以感觉他的感觉,并把他的意识确立为世界实在性的唯一保证。哲学家不再为了逃避欺骗性的、易消亡的世界而转向另一个永恒真理的世界,而是同时逃离了这两个世界并退回他自身。他在内在自我中发现的,也不再是一个以其永恒而能被观照和沉思的形象,相反,是感性知觉不停歇的运动,和同样不停歇的思想的活动。”其后果就是,“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6]卞之琳在小说叙述中的经验化与碎片化,确实与他的观照方式以及对时代经验的意识有关,《山山水水(小说片断)》几乎是试图“客观”呈现一切时代经验,而可以构成“风格”的作者声音却隐没了。
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联系卞之琳由诗歌写作所呈现的思考方式与道德关切,以及从诗歌到小说的文体转折所呈现的对时代经验变化的洞察,并且把他置于一个其来有自、具有独特精神品格的文化社群中来考察的话,我们确实很难理解卞之琳小说中所呈现的美学风貌,所谓叙述不能推动情节,而是显现为叙述的碎片化。结合小说叙述中人物关于时代经验看似“零碎枯燥”的谈论,这里所表达的对于清晰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已经不再仅仅是文体意义上的。卞之琳认为小说应该容纳准确的事实呈现和现实主义的场景,而不是如赛珍珠那样,迎合现代西方一般读者对现代中国由误解而引起的偏见,也不应该如林语堂那样“美化”。如此,以一种非情节化的叙述容纳“零碎枯燥”的经验碎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形式结构上的螺旋交错不仅是作者认识论式思考方式的外显,更寄托着作者“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的世事关怀。
从《山山水水》残存的七个片断来看,其中两个片断(“山水·人物·艺术”与“山野行记”)分别展现男女主人公梅纶年与林未匀的主体经验,另外五个片断则分别以男女主人公为叙述角心,勾画五个容纳诸多人物及诸多视角的核心场景:
场景一:“春回即景一”以女主人公林未匀为叙述线索,核心事件是“武汉重聚与遭遇空袭”。小说由女主人公林未匀牵引出1938年早春流亡中北平两代知识人在武汉的重聚,由此勾画面对突然爆发的战争,战时众人的不同品格与选择;其间,有人贪生畏死,有人被激发出民族主义热情与左翼情怀,亦有人秉持由文化传统浸染而来的沉思习惯。
场景二:“春回即景二”是“即景一”的延续,依然以女主人公林未匀为叙述线索,核心事件是“寻找敌机”。1938年2月18日,面对武汉防空战中击落坠亡的“敌人”,年轻一代遭遇人性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相互挤压,有人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人则犹疑于普遍的人性情怀——“敌人”的“死”中亦包含值得追念的人性经验。
以上两个场景中,卞之琳试图勾画战争时代北平两代知识人对时代的不同回应,战争摧毁了过去的生活,也在重造新的生活与选择。
场景三:“桃林:几何画”则以男主人公梅纶年为叙述线索,核心事件为“桃园聚谈”。小说由男主人公梅纶年牵引出1939年春夏间年轻一代的延安生活,如果说奔赴西南后方的知识人似乎重建了“过去的生活”,而奔赴西北后方的年轻一代却在“延安生活”中获具完全崭新的经验。虽然由晚近以来日渐加深的危亡意识而激发促迫民族观念的形成,但是在向具体而微的社会实践与艺术表达渗透与展开的过程中,“延安”却具有特殊的经验与选择——桃园座谈中,年轻一代就“何为民族形式”问题展开热烈争论,但是更具有“革命经验”的“新人”却对这种“(空洞)聚谈”形式充满深刻否定,“也只有我们知识分子,改不了旧习惯,才这样来利用,这样的看重。”“行动”的价值被彰显,“桃园聚谈”这样一种知识生活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旧习惯。
场景四:“海与泡沫”继续以纶年为叙述线索,核心事件是“延安垦荒”。小说围绕纶年的垦荒经验,展现知识人面对新的政治文化——对劳动的推崇、对沉思的贬抑——呈现知识人对自我存身方式的审视与怀疑。劳动原本只是一种为了满足基本生存而进行的非生产性活动,这里所谓的“生产性”是指人从“生存必须性”中挣脱出来、不以自然性生存为基本目的的活动。而在劳动中,彰显的恰恰是个体所经受的“生存必须性”的束缚,其所产生的业绩也总是指向满足个体自然性生存的必然消耗。因此,“古代人排斥劳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基于人对于克服必然性的自由的需求。”[7]
但是,在延安的集体劳作场面中,“集体”所产生的力量使得“劳动”之于“个体”的意义产生某种变形。如果要说古典时代有限的“家族性”集体劳动面对自然的无限难免令人产生无限的劳役之苦的话,现代场景中的“超个体”、“超家族”的劳动才真正实现了“历史主义的乌托邦”,“全民劳动”的集体主义场景确实能令个体产生“超越性”幻觉,“纶年很得意地觉得自己今天很强壮”;相形之下,“沉思”不会产生任何“业绩”,这里由劳动业绩所带来的满足感被混同于创造的喜悦,对沉思生活构成质疑。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场景所呈现的延安经验与场景一、场景二中的北平知识人的战时经验以及过去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在此,我们不难洞察卞之琳的抱负——他想呈现时代的全景及全部经验的复杂性。于是,场景五中男女主人公的经验交汇以及穿插于五个场景中的两个片断就有反思与总结意味,这是卞之琳对自身所来自的文化社群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的审察。
场景五:“雁字:人”以1940年夏末至1941年初男女主人公梅纶年和林未匀在昆明的重聚为核心事件,集中呈现经历过如许复杂的时代经验的纶年和未匀,这个“新时代的儿子”和“上一代的女儿”如何认识自己所身在的文化社群和所来自的文化传统。可以看到,1930年代以来,以北平为中心,确实形成一种由妙趣横生的谈吐、对诗歌与艺术的机智品鉴所构成的风雅文化,它的集中表现即是被称为“京派”的文化社群。在《山山水水(小说片断)》中,存在着一群品德完备的人,他们既是对“京派”知识人的典范描写,也足以呈现作者的自我映像。在这些虚构人物背后,虽然多少有些距离,但确实潜藏着真实人物。他们的言谈、举止、装饰、交际,无不表现出典雅的风姿。
透过卞之琳彼此互证的文字,很容易看到这部虚构作品的“实事”痕迹。当然,对于这种“真实”,值得看重的并不是所谓“实事”,而是其中的“精神”摹写和呈现。卞之琳在“《冯文炳选集》序”一文中写到,1937年春,当时他在江南,收到废名《寄之琳》一诗,原文如下:
我说给江南诗人写一封信去,
乃窥见院子里一株树叶的疏影,
他们写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写一首诗,
犹如日,犹如月,
犹如午阴,
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因为喜爱这首诗,于是在《山山水水》中,卞之琳“就借这几行真诗大做了一番假文章”[8][P345],小说即或是“假”的,但是其中自有人物“真”精神。这也是多年之后卞之琳在所难忘的,“开玩笑中,如今回想起来自有难忘的挚情”。此后,《山山水水》残篇中,男主人公梅纶年的延安之行以及重返西南后方的经历,就更多契合着卞之琳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而女主人公林未匀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态度,也颇多卞之琳终身恋慕的张充和的风姿和身影。
卞之琳在晚年满怀追慕之情地回忆30年代前期北平年轻一代的聚集,那种充满风雅趣味与心智活力的生活。那时,大约是1932年,靳以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在天津老家转了一转之后,来到北平;在刚从上海北来、改教燕京大学的郑振铎主持下,租了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前院办大型刊物《文学季刊》。之后,这个小去处就成了一个小型的文人交流中心。除了靳以、巴金在那里设有常座,在一起隔座看稿、谈话、评论,常来的还有靳以在南开的旧同学、当时还在清华的万家宝(曹禺)和未婚妻郑秀,以及清华研究生曹葆华等等。除了沉浸于浓郁的新文学生活,以之作为事业与努力的方向,这些年轻人在私人性的心智爱好中,竟然也倾心于古老的传统艺术——“靳以懂一点昆曲,常带几个住东城的年轻朋友,以及还没有搬进景山东街北大宿舍,暂时住在西城她三姐夫沈从文家的张充和,雇几辆洋车去吉祥戏院或者前门广和楼看北昆韩士昌、白云生昆曲戏班子演出。常常与北大教英文的英国少爵爷艾克敦面对紫色金字的帷幕上绣的一对古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共同做了活图解。由靳以护送几辆洋车浩浩荡荡回家,我也几度参与了这个行列,至今回想起来还别有风味。”[8][P129]
不难看到,《山山水水(小说片断)》中所呈现的诗意经验绝非一种文学传统的形式摹写,毋宁说它有着真实生活的印迹,而卞之琳在时空交错的螺旋结构置入这样的经验,实在是有着“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的世事关怀。小说中,经历从“过去生活”中的出走,在获具崭新的“延安经验”之后,男主人公梅纶年对现代危机有了更深的体察与更宽广的理解,也自信能够承载女主人公林未匀——这个“上一代的女儿”交付给他的现代难题:我们究竟应该拿“过去”怎么办?在纶年看来,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对形式技法的恪守可以转而为精神性的理解与继承,如此,“影响的焦虑”在观念上可以被较为轻易地超越。
两个片断:“山水·人物·艺术”与“山野行记”分别呈现男女主体的经验世界。可以看到,古典传统经验构造了女主人公林未匀这个“上一代的女儿”的主体意识世界,新的时代经验让她产生困扰;而男主人公梅纶年虽然亦来自传统的士绅阶层,浸淫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中,但是这位“新时代的儿子”自觉到有义务以一种“客观性的寻求”,来了解异己的生存经验与文化经验,如此才能担负未匀交付给他的问题——“另一个世界”只能是过去的世界吗?
作为“上一代的女儿”,面对“父辈”数千年情感、智慧、想像力的结晶,未匀不能不在急剧变动的铁血时代,遭遇自我认同的迷惘与痛苦。这也是卞之琳在写作《山山水水》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对于时代危机的省察,一种内在而深沉的文化眷念。但是,面对“上一代的女儿”的困惑,“新时代的儿子”以一种无畏而乐观的信心——恰如纶年所办小小刊物上,一位现代法国作家的议论,“把喜悦当德行来赞颂”——这种信心来自于,“他总以交通史研究者的资格而津津乐道一位现代西洋作家关于文学作品说的古今‘同时存在’。”一种建基于广泛经验的自我审视和新的秩序被提出,这种浑融一体的时空哲学见之于文化与历史,就表现出一种高迈的超越,挣脱了“古今、中外、雅俗、左右”等等二元对立项的限制,卞之琳努力要在不同文化时态与形态之间“搭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纶年理解并恋慕未匀的风姿、言谈,并且以一种理性的自明对未匀所困惑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充满信心。但是,卞之琳却不能预料左右意识形态分野对于文化问题的撕扯,更未曾预料新时代的延安经验将会对其所来自的文化社群与自我认知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从诗歌到小说,卞之琳对不同文体的选择与他对文学的功能理解有关。文学之于卞之琳,毋宁说是一种“思”的方式,他的抒情诗写作追求的是“智性之美”,一种体现为“客观性寻求”的精神活动与理解过程,由此呈现的这个现代自我就不是存在论式的主体,而是认识论式的。他并不追索终极意义问题,而凭借“悟”得的“大道理”,对世事形成独特的世界观与回应方式,即“在精神上,文化上,竖贯古今,横贯东西”,以求“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对于观念层面左右意识形态的对立碰撞,文化层面中西古今以及左右雅俗之间的穿插交织,以及主体微妙而内隐的个人情感意识——这一切,卞之琳都试图以对客观性的寻求与表现,获得沟通与理解,从而建立一种交互溶融的主体间关系。以此,面对现代危机,作者的社会价值通过写作这一“思”的行为而得到实现。但是,恰恰是在《山山水水》中,写作者呈现对自我存身方式的深刻怀疑——在“客观性的寻求”与体察中,异己的生存维度被引入进来,延安垦荒的集体劳作场面最终在“以思考为业”的写作者身上引发一种奇特的自我否定:“沉思与行动的倒转”——在这一由阿伦特所概括的现代现象中,“不是真理和知识不再重要了,而是真理和知识只能靠‘行动’,而不是靠沉思来获得。”[5][P230]
四、结语
从诗歌到小说,卞之琳的文体转变既与他的文学观有关,也与他对现代危机的审察有关。当淮海战役打响,震动时在英国留学并译改小说《山山水水》的卞之琳,以至他对“写作”这一“以言行事”的存身方式产生深刻怀疑,“在这种丰功伟绩前面,我竟在那里集中精力,弄我无聊的笔杆!”数年之后,卞之琳更是自我否定,一把火烧了《山山水水》,因为“知识分子”和“儿女情长”都已无在历史中存留的必要。⑤然而,卞之琳对自我尚有“否定之否定”。同样是在《山山水水(小说片断)》“卷头赘语”(1982年)中,卞之琳谈及,三四十年后重读小说断片,认为“值得留痕”。他亦如昔年写作《距离的组织》时自注自解,标明线索,指点阅读——但是,这一次他试图将文本从创作语境中割离,从而将过去的“自我”保守在秘密之中:“谈论任何人的作品,我总倾向于着重作品本身。写作意图、写作和修改结果、反应和效果试探、全盘作废又局部保留的情况、自己改变处理的想法,在此,比诸作品本身,实际上都无关宏旨。即使涉及作品本身,艺术手法之类,也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内容。”[2][P271]卞之琳决不喜欢研究者对自己作品持一种“索隐癖”式兴趣,也反对那种传记式研究方法,认为还是应该寻求“内容”所承载的表现与理解,由此基于个人情事的创作及焚毁动因皆被隐匿了——如果研究者不能洞悉这一点,一个有着多重经验的“个体”确实是消隐于历史的宏大叙述之中。
相比于沈从文遭遇的长期精神“磨难”,卞之琳似乎并无困难地完成了自我转变——这不禁让人诧异。“语词是一种光”,是在自我澄明之中对世界的照亮。然而,在宏大的历史压力以及时移世易的个人存身情境变化中,卞之琳焚毁书稿,将自我长久保守在一片神秘的黑暗之中。事实上,他的沉默和他的言说一样令人思索。
[注释]
①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钱理群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中对叙述者关于“我”/“群”关系思考的揭示,刊载于《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亦有青年学人李松睿在《时代·个人·小说——论卞之琳〈山山水水〉》结合作者创作意图以及叙事结构与叙事观点对小说形式背后潜藏的政治无意识的探察,刊载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年第3期;李松睿另有《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对卞之琳小说断片的文体结构做了更为全面的剖析,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丛刊》2012年第4期;吴晓东则从政治意识与审美的对立入手探讨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矛盾与困扰,参见《〈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未定稿)》,刊载于“新生代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会议论文集《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1937-1952)》。
②见:姜涛.小大由之:谈卞之琳40年代的文体选择[J].新诗评论, 2005(1);另外,解志熙《灵气雄心开新面——卞之琳诗论、小说与散文漫论》亦从创作者的叙事追求论及《山山水水》的创作,刊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③ 见:吴晓东《〈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未定稿)》,收录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14年《“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会议论文集》,第14-15页。
④ 见:李松睿《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虽然李松睿注意到卞之琳小说结构上的整体性,但是他对文本内部的纷呈经验、尤其是诗意经验并未更多涉及。
⑤ 所谓“儿女情长”已无在历史中存留的必要,事关卞之琳对张允和的单向濡慕及失落。在对沈从文的传记式批评中,研究者多有猜测,认为沈从文对张允和有过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爱恋。虽然个人的隐秘情事很难坐实,但是卞之琳的幻灭感倒似乎是一个可供“八卦”的注脚。相关考证可参看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证》,刊载于《十月》2009年第2期;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下)》,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两位研究者皆力证沈从文1940年代沈从文爱欲书写与其隐秘情事之间的实证关联;反驳文章则有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1]范志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上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社, 2002.
[3][英]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80.
[4][美]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2卷)[M].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
[6][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232,230.
[7]张闳.愚公移山,或古典时代的劳动[J].上海文化,2013(9): 102.
[8]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社, 2002.
DiscussingBianZhilin'sChoiceofLiteraryStylesinthe1940s
CHENYan
(School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round1941,BianZhilinwasconsciousofthecrisisinhispoeticwriting,whatmadehimtransfertothenovel.Hecreated thefull-lengthnovelMountainsandRivers,whichnowisleftfragmentary.Frompoetrytonovel,althoughthestylechanged,his formofthinkingpresentedbyhispoetryextendedtothenovel.ThesearchingforspiritofepistemologyurgedBianZhilin'snovelto containmoredetails.Sonarrativefragmentationandcontextualizationwerenotonlyowingtoaestheticprinciple,butalsotheresult ofthepursuitofobjectivity.However,whentheactiontookprecedenceoverthethought,deepercrisisoccurredtoBianZhilin,becausetoperformheroicdeedsseemedtohavecancelledthemeaningofcontemplations.
BianZhilin;creativewriting;choiceofliteraryform
I207.25
A
1672-934X(2014)05-0066-09
2014-08-26
陈彦(1973-),女,江苏淮阴人,副教授,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京派文学与文化、西南联大诗歌与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