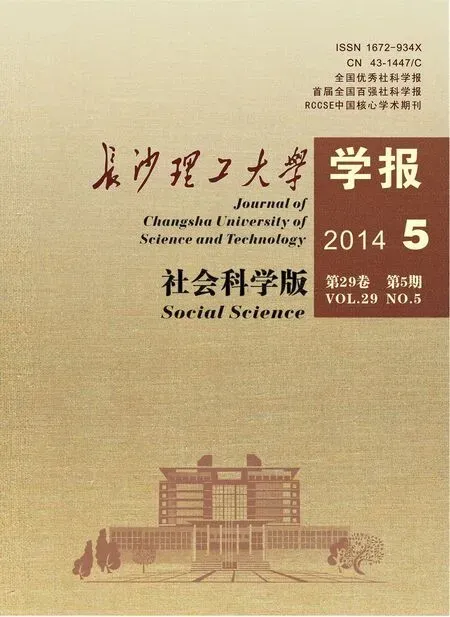沈钧儒的冤狱赔偿思想与实践
陈雅丽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沈钧儒的冤狱赔偿思想与实践
陈雅丽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沈钧儒积极倡导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开展冤狱赔偿运动。他认为,冤狱赔偿制度可以限制司法权力以保障人权;冤狱赔偿制度主要适用于受冤处刑、被冤遭判、无辜受羁押三种情形;对于冤狱赔偿案件应设冤狱专门审判庭与特别程序。同时建议,对司法者进行责任追偿。沈钧儒提出的冤狱赔偿思想对促进当时的冤狱赔偿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沈钧儒;冤狱赔偿;人权;实践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批留学归国人士、爱国人士积极投身于冤狱赔偿运动中,力促冤狱赔偿制度入宪以及政府出台完整的国家赔偿法,沈钧儒即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诚如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所说,“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是沈钧儒推动而组织起来的,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冤狱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赔偿制度包括司法赔偿与行政赔偿,其中,司法赔偿制度,又被称为刑事赔偿制度、冤狱赔偿制度,主要是国家对司法机关的错误逮捕羁押、错误刑事判决、错误执行等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沈钧儒为代表倡导的冤狱赔偿运动,主要针对当时司法机关违法逮捕、判决和关押爱国学生、救国人士的行为,力图通过制定和出台国家赔偿法使这些爱国人士得以获救,并防范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更多爱国人士的迫害,以保存救国力量。
一、倡导冤狱赔偿制度之动因
沈钧儒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倡导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开展冤狱赔偿运动的潮流中,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
(一)冤狱赔偿制度在西方主要国家建立
1931年,学者陈文彬即撰文陈述,“关于冤狱赔偿制度,在西洋已经从学说的鼓吹进到立法制度的确立了”[1],例如,德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以沈钧儒、陈志皋为代表的上海律师公会比较全面的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冤狱赔偿立法制度,认为“自十九世纪末叶以降,随时势之变迁、法人责任理论之进步,在公私法方面对于人民、因机关之权力行动所发生之损害,以给予赔偿为通例”,“其立法例,有为之制定特别法者,若德奥是;有为之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者,若法意是;更有为之著成判例者,若英美是。”[2]即综观西方国家有三种立法体例,一是制定专门的国家赔偿法,二是将冤狱赔偿规范在其它法律中,三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形式。冤狱赔偿制度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建立为沈钧儒等人审视当时国内的相关制度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沈钧儒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对西方的宪政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归国后依然保持着对西方宪政制度的高度关注与敏感,试图从西方先进的制度中寻找到救亡图存的良药。因此,西方冤狱赔偿制度的确立吸引他的目光、引发他的思考便不足为奇了。
(二)国内冤狱案件普遍发生
沈钧儒之所以积极投入冤狱赔偿运动中,与当时国内的时代背景也是的分不开的。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政策,使当时的中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批的共产党员与爱国人士、进步学生被捕、被杀,人权被蹂躏践踏,冤狱现象较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沈钧儒一方面以律师身份亲自出面为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进行辩护、办理保释、营救出狱,据统计,1930年至1935年期间,被他营救的革命者达19人之多[3];另一方面,沈钧儒致力于推动冤狱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包括提交《冤狱赔偿法提案》、担任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主席、设6月5日为冤狱赔偿日、推动冤狱赔偿运动,携《冤狱赔偿法案》赴南京向 “五权大会”请愿等。
二、冤狱赔偿制度之价值在于保障人权
人权是沈钧儒一生所珍视的价值,称其为“人权斗士”一点都不为过。生命权与自由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除此之外,沈钧儒还特别论述过公民的参政权、言论出版权等政治权利,妇女与儿童的财产权和受教育权,囚犯的合法权利等。
沈钧儒等人认为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可以限制司法权力以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主要指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冤狱赔偿法提案》①开宗明义指出,“为提议大会应建议立法院制定冤狱赔偿法,借以彻底维护人权,澄清法治而免冤抑事”[4],“冤狱运动之发起,全为保障人权,改进司法。”[5]提案认为,产生“冤狱”的直接原因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当考所谓冤狱,其成因不外:(1)过失的冤狱。(2)故意的冤狱。(3)权威的冤狱。”“无论其为过失、故意、与权威之冤狱,其根本原因,更不外乎:(1)贪官污吏以作官为生财之道。(2)司法官吏生活无保障。(3)司法官吏误解裁判不受干涉。”[4]即认为,造成错捕、错判的原因在于部分司法者的职业道德丧失、法官保障制度缺失以及法官错误理解了司法独立原则,将司法独立原则理解为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与限制。1935年的冤狱赔偿运动会宣言指出,司法的腐败、司法人员的不负责任是造成冤狱的直接原因,司法者“或操行不检、嗜货渎职、或学识浅陋、轻率定者,则所在多有,用使无辜蒙罪、号泣罔闻、哀我孑黎。坐是破家戕身者,不知几何人,颓惰萎靡,不克自振者,又不知几何人……亟求实现冤狱赔偿制度、以保障我人民生存之权利。”[6]可见,沈钧儒认为,面对司法的腐败、枉法裁判,必须通过冤狱赔偿制度以防范司法者滥用审判权力,以保障人权,“倘无明文赔偿之规定……何以克尽法律保障人权之原意?而反致便利贪赃枉法之徒,得以法律为其个人任意出入人罪之工具。是而不惩,国无宁日,法无平日矣。”[4]
人权保障是宪政的应有之义,冤狱赔偿制度是宪政的具体落实。宪政是沈钧儒为国家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称自己是清末宪政请愿运动的“开头人”。1907年,沈钧儒与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向清廷呈递了《民选议院请愿书》,该请愿书是当时留日学生和民间的第一份请愿书,并成为后来国内兴起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民国批国民革命期间,以政治律师的身份参与到冤狱赔偿运动中;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组织宪政促进会和宪政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全程参加起草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可以说,沈钧儒一生都对宪政锲而不舍,乃至于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后,他无不激动的说:“我一生搞宪政运动,化了多少心血,今天才有了一部人民的宪法。”②冤狱赔偿制度是宪政得以具体落实的环节之一。一方面,冤狱赔偿制度通过救济程序,可以对损害了的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予以一定程度的事后恢复、补偿和救济,从而有助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另一方面,冤狱赔偿制度通过对司法者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对司法权力的滥用予以事先防范与限制。诚如沈钧儒所在的上海律师公会的冤狱赔偿运动宣言所说,“惟吾人以为,健全国家,必须保障人民。宪政实施在即,苟无冤狱赔偿制以为之辅,则所谓人权保障仅属粉饰文明。人各不能保其生存权利,尚有何安内攘外之足云。”[7]
三、冤狱赔偿制度之具体方案
沈钧儒等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冤狱赔偿运动中,不仅提出冤狱赔偿运动的宣言与口号,而且设计了冤狱赔偿制度的具体内容,将这种设计置于今日也未必落后,其与我国如今的国家赔偿制度相比,存在诸多相通之处。
(一)设冤狱专门审判庭与特别程序
《冤狱赔偿法提案》指出,冤狱赔偿制度应该严密而合理。一方面,要注重保护公民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能被恶意诉讼者钻了法律空子。因此,冤狱赔偿立法不能过严,也不能过简,“倘失之过严,则除能力丰足之人而外,平民乡愚仍无昭雪之机会,殊无保障人权之原意不符;倘失之过简,则莠民好事之徒遇案捣乱,狡猾奸恶之士造谣生事,亦于澄清吏治不合。”[4]据此认为,应在原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再在高等法院所在地或者首都所在地,设置冤狱专门审判庭,冤狱专门审判庭专门受理和管辖冤狱赔偿案件。
这种对冤狱赔偿设置不同于一般案件程序的观点在我们当今的国家赔偿制度中依然适用。首先,我们的国家赔偿制度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遵循了保护弱者利益的原则,由赔偿义务人、司法赔偿诉讼中的被申请人,即司法机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申请人或受害人只需证明存在损害行为,以及造成了损害结果即可,质言之,司法机关若不能举证证明受害人的损害与自身的司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毕竟,司法机关掌握着主要材料、文书和证据,处于诉讼中的有利一方,这种举证责任的设置有利于平衡司法机关和申请人之间的力量,有利于申请人的求偿权实现。其次,我国当今的刑事赔偿也由特殊的审查组织受理和裁判。根据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法规范,在法院内部设置了司法赔偿委员会专门负责受理和审查刑事赔偿案件,司法赔偿委员会由7-11人左右的单数构成,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制,从而有助于防范个别人的专权。最后,不同于一般的刑事诉讼,冤狱赔偿的申请人是受害人,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其近亲属以及财产继承人都可以成为赔偿申请人。这一规范与沈钧儒等人的《冤狱赔偿法提案》中的观点不谋而合,提案指出“冤狱求偿权,其能力应及于本人,及其配偶、其父母、其祖父母,及其继承人与代理人。”[4]根据一般的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如果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其近亲属应为诉讼原告,而国家赔偿法则规定,不仅其受害人的近亲属、其财产继承权人也具有原告资格。这种特别规范具有合理性,因为冤狱赔偿的权利救济方式之一是金钱赔付,尤其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金钱赔付是最主要的赔偿方式,直接增加财产继承权人为赔偿申请人,可减轻诉讼与审理之赘。
(二)适用情形
冤狱赔偿的适用情形,或曰冤狱赔偿的范围,是什么行为可以适用冤狱赔偿制度予以调整的问题,也是冤狱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件。关于这一问题,沈钧儒等人归结为三种情形:(1)被冤处刑; (2)被冤遭判;(3)无辜受羁押。“被冤处刑”是指违法或错误判决,而且这种错误判决已经执行的情况,包括“无辜被罚”与“轻罪重罚”两项。“无辜被罚”即无罪的人被判有罪并执行有期徒刑或死刑,以及应判决轻罪但错判成重罪并已执行的情况。“凡经证实其为完全冤抑,或罪轻罚重者,关于冤曲及入重之部分,应酌量情形予以申明冤曲,赔偿损害,或相当之救济。”[4]“被冤遭判”是指判决未确定或者判决已确定但尚未交付执行的情形,虽然未被执行,但在审理期间,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难免遭到了限制和侵害,如果证明公民是没有犯罪行为而限制了其人身自由权的,也应属于冤狱赔偿的范围。“无辜受羁押”,是“在审理期间合法取保,遭受拒绝,或非法延宕,至当事人感受羁押之累者”[4],即指在刑事侦查阶段的非法羁押、刑事拘留等情形。对于这些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沈钧儒认为,不仅应按照羁押的每日支付赔偿金,而且还应登载公报以恢复其名誉。
从上述情形可看出引发冤狱赔偿责任的行为应满足三个特点:一是该行为是司法职权行为;二是该行为违法或错误;三是该行为对公民造成了客观损害结果。处刑、判罚、羁押等均是法律授予司法机关行使的司法职权行为,同时这些行为必须是违法或错误的,而且已经实施并给公民的权利造成了损害后果。这三种情形均是典型的冤狱赔偿的范围,时至今日,已建立刑事赔偿制度的国家无不将这些情形规定为国家赔偿的范围,并且,除了规范金钱赔付的责任方式之外,也注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救济方式,有同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趋势。
(三)对司法者实行责任追偿
冤狱赔偿,是国家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这种赔偿责任或金钱赔付由国家税收支出,相当于由全社会纳税人分担了冤狱赔偿金,倘若司法者出于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也由纳税人分担,一方面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司法权力的限制与监督。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国家赔偿制度都规定了追偿制度,即具体的权力行使者行使侵权行为时,如果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国家在对受害人或其亲属、财产继承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应当追究具体权力行使者的个人责任,将国家赔偿责任转嫁到权力行使者个人身上。
沈钧儒非常注重建构对司法者进行责任追偿的制度,《冤狱赔偿法提案》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对此予以论述。提案指出,“关于平反冤狱,中国古代法制本有严格之规定,凡官吏失入失出均应处罚”,并考察了我国从汉代到清朝的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发现这一制度在我国唐朝和清朝的法律当中有相应的规范。《唐律》规定,“诸官司出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徙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徙流,从徙流入死罪,亦全以罪论……”《唐律》也以官吏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责任追偿的前提要件,“凡听诉,依状以鞠情,如法以决罚,据供以定案,凡出入增减,则别其‘故者’、‘失者’论之,以惧庶狱。”[4]清朝法律对于官吏的责任追究规定得更为详细和严格,同样的,根据官吏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分别论处,“出入人全罪者,以全罪坐之;增轻作重,减重作轻者,笞杖流徙,以折杖法通计。除该犯应得本罪,坐官吏以增减余罪。致死者,坐以死罪。若失入者,减所入之罪三等。失出者,减五等。”可见,清朝对官吏的错误判决行为,不管是重罪轻判,还是轻罪重判,法律均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清朝的法官职位被视为“畏途”。除此之外,沈钧儒等人还考察了当时苏联、日本等国家对责任追偿制度的重视与规范。苏联刑法规定,“非法之拘押,非法之逮捕,以及审问时强迫口供笔录等事,如系承办侦察之公务员,以非法方法出之者,处有期徒刑一年。”
沈钧儒等人认为,当时政府应借鉴古代与苏联的做法,制定完善的责任追偿制度,“苏联刑法及中国旧制均有可采,清律别其过失与故意,而轻重其主从人员,尤为妥切,然其处罚之程度,《冤狱赔偿法》自应有假想之规定,俾处理者有所遵循,未犯者知所警惕。”[4]
四、沈钧儒冤狱赔偿思想的实践
沈钧儒不仅是一位法律思想家,也是一位法律活动家。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并非对冤狱赔偿思想和理论坐而论道,而是身体力行的推进冤狱赔偿思想的实践,为冤狱赔偿制度的确立奔走呼告。
1933年6月,沈钧儒向在青岛召开的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提交《本会应建议立法院制定冤狱赔偿法案》,并转呈南京政府,但未被采纳。1934年9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律师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组织了全国律师协会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沈钧儒任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委员。1935年5月5日,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在苏州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推选为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主席,会议讨论了《冤狱赔偿法草案》、逐条修正并通过了《冤狱赔偿运动工作大纲》、《冤狱赔偿宣言》等重要文件,其中《冤狱赔偿法草案》是我国第一部旨在保障人权,实现国家赔偿冤狱的法律草案。同时,这次会议确立了每年的6月5日为冤狱赔偿运动日,以期通过运动的形式扩大宣传,以推动冤狱赔偿的正式立法。1935年6月5日,在全国各律师公会的推动下,各地同时举行了第一次冤狱赔偿运动,并在各大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上发表了《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冤狱赔偿运动宣言》、《冤狱赔偿法草案》。在上海,上海市律师公会则举行了招待会,邀请了党政司法界各界人士及各界公团代表参加,会上沈钧儒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及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了冤狱赔偿运动的意义与经过。第一次冤狱赔偿运动促使了国民政府司法部、立法院决定秋后讨论冤狱赔偿法草案。1935年10月,该草案获得了司法会议通过,并转呈立法院。
1935年11月10日,在浙江杭县湖滨性存路杭县律师公会处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议,讨论了推进赔偿立法的具体方针,推选向五全大会请愿人员以及号召各地律师公会一致致电请以促成冤狱赔偿立法等。1935年11月12日,沈钧儒、陈志皋携《冤狱赔偿法草案》赴南京,向“五全大会”请愿,但草案不幸被立法院搁浅。虽然冤狱赔偿未能正式立法,但沈钧儒等人依然孜孜以求。1936年2月,沈钧儒被全国律师协会推选为冤狱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5月,沈钧儒独自一人再次奔赴南京,呈文立法院、司法院。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终于在第二章“人民权利”写入了国家赔偿制度,虽然无下位法落实,但冤狱赔偿立法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沈钧儒等人功不可没。1936年6月7日,沈钧儒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冤狱赔偿运动,并在该活动中报告了冤狱赔偿运动的意义,及数年来运动经过,积极联合各界促成政府进行赔偿立法等。不幸的是,冤狱赔偿运动还未取得最终成功,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等七人便因救国会活动而蒙冤入狱,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沈钧儒自身也成为了错捕错判的受害者。
沈钧儒的冤狱赔偿思想是顺应历史时代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以国外制度为参考,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勾勒出了冤狱赔偿制度的目的、具体方案和内容,这些思想虽然没有促使冤狱赔偿制度在当时最终建立,但却促进了冤狱赔偿运动,挽救了一批革命爱国人士。而且,沈钧儒提出的冤狱赔偿思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待也并不过时,与我国当代的国家赔偿制度有着相通之处。
[注释]
① 此提案由陈志皋代表上海律师公会撰写,沈钧儒代表上海律师公会向1933年6月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提交。
② 《访问王健同志的记录》,转引自:陈水林,陈伟平.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9.
[1]陈文彬.冤狱赔偿制度与我国今后之立法[J].法律评论,1931 (02):3-6.
[2]律师协会冤狱赔偿运动会[N].申报,1935-5-7.
[3]陈水林,陈伟平.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13.
[4]陈志皋.冤狱赔偿法提案[J].法学丛刊,1933(02):93-102.
[5]律师公会昨日举行冤狱赔偿大会[N].申报,1935-6-6.
[6]律师协会冤狱赔偿运动会[N].申报,1935-5-7.
[7]上海律师公会冤狱赔偿运动宣言[J].法令周刊,1936(310):2-3.
Shenjunru'sCriminalCompensationThoughtsandPractice
CHENYa-li
(SchoolofLaw,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1121,China)
ShenJunruinvolvedinthecampaigntorescueandsavethenationpoweractivelywithsuggestionsthatcriminalcompensationsystembesetupforunjustverdictstoprotecthumanrightsthroughthelimitationofjudicialpower,whichcanbemainlyapplicabletothethreecasesofwrongpunishment,wrongedsentence,andinnocentdetention.Specialcourtandspecialprogrammustbe establishedforthecriminalcompensationofunjustverdict.Meanwhile,recoverymustbepursuedonthepartoftheresponsibilityof thejudge.Shenjunru'scriminalcompensationthoughtssignificantlypromotedthepracticeofcriminalcompensationathisowntime.
ShenJunru;criminalcompensationforunjustverdict;humanrights;practice
D921
A
1672-934X(2014)05-0124-05
2014-07-11
陈雅丽(1979-),女,湖南郴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