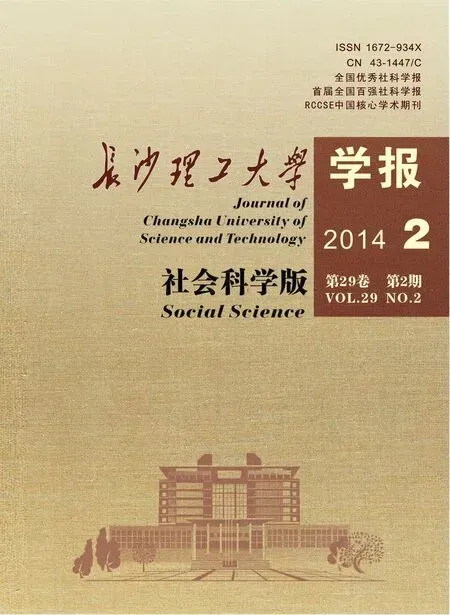简论柯旺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及其特点
章梅芳,龚 艺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简论柯旺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及其特点
章梅芳,龚 艺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以性别观和技术观的嬗变为视角,考察柯旺的技术研究进路及其特点,认为她的技术思想经历了从“技术决定论”到“建构论”的转向;其研究对象经历了从家用技术、生产技术到生育技术的基本变迁;研究视角从强调技术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逐渐转变为强调它们在文化上的相互建构关系。
女性主义;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柯旺
露丝·施瓦茨·柯旺(Ruth Schwartz Cowan)是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其早期的技术史著作《给母亲带来更多的工作:从平炉到微波炉的家用技术的讽刺故事》被国际技术史学会(SHOT)授予德克斯特奖(Dexter Prize,1984);关于生育技术的史学研究著作《遗传与希望:为基因筛查辩护》被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4S)授予J.D.贝尔纳奖(J.D.Bernal Prize,2008)。柯旺擅长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技术展开经验研究,尤其对家用技术、生产技术和生育技术进行了历史梳理和个案分析,揭示出技术与性别、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分析其技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变化特点,有助于把握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整体概貌和学术价值。
一、“技术决定论”与家用技术研究
强立场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技术的进步,而技术革命则意味着社会革命。生产关系的发展亦应归结为技术组织结构的变化,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地形成新的社会关系[1]。
柯旺对家用技术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早期的研究思路体现出了一定的“技术决定论”的色彩。她通过考察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家用技术的演变,揭示了家用技术变革对女性以及美国社会劳动性别分工的深刻影响,尤其对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种类、时间和总量的影响。
首先,在柯旺看来,工业化条件下的家用技术系统为把两性分离到不同的工作场域创造了物质条件。例如,铁炉具的出现节省了相对以前一半的燃料,为此男性承担的砍柴、运柴、劈柴的劳动量相应减少了一半;而对传统意义上负责烹饪的女性来说,劳动量却没因此而减少。因为在铁炉具上烤肉和以前在壁炉上烤肉的程序几乎没有区别,而且不像以前在壁炉里烹饪食物那样一锅煮的做法,铁炉具的出现可以实现各种烹饪方法。这使得美国人的家庭饮食在19世纪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同时家庭中的烹饪事务也变得更为繁杂,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当男性的家务时间因炉具等家用技术产品的出现而减少时,他们就有机会外出寻找一些季节性工作或兼职工作赚取现金以购买家庭必需品和奢侈品。同时,其下一代中的男孩也越来越不知晓应该如何完成这些事务,他们更关心如何找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而每一代的家庭主妇及其女儿们所承受的家庭负担却因此而越来越重,也因此更加不可能外出工作,除非遇到极端的事情发生,例如经济大萧条、家庭变故等[2](P63)。
其次,柯旺认为技术革新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体力劳动负荷,但也给家庭主妇增添了新的劳动项目,增加了更多劳动量和劳动时间,进而给家庭主妇带来了更大的劳动负担。例如,铁炉具、电冰箱等家用技术产品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家庭饮食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烹饪食物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精细化和复杂化,洗碗机、清洁剂等产品的出现,以及“细菌”概念的产生和流行,使得家庭清洁标准也不断提高,这些均给女性而非男性带来了新的劳动任务[2](P9)。在柯旺看来,主妇的家庭背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几乎不影响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长短,重点在于家用技术强化了传统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家用技术的革新不断让男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女性在家用技术的帮助下,虽然家务劳动不像以前那样艰苦费劲,但它们依然是耗时的劳动[2](P199)。换言之,现代家用技术减少的是苦差事(drudgery),而不是劳动(labor)[2](P100)。
最后,柯旺认为新家用技术系统带来的高生产率最终瓦解了人们原有的性别意识形态。工业化之前,男人与女人共同照顾家庭成员和从事家务劳动。工业化之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独自承担着工业化之前男人、家庭主妇和仆人们共同完成的家务劳动以及新增的家务工作,如开车接送小孩、送家庭成员就医、采购生活物品等。家用技术促使家庭主妇不得不从事更多的无偿劳动,以创造舒适的家庭环境、多样的饮食、更高的个人和公共卫生健康水平,这改变并巩固了日常生活模式和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给社会营造了女性照顾家庭是美德的性别意识形态[2](P99)。
在柯旺对家用技术的历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始终是技术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而基本没有考虑在这一时期家务劳动分工和妇女家务负担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更没有关注这些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反向影响。柯旺采取的基本立场是“技术决定论”,正如她本人所承认的,她的这一思想来源于梅森(Stephen F.Mason)的《科学史》(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1962)和贝尔纳(J.D.Bernal)的《十九世纪的科学与工业》(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53)的影响,以及麦克德莫特(John Mc Dermott)的《技术:知识分子的鸦片》(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一书的激励[3]。在柯旺看来,尽管麦克德莫特关注到越南战争、军事技术、马克思主义、现代技术的社会效应等现实问题,但其研究仍然缺乏实证。为此,她决定着手进行经验研究,并打算以此为“技术决定论”提供更多的论据[3]。
尽管如此,柯旺并没有因此走向惧怕技术失控的悲观主义立场。在她看来,技术给家庭主妇带来了更多的劳动负担,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重回过去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摧毁带给人们便利生活的技术系统,更不是终结作为社会机构的家庭单位,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技术、了解技术。正如她在《给母亲带来更多的工作》一书的后记中所言:“如果人们能够选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有意义的规则,人们就能理性的掌握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控制,如此一来,技术的真正潜力就能实现了。”[2](P215)
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与生产技术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形成并蓬勃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是建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技术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社会学扩展到技术研究领域,创立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SCOT),他们坚持技术同样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逐渐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并非是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是社会的性别观念使然,为此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
正是在此学术背景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柯旺的技术史研究在理论取向和概念系统方面都发生了较大转变,不再只是关注技术对女性和社会的影响,对于技术自身的发展,除早期在关于电冰箱的案例分析中所关注到的经济利益对技术的推动之外,还更为明确地强调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技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相互形塑和建构的关系。这一时期,她将关注的焦点从家庭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从对家用技术转向了对生产技术的经验研究。她要说明的是,在生产技术的发展史中,社会性别的因素介入和形塑技术发展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生产技术领域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的不同表现。
以美国雪茄工业中雪茄包装切割器的发明为例,柯旺阐释了性别因素对技术发展速度的影响。19世纪中叶,美国的雪茄全部由熟练的男性工人手工制造,但是为了瓦解1869年纽约雪茄制造者的罢工,制造商开始雇佣虽然不如男性熟练但是工价低廉的女性移民。女工人的出现有效地终止了男工人的罢工,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她们能像那些熟练的男性工人那样又好又快地生产雪茄,以及彻底解决男性熟练工人的再罢工问题,代替和辅助手工生产雪茄的包装切割器便有了迫切的需求。在柯旺看来,女工的加入无疑加速了雪茄包装切割器的发明进程,进而推动了19世纪后半叶雪茄工业的发展。与之相反的例证是制衣行业的情况。19世纪后期,制造商本可以用蒸汽和电动力使剪裁和熨烫这些辅助缝纫过程的技术环节自动化,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原因除了许多小公司无法负担蒸汽和电动力的巨大费用之外,更在于当时的缝纫制衣行业的工人主要是女性,与操作机器的男工人相比,支付给操作缝纫机的女工的工资明显要低得多。为此,大多数制造商放弃了对制衣技术自动化的投资,而是选择了熟练而廉价的女性作为生产动力。柯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性别因素的影响,减缓了原本在20世纪就可以实现自动化的缝纫技术的发展速度[4]。
显然,柯旺对生产技术的研究体现了技术社会建构论的基本思想,即技术的发展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雪茄包装切割器在资产阶级镇压男性雪茄工人大罢工的社会与境中产生;自动化缝纫机因为连续的移民浪潮、昂贵的蒸汽费用和电力成本的阻碍,以及女性制衣工人工资成本的低廉等因素的影响而发展缓慢。值得指出的是,她并没有进一步强调技术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只是认为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两个案例除了表明性别因素可以成为影响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之外,同时也反映出女性工人在技术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受压迫的地位。她们与男性同工不同酬,而且往往被排挤在高技术之外,从事着技术含量低的、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这正是生产技术领域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并且,虽然女性工人在这两个行业占据了多数席位,表面上看起女性的地位似乎提高了,制造商的做法似乎促进了女性的平等就业,但实质上却是资本家为了减少生产成本,获取更多利益价值的一种手段。一方面,女性的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当一项技术既可以被男性操纵也可以被女性操纵时,这种技术的劳动力供给就更为丰富,那么在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其价格也会因此而下降,女性劳动力则随之变得更为廉价。马克思认为,技术革新(机器升级)是压榨、剥削和控制劳动力的手段[5];柯旺则强调,新生产技术产生的结构性原因是为了获取更加廉价,更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女性则更进一步沦为生产技术领域中资本与劳动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三、技术使用者、文化与生育技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对女性内部身份差异的关注,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也逐渐迈向了“多元化”阶段,并且其对性别和技术有了文化层面的深入理解,研究内容开始出现文化转向。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也实现了从“技术中的女性问题”到“女性主义的技术问题”的理论转向[6],“文化转向”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这首先反映在相关研究已开始关注到女性与男性内部因种族、年龄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差异性及其在技术领域的体现;其次表现在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性别和技术本质上均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与境,且更为强调技术和性别身份、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这其中,生育技术和身体技术的研究已成为技术文化研究的重要场点。柯旺对优生学历史的分析,尤其是对基因筛查技术包括“德系犹太人群的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筛查”、“塞浦路斯人的地中海贫血症基因筛查”和“非裔美国人的镰状细胞病基因筛查”的案例分析,体现了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多元化”和“文化史”的发展趋向。
首先,柯旺在探讨这些基因筛查技术时,充分考虑了疾病确认和命名过程中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影响。以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筛查为例,此病常发于德系犹太人群,它最早描述者是英国眼科医生沃伦·泰伊(Warren Tay),其确定者是美国德裔神经学家伯纳德·萨克斯(Bernard Sachs),其父母均为德国犹太移民。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医生在世界上首先倡导在显微镜下检查尸体组织并进行病理解剖,德国的医疗实践经历对萨克斯的研究十分关键,他最终于1896年将该基因遗传病确定并命名为“家族黑蒙性白痴病”。“白痴”是指患者从来没有正常的心理功能;“黑蒙”是指患者开始为视力不佳,最终变得完全失明;称之为“家族”是因为所有病患的资料都显示他们具有犹太血统,一些病患是兄弟姐妹关系,还有相当大数量的病患父母是近亲结婚。由于许多患者家属认为“家族黑蒙性白痴病”这一名称让他们倍感受辱,考虑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后人倾向于按其研究者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泰伊-萨克斯二氏病”[7]。
其次,柯旺充分考虑了技术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及其对技术使用和推广的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泰伊-萨克斯二氏病不能治愈,只能依靠药物或者饮食延续患者的生命。于是,针对该病的研究方案重心从治疗转向了预防。研究者们开发了针对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的测试技术,并在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城市进行宣传。该预防方案立即遭到了犹太领袖和一些会众的反对,尤其是传统的正统犹太教教士,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加污名于犹太人的做法,也是纳粹主义的延续,而且与犹太教反对堕胎和避孕的精神相违背,这些顾虑正是筛查泰伊-萨克斯二氏病的严重障碍。直到1983年,犹太教领袖爱泼斯坦(Joseph Ekstein)在遭受第四个患病儿出生的打击后彻底顿悟,提议测试青少年身体状态,创建一个对外(包括被测试者)绝对保密的机密化验结果注册表,呼吁年轻人在想结婚或生育小孩时去调用注册表。许多了解这一疾病的人对此筛查方案十分注重并积极参与,他们以社区为基础在学校、犹太会堂和社区中心设立机构,大规模筛查具有泰伊-萨克斯二氏病风险的成年人,几乎所有承担风险的夫妇都自愿接受产前诊断并决定终止受患胎儿的妊娠。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医学遗传学家组织者本身就是犹太人,许多咨询者是犹太人,测试技术资金也经常来源于犹太慈善机构。截止到2000年,世界上有15个国家建立了上百个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测试点,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的质量保证服务系统,拥有国家和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及相关疾病协会的资助,同时追踪所有的社区筛查方案,并进行年度质量控制评估。在此情况下,泰伊-萨克斯二氏病这一毁灭性的遗传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困扰的民族共同体以婚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这两种手段所击败[7](P143)。
同样地,地中海贫血症基因筛查的案例研究也表明作为技术消费者的塞浦路斯人在该项基因筛查技术推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7](P198-208)。相反,镰状细胞病基因筛查技术在美国发展的历史却没那么顺利。这正是因为美国各群体对此没有形成道德共识和政治共识,而且美国诸州的法律法规各有差异,镰状细胞病基因筛查从来没有被制度化。在医疗上,测试方法上的漏洞导致误诊误判,从而引起了非裔美国人的反感;在政治上,黑人群体认为镰状细胞病基因筛查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政治策略,各类慈善组织也采取了回避态度。这些因素使得镰状细胞病基因筛查技术因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互相争斗而寸步难行[7](P180)。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柯旺的研究旨趣从早期的技术与女性、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问题,转向了技术与移民、遗传病患者、少数民族等边缘群体的关系;尤其注重解析技术使用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切身体验,剖析隐藏在技术背后的各种利益动机,强调技术使用者接受、抵抗、协商、形塑技术的实践与意义;强调技术的发展是各种文化、社会因素共同建构的产物,同时它的影响也进一步深入到包括性别观念在内的各种文化思想的变革之中。
四、结语
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家庭生活经历、受教育背景和第二代女权主义浪潮的触动下,柯旺开始从性别的角度研究技术。但其关注的问题基本是技术对女性的影响,在技术观上采取的“技术决定论”的基本立场,对性别的看法也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社会性别理论、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启发下,柯旺开始致力于解构技术背后的利益动机和父权制内涵,重视性别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渐深入,柯旺进一步强调技术使用者和边缘群体对技术发展的形塑作用,并同时关注技术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之间的建构关系。
从柯旺的技术研究内容和范式的变化发展中,我们亦可管窥整个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所经历的类似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同时她的工作也彰显了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独有的学术价值。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运用边缘人群的经验立场、生活体验、知识背景来解读技术,强调不同的技术知识与其相关群体的国别、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相互联系,其研究进路对STS研究和女性主义学术自身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女性主义强调考察和研究那些未被充分关注的包括家用技术和生育技术在内的技术类型和技术场域,不仅扩充了技术研究的视界和范围,更拓展和改变了对技术自身的理解。
[1]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411.
[2]Ruth Schwartz Cowan.More Work for Mother: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M].New York:Basic Books,1983.
[3]Ruth Schwartz Cowan.Looking Back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John McDermott’s“Technology: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J].Technology and Culture,2010,51(5):199-215.
[4]Ruth Schwartz Cowan.Gender and Technology Change[A]. //Donald A Mackenzie,Judy Wajcman.ed.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C].Michigan:Open University Press,1985:53 -5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57-458.
[6]易显飞.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特征探析[J].哲学动态,2013(7): 92-97.
[7]Ruth Schwartz Cowan.Heredity and Hope:The Case for Genetic Screening[M].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135.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Ruth Schwartz Cowan's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Zhang Mei-fang,Gong Yi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Beijing 100083,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s of technology and gender,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roach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wan's technology study.It suggests that Cowan's view of technology has changed from"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to"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the objects of her study have expanded from"household technology"to"production technology"and"reproductive technology";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have shifted gradually from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gender to the cultural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shaping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
feminism;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Ruth Schwartz Cowan
N0
A
1672-934X(2014)02-0027-05
2014-03-10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20059)阶段性研究成果
章梅芳(1976-),女,安徽安庆人,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为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龚 艺(1986-),女,湖北洪湖人,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史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