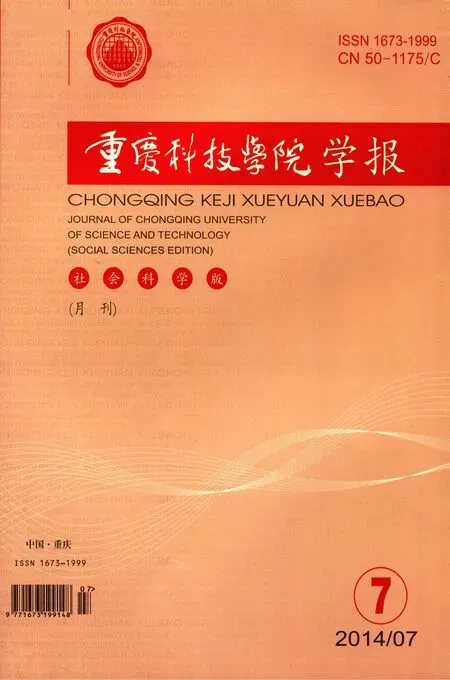“伤痕文学”概念探微
刘 杨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这一基本判断已被许多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所承认。然而作为一个概念,“伤痕文学”逻辑上的内涵与外延具体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而且在具体使用或者论述这一概念的时候却存在着一些分歧。如今“重返80年代”的工作有许多学者在做,我们在重返的过程中,不仅要以历史化的眼光重新发现被掩埋的真相,还要立足于基础工作,从基本概念入手清理学术遗留问题。
从现有的学术成果(包括文学史和相关研究论文)来看,对于“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分歧不大,但是要讲清楚其外延则较为困难。笔者梳理了一下,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关系的处理。在这一问题上,较为通行的认识是“伤痕文学”指那些侧重于揭露文革和极“左”思潮对于人们造成的伤痕(trauma,也译作“创伤”),这包括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而“反思文学”更侧重于对于伤痕背后的原因(如极“左”思潮的成因等内容)的反思。从逻辑概念上说,对于这两个思潮的内涵的区分勉强可以成立,但是,对其外延的认识就会产生很多分歧,因为伤痕叙事往往是反思的起点,而反思叙事往往又包括伤痕。例如《天云山传奇》是属于“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不同的研究者就有不同的认识,在有的文学史著作中视其为“表现‘伤痕’的作品”[1]258,而有的文学史著作则视其为“反思文学”[2]202。
第二,“伤痕文学”的文体范围问题。一般而言,在文学史中叙述者常常有意识地将 “伤痕文学”与“伤痕小说”等同起来,然而,这样做无疑是将“伤痕文学”范围窄化了。在新时期文学肇始的时候,各类文体中都有作品可以被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举例来说,在散文中,巴金的《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都可以说是“伤痕文学”;在戏剧作品中,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等作品如果按照“伤痕小说”的叙事主旨来看也可视为“伤痕文学”;在诗歌中,由于文体的自身特点易于抒情,更是有一大批“伤痕诗歌”。照此看来,“伤痕文学”的文体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而当下对“伤痕文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小说层面有所侧重。
第三,“伤痕文学”与“知青文学”(或者说“知青写作”)的关系问题。本来“伤痕文学”与“知青文学”是两个范畴,“伤痕文学”是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被提出来的概念,“知青文学”是从创作群体的角度被提出来的概念。但是,由于“知青文学”的写作一直持续到当下,所以有些研究者亦将“知青文学”看成是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思潮。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两个概念是有交集的。因此,在对“伤痕文学”全面的研究过程中,有必要厘清“伤痕文学”的具体内容,避免在文本分析时引起混乱。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伤痕文学”的内涵相对较为固定,但是它的外延却不是那么容易确定,而有论者在研究时认为“‘伤痕文学’有着很多面向,也存在着不同层次”[3],这样的策略性处理不是不可,但是作为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依据文学词典将其内涵定义为“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样式。这类文学以1977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的发表为起点,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而得名。这些作品的特征是揭露和控诉‘文革’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4]516但是,对于其外延的范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被指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总应该有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对“伤痕文学”外延的认识。
从文学体裁来看,“伤痕文学”的作品以小说为主,包含有戏剧、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有些研究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例如有学者就曾经提出:“70年代末的这股‘伤悼’诗潮是本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172。但是在“伤痕文学”思潮中,产生较大影响并且为文学史接受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从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小说的地位和影响一直都是“最上乘”。“伤痕文学”中的小说作品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思潮的命名即以小说《伤痕》命名,但是我们在对“伤痕文学”进“历史化”研究的时候,有必要把被以往文学史遮蔽的或谈得较少的其他体裁的作品纳入研究视野,这样才能对“伤痕文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叙事内容来看,“伤痕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是苦难经历叙事。从“伤痕文学”的文本实践来看,口号上的“向前看”和文学创作上的“向后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产生了不小的论争,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5]。“伤痕文学”的主要叙事内容是主人公的苦难经历,所谓“伤痕”包括肉体上的伤痕,也包括精神上的伤痕,而且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伤痕。要表现精神上的伤痕,作者往往就叙述主人公的苦难经历,像被批斗、劳改、坐监狱、受孤立等等情节经常出现,像《天云山传奇》这样的作品虽然也有反思倾向,但是由于作者的叙事内容与“伤痕文学”的典型作品诸如《伤痕》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因此可以看作“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交叉作品,将这些作品纳入“伤痕文学”的外延,对于其中伤痕叙事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伤痕文学”的认识。
从情感倾向来看,“伤痕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是带有同情或感伤情感。“伤痕文学”的作品大都是悲剧或带有悲剧色彩,这样可以更为强烈地批判 “文革”乃至极“左”思潮对人的精神创伤,那么作者在叙事时往往就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情感倾向。而在一些典型的“反思文学”作品中,作者在叙事时不再带有强烈的情感,而更多的是一种冷静的思考,不仅仅对于笔下的人物也包括对于自己所叙述的故事情节,例如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作品。因此,“伤痕文学”的典型作品区别于“反思文学”的典型作品的重要之处就是:“伤痕文学”作品的叙事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例如,在《天云山传奇》中,作者对于罗群这样的形象是极力赞扬的,对于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深表同情的;在《班主任》中,作者更是直接站出来呐喊“救救孩子”。
从接受层面来看,能够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最重要的、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在于其中的伤痕叙事。“伤痕文学”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与文学接受状况不无关系。“伤痕文学”的典型作品常常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我们必须承认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几年中,文学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是因为那时的主流文学作品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例如在《天云山传奇》发表之后,中央也加快了“右派”政策的落实工作。为什么这些作品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除了权力话语的加入,笔者认为这些作品打动读者的部分主要是其中的伤痕叙事,它让许多读者能感受到切肤之痛,这也与“伤痕文学”的主要叙事内容有关。
从创作手法来看,“伤痕文学”的大部分作品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在17年时期,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等方法,至“文革”时演化为背离延安文学传统的“三突出”。而“伤痕文学”由于其内容多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所以其创作方法也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而在“伤痕文学”的创作中,现实主义方法的运用也出现了分野,有一些作家自觉坚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延续了17年时期的写作范式,比如从维熙的“大墙文学”系列,这类作品最终要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同构;有一些作家的创作则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虽然在当时“批判现实主义”还没有被主流话语完全接受,但是从创作实践来说,一些作品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没有差别,比如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这类作品中更多的蕴含着批判性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意旨拉开差距甚至相去较远。需要指出的是 “朦胧诗”中的一些属于“伤痕文学”的诗篇也有一定的现代主义色彩。
从产生时间来看,具有较大影响的“伤痕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产生于1978年至1983年。进入19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更迭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因此,“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思潮也偃旗息鼓。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发表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如《随想录》中的作品,由于巴金的持续写作,这些作品是在1980年代陆续发表的;像老鬼的《血色黄昏》这样的作品,“由于描述的直率, 几家出版社先后拒绝”[1]258,因而也是到1980年代后期才出版的;还有一些长篇小说,由于创作过程较长的原因出版往往较晚,比如《蹉跎岁月》等等,不过这样的现象不是普遍的。由于我们是重新梳理这段时期的文学,是进行“历史化”的研究,因此1980年代发表的一些作品也应该纳入本文框架。而对于“知青文学”来说,笔者认为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这一时期的知青创作也应该纳入 “伤痕文学”的范围中,例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品。
当然,不同的学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自己不同的认识。笔者用简短的篇幅对“伤痕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是希望在拉开一段历史距离之后,为了深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要进一步厘清不同文学思潮的区别,对一些曾经似是而非或者界定不清的问题作一个较为明晰的分析。当然,笔者这样处理无意颠覆既有文学史叙事,只是希望在“重返80年代”的背景下对“伤痕文学”的概念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认识。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8.
[2]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02.
[3]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J].当代作家评论,2008(3).
[4]王芸.文学知识手册[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516.
[5]于逢.“向前看”“向后看”剖析:关于广东文艺界最近的一场争论[N].光明日报,1979-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