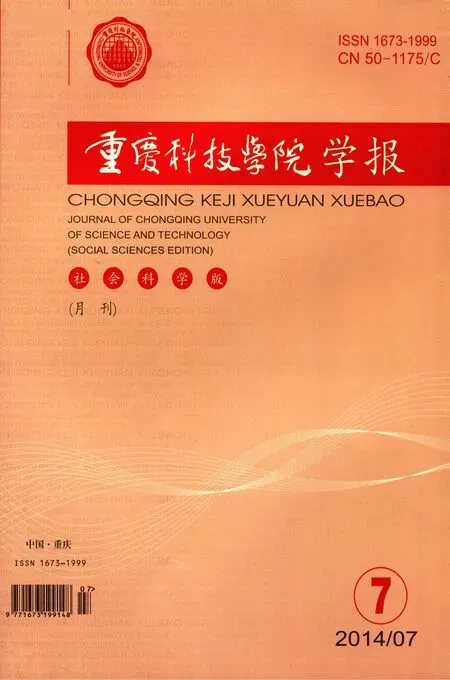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论析
王 玉
一、柳宗元思想的时代背景
柳宗元,字子厚,他所生活的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方面地方藩镇割据势力日益膨胀,朝内宦官和大地主、大官僚专权日益严重,边疆奴隶主贵族不断策动叛乱;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加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荣辱莫测的家境,动乱不安的时代,在柳宗元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柳宗元登上政治舞台后,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危机,深切地担忧唐王朝的前途和命运,决心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当时,具有革新政治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王叔文、王伾、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晖、凌准、程异等志士仁人,组成了一个政治革新派。王叔文是皇太子李诵的侍读,深受李诵的赏识和信任。柳宗元同这些新派人士一见如故,“定为死交”,并积极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
但是,“永贞革新”失败后不久,王叔文惨遭杀害,王伾被逼死,韦执谊也因忧愤病死,柳宗元也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唐宪宗改号为元和那年,全国大赦,却特别规定“八司马”不在赦免之列。柳宗元过着“罪人”一样的生活,他的住处五年内被烧了四次,弄得“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住”。但是,柳宗元没有因此消沉,一方面他“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认真攻读,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探“理乱之本”;另一方面接触下层社会,考察官府的橫征暴敛和民间的疾苦,思索利弊之所在。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积极参与的革新运动是正确的,他的革新思想和革新理论更加成熟了,可惜无法付诸实施,他立志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自己的革新主张,以便将来东山再起。于是,他克服了生活和疾病的重重困难,“勇不自制”地奋起疾书,写下了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诗文,为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增添了宝贵的篇章。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唐宪宗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应诏回到长安。他喜出望外,以为自己有希望重新被起用,继续实施自己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宦官和藩镇势力仍然视他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排挤、诬陷她。结果他又被贬到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当刺史。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柳宗元感到无限的悲愤。他决心运用柳州地方最高长官的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改革措施,同时著书立说,批驳敌人的各种谬论。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月,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结束了他为革新政治思想而战斗的一生,享年47岁。柳州地方人士为了纪念这位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后来在他的灵柩停放的罗池兴建了他的衣冠墓和“柳侯祠”,立碑刻上他的肖像和诗文。直到今天,古色古香的“柳侯祠”依然供游人凭吊。
二、柳宗元提出的重“势”无神论思想
柳宗元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都收在 《柳河东集》里。其中,大部分诗文是他在前后贬谪十四年、身囚山水、潜心史籍时的“孤愤之作”。
“永贞革新”失败后,韩愈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以“论史”为题,直接批评和教育柳宗元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邢”,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赏功而罚祸”,永贞革新违背了天意,因此柳宗元等人是罪有应得,并劝柳宗元改邪归正。柳宗元当即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天说》等文,批驳韩愈的唯心主义有神论说教,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为了全面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他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和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写下了《天对》。《天对》是以回答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作《天问》的形式写成的。此外,他还先后写了 《非国语》《封建论》《贞符》《断刑论》《时令论》等重要哲学著作,自成中唐时代的一家之言。
(一)提出了“元气”一元唯物主义无神论
柳宗元认为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物质。“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天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跟瓜果草木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他又说:“曶黑(黑夜)晰眇(白天),往来屯屯(不停歇),庞昧(蒙昧)革化(变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天对》)认为“元气”是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原始物质“元气”构成的,不是由谁创造的。因此,所谓上帝创造九重圆天,女娲补天之类的神话,不过是古人的迷信妄说,完全不可信。
柳宗元认为世界是无限的。他说:“天地之无倪(无边),阴阳之无穷,以鸿洞(弥漫)交错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或轮或机。”(《非国语》)认为天地是广大无边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着。他还提出天地无边无际,谁也不能衡量它们的长短大小。因此,所谓天地的产生必须依赖某种有限的框框如“太极”之类的神秘东西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
柳宗元还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具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在回答《天问》中关于“阴阳三合,何本何化”的问题时说:“合焉而三,一以统同。吁(慢)炎吹(快)冷,交错而动”(《天对》)。意思是说,阴、阳、天地三者结合在一起,统一于元气,而元气本身又分为阴阳这样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阴阳交错对立的运动,促使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他运用这一具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世界,阐发了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驳斥了一切唯心主义有神论的邪说。他指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怎么)乎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安排)?”(《非国语》)就是说,山崩地裂、河枯水断等自然界的变化,都是元气内部阴阳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引起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不是什么人去安排或创造的。他举例说,天广大无边,都是游离的气体,不是相互连接的固体,没有、也不需要依靠八根栋梁来支撑。古代神话说有八根大柱支撑着,共工和颛顼打仗,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那完全是古人幻想编造出来的。地球对着太阳就是白天,太阳照不到地面就是黑夜,所以天亮不是天门打开,天黑也不是太阳隐藏起来,总之,天体旋回转动是它们自然而然的运动(《天对》)。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里,以种树的道理说明了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他说橐驼所种的或移植的树,长得高大茂盛,结果早而且多,这并不是因为他能使树木活得年岁长而且生长快,而是因为他能按照树木生长需要的自然条件去适应它的习性,既不损害它的生长,又不损害它的结果。而别人种树则不是这样,不是随便简单了事,就是爱护过分,经常用指甲去抠树皮,摇树干,不能按照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去种植护理,结果树木生长得不好。因此,柳宗元认为只有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否则,事物就要遭到破坏。
柳宗元从元气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继承和丰富了荀子、王充、范缜的无神论思想。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人事的好坏,国家的兴亡,跟天没有关系,“攻者自攻,祸者自祸”(《天说》),决不是什么天赏罚的结果。“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元而已。其事各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因此,他肯定自然的生长繁殖和社会的治乱,各有各的规律。人与天 “各不相预(干涉)”,而那种希望天的赏罚或祈求天的怜悯宽恕,让天来主宰人类命运的想法,是极大荒谬的。柳宗元对世界的本质作出唯物主义的回答,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以韩愈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论,闪烁着战斗的光辉。但是,柳宗元毕竟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对当时流传甚广的佛教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相反,他还写了宣扬佛教的文章,对它作了某些妥协,甚至采用佛教“戒杀“的迷信来反对杀牲敬神的迷信。这反映了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二)提出了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
柳宗元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超过先期唯物主义哲学家的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这些进步观点主要体现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中。
首先,柳宗元指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贯穿这个过程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他说人类最初同其他动物一起生活在森林里,“人不能博噬”,斗不过野兽。为了生活和自卫,必须利用工具。由于人们彼此之间不断发生争夺,这就需要有“能断曲直”的人来调解纠纷,这些人便成为“群”的首领。如果首领调节不下,就要依靠“刑政”、暴力来进行统治,因此产生了“君长刑政”。群与群发生争执,需要有优秀的人出来管理,这些人便成为“众群之长”。这样逐渐“推戴”出诸侯、方伯、连帅、天子,伴随着形成了道德、刑政和政权(《封建论》)。一句话,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类生活的实际需要。柳宗元用这种道德史观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当然不是唯物史观,但他企图从社会历史内部、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来探索国家的起源,这对于反对神学历史观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柳宗元指出历史的治乱兴衰、制度变革都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他认为封建制(分封制)的产生、发展以及被郡县制所取代,既不是“圣人之意”,也不是神的旨意,而是有其客观的必然趋势。过去社会分封国土、建立诸侯国的制度,在当时是必然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封建制度虽然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产物,但它是一种“私”的制度,“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到了周朝,封建制就暴露出许多问题。后来,秦始皇用“公之大者”的郡县制取代了“私其力”的封建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虽然死了,但秦朝的制度仍然存在。这就生动地说明了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封建论》)。柳宗元以“势”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当然不是科学的,但他提出的“势”,一方面与“神”对立,另一方面与“圣人”对立,打掉了上帝和天子头上的神圣光环,这种思想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再次,柳宗元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出发,系统地批判了历代有关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等神学史观和君权神授思想。西汉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提出“天人感应”的谬论,编造“符瑞”,用自然界的阴阳变异附会人类的治乱兴衰,作为“君权神授”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据。“永贞革新”期间曾经发生雨涝,韩愈等人便附会说这是革新派上台执政的结果。柳宗元针对这些谬论,特地写了《贞符》等文加以驳斥,他明确指出:帝王“受命于人,于其人;休符(美好的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任之人,匪祥于天”“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认为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受命于“生人之意”,即民众生活的要求和意愿;只有得到人民支持的政权,才能维持长久。而董仲舒之流宣扬“符命”思想,是以讹传讹,荒诞可笑的,是用以欺骗后人的。柳宗元还特别总结了汉唐王朝兴衰的原因,着重阐述了汉刘邦、唐李世民所以兴盛,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之意”,依靠政治革新。这就不难看出,柳宗元这种重“势”的进步历史观是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是为他所参与的政治革新运动的合理性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三、柳宗元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第一,他把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斗争同坚持“永贞革新”的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柳宗元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般都是从事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没有或很少直接参加当时的重大政治斗争。柳宗元则不同,他不仅在哲学上坚持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而且亲身参加当时最重大的政治斗争——“永贞革新”,同坚持唯心主义天命论的宦官和藩镇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仍然在理论战线上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作论证。这充分表明,柳宗元的哲学体系具有难能可贵的实践意义。
第二,柳宗元依据当时的科学知识,比较全面、系统地坚持了“元气”一元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而且对许多自然现象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例如,他把阴阳两气看作元气内部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的交错对立促使物质世界的多样变化,这显然是对老子的朴素辩证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他认为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是物质性的“元气”自己的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显然是对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传统的丰富和发展。他运用唯物主义无神论去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不仅打击了神学历史观和“圣人”创世说,而且还天才地洞察到了封建主义的一些特点,指出古代氏族贵族专政的特权制度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的东西,认识到当时社会中贫与富的对立,并试图探究贫富不均的根源,甚至提出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大胆地肯定“贱者”“远者”和“新者”(即中小地主和人民群众)对于“贵者”“亲者”和“旧者”(即大地主官僚等豪门贵族)的抗争是合乎规律的,这表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民性。
第三,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学熔为一炉。他不仅是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散文家、优秀的诗人。元和以后,他一直过着贬谪生活,在钻研史籍的同时,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撰写了许多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具有很高水准的诗文。他采用寓言的形式写了许多哲学著作,例如《三戒》就是一组代表性的哲学寓言。其中《永某氏之鼠》批判了天命论,文中说永州有一个非常相信“天命”的人,因为他生于子年(鼠年),所以把老鼠当作神灵,千方百计加以保护。家里的老鼠依仗主人的宠爱,越来越猖狂妄为。后来,这个房间换了主人,新主人认为老鼠是“阴类恶物”,便设法捕杀,结果老鼠尸体堆积如山,臭气冲天,数月才消。柳宗元在这里把那些以“天命”为精神支柱的宦官和藩镇势力比作老鼠,指出他们终将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下场;同时也愤怒地揭露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象属鼠的主人一样愚昧无知。这样的哲学文章,形象生动,说理透彻,具有俗雅共赏的风格。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哲学体系是别具一格的。他的“元气”一元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不仅是对荀子、王充、范缜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继承和丰富,而且对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启发作用。因此,尽管柳宗元的哲学体系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在我国哲学史上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1]侯外庐.柳宗元哲学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德哲学[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