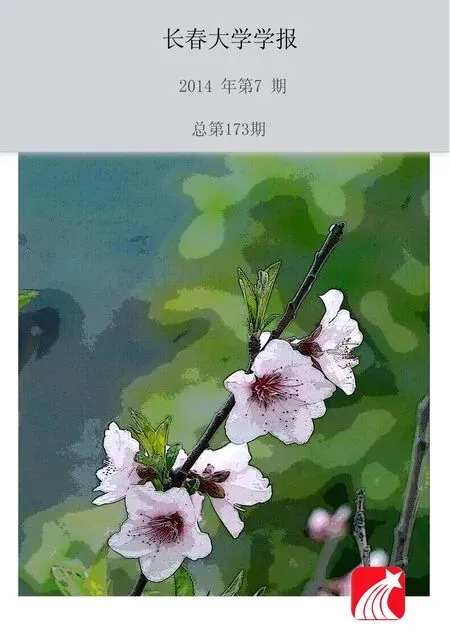从辐射视角看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以《游仙窟》《仙女红袋》为中心
孙惠欣,付晶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 133000)
从辐射视角看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以《游仙窟》《仙女红袋》为中心
孙惠欣,付晶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 133000)
在古代亚洲的汉文化圈里,中国文化长期占据辐射中心的位置,而朝鲜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文章从辐射视角切入,以《游仙窟》《仙女红袋》为中心,从故事情节、思想内容、文体特征等方面探讨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学;朝鲜文学;辐射;影响;《游仙窟》;《仙女红袋》
在古代亚洲的汉文化圈里,中国文化长期占据辐射中心的位置,汉文与汉字、儒释道、相似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是东亚文化圈的基础,而东亚文化圈是以汉文化作为核心而得以形成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汉文学无疑是这种辐射作用的直接体现,其中就汉文学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数量而言,朝鲜半岛无疑居于首位。据史料记载,朝鲜三国时期,中国的典籍就已经大量传入朝鲜了,“奉使入宋,所赐金分与从者,余悉买书籍以归。”[1]古代朝鲜新罗(公元前57年-935年)末高丽(918年-1392年)初期,中国和朝鲜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关系都比较密切、频繁,大批遣唐留学生和留学僧负笈求学,通过和唐代文人的接触交流,积极揣摩文学内涵。沿袭了六朝志怪创作经验的唐传奇的传入为朝鲜传奇作品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并对之后朝鲜传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仙女红袋》就是典型的实例。本文从辐射视角切入,以唐代传奇作品《游仙窟》、朝鲜新罗末期传奇作品《仙女红袋》为中心,探究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1 《游仙窟》与《仙女红袋》
1.1 《游仙窟》
《游仙窟》是唐代的一篇传奇作品,成书于武则天执政时期。作者张鷟(约660年—740年),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是唐代著名的文学才子,在士林中曾赢得了“青钱学士”的雅称。《游仙窟》是其自叙体传奇小说,描写作者奉使河源,夜宿“神仙窟”与两女子调笑戏谑、把酒言欢、歌舞宴饮的风流韵事。据《唐书》记载,当时张鷟的文章“被新罗、日本的使臣争相重价购买”,由此说明,早在公元后7世纪《游仙窟》便已经流传到周边各国并被当地文人学者接纳、研读。《游仙窟》从唐朝之后就失传了,直至晚晴,学者杨守敬从《日本访书志》中将此书从日本抄回中国本土,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1.2 《仙女红袋》
《仙女红袋》是朝鲜新罗末的一篇传奇作品,又称《双女坟记》《崔致远》。《仙女红袋》构思巧妙,辞藻华美,描写的是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的一段风流韵事,是现存《新罗殊异传》①《新罗殊异传》是朝鲜新罗时期一部志怪、传奇作品集,其作者说法不一,作品以汉文文言文写成,传至今日。《新罗殊异传》遗文共13篇。中篇幅最长、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篇传奇作品。关于其作者,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有学者根据此篇作品主人公名字与新罗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崔致远同名,而且崔致远在中国期间,也的确有凭吊双女坟之举,便推断此作品为崔致远所作。但此作品并未收录到《孤云先生文集》和《孤云先生续集》中。韩国历史学家李基白于1972年为《崔文昌侯文集》而写的《题解》中,更明确认定《新罗殊异传》中的该作品不可能是崔致远本人所作,属别人假托,认为该传奇很可能是新罗以后的作品[2]。
中国现今最早关于《双女坟记》的记录便是南宋张敦颐所著《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三。“而在韩国现存的关于《双女坟记》最早记录则出现于朝鲜朝初期的《太平通载》卷六十八,其版本也是最为完整的,并且标明录自高丽《新罗殊异传》,其题为《崔致远》。”[3]
2 辐射视角下中国文学对《仙女红袋》的影响
“辐射与定理一样属于科学术语,但是比喻的方法可以使它表达另一个比较研究的公设。”[4]这是布吕奈尔和谢弗莱尔在《简明比较文学》一书中对辐射研究的定义。所谓辐射,其“发生包括辐射中心和辐射范围,辐射中心在整个辐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5]。辐射中心的形成是由中心区域内在的人文条件所决定的,所谓辐射中心就是该区域人文要素所收敛而形成的中心点,其辐射作用表现为在被辐射区域的发散过程。而辐射中心的文学作品,正是其社会人文背景下个体思维经过收敛与发散后的主观表达形式,同时也成为辐射中心的文化要素之一。而这种反复多次并且范围愈加扩大的群体性思维发散与收敛的过程,就是辐射的过程,辐射的过程也是新要素融入辐射圈的过程,二者是辨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在东亚文化圈内,中国文化的辐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尤其是对朝鲜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等。而这些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朝鲜文人,其创作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印记,《仙女红袋》便是很好的例证。
2.1 故事情节的影响
《游仙窟》与《仙女红袋》男主人公的官职都是县尉,描写的都是尘世男人和冥界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游仙窟》中主人公自诩为“下官”,奉使河源,旅途中夜宿“神仙窟”,与两女仙十娘五嫂艳遇,互相诗书言情,调笑戏谑,宴饮歌舞,共度一夜良宵之后,以凄然的心境作别;《仙女红袋》中写崔致远在就任溧水县尉途中,在县南招贤馆因诗与两女子鬼魂相遇,作诗唱和,共枕缠绵,最后别离的故事。“一男两女”作为一种特定的“情境”,在这两篇传奇里向我们展示了人物间的特殊关系,从而衍生出复杂的故事情节。两篇传奇对女人的称呼也很相似,《游仙窟》中的双女名为“十娘”“五嫂”,年方17、19;《仙女红袋》中双女名为“八娘子”“九娘子”,年方18、16。两部作品中都有侍婢的介入,《游仙窟》中的桂心成为“下官”和十娘、五嫂之间感情传递的重要纽带,在“下官”和十娘、五嫂作诗唱和之时在一旁侍奉酒席,另一侍女绿竹在酒席间弹筝;《仙女红袋》中的翠襟,成为崔致远和八娘子、九娘子之间感情的传递者。由此可见,侍婢成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两部作品引诗入小说的描写也很相似,《游仙窟》中,“下官”去拜访五嫂,侍婢桂心将男子引至堂间与十娘相见,又去请五嫂赴宴,席间三人饮酒作诗,交谈唱和,以诗歌酬答的形式相互调情,缠绵之后默然相别;《仙女红袋》中,崔致远凭吊双女坟,同样是通过赋诗形式盛邀八娘子九娘子前来相见,饮酒之时又是以诗传情,最终缠绵一夜之后别离。
《仙女红袋》故事情节与载于《搜神记》的《天上玉女》,载于《搜神后记》的《白水素女》,南朝宋人刘义庆所撰之《幽明录》似乎都有关联。《天上玉女》中其人神遇合,赠以信物,歌诗酬唱,离别等故事情节,《白水素女》《幽明录》中人神相恋的故事模式,均在《仙女红袋》中体现出来。
同时,《仙女红袋》还受《任氏传》《五行记》的影响。九娘子寄给崔致远的七言律诗开头:“每希秦女能抛俗,不举任姬爱媚人。”其中的任姬就是沈既济所作《任氏传》的女主人公。崔致远与八娘子、九娘子开玩笑时说:“不向闺中作黄公子之婿,翻来冢侧夹陈氏之女奴。”其中的“陈氏”指的是《五行记》所载的《陈朗婢》的“陈朗”[6]。
2.2 思想主题的影响
《游仙窟》和《仙女红袋》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基本是一致的,都表现出了对自由恋爱的大胆追求和相爱之人不能长相厮守的悲哀。
在信奉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礼教下,是不会允许文人学士自由爱情的存在的,《游仙窟》《仙女红袋》中浓重的凄婉结局就印证了这一点。《游仙窟》中的“下官”终将启程,“少时,天晓已后,两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胜。侍婢数人,并皆嘘唏,不能仰视”;《仙女红袋》中崔致远再留恋八娘子和九娘子也不得不曲终人散,“数声余歌断孤魂,一点残灯照双泪。晓天鸾鹤各西东,独坐思量疑梦中;沉思疑梦又非梦,愁对朝云归碧空。马长嘶,望行路,狂生犹再寻遗墓;不逢罗袜步芳尘,但见花枝泣朝露。”
这两部作品中对渴望自由爱情女子的描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较早地表现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仙女红袋》中死于父命威逼之下的两女子,宁肯牺牲生命,也不愿做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表现出极为勇敢的一面。而当她们遇到心仪之人时,则表现出极为大胆的一面,勇敢地追求并实现自己的爱情,尽管这爱情仅仅是短暂的一夜,也终生无悔。这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三从四德”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表现出作者对压抑人性的封建传统礼教的批判精神,具有进步意义。
两部作品的作者都生活在封建社会,其社会背景、人文背景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所接受的教育也均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在古代亚洲的汉文化圈里,中国文化长期占据辐射中心的位置,而在历朝历代中,经济兴盛、文化发达的唐代,其中国文化的中心辐射作用就更为突出,唐代文人的文学思想与创造思维在当时的亚洲是具有先进性的,《游仙窟》中对封建传统礼教的批判精神便体现出唐代文人的进步思想特征,这种进步思想对周边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辐射,《仙女红袋》便是例证,从这部作品中能够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朝鲜文人受到辐射后其思想主题向辐射中心靠拢的倾向。
2.3 文体特征的影响
《游仙窟》全文以散文叙事,人物对话多以诗歌代之,以韵语对话,文辞浮华艳丽,结构严谨完整,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颇有汉魏六朝辞赋的韵味。与变文韵散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写得生动活泼。它标志着自六朝志怪向唐传奇的转变,在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有人称之为“新体小说”。《仙女红袋》与《游仙窟》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的,韵散结合,讲究音律,注重意趣。引大量诗歌韵语入小说也是《仙女红袋》借鉴《游仙窟》所至,这部作品在韩国汉文小说史上开了“引诗入小说”的先河,诗歌在文中所占比例竟高达41%。其诗歌以三言、七言为主,韵趣十足。《仙女红袋》是现存新罗末高丽初传奇中最长的一篇,艺术水平很高,“就其思想艺术水平以及创作意识和虚构意识来看,《崔致远》已经达到了真正的传奇小说的水平。”[7]
通过上述对《游仙窟》与《仙女红袋》之对比分析,明显看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对朝鲜古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仙女红袋》中有着明显的中国文学的印记。通过对朝鲜半岛汉文学的研究,不但可以揭示出亚洲文化圈内中国古代文化的辐射方式,还可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在亚洲范围内影响的深度,挖掘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渊源,从而确立中国在世界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
[1]郑麟趾.高丽史:九十五卷列传卷第八[M].首尔:新书源出版社,1958:196.
[2]韦旭升.朝鲜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2-53.
[3]徐健顺.《双女坟记》的创作与流传过程辨析[J].东疆学刊,2010(3):17-24.
[4]Brunel Pierre,Yves Chevrel.Préc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9:48.
[5]陈蜀玉.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辐射方式的个案分析:以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165-167.
[6]朴熙秉.新罗末高丽初时代传奇小说研究[J].大东文化研究(S1225-3820),1995(3):13.
[7]金宽雄.韩国古小说史稿[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277.
责任编辑:柳克
A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Korea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diation —With the Cases of A Tour to Fairy Cave and The Fairy's Red Bag
SUN Huixin,FU J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Yanbian University,Yanji 133000,China)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Ancient Asia,Chinese culture always occupies the center of radiation,while Korea is a countr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most deeply.From the radiation angle,centering on A Tour to Fairy Cave and The Fairy's Red Bag,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mpac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Korean literature from the plot,ideological content,stylistic features and so on.
Chinese literature;Korean literature;radiation;affection;A Tour to Fairy Cave;The Fairy's Red Bag
I207.41
A
1009-3907(2014)07-0921-03
2014-03-31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WW020);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13-0992)作者简介:孙惠欣(1968-),女,吉林安图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韩文学比较研究。
——关于文学游仙的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