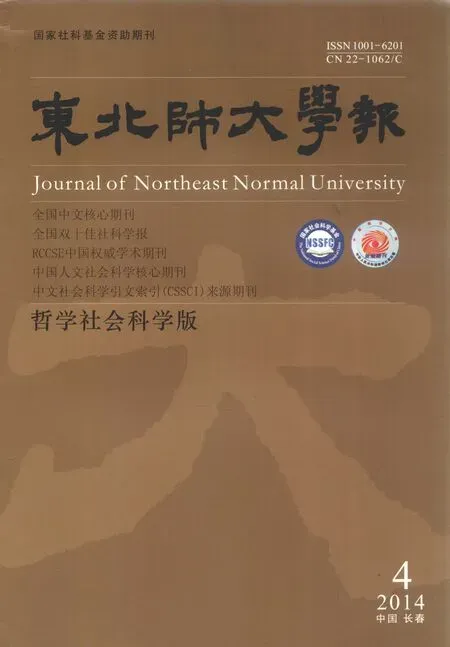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与HPC*
张存建
(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与HPC*
张存建
(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经典名称语义理论没有专门讨论自然种类的划分与存在,而自然科学研究不断得出结论质疑语言哲学家对自然种类的解释。在对语义问题的反思中,逐渐形成一个依托性质界定自然种类的研究传统,并形成关于自然种类的两个解释:“类本质主义”和HPC。二者对性质之间的关联有不同把握。HPC避开了揭示本质性质探究的困难,因为纳入较多认识论思考而能够相对充分地解释自然种类的稳定存在。
自然种类;本质主义;性质
自《命名与必然性》(1980)出版以来,自然种类词项(natural kind terms以下简称NKT)的语义研究逐渐成为语言哲学的热点。最近10年间,克里普克(S.Kripke)和普特南(H.Putnam)关于NKT语义的研究格外引人瞩目,两人先后因此获得被誉为哲学“诺贝尔奖”的“肖克奖”。然而,迄今并没有广为接受的关于NKT的定义。在相关讨论中,一般把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文本中分析的一些自然种类名称视为NKT,这些名称是对自然中发现的对象的命名,如“水”、“虎”、“柠檬”、“黄金”、“玉”、“哺乳动物”、“橡树”等都是NKT。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原因是,学界对“NKT指称什么”没有统一认识。传统的回答接受外延主义(extensionalism),认为NKT指称实在的对象。但这一回答遇到两个困难。首先,油、水等NKT所意谓的对象无法量化,难以确定其外延,而当出现临界对象(如鸭嘴兽)时,人们往往改变原有NKT的外延。其次,在克里普克引领的名称语义理论中,NKT具有严格性(rigidity),是严格指示词,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指称同一对象[1],但严格指示词思想与外延主义冲突。如果认为“虎”严格指称实在对象虎,则必须接受一个荒诞的要求——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虎的数目相同;如果认为“虎”指称由某种“虎性”决定的类,则任何名称(甚至包括一些摹状词)都将因为指称“…性”决定的类而成为严格指示词,使得严格性成为一个不足道的术语。为此,部分学者反对将严格性从专名类推到NKT,但他们相信科学已经揭示出一些自然种类的存在,认为NKT指称自然种类[2]。这就是“类指称说”。“类指称说”实际是将指称问题转变为自然种类的界定问题,属于外延主义的变种。但如何界定自然种类?或者,根据什么标准将某些对象划分为一个自然种类?
一、历史与挑战:关于自然种类所意谓对象的本体论研究
“类指称说”的拥护者很少区分自然的类与非自然的类,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类之存在作出探究。蒯因(W.Quine)对现代版“类指称说”作出总结。他将“类”之存在限定到集合,并将类与相似性及归纳结合起来[3]550-557。然而,集合是一个数学术语,而自然语言中的词项并不具备数学意义上集合的特征。例如,有的对象是“兔子”的指称,有的对象肯定不是“兔子”的指称,但还有一些边缘性对象,不存在一个用以判定它们是否是兔子的标准[4]。“类指称说”寄希望于科学探究界定自然种类,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不断得出一些否定“类指称说”的结论。一些生物哲学家因此提出“个体说”,主张把生物体视为有时空片段特征的个体[5]。但是,把握“个体”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象的认知,但我们很难从相关文献中找到关于个体的本体论探究。
对个体的关注刺激和助推了语言哲学家对“类指称说”的反思,他们试图通过语义分析修补“类指称说”。“描述论”(the description theory)者首先给“类指称说”以辩护。接受“描述论”的必要性在于,人们不得不用某个/些摹状词(description)解释表达式的意义。例如,当被问及“水是什么?”时,多数情况下人们用“无色、无味、透明、可以饮用的液体”之类的短语所描述的性质作答。以性质描述界定名称的外延,这是“描述论”的突出特点。但也正因为如此,克里普克等人批判“描述论”的论证都可以被类推为对“类指称说”的批判。
克里普克等人以“三大论证”(即模态论证、语义论证和认知论证)重创“描述论”,他们随之构建对指称过程的“因果论”解释,但“因果论”延续了“描述论”以性质揭示自然种类外延的做法。“因果论”者提出关于自然种类的一种新解释——“性质说”。克里普克把拥有本质性质视为对象成为类之成员的充分必要条件,给出本质主义的基本思想。普特南(H.Putnam)、索姆斯(S.Soames)、戴维特(M.Devitt)、博德(A.Bird)等认为本质主义“太强”,转而接受某种弱的本质主义。例如,索姆斯以“粗糙生成的性质”界定自然种类,并认为这些性质中可能存在一些“关键”性质,关于自然种类的“性质说”也不断遭到批判。但总体上看,以性质界定自然种类,接受类与性质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语言哲学家的一个共识,而且,这一共识得到一些科学哲学家的认可[6]。
自《命名与必然性》发表以来,本质主义始终是语言哲学的一个热点,而对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解释首当其冲。但整体上看,语言哲学家给出的外延主义方向及其推进并没有被其批判者彻底否定,双方都不否认以揭示对象性质的方式解释自然种类的存在;自然种类的“性质说”给出了一种对“类指称说”的诠释,其推进有赖于对本质主义作出进一步的审视。
二、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解释
系统的关于本质性质的思考始于洛克(J.Locke)。洛克将本质分为“名义本质”和“实在本质”,“名义本质”是人们在某个历史阶段划分与命名对象时所依据的性质。例如,黄金的“名义本质”是黄金这个语词代表的复杂观念,如黄色的外形、有重量、可以锻造、有熔点等。“实在本质”则是一簇性质,它们是事物成为某个类之例示(instance)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洛克对发现事物的“实在本质”表示悲观,认为不可能通过实践观察把握实在本质性质[7]。300年后,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捡起洛克关于“实在本质”的话题,他们对凭借科学获得确定性知识满怀信心,认为可以由专家完成对实在本质的探究,提出本质主义思想。在克里普克看来,摹状词不是严格指示词,专名和NKT都是严格指示词。对于严格指示词A和B而言,如果A=B表达一个真命题,则A=B就是一个必然真命题,因而,可以根据B的内涵解释A的本质。例如,水的本质是“分子式是H2O”。普特南则以思想实验构筑其本质主义思想,他把对象共有某种潜在“微观结构”视为其本质。普特南很少提及“本质性质”(essential property)一词,他代之以“本质属性”(essential attributes)。这也许是普特南防备不可知论的一个策略。毕竟,现有自然种类主要是由普通人而非专家界定,将本质性质的探究交给未来专家,意味着接受对现有自然种类划分的可能修正,而这随时可能与相对主义挂上钩。
最初的本质主义主要强调本质性质的存在,认为专家在揭示本质性质方面有无可替代的权威。自然主义者则关注本质性质与其他性质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对象的本质性质决定匹配给类之成员的一般性质。例如,黄金的原子结构决定黄金在某个温度融化[8]。有学者把经过如此丰富的本质主义称为“类本质主义”。“类本质主义”预设本质性质的存在,它关注NKT及其语义在科学解释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拉近了NKT语义分析与世界之实在的关联,或者说,“类本质主义”给出了一种诉诸语用界定自然种类的方向。但“类本质主义”遇到的批判也主要来自对科学探究事实的解释性反思。下面分析生物学领域对“类本质主义”的两个批判。
首先,接受进化论,则必须否认本质性质的存在。现代生物种从古代物种进化而来,进化导致物种改变,因而不可能存在决定生物种的本质性质。苏波(E.Sober)认为这个论证无效,其依据是,氧可以转化为氮,但这并不证明关于化学类的本质主义为错[9]356。笔者赞同苏波的观点。当我们说生物种进化时,并不是说生物种这个类的进化,而是说生物种的后代逐渐变得不同于其祖先;“恐龙进化为鸟”不是说一个抽象的实体可以变成另一个抽象实体,而是恐龙的一个例示(instance)可以产生鸟的一个例示。因此,以进化否证生物种是自然种类的做法有混淆语义问题与本体论问题之嫌。
第二种对“类本质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否定本质性质的存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引入一种界定生物种的方式——群组思想(population thinking)。群组思想按照特征分布来描述生物种,认为生物种是由异质个体杂交而来区域种群,它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性质表现,诸如杂交之类的集体行为使得生物种具有产生新物种、灭绝及适应性改变等特征。批判者把群组思想视为一种关于实体的本体论主张,认为只有构成种群的个体才是实在的,其他存在都是抽象物[9]352。如果接受这种批判,如何认识种群和生物种这样的范畴?否认其实在,则大部分后达尔文生物学研究都将变成一派胡言。上述关于群组思想的解释是不妥当的。笔者赞同另一个解释,即把群组思想视为解释自然种类划分与存在的工具,将它理解为关于性质的本体论解释[10]。基于这一解释反思“类本质主义”,则应该关注性质的解释作用,而不是集中于否定本质性质的存在。
对“类本质主义”的批判突出了推进“类本质主义”所需关注的两个方面:(1)本质性质的揭示问题。如何从对象拥有的诸多性质中识别出本质性质?(2)本质性质在科学解释中的作用问题。如何认识性质在科学解释中的作用?事实上,许多生物哲学家并不否认生物种有本质,他们关注第一个问题,将论题转向本质性质的认知。例如,莱坡特从概念修正的角度认为本质是约定的结果,劳维(J.Lowe)则给出其“理解性思考”(comprehending thought)论证,认为“本质可以先于存在”,除非假定存在一些本质性质并假定知道这些本质性质,不可能在“理解”的层面谈论或思考对象[11]。本质性质的认知依赖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认知本质性质的困难随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发现与日俱增,任意一个关于本质性质的概括似乎迟早都要被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所否定。例如,人们原以为“拥有分子结构H2O”是水的本质,但逐渐发现一些动摇人们关于如此信念的事实:常态的水是混合物,水中含有重水和超重水,即便纯粹由H2O构成的水也非多个H2O分子的堆砌,水以齐聚物(oligomers)的方式存在。理论上,揭示本质性质的努力没有止境,但在实际科学探究过程中,现有关于自然种类性质的界定总能实现与科学的“视域融合”;科学史上存在这样一种主流取向:接受科学探究对类之本质性质的修正,甚至接受对类之解释的“革命性”重构,但不否认原有解释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解释力。“燃素”、“以太”这样的类的境遇就是如此。这说明,“类本质主义”遇到的两个问题是同一的,揭示本质性质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学解释的困难,它们都需要一种解释学的回答。
以认识论过程检验对自然种类的语义解释,这是“类本质主义”暗自接受的一种方法论,其实质是,以NKT的使用裁剪对自然种类外延的解释。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自然种类的存在先于关于自然种类的探究;在有了水的名称之后,才有了关于水的性质的探究,并将“分子式是H2O”作为水的本质性质。就知识的存在与辩护而言,水的所有性质都在发挥解释作用。因此,在解释层面,存在一种超越本质主义解释自然种类的可能:对于描述对象的那些性质而言,如果它们能够达成理想的科学解释,则可以认为它们共同决定一个自然种类。这一解释搁置本质性质的探究,但需要关注决定对象属于某个类的性质之间的关联。在解释对象的那些性质之间,除了存在“类本质主义”所谓的本质性质与一般性质之间的决定关系,还可能存在其他关系,如制约、影响、聚合等。事实上,在科学探究中不乏以性质之间关联界定自然种类的情形。例如,对于解释水的各种形态、金刚石与石墨的差别、蝌蚪变成青蛙等论题而言,如果说科学家诉诸本质性质,也是诉诸某种由性质之间关联机制决定的东西。当然,使上述界定自然种类的可能性由应然走向实然,需要探讨性质之间的关联机制,把它作为划分自然种类的关键。
三、关于自然种类的HPC
界定自然种类的基本条件是,它所意谓的对象有同样的特性,允许归纳和全称概括。这是支持“类本质主义”的一个坚实直觉。然而生物学家意识到生物种所意指的个体之间存在差别,所谓“归纳”和“概括”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如果将生物种从自然种类中排除,则“类本质主义”的合理性无疑会大打折扣。蒯因为此给出一个关于类的“宽容”(liberal)解释:并非所有集合都是类,但其成员共有某些性质的所有集合都是类[3]531-535。之后,部分哲学家采纳蒯因这一解释并对之作出推进,生物学哲学家博伊德(R.Boyd)就是其中之一。1988年,博伊德在《道德实在论文集》中给出了如此努力的一个榜样,他明确拒绝关于生物种的“个体说”,提出关于自然种类的“自我平衡性质簇说”(the homeostatic property cluster view of natural kinds以下简称HPC),日渐引起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人类学、解释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
HPC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种类由一簇性质决定,它们历时地簇集在一起,使得自然种类成为一个有缺陷但可以自我平衡的整体;可能其中部分性质会促进其他性质的呈现,但在自我平衡机制的作用下,这些性质倾向于共同出现;对于成其为类之成员而言,没有哪一个性质可以保证某个对象必然是类的成员[12]。博伊德所谓自我平衡机制,指基因流变(gene flow)、杂交、共同遗传、生态学选择等生物学术语表达的东西,它既是关系性质也是因致过程,不为生物种的某个成员所单独拥有;决定自然种类的自我平衡机制并不唯一,自我平衡机制决定性质簇的一个子集,多个自我平衡机制共同决定自然种类之为类的同一。自然种类外延中的对象可以例示性质簇的不同子集,但生物种仍然是由同一簇性质决定的实在,对象因为例示性质簇的子集而属于类,同一类对象之间的差异则由其例示之子性质簇作出解释。因此,自我平衡机制给自然种类以相对的解释灵活性,允许不同学科领域根据其研究需要对对象作出不同划分,或者说,它允许不同自然种类之间的外延重叠,给解释生物种的内在异质性留下了余地。
HPC使得生物种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做出生物学解释及预测的条件,而支撑这种解释整体性的是自我平衡机制[13]。然而,HPC的批判者首先批判的正是这种解释整体性。批判者认为,与最初的本质主义类似,HPC不能解释生物种历时进化这一现象[14]。但自我平衡机制仅仅是一个技术术语,其工具性体现于解释断定类之边界的因致过程,并不保证生物种不发生改变。在HPC的视域下,生物种是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整体而进化,但这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进化,并不排除进化过程中生物种内区域种群的变异。如果生物种内的某个区域种群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将通过基因流变等方式传递到其他区域种群,整个生物种随之发生改变。应该说,HPC允许把生物种视为历史实体,但不强调生物种的历史性,它并没有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
对HPC的另一个批判是,HPC预设存在决定对象属于某个自然种类的一簇性质,如此预设相对集中于生物种所有成员共有的某些特征,因而HPC忽略了生物种内的个体多态性[15]。“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与之类似,生物个体之间总是存在差异。上述批判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如前所述,HPC可以解释生物学种类之间的内在异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HPC肯定个体多态性的存在。而且,根据博伊德对自我平衡机制的解释,即便个体发生了变异,也是发生了由自我平衡机制维系的变异,正是在如此生物学机制的维系下,生物种内的变异才不至于变种。还应该看到,解释生物种内个体多态性固然对于生物学而言至关重要,但HPC旨在界定生物种类,并不针对解释生物种内的个体多态性。
从博伊德及其支持者对HPC的分析来看,自我平衡机制不仅服务于科学探究,还来自于科学探究;科学家在裁定自然种类方面仍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权威性。然而,由于存在实验条件、实践或理论兴趣的局限,科学家可能对自我平衡机制做不同的解释。博伊德并不讳言HPC的认识论取向,他还将社会学的类解释为自然种类,认为它们展示了一些满足社会科学归纳或解释任务要求的稳定关系[16]。着眼于科学解释和推理的需要解释自然种类,这就为将HPC由生物学类推到化学、物理学、人类学、科学哲学等领域奠定了基础。
四、结 语
关于自然种类划分与存在的研究源于对NKT语义问题的分析,在自然科学研究结论的激发下,逐渐形成一个依托性质界定自然种类的研究传统。较之于“类本质主义”,由于纳入较多认识论思考,尤其是纳入对归纳和解释需要的思考,HPC可以相对充分地解释自然种类的划分与存在。“类本质主义”肯定本质性质对一般性质的决定作用,但遭遇本质探究方面的困难。HPC着眼于性质之间的非因致关联,可以借助性质之间的自我平衡机制给自然种类以解释灵活性,但HPC对性质之间何以簇集的解释预设某种性质实在论,搁置了性质探究问题。在此意义上讲,HPC表达了一种弱的“类本质主义”。但是,HPC不是“类本质主义”的替代品,它在保有自然种类之解释整体性的同时,为解释相近NKT之间的语义重合留下了门径。相比之下,HPC在解释自然种类之稳定存在方面对“类本质主义”做出了推进,它为解释“NKT指称自然种类”,以“因果论”解释指称改变、理论改变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而回应库恩“不可通约”论题创造了条件。
[1]Kripke,S.Naming and Necessity[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48.
[2]Schwartz,S.P.Formal Semantics and Natural Kind Terms[J].Philosophical Studies,1980(38):189-198.
[3][美]苏珊·哈克.意义、真理与行动[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4]陈波.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451-52.
[5]Ghiselin,M.T.Species Concepts,Individuality,and Objectivity[J].Biology and Philosophy,1987(2):129.
[6]LaPorte,J.Natural Kinds and Conceptual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5.
[7]Jolley,N.Leibniz and Locke on Essence[M]//In Leibniz: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Hooker,M.(e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87:196-208.
[8]Ereshefsky,M.Species[J/OL].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10 Edition).Edward N.Zalta(ed.).URL:<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0/entries/species/>.
[9]Sober,E.Evolution,Population Thinking,and Essentialism[J].Philosophy of Science,1980(47).
[10]Nanay,B.Three Ways of Resisting Essentialism about Natural Kinds[M]//In Carving Nature at Its Joints:Natural Kinds in Metaphysics and Science.Campbell,J.K.edit.MIT Press,2011:190.
[11]Bird,A.A Posteriori Knowledge of Natural Kind Essences:A Defense[J].Philosophical Topics,2009,35(1-2):293.
[12]Boyd,R.N.Realism,Anti-foundationalism,and the Enthusiasm for Natural Kinds[J].Philosophical Studies,1991,61:127-148.
[13]Wilson,R.A,Matthew J.Barker,Ingo Brigandt.When Traditional Essentialism Fails:Biological Natural Kinds[J].Philosophical Topics,2007,35(1-2):189-216.
[14]Kluge,A.The Repugnant and the Mature in Phylogenetic Inference:A temporal Similarity and Historical Identity[J].Cladistics,2003,19(4):234.
[15]Craver,C.Mechanisms and Natural Kinds[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2009,22:575-594.
[16]Boyd,R.N.Homeostasis,Species,and Higher Taxa[M]//In Species: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ed.R.A.Wils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9:141-185.
Two Ways of Defining Natural Kinds:Essentialism and HPC
ZHANG Cun-jia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While classical semantic theories of names talk little about the division and existence of natural kinds,scientific researches give increasingly conclusions refuting the traditional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of natural kinds.Based on reflections of semantic issues,there has been a study tradition in which philosophers generally define a natural kind on basis of some properties.Then two new interpretations of natural kinds appeared.They are so called“kind-essentialism”and HPC.They take the relations among properties differently.HPC differs from“kind-essentialism”.It avoids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essential properties.Because of taking more epistemic considerations,HPC can serve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ble existence of natural kinds.
Natural Kinds;Essentialism;Property
B087
A
1001-6201(2014)04-0066-05
[责任编辑:秦卫波]
2013-04-0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6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3SJB720002);江苏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12XWR011)。
张存建(1971-),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本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作者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