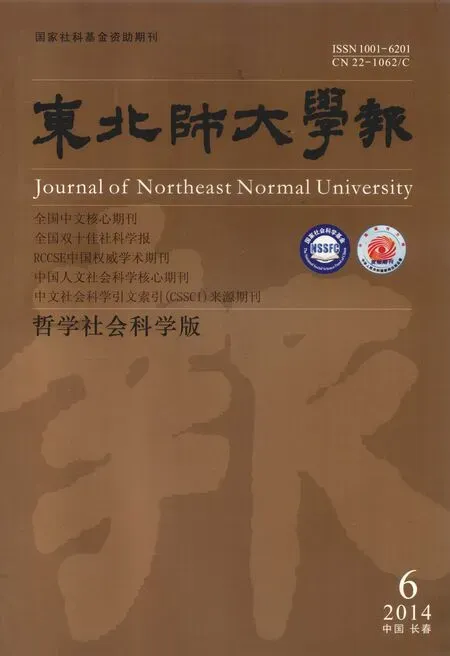从“西域”到“西北”
——西北边疆拓殖与开发的历史启示
杨 斯 童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从“西域”到“西北”
——西北边疆拓殖与开发的历史启示
杨 斯 童
自汉代开始在西域设立属国和都护,以迄清代的西北治理,不难发现,西北边疆地区经历了一个由被内地争权羁縻、争取的外围地域即“西域”,逐渐演变、被整合为中国国土即“西北”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即由“西域”到“西北”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指称上的改变,其实质性的内容是“西北”边地内化为“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北”成为“中国”的西北——尽管这一历史进程中曾经历战乱、分裂、割据,但其总体的趋势却是指向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格局的最终形成。
西北边疆;拓殖;开发;西域;西北
一、“西北”:“西域”之再发现
“边疆”是一个历史性、流动性的概念,它随着历史上的中国国势的消长、疆域的膨胀或紧缩而有所伸缩,并且与文明的传播有莫大的关联,正如梁启超在写于1902年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所说:
大抵中国地理开化之次第,自北而南。三代以前,河北极盛;秦汉之间,移于河南,浸移于江北;六朝以后,江南亦骎骎代兴焉。而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江、河之间原野。……淮汉民族之在中国,其犹近世条顿民族之在世界也;而点缀其间者,则有幽、燕、赵、代、陇、蜀诸族……。此外位其南者,未尝有能为一国之重轻者也;其有之,则近百数十年始也[1]。
梁启超所描述的中国文明开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疆域拓展的历史大致不错。但是,梁启超所关注的是“文明开化”的历史,因而他将关注的中心放在了黄河、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域,却认为诸多少数民族和地域仅是中国的“点缀”。这种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论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诸多外患之际,显得过于迂腐[2]。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现今地理,可概分为两部:一曰本部,十八行省是也;二曰属部,满洲、蒙古、回部、西藏是也”——这种以“本部”和“属部”将内地和边疆对峙起来,重“本部”而轻“属部”的历史态度,在列强蓄意瓜分中国,纷纷染指中国边疆的时代,不能不为顺时而起的边疆史地研究所取代,而其所忽视的边疆,也成为一时显学。“西北”之再发现,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得以实现的。
“西北”在19世纪就已经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魏源等人的西北舆地之学在论及边疆开发时,已经注意到“西北”在战略上的重要性[3]。到了20世纪,时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北”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比如朱希祖在给《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所作的序中开篇就说:“西北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则为中枢。”[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论者对“西北”的高度关注。几年后,贺岳僧所著的《西北史纲》,更从文明起源的角度,将“西北”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呼吁人们改变对“边疆”的偏见[5]。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于西北边疆的称呼,已经习惯于使用“西北”而非“西域”,尽管“西域”一词由于历史的惯性,直到现在依然活跃,但它模糊不清的“国属”指向性及其所带有的文化偏见,使得人们更愿意用“西北”来指称那片广袤、重要的国土——“西北”是在中国的广大时空之下而言的,西北“是一个方向,因为有中国的存在才存在的一个方向,是从中国方向意义的一个命名。”[6]而“西域”,则在一种“异域”、“异邦”的色彩中削弱了人的认同感。比如较早提到西北地区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都把西北的广大区域描述为不毛之地,充斥着奇异怪诞的人种和国度[7]——姑且不论其记载是否属实,单看古人的态度,不难发现,“西域”实乃“化外之地”。直到汉代的《神异记》中,虽然西北的拓殖与开发已有了较为长久的历史,在人们眼中,“西域”依然如故[8]。
事实上,人们早就对西域乃至更为遥远的西亚、欧洲有了较为确切的认识,比如司马迁的《史迹·大宛列传》中关于条枝、安蔡、黎轩等国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人对伊朗、罗马乃至意大利半岛都有确切的了解[9],但人们更愿意相信“传说”、“神话”中怪诞不经的“西域”,这其中,大概暗含了中国人以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自居中心的心态。而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地位的陡然降低,中国面临的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西北”等边疆的再发现无疑是重要的,它告诫世人在国家界限分明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和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疆土哪怕是偏远边陲之地,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都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二、中国西北的拓殖与开发史
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中,曾问吾将中国自古以来对西北边疆的拓殖与开发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自汉至明,清朝,民国以来,并注重介绍了各阶段经营西域的主要政策。他认为,汉代之经营西域,主要有两种政策:羁縻及监督,屯田;唐主要有列置州府和军府两种方略;五代及两宋时期,由于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遍布各少数民族政权,因而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主要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元代蒙古西征,将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并设立四大汗国统治西域,且有三行省、三宣慰司;明代则以朝贡关系维持中央政权与西域的关系;到了清代,中国版图基本确定,西域基本成为中国西北稳定的疆土,清政府在新疆等地正式设置官府、驻兵屯田,以此为根据地羁縻中亚各国。这一历史线索大致反映出西北疆土之由“西域”逐步演变为中国“西北”并不断巩固的历史进程。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化,中国历史上的西北政策逐渐明晰、细致地展现出来。据考证,夏商周时代,中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今天的甘南、敦煌一代,甚至敦煌以西的广大沙漠地区,也在其影响力所及之内[10]10-11;而夏商周时期中国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以通婚和封国羁縻为主,这开启了后世中国边疆政策的先河。根据《左传》、《国语》、《史记·周本纪》等文献的记载,西域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那时已经非常频繁,且周王朝以“五服”制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羁縻,比如《国语·周语上》记载犬戎在当时为“荒服”,按照规定,承认周王为天子,一世一朝见即可。但周穆王对此不满意,要将其升为“宾服”,要求每年朝贡四次[10]10-11。——由此可见,早在上古时代西北地区即成为中国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在中原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威慑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下,作为“边疆”的“西北”正在不断被开发、影响、同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向更为辽远的西北拓展。到了春秋时代,秦国的崛起与称雄,充分说明这一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经完全“中国化”了,而它所控制、影响下的广大西北地区,又成为新的边疆。
秦灭六国,建立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中央集权国家(《史记·秦本纪》);汉兴以后,多次派张骞等人通西域,并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将西部边疆拓展到天山南北和以西的乌孙、康居地区,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地理格局。中央政权在西北边疆的政策主要包括:一、设立属国和西域都护,如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在西域屯田养边并由专门的屯田校尉职守其事;二、赐封少数民族政权,加强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支援边疆经济文化建设,促进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11];三、与匈奴等西域属国通婚“和亲”,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怀柔边缘少数民族政权,在“战”与“和”互济的军事策略下维持国家的和平与统一,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下来。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据有北方的曹魏政权,大致承继了汉代的西北边疆政策,维持了对西北边疆的有效行政管辖,东晋十六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在西北边疆曾前后出现前凉、后凉、南凉、西秦、北凉、西凉、成汉等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多个政权的分峙并立及其相互征战、替代,加强了西域各部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进而为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中国重现“大一统”局面,对包括西北边疆在内的地区采取“怀柔”、“羁縻”的策略,在西北边疆设立羁縻州县,并加强军镇屯戍,设有西域都护和北庭都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西北边疆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屯田、互市以及民间自由贸易等各种途径,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联系深化到一定程度,并充分重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因而,这一时期的边疆政策被认为是比较开明、开放的[12]。辽、宋并峙时期,宋政权失去对西北边疆的控制,而辽则在唐代西北政策的基础上,将羁縻州府改制,向诸多少数民族地域派置节度使,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行政管理[13]。金政权勃兴以后,继承了辽朝所控制的广大西北边疆区域,在政策上也基本沿袭了前者,进一步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对内地的接近。
元朝中国疆域实现了空前拓展,为实现对如此辽阔的疆域的控制,元统治者采取了多种边疆政策,仅在西北,就实施了分封汗国、设立行省、设置宣慰司、都元帅府、驿站等策略,一方面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北边疆的直接行政掌控,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威慑和怀柔政策,笼络西北乃至中亚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统治者多次遣发蒙古族、色目族和汉族在西北诸地驻戍屯田,可以说,元朝加强边疆地区的施政,建官设制,多方经营的边疆政策,对于开发和扩大我国疆土意义深远,元代发军屯戍,移民实边的措施,对于边疆的开发和保卫,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4]。明代边疆政策尤其是西北边疆政策以“守”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军事卫所和羁縻卫所,并辅之以屯田;其所确立的朝贡和互市的制度,有效维系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富民兴边:西北边疆拓殖与开发的历史启示
西北边疆地区经历了一个由被内地争权羁縻、争取的外围地域即“西域”,逐渐演变、被整合为中国国土即“西北”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西域”到“西北”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指称上的改变,其实质性的内容是“西北”边地内化为“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北”成为“中国”的西北——尽管这一历史进程中曾经历战乱、分裂、割据,但其总体的趋势,却是指向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格局的最终形成。
纵观两千余年的西北边疆政策,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历史启示,对于今天而言,是尤为重要的:
其一,必须加强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卫和保护。从战略位置上讲,西北边疆地区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枢纽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就像前引朱希祖所言,自西北,东可直抵中国腹地,南可下中亚、南亚次大陆,西可控西亚乃至欧洲,北能抵西伯利亚地区,在当今军事科技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和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虽然中国一贯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方略,然而也要防患于未然,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卫和保护。这既有利于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为边疆开发和发展提供有力的军事保障,又对国家安全和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必须加强边疆地区的开发,提高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实施富民兴边战略。历史上的屯田政策和措施,正是富民兴边战略的雏形,无疑极大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减轻了内地在访边、输边上的压力,激发了边疆地区人民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力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在当今时代,要有效维护边防安全和国家统一,富民兴边战略是不可或缺的。唯有富民兴边,才能真正巩固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
其三,要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的高度来重视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交流。实施富民兴边战略,不仅要注重开发边疆经济,还要高度重视边疆文化发展,尤其是要着重推动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推动民族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西北边疆地区虽然与内地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它与内地一样,都是中国辽阔广大国土的一部分,西北边疆人民的文化,更是中国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巩固,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的保卫,中国大一统格局的维护,有赖于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实施富民兴边战略事关重大,不可忽视。
[1] 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937-938.
[2] 赵强.“中国文学”发现自身的方式[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1):37.
[3] 伍成泉.魏源的边疆开发思想浅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0-35.
[4]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
[5] 贺岳僧.西北史纲[M].重庆:文信书局,1943:2-11.
[6] 张未民.《东北论》关于“东北”的论述[J].东北史地,2004(4/5):47-54/54-64.
[7] 山海经[M].袁珂,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251,443;张耘点校.山海经·穆天子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227.
[8] 王根林,等,校点.汉魏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6.
[9] 张政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13.
[10] 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0-11.
[11] 王宗维.秦汉的边疆政策[M]//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1-76.
[12] 林立平.隋唐的边境政策[M]//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53-173.
[13] 林荣贵.辽朝的政区双轨制及其对北部边疆的管辖[J].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188-190.
[14] 罗贤佑.元朝的边疆政策[J].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259-261.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秦卫波]
2014-07-03
K207
A
1001-6201(2014)06-0267-03
——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