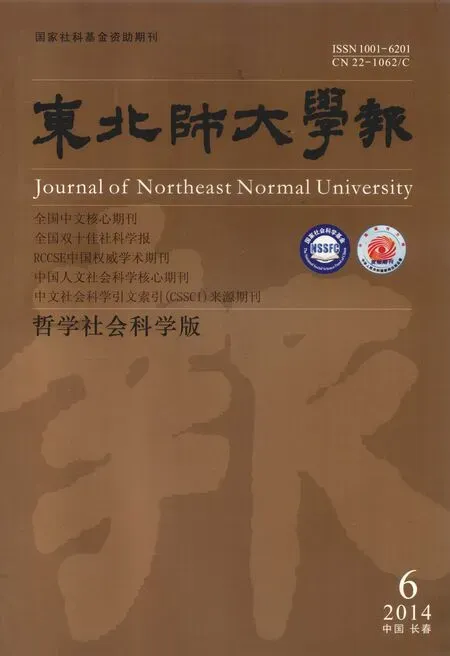殖民语境下身份的焦虑
——《夹竹桃》的文化意蕴
蓝 天
(1.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广东开放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1)
殖民语境下身份的焦虑
——《夹竹桃》的文化意蕴
蓝 天1,2
(1.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广东开放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1)
《夹竹桃》是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发表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该文以抗战中沦陷区北平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困难生活。文中混杂着作者复杂的情感,同时,作者通过“反历史书写”和“双重语气”等策略,揭露了殖民者的虚伪,否定了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钟理和;身份认同;夹竹桃;混杂;反历史书写;双重语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乡土文学”在台湾岛内崛起,该文学思潮既是对岛内50年代盛行的“战斗文艺”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修正,也是文学回归民族、回归现实的历史必然。一批才华横溢的台湾省籍作家崭露头角,成为“乡土文学”的主力军,其中钟理和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钟理和一生坎坷,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生长于台湾的殖民时代,幼时入乡塾学习汉文,后又进公学校学习日文,是日据台湾时期为数不多坚持用汉文写作的本省作家。抗战爆发后,他携妻逃离台湾,先后在伪满和北平生活8年。抗战胜利后返台,一直居住在台南封闭的山区,贫病交加,“与外界绝少来往”,但笔耕不辍,“在乡土文学史上留下了震烁的、撼人心弦的一章。”[1]
《夹竹桃》是钟理和早期的一部作品,1945年与其他三篇小说合集以《夹竹桃》为名在北京出版,这也是作者生前唯一公开出版的专集。此后沉寂了20多年,直到70年代才在台湾公开发表,一时成为许多人竞相批评的对象。受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或多或少掺杂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偏离了审美的轨道。今天,当我们回归到艺术创作的原点再去解读它时,才能真正感受到殖民时代中被殖民者的痛苦。
一、“身份认同”的混杂
夹竹桃是一种常绿灌木类植物,茎部像竹,花朵像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钟理和以此为题,不正是想要表达自己当时“身份认同”的困惑吗?
身份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成员身份即文化归属的认同感,包括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是内与外的一个桥梁,是个人与社会的桥梁。我们把自我投射到这些文化身份上,同时也把这些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内化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2]而霍米·巴巴认为,“身份是一种异源集合体,它并不是人们生而固有的东西,而是在历史、文学、科学、神话等众多文本中被建构出来的。因此,身份是就特定条件进行认同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固定的,而是临时和变易的。”[3]对于在殖民环境下接受殖民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其自我意识是通过与宗主国(殖民者)进行认同而建立起来的,这个“他者”的在场,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有一个稳定的主体身份,他的身份必定是分裂而又双重甚至是多重的。生长在殖民时代台湾的钟理和,其文化身份构建既受到了来自所属族群的内部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来自殖民者强加的外部认知的作用,形成了文化身份的杂交性。他的自传体小说《原乡人》就形象地叙述了被殖民者杂交身份构建的过程。
小说中,一方面,“我”的祖母和父亲固守和传承着族群的历史文化,不断地向年轻一代述说着族群的移民史:“我们原来也是原乡人”[4]1,“我们便是由中国广东省嘉应州迁来的”[4]5。通过言传身教,长者们帮助族内成员建构着自我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我”被迫进入日本人开办的公学校,接受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在学校,日籍教师经常把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将他们描述成“衰老破败”、“怯懦,不负责”、“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形象,这些丑化中国人的言论,对于年幼的“我”是“无法弄明白……(不知)自己该不该相信”[4]5的。通过这种“认知暴力”的手段,殖民者把他们的价值观移植到被殖民者的头脑中。
当钟理和踏上原乡之后,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始终困扰着他。他曾在《祖国归来》一文中写到,刚到大陆时,“有一种感觉使他们高兴:即回到了祖国的感觉。”[5]32然而,由于“生活的牵连与环境的累赘”,钟理和只好“系于伪政权之下”[5]33。在大陆的几年中,他衣兜里“一边揣着中国政府颁给的居住证明书”,“一边放着日本居留民团的配给票”[5]33。这种身份的困惑在《夹竹桃》中表露无遗,作者从地域、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给主人公曾思勉设定了南方人、人道主义者、文化批判者三个身份,这些身份有时同一,有时分裂,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游移。
曾思勉在某机关做事,是“由南方的故乡来到北京”。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实则透露出作者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曾思勉与大杂院里其他人家仅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差异,他眼中的北京人,是“一家一单位,他们彼此不相闻问,他们这么孤独而冷僻地,在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不想过往,他们的门,单独的闭着”[4]109,这让“生长在南方那种有醇厚而亲昵的乡人爱的环境里”的曾思勉感到了“索寞与冷淡”。南方山区的乡村,聚族而居,相对封闭,与以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大杂院相比,自然拥有“醇厚而亲昵”的一面。曾思勉以南方人的视角来批判“只扫自己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邻居们,虽有偏颇之处,但还是处于同一个民族话语的架构中。
曾思勉还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这种身份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使他总是站在一个所谓客观的“他者”立场,审视着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他们”。曾思勉批评同院中“多愁善感”的哲学系学生黎继荣所说的“道德与法律”上的人道主义:“趁早收起了你那一文不值的人道主义吧!告诉你,那种东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它离实际太远,至少在现在!”[4]108他认为“在生命得不到保障的这些人们身上,使用道德与法律,那是怎样可笑而且无聊……只要你饿三天,那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学得了怎样巧妙地去觅得你要求的两个窝窝头的方法的。很简单,肚子会教你做很多事情。”[4]108黎继荣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曾思勉的人道主义是人类共有的悲悯之心,还无法进入民族的正体,将民族的苦难归结到“他们是命运的傀儡”这个宿命论上。
曾思勉还是一个文化的批判者,他时而站在民族立场上进行文化自省;时而又将自身与大杂院中的“他们”隔离开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甚至隐含着一种殖民者的思维方式,对遭受深重苦难的同胞进行尖刻的嘲讽。作者文化身份出现了分裂,认为自己与大杂院里的那些“他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与生活观念”,继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惑,这正是殖民时代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的缩影。
黑暗的旧中国让许多仁人志士失望,他们在不少作品中吐露出内心的悲哀与愤怒。但这一切的悲愤“有一个下限,就是这悲愤源于对中国深切而焦虑的爱”和“不丧失批评者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立场。”[6]105生长在台湾的钟理和,毫无大陆经验,他对大陆的认识一部分来自于家族内部成员碎片式的叙述,还有不少是获得于扭曲的殖民教育。当他目睹了战争中大陆的凋敝与衰落,内心的失望与不满使他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了信心。
小说中的曾思勉虽然生活在大杂院,却与其他住户少有来往。曾思勉总以第三人称的“他们”来称谓邻居,无形中拉开自己与民族的距离。曾思勉的言行不正是一个被殖民者身份认同困惑的真实写照吗?
二、历史的书写与反书写
钟理和的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特点,是小说与传记混合的文体。他的作品常常出现两个自我形象:一个是历史的叙述者;一个是历史的评判者。两个自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证了文本中史实的真实性,弥补了一般自传文学缺乏客观性的不足。《夹竹桃》掺杂着复杂的情感,但作者对战时北京城内底层人民悲惨、落后生活的描写,连批评过这篇小说的陈映真先生也说:“在这大杂院里充满着不堪的贫困和道德的颓败——吸毒、自私、偷窃、幸灾乐祸、卖淫和懒惰。如果这就是大杂院,就是当时的北京城;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人应该对他的现实性有丝毫的怀疑。”[6]200
殖民时期,殖民地历史的书写是由殖民者主导的,殖民者“出于一种邪恶的逻辑”,对殖民前的历史进行贬低,对过去肆意地歪曲、丑化、毁坏,其目的是“凭其不知羞耻的暴力,在政治、社会、军事、文化一切生活的诸面上,支配殖民地民族。在心理上,支配者眼中殖民土著,是卑贱、愚蠢、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7]132在被刻意扭曲的历史面前,殖民地人民对自己民族种性、文化和传统,往往怀抱“深层的厌憎和自卑,丧失民族主体意识”[7]133,甚至是绝望。法农将殖民者的这种伎俩称为文化暴力:“殖民者在肉体上限定被殖民者的空间,即借助警察和宪兵,这样是不够的。为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特点,殖民者使被殖民者成为一种恶的精髓。被殖民的社会并不仅仅被描绘成一个无道德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道德标准抛弃了被殖民者世界,或从未在那儿停留过……土著被公然宣称为抵制伦理学,缺乏但也忽视道德标准。”[8]殖民者通过对历史的改造与扭曲,将被殖民者丑化为“恶的精髓”。
钟理和自传体小说《原乡人》也真实记录了这段殖民历史教育对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伤害。小说中的那位日籍教师有意给学生们编造了一个“支那人”的故事:“有一回,有一个外国人初到大陆,他在码头上掏钱时掉了几个硬币,当即有几个支那人趋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动得尽是道谢不迭。但结果是他弄错了。因为他们全把捡起的钱装进自己的衣兜里去了。”[4]4这位日籍老师的“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在被扭曲的历史面前,台湾的年轻一代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巨大困惑。
《夹竹桃》里的大杂院,是旧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下一步步走向破落的历史写照。作者受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对大杂院中的人和事的书写有部分错误的见解。小说的主人公曾思勉,与邻居们始终隔着距离,他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他们”。在他眼里,院里的女人“吝啬、自私、卑鄙、贪小便宜、好事、多嘴、吵骂……等等,这是她们的特性。对别人的幸灾乐祸,打听谁家有没有快人心意的奇殃,是她们日常最大关心事之一。”[4]106男人们则为“维系他们的那半死的生命,总在等着把他们的运命与机会,作孤注的一掷,而不顾一切。”[4]107作者笔下的“他们”,其言行与殖民者主导的历史教育中“支那人”贪婪自私的形象不正好吻合吗?从这个角度看,《夹竹桃》所反映的历史似乎是殖民者主导的历史,因此,陈映真先生批评主人公曾思勉是个“旁观的、犬儒的、恹恹然欲自外于自己的民族和民族的命运的人”[6]202,认为“钟理和的民族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危机”[6]201,作品“并没有在一片令人作棘心之痛的落后和悲惨的中国生活之内,看见隐藏在其中的中国的正体。”[6]206
尽管钟理和受到殖民者的历史观影响,甚至表现出对自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但是,他的立场和身份绝非是与殖民者重合的。这部自传体小说,记述了作者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见证了本民族在殖民者的压迫、剥削下悲惨的命运,瓦解了居于中心地位的殖民者书写的历史,具有反历史书写的意义。作者的叙述风格冷峻得近乎残酷,以致让人感觉他“拒绝和自己的民族认同”。这种叙事风格呈现出历史写真的美学效果,也使《夹竹桃》成为殖民历史的一段真实记录。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大杂院里,作者的叙述也仅局限在这个封闭的环境。这里的人们“像蝙蝠似的匍匐在那里头。他们在这里转着、滚转着,没有目的地滚转着。然而他们住得很和气,很相投,而且时或彼此照顾,虽然他们多半是那么谁也不管谁。”在表面“和气”和“相投”的下面,却是猜疑、嫉妒、吝啬、冷漠、懒怠、虚荣、偷窃等“一切用丑恶与悲哀的言语所可表现出来的罪恶与悲惨”。作者有意回避院外的世界,他把这一切归结为贫穷、命运和道德的缺失,据此,有人认为钟理和的“世界观太狭隘”。不可否认,《夹竹桃》混杂着文化分裂的困惑,然而,钟理和并没有与殖民者为伍,小说主人公曾思勉对大杂院的残破与落后流露出的“深恶痛绝”的嫉愤,是因为他没有弄清楚这一切的根源,看不清“中国的实相”,隐含着身份的苦闷和对原乡的失望。钟理和运用写实的技巧,通过一些细节揭示出历史的某些真相。大杂院里的西服匠林大顺,本为京郊农民,靠三亩地艰难度日,“事变发生,乡下生活日更日难过起来……在一个严寒的冬日,到了北京城”[4]120,他的日子非但没有好起来,反而哥哥失踪,乡下的地也卖了,“生活就愈感痛苦”。“事变”就是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华北的土地,像林大顺这样的普通百姓从此更加穷困潦倒。作者将林大顺的遭遇归因于“事变”的发生,在当时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此外,作者在作品中还写到大杂院里的孩子们常常在夜里到附近的粮店排队买“配给的杂粮”的细节。“配给制”是侵略者为掠夺物质,对占领区的百姓实施口粮控制,供给很少的棒子面一类的“杂粮”。侵略者的压榨与剥削,让大杂院里的人们无论“如何辛苦……日子并不因此而好转”,饥饿让他们失去了尊严和道德感,“恰如缢梁的人愈挣扎,而系在脖子上的绳结,便也愈收紧起来。”
钟理和受过“日本的教育宣传”,被“灌注带有轻蔑与不肖”的殖民者意识,“祖国意识”被掩藏在内心深处。这种文化分裂导致的困惑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得到释放:一方面,钟理和将被欺凌的同胞作为叙事的主体;另一方面,他用复合多元的历史书写角度和书写手段,瓦解了殖民者的历史书写霸权,使作品成为历史的见证。
三、“双重语气”的混合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一文中讨论了小说话语的杂交性,他认为这是“小说作品十分重要的得天独厚之处”。杂交性描绘的是语言,“它是在一个单一的话语范围内,对于两种社会语言的一个混合。是在一个单一表述的竞技场上发生于两个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一个遭遇战,这两种语言意识要么是由于时代、要么是由于社会分化或者其他因素而相互分离开来。”[9]杂交性描述了语言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的特征,德里达称之为语言的振荡性。他认为在针对听众的任何单一的话语中,一个声音具备讽刺并揭露另外一个声音的能力,是语言表达的“有意杂交”。
钟理和在《夹竹桃》及同时期创作的《门》中,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沦陷区百姓的负面描写引起过很多争议。陈映真在《原乡的失落》一文中,将他贴上了“殖民地丧失自信的知识分子”的标签,并指责他“对祖国的落后,发出辛辣、恶毒的批评,在这个批评中,看不见他自己的民族立场,从而拒绝和自己的民族认同”[6]206,让人“感受不到一丝一毫对残破而黑暗的旧中国里的同胞爱”。陈映真先生所说的“辛辣、恶毒的批评”在两部小说中似乎有不少,有些是讽刺,有些是尖刻的批判,有些是直接的辱骂,但这些是否就反映出作者“拒绝和自己的民族认同”呢?解读作品,必须将作品置于“其所来自的殖民情境与社会脉络之中,尽可能地让作者和作品发声,而非抽离式的只是解读文学本位的解读策略。至于解读的目的,不在清算殖民作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正确,不在谴责作家当时思想与情感的幼稚,未能超越殖民情境,未能具备高明的洞察力与积极的行动力”[10]259。今天,我们解读钟理和的这部创作于殖民语境下的作品,既要对掺杂在其中的错误认知进行批判,同时也要用“更多的理解、同情与包容”的态度,分析“潜伏在字里行间,幽幽地发出痛苦的挣扎与微弱的叹息”[10]259。
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他们“头一个愿望是脱离台湾,其次的愿望则是踏入祖国的土地”[5]34。在谈到自己和恋人出走到大陆的原因时,钟理和认为,“当初,我们原抱定了誓死不回的决心出走的。这里面,除开个人的原因外,似乎又有点民族意识在作祟。”[11]116虽然台湾被殖民数十年,殖民者的同化教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自幼接受汉语教育的钟理和,在族群文化的熏陶下,培养出了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对身处异族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来说,民族情感与殖民者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分处不同的意识领域,所以,钟理和在《原乡人》中追述当年离开台湾的心情时写道:“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回大陆之前,钟理和对于原乡的想象无疑是“古调苍然”的,不符合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同时,也掺杂了殖民教育下的歪曲意识,正如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吴浊流先生所说:“依日本教科书的教育,邻国是个老大之国、鸦片之国、缠足之国,打起仗来一定会败的国家。”[12]50当目睹原乡的种种“畸形的黑暗的社会文化”[12]234之后,他“沸腾”的原乡情感从感性向理性回归。
《夹竹桃》中的曾思勉是个“南方人”,他虽与大杂院的“他们”隔离开来,但这个距离不是心灵上的,而是美学的。对钟理和来说,“他们”不是殖民者口中的“支那人”,而是“我所爱并且尊敬的人”,同时也是“最为世人所不齿,在生活中间发现自身的命运、发现爱、与归依、与幸福,且以真挚对待人生的平凡的人”[4]79。面对这些他“所爱并且尊敬”的人们,作者却在《夹竹桃》里把他们比成“野猪”、“蝙蝠”、“牝鸡”,把他们居住的大杂院比成“肮脏又潮湿的窝巢”,由此让人感到“深恶而痛绝”。作品中的男女被塑造成自私、冷漠、懒怠、吝啬、虚荣等负面形象,仿佛是一群“栖息在恶疫菌里的一栏家畜”,“滚转在动物的生存线上”。这部作品如果仅发出这样一个单声道的声音,那么,钟理和的确是“丧失了民族立场”;然而,作品中还混杂着另一个声道,这个声音中有对“他们”生活处境的理解与同情,也有对“他们”精神缺点的批评与反思,正如他所说的“憎之而又爱之,爱之而又不能不憎之”[4]61。
对于“他们”生活中的“罪恶与悲惨”,钟理和既归因于“他们”内在性格中的“忍耐、知足、沉默”;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恶劣的外部环境是他们“不顾一切”作“孤注的一掷”的必然:“他们是生长在硗脊的沙砾间的、阴影下的杂草,他们得不到阳光的抚育,得不到雨露的滋养”[4]107,对于这些“生命得不到保障”的人来说,“适用道德和法律,那是怎样的可笑而且无聊”。作为一个刚从殖民地踏上祖国的青年人,之前,他仅从家族内部获得了一些原乡的知识,培育出朴素的民族情感。当真正踏上战乱中的原乡,面对饱受战争蹂躏的沦陷区百姓,由此产生的“爱”与“憎”的情感混杂在一起,就如《夹竹桃》中一面充斥着“深恶”、“痛绝”、“痛恨”、“憎恶”、“鄙夷”这些所谓“辛辣、恶毒”的词语;另一面,他又以写实的手法,真实地描写了“原乡人”“劳碌于生死的歧途,死与饿,时时展开在他们的面前”的悲惨生活境遇,作者虽然不能完全揭示出“死与饿”的真正原因,却传递出对“他们”的爱与同情,这种声音否定了“憎”的声音,揭示和讽刺了“憎”的殖民性和虚伪性。《夹竹桃》中“双重语气”的杂交,隐含了作者对殖民者的否定声音,在殖民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对殖民统治的一种反抗。
四、结 论
《夹竹桃》发表不久,钟理和在北大化学系工作的同乡陈先生就对作品提出了批评:“由这书所表示的态度来看,是应属于林语堂与周作人……一派的有闲主义的作家的。因为曾思勉有超然社会生活之上的漠不关心的那种态度。”[13]40这位友人与后来的陈映真一样都认为作者及作品中的主人公是“怏怏然欲自外于自己的民族和民族的命运的人”,他们是个“旁观者”,没有能够进入民族的正体之中。钟理和在十多年之后给友人的信中也认为《夹竹桃》是“不成熟的劣作”[13]41。
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却真实记录了殖民时代被殖民者的生存的困境和身份的困惑,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这是我们民族一段苦难历史的艺术写真,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只有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将作者及作品置于创作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才能体会到《夹竹桃》中的文化隐痛,以及钟理和对殖民者的揭露和批判。
[1] 叶石涛.钟理和评介[A].钟理和.钟理和集[C].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252.
[2] 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 翟晶.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9.
[4] 钟理和.钟理和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5] 钟理和.钟理和文选[M].高雄: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
[6] 陈映真.陈映真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2009.
[7] 陈映真.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M].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
[8] 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8.
[9] 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05.
[10] 张惠珍.纪实与虚构[A].应凤凰.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C].台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1.
[11] 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M].高雄:高雄县立文化中心,2009.
[12] 吴浊流.吴浊流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0.
[13] 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M].高雄:高雄县立文化中心,2009.
[责任编辑:张树武]
Under the Colonial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Anxiety——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Oleander
LAN Tian1,2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2.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91,China)
“Oleander” is a famous Taiwan writer Chung Li and published in the early for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works. In this paper,the war in the occupied areas to Peking as the background,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underlying difficulties of living people. Mingled with the text of complex emotions,while author “anti-historical writing” and “dual tone” and other strategies,to expose the hypocrisy of colonists,denied the legitimacy of colonial rule,has a unique aesthetic value.
Chung Li-ho;Oleander;Identity;Promiscuous;Anti-historical Writing;Dual Tone
2014-06-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ZW090)。
蓝天(1970-),男,安徽蚌埠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开放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I206.6
A
1001-6201(2014)06-01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