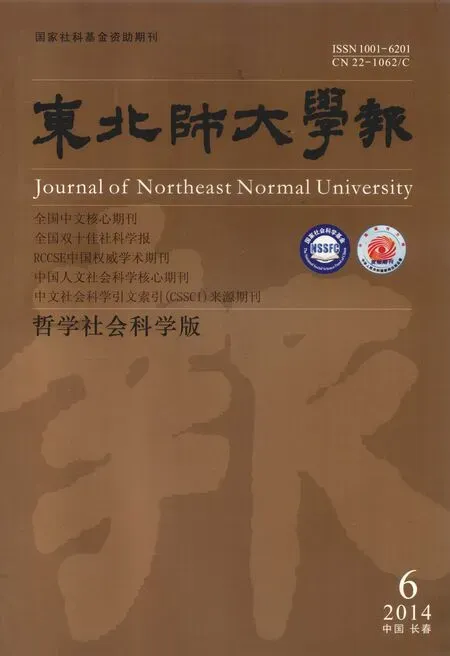论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
——以《鞑靼疾风录》为例
高义吉,杨 舒
(1.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2.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024)
论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
——以《鞑靼疾风录》为例
高义吉1,杨 舒2
(1.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2.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024)
在历史小说《鞑靼疾风录》中,司马辽太郎将主人公虚构为一个叫桂庄助的日本青年,以他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为核心,通过客观叙事、主观分析与阐释、综合营构等多种历史叙述方法,对17世纪初期的东亚史进行色彩润饰,审美化的叙述,构造历史景观,进行历史认识与意识形态的制作。
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鞑靼疾风录
历史叙述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描述,具有生命力,不断发展变化。与以叙事为主的传统历史叙述相比,西方现代的历史叙述以分析为主,侧重结构性叙述,追求一种总体性的阐释[1]43-44。近年来,历史叙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比如,美国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和日本野家启一的《历史的哲学化》分别探讨了历史叙述的特点和新形势下作为物语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作为个案的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叙述具有自己的特征。津田左右吉指出,日本没有英雄史诗。历史小说为一种历史叙述作品,在说“史”、讲“史”,实为一种建构,意在争夺话语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参与了此建构。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从大量的史料中挖掘人物或事件的材料,描绘出许多生于偏僻之地、经过奋斗成就功名利禄的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些奋斗史的背后,作者构造了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鞑靼疾风录》是他小说创作的绝笔之作,1984年1月—1987年1月连载于《中央公论》,为其赢得了1988年的第15回大佛次郎奖,2011年1月中文译本(《鞑靼风云录:大清崛起》,重庆出版社)出版。虽然作者在小说中提出意在“描写半鬓庄助的不幸的半生”[2]10,但山田笃朗、北山章之助、成田龙一等都认为小说的主题为描写朝鲜、明朝、女真族等的17世纪初期的东亚史[3]。本文认为,《鞑靼疾风录》是一部能代表司马辽太郎创造力与创作思想的厚重之作,继续着司马辽太郎叙述历史的主题,但创新了他的表达式样,着眼于宏大叙事,超出日本与日本人的囿域,将视角扩大至东亚。这部作品将主人公虚构为一个叫桂庄助的日本青年,以桂庄助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为核心,对17世纪初期的东亚史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当时的文化、风俗进行散点透视,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思考得非常深刻。换言之,马辽太郎并未停留于东亚史的简单叙述,而意在通过文学方法建构历史景观,表达历史认识,探讨民族如何生存的深层问题。小说中,司马辽太郎主要通过客观的叙事、主观的分析与阐释、综合的营构等方法来描写历史的风景。本文将从这几种方法入手,分析司马辽太郎的叙事艺术,探讨它们在小说创作中的意义。
一
叙事为传统历史叙述的主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现代的历史叙述所继承,比如,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既然是描写历史,则应有叙事。在叙事部分,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与中间的链接难以被了解,作者多靠自己的主观推理来补充、叙述;可知的历史有时会被作者相对客观地描述、评价。在相对客观叙事时,历史小说家有自己的方法。如,对读者熟知的历史,作者可能平铺直叙;对读者未知的部分,或许会引用文献资料进行辅助说明。当然,历史小说家进行客观叙事的具体目的也不统一。有时是为了交代文中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抑或是为了抛出评论的对象。但可以确定的是历史小说家的创作目的并非在于向读者讲述客观的历史,因为历史小说家并非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司马辽太郎在其历史小说中向读者展现了客观叙事的方法。《鞑靼疾风录》主要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侍奉日本平户藩松浦家的桂庄助被令护送女真公主艾比娅回我国东北兀良哈,途经朝鲜半岛,最后到达女真族居住地,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时代,又返回日本。司马辽太郎以讲历史故事的形式将17世纪初期的东亚史呈现给读者。他首先以岛主松浦氏为切入点,参考《魏志·倭人传》,将故事发生地平户岛的历史追溯至日本的上代、大和时代、镰仓初期及末期。当然,小说还有《明史》、《光海君日记》、《论语》、《太祖实录》、古诗、书信、歌词等其他文本的穿插。作者对那些历史没有真切的个人体验,因此多用一些文献资料来讲述。有时,此方法会使叙述空洞,但这些文本与小说中的历史故事构成了互相阐释、互为补充的互文关系,从而向读者比较客观地展现了历史,拓宽了小说描写历史的维度与视角,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思想与审美形态。
在叙述平户岛的“松浦党”的倭寇时代时,司马辽太郎描写出丰臣秀吉如大倭寇般意欲独占贸易之利,甚至侵略朝鲜。对于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司马辽太郎数次写入插话,用“朝鲜侵略”一词进行直接评论。据笔者统计,该评价在小说中至少出现过五次。司马辽太郎虽然早在1958年的《枭之城》中对此历史事件已有涉猎,但仅以“秀吉攻入朝鲜﹑大明”[4]等语句进行叙述。从司马辽太郎前后历史认识的变化来看,他在《鞑靼疾风录》中一开始就如此重复直抒观点,意欲展现一个客观评价历史的姿态,把尊重客观性作为自己在文本中叙述、评价历史的一个准则。
在叙述完平户岛史后,作者让主人公桂庄助登场。在小说中,他的命运与平户藩主密切相关。1614年5月26日,平户藩主法印镇信病逝。桂庄助因服丧期间骑马受到惩罚,被贬为平民,剃掉了半边鬓发,从此他“不幸的半生”开始了。桂庄助被福良弥左卫门命令去度岛寻找遇难的船只,在那里遇到了女真公主,之后又被新藩主松浦隆信命令送公主回去。由此,主人公的“旅行”、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叙述拉开大幕。桂庄助离开平户藩出海,首先经过朝鲜半岛。在此,作者延宕桂庄助的行程,改变叙事的方向,叙述朝鲜的故事。司马辽太郎认为朝鲜“自负的以为,他们与儒教的发源地大明国相比更像是礼教之国。且其官学是惯于分析事物的、喋喋不休的、形而上学的朱子学。这类论者的通病是,在讨论时忘记了实际情况,如果与对方存在差异,就将此差异扩大,漫骂对方。结果是,议论仅如空中闪光,实际问题被轻视未能真正解决”[2]102。参考研究者的论著[5]可以看出,司马辽太郎比较客观的描写、评价了当时朝鲜在儒学方面学习明朝的状况。此外,在叙述明朝灭亡、清政府建立这样的宏大事件时,他亦能较客观的描述出大体的情况。
比较客观叙述历史的方法不失为司马辽太郎在《鞑靼疾风录》中叙述历史的一个策略。历史小说为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但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构筑历史故事。司马辽太郎在《鞑靼疾风录》中选择史实的“数据”后描写“数据”,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亦能遵循这一范式。他相对客观的讲述了文中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描述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为了分析历史进程、思考民族的兴衰成败。总之,司马辽太郎在叙述对象方面不能脱离客观叙事的原则,虚构历史,描写一段伪历史。在评论历史事件时,他亦能有时较客观地给予评价。这主要是由于如此评价无碍于作者创作目的的实现。
二
分析与阐释成为现代历史叙述的中心内容。现代的历史叙述者多以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促使问题产生的原因,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探讨历史人物采取行动的表面缘由与深层因素。这种以问题为中心进行逻辑式推进与阐释的叙述并非以时间为顺序罗列事实,而是在历史的时空中进行立体的演绎。纵横交错的历史画面成就了一种叙述结构与模式[1]44-46。与历史研究者相比,历史小说家的问题意识往往服从于其创作目的与历史审美。他们能够利用自己作品的文学特点,相对易于摆脱史实的束缚,运用虚构等手法在广阔的立体空间内驰骋,将文中的历史叙述得更加丰满,解释得更加流畅与真切。因此,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与历史研究者的历史相比,被更进一步的改编与阐释。司马辽太郎在《鞑靼疾风录》中通过主观的分析与阐释,建立了历史解释的模式。
日本著名哲学家野家启一认为讲历史故事只是一种具备“既成事实﹑语境和时间序列”要素的、制作过去的言语行为[6];人并非神,带有主观性[7]19。历史小说家必须在历史的政治判断和主观的道德规避之间作出选择,介入自己的立场。所以,在历史小说中,被阐释的历史已经变成了现存的“视域”,其本来面貌被作家故意饰改了,历史已经成为了将事实和意义相综合的话语。作为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并非为了客观地叙述历史,而是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意欲将许多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赋予某种意义,使它们在艺术中获得新生,表达历史认识,从而实现重新叙述历史的目的。因此,他的历史故事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
司马辽太郎在解释朝鲜儒学只注重空理空论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特征时,将之与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联系起来,在相关叙述中实现历史意义的建构。在小说中,作者将朝鲜军总帅姜弘立的降服描写为明军大败的主因。与史料文献、研究著作[8]12相比,司马辽太郎凸显了姜弘立投降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在司马辽太郎看来,这是因为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其儒学只注重形式,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与此相比,明朝的儒学迥然相异。朝鲜军中的明将乔一琦为朱子学信奉者,耻于被投降的朝鲜军交给女真族,自杀身亡。司马辽太郎将姜弘立的降服解释为朝鲜形式性的学习明朝的儒学所致。之所以如此描写,司马辽太郎意在为朝鲜学习明朝儒学所带来的弊端制造一个例证,试图阐释儒学文化的误植导致了朝鲜军的投降。质言之,作者运用意义生成系统为历史中的事件建立一种连贯性,将事件构建在一定的整体秩序上,赋予一定的意义与功能价值,营构一种因果性的发生结构。
在小说中,萨尔浒之战对于作者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朝鲜儒学的特征,还在于表现女真族的足智多谋与英勇善战。在萨尔浒之战中,面对十几万的明兵和朝鲜兵,女真兵只有少数几万人,“在世界战史上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2]103。故萨尔浒之战成为了作者阐释历史事件的一个载体,对它的叙述生成了多种意义,即历史事件之间被赋予一层或多层因果关系。历史的时间性使得这种因果关系成为了一种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历史叙述在一种因果关系中展开。这种书写历史的策略普遍存在于司马辽太郎及其他历史小说家身上。
《鞑靼疾风录》有广阔的空间跨度,涉及了许多的历史人物、场景与故事。司马辽太郎的意识形态深藏于关于新兴的女真族和没落的汉族对决的描述中。在这些描述中,作者多进行主观的分析与解释。在小说中,桂庄助经过朝鲜半岛后到达我国东北地区。女真族的状况进入了主人公的视野,成为作者浓墨描写的对象。对于女真族的历史,司马辽太郎以女真人的民族特征为基点,展开对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带领女真人兴起、建立清政权的历史进行叙述。
司马辽太郎将努尔哈赤的出场安排在桂庄助与女真公主艾比娅的对话中,公主称之为英雄,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努尔哈赤的总体评价。其后,围绕着英雄的评价,作者展开对努尔哈赤的性格、战绩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进行叙述。对于努尔哈赤的欺骗他人,为了将权力集于一身,铲除异己、吞并其他部落,甚至杀害追随自己多年的亲兄弟舒尔哈齐,司马辽太郎轻描淡写抑或辩护道,这是出于统治上的必要,杀害亲人则是女真族的天性使然,只要是统治上的需要杀人什么的都可以。参考关于历史人物努尔哈赤的文献资料[9]126,笔者发现司马辽太郎辩护中隐含的道德判断是十分明显的。作者熟知历史,却从女真族的民族特点和清政权的建立这一结果出发来粉饰努尔哈赤。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并未如编年史般记录、叙述历史,而是将作者的兴趣、目的编织到历史的书写中,使历史成为一种以小说话语为形式的叙事故事,在故事中给历史事件以诗意的解释和再现,使其小说充满作者的意识形态和创作目的。质言之,作者通过粉饰的方法为已然发生的事实建立一种合作者之情的阐释,产生一种合理效果,这种合理利用人的思维模式推动着读者的思考和感情逻辑式地发展,最后实现作者的创作目的。
在对皇太极的描写中,司马辽太郎轻描淡写他的连战连败,将他刻画为勇敢、沉着冷静、对内完善官制和对外恩威并施的统治者,借用女真人的口舌歌颂道,完全合并蒙古族的势力、改国号为清的皇太极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司马辽太郎运用虚构情节的方法赞叹他为女真人顶礼膜拜的君主。概言之,司马辽太郎有意识地回避描写皇太极的专制独裁,侧重于他对清政权建立的贡献,对他进行间接的歌颂。对于历史,历史小说家首先有意识地从多面中选取片面,然后对此进行精雕细琢。无需赘言,在此过程中,作者会运用比喻、夸张等文学手法,通过修辞使被描写物体更加丰满。在历史小说中,修辞能够在量上和质上有助于作者的历史叙述,在量上可以加深作者所表达的程度,在质上也可以为作品从整体上定下一个基调。比如,作者可以通过悲剧论或喜剧论的文学修辞表明他对所描写历史的态度。
司马辽太郎选择历史人物的片面、不惜笔墨描写于己“有用”的方面,浅描淡写抑或漠视“反面”的手法,亦可见于他对多尔衮的描写。历史上的多尔衮攻破李自成的农民军,掠夺汉人粮食与衣物,发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种族屠杀。作者对这些先验的历史图景,并未在情节上体现出应有的判断。他虽然也指出多尔衮诡计多端,但更多地描写多尔衮在萨尔浒之战中用兵如神,为多尔衮增添传奇色彩。由此,作者赋予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以英雄色彩和传奇色彩。从中可以得知,他意在颂扬女真族,从这一目的出发,选取事实,将无关叙事目的的一些事实排除出去,对历史事实进行一种叙事性阐释。换言之,在小说中,司马辽太郎删减、省略甚至曲解事实并不是为了讲述关于女真族的全部事实,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创作要求,构造关于女真族崛起的一种真实。
此外,为阐释明末社会的黑暗,司马辽太郎以此为原因,将农民起义作为结果叙述出来。在小说中,重税和饥饿使农民怨声载道、揭竿而起,出现了以李自成等为首的武装团体。司马辽太郎不仅描写了农民的起义状况,还丑化了李自成、张献忠、刘宗敏等起义军首领的形象。在司马辽太郎看来,明末朝廷汉人的腐败埋葬了自己的政权,农民起义军的破落也使得汉人的农民政权无立足之地。场景是规律、原理的显示抑或形式[10],所以作者让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小说的表现对象,这也是作者所要描写出的目标,为作者表达历史认识完成了铺垫。总之,司马辽太郎通过主观的分析与解释,对17世纪初期的东亚史进行了色彩润饰,建构了思想反思的基础。
三
实现一个历史叙述目的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现代历史叙述中,特别在历史小说中,作者除了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叙事、主观的分析与解释之外,还需要利用一些“道具”从整体上更加完善自己的构造。在《鞑靼疾风录》中,司马辽太郎在选题、题目等方面精心设计,也运用了历史叙述的一些策略。他在《鞑靼疾风录》的小说文本及后序中多次提及、参考《鞑靼漂流记》。《鞑靼漂流记》[11]记录了1644年日本越前藩58名商民在日本海遭遇大风漂流到中国东北地方,其中43人被当地人误杀,幸存的15人受到清政府关照,被送到沈阳、北京,在北京停留一年后经朝鲜转送回国。文中大部分内容是幸存者的身边琐事及清军入关时的政治、军事和习俗等方面的记录。司马辽太郎借用《鞑靼漂流记》中的日本人漂流到中国东北的经历,将主人公虚构为日本青年桂庄助,编织了一个桂庄助护送女真公主回中国东北的故事。在小说中,这个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周围的故事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对这些所进行的描写、所进行的叙事性阐释为小说的中心内容。
通过设置小说的题目去更好的实现创作目的也是作者书写历史的一种策略。《鞑靼疾风录》中的历史故事虽然在日本的平户岛开始,但主要发生在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因为鞑靼在这里崛起。本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应该说是鞑靼。鞑靼在《明史·鞑靼传》中指蒙古人。从司马辽太郎在小说后序中对《明史·鞑靼传》的引用来看,作者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作者运用小说中人物财神的话明确了鞑靼的内涵:“鞑靼这个说法已变得不那么严密了,其指代的地域、人种也越发模糊了。现在一般指生活在长城外的、野蛮的、非汉族人群”[2]43。小说中的鞑靼具体指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天然规定了宏大叙事的特征,作者在文本中着力描写了女真族如疾风般崛起、席卷中国、建立清政权的事件,描绘出了女真人的那种爆发力、蒸蒸日上的状态,并对此反复绝赞。并且,作者描写出的一个较短时间跨度的历史,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如闪电般迅速兴起、疾速摧灭明政权和农民起义军的感觉。因此,题目一针见血道出了作品的这一主题,并向读者制造了一个能够感觉到这种氛围的想象空间。
隐喻作为一种叙述策略更加巧妙的完善了司马辽太郎的创作。在小说中,女真族依靠武力实现了民族的崛起。从司马辽太郎对女真族的赞赏来看,作者的格调是英雄的、好战的,赞成用武力实现民族的发展。换言之,这是一种武力第一的论调,推崇弱肉强食的理论。这种由武力决定胜负、轻视文化等内涵因素的生存法则给读者带来一种直逼人心的震撼,让我们联想到这是在肯定近代的日本。在近代史上,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迅速走上了强国之路,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用武力侵略他国、支配他国。女真族通过武力实现民族崛起与日本用武力侵略他国这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辽太郎为了实现肯定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的目的,运用隐喻的手法用他民族暗喻自民族进行最后的营构。
综上所述,在《鞑靼疾风录》中,司马辽太郎以主人公护送女真公主回中国东北作为故事线索,以其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为核心,主要通过客观叙事、主观分析与阐释、综合营构来描写东亚史的风景。他引用文献资料,相对客观地展现具体的历史,阐明了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客观叙述历史的大体轮廓,为作者探讨民族生存的深层次问题、表达历史认识与历史审美累积基本的“材料”。相对客观地描写历史也拓宽了历史叙述的立体空间,为小说的虚构填充真实的要素,为《鞑靼疾风录》构建历史性。作者对故事中的具体历史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展现了其评价历史的姿态,为其叙事中的主观性裹上客观性的“外衣”。然而,作者更多地进行主观性的分析与阐释,针对性地选择历史的片断,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通过因果性的关系将历史时空中的零散历史整合成一个大的事件。在这一演绎历史、阐释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得出抽象性的历史认识、观念与审美,建立历史叙述的结构与模式。在历史故事之外,作者还从选题、小说题目等方面进行结构性、综合性的营构,这无疑又完善了作者的叙事结构,使得作者的创作目的更加清晰。在这些叙述策略的作用下,17世纪初期的东亚图景被审美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完成了小说历史场景的建构,建立了作者意识形态制作的基础。
[1]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全集:第52巻 韃靼疾風録[M].東京:文芸春秋,1981.
[3] 山田篤朗.韃靼疾風録[J].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別冊 司馬遼太郎の文学世界,2002(7):281
[4] 北山章之助.手掘り司馬遼太郎:その作品世界と視角[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3:299.
[5] 成田龍一.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M].東京:筑摩書房,2009:270.
[6] 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全集:第1巻 梟の城·上方武士道[M].東京:文芸春秋,1981:73.
[7] 刘沛霖.儒家思想东渐及朝鲜儒学的基本历程—朝鲜思想史散论(一)[J].解放军外语学院报,1991(6).
[8] 李宜春.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及其特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
[9] 李甦平.韩国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野家啓一.物語の哲学[M].東京:岩波書店,2005:11.
[11] 野家啓一.歴史を哲学する[M].東京:岩波書店,2007:51-52.
[责任编辑:张树武]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Historical Novels——TakingDattanShippurokufor Example
GAO Yi-ji,YANG Shu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22,China;2.Preparatory School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Japa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Katurasyousuke,a Japanese young man,is the fictional leading character in the historical novelDattanShippurokuby Shiba Ryotaro. Centering on what was seen and heard by Katurasyousuke,Shiba Ryotaro aesthetically retouched 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the early 17th century with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methods as the objective narrative,subject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integrated construction and so on,to construct a point of view and lay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ideological production.
Shiba Ryotaro;Historical Novel;Dattan Shippuroku
2014-06-2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WW007);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WYKY201402);济南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B1413)。
高义吉(1981-),男,山东临沂人,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日本文学博士;杨舒(1956-),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副教授。
I106
A
1001-6201(2014)06-01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