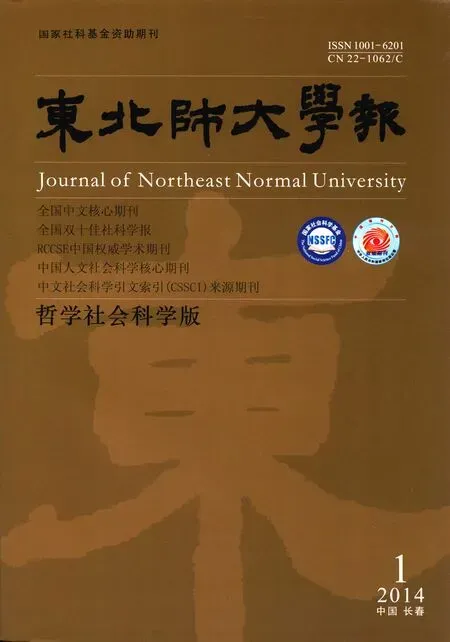伯唐父鼎与周穆王治理荒服犬戎
王 海,张利军
伯唐父鼎出土于陕西长安县张家坡M183墓葬中,鼎内铸有铭文66字,对于研究周代礼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发掘报告根据M183所出陶器、青铜礼器、兵器的形制分析,墓葬的年代可能在西周穆王前期[1]。那么伯唐父鼎的时代当在周穆王初年。自鼎铭公布以来备受学界关注,主要针对伯唐父鼎的时代与铭文内容,特别是铭文反映的祭祀礼仪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近研读伯唐父鼎铭文,觉其为探讨周穆王征伐犬戎以及对荒服的治理方法提供了新材料。试述如下,不足之处,望专家批评指正。
一、周穆王征伐犬戎实为改革服制
周穆王时期发生了征伐犬戎的大事,《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劝谏周穆王不要征伐犬戎时谈到了周代的服制: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2]4。
这则材料中“服”为“事”义,包含职事和贡赋两层含义。“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是周成王时期确定的朝贡服制的服名,与商代和周初“侯、甸、男、卫、邦伯”为外服诸侯名号是不同的。要之,五种服表明西周王朝对地方诸侯、方国的治理方法,即将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诸侯、方国纳入到周王朝的朝贡体系之中,使其更好地为周王朝服务。
周成王时确定的服制规定,邦内的诸侯国属于甸服,向周王朝履行每日助祭祀的义务。邦外且距离邦畿较近的诸侯属于侯服,向周王朝履行每月助祭祀的义务。侯、卫等诸侯属于宾服,向周王朝履行四时来享祭的义务。东部、南部的蛮夷属于要服,向周王朝履行每年来朝贡的义务。西部、西北部的戎狄属于荒服,向周王朝履行朝见嗣王及己即位来朝贡的义务。依韦昭注犬戎为西戎别名,“西戎者,西方之戎也,上古中国西部地区非一种少数部族,故‘西戎’应是对中国西部所有少数部族的泛指,并非一种少数民族的专称。”[3]79按照周初所确定的朝贡服制,犬戎属于荒服,执行朝王的职责,以其特产朝觐周王朝新嗣王或犬戎新即位者以其特产朝觐周王的职责。《国语·周语上》载“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2]7,犬戎的二君大毕、伯士死后,犬戎氏嗣位之君以其职贡白鹿、白狼来朝觐周穆王,遵循了周初制定的朝贡服制。但周穆王以犬戎不以“宾服之礼”即四时献祭的义务来朝觐为借口,征讨犬戎。尽管祭公谋父以先王之服制不可改易来劝谏周穆王,但周穆王没有听从劝谏,决然征讨犬戎,结果擒获犬戎五王、四白鹿、四白狼而归。导致从此荒服方国不来朝觐周王。据《史记·周本纪》载,周穆王继位时年事已高,王道衰微,诸侯不睦。周穆王任命甫侯为相,重整社会秩序,制定刑罚并颁布于四方诸侯,使四方诸侯谨而行之。周穆王因犬戎不以宾服之礼朝王,而大举讨伐之,反映了周穆王欲对周初确定的朝贡服制进行改革,加强对荒服进行管理,达到恢复王道、重整社会秩序的目的。据贾逵、韦昭注《国语》,白鹿、白狼为犬戎向周王朝贡献之物,白鹿、白狼当属稀少品种,特别地珍贵,为犬戎特产。那么,周穆王所擒获四白鹿、四白狼而归,象征着征服了犬戎。但事实上犬戎并没有屈从,而是从此脱离了周王朝的管辖,并且导致西部和西北部的诸戎狄部族、方国皆不再朝觐周王,尽荒服职贡的方国摆脱了周王朝的管辖。这表明周穆王改革服制,加强对西部和西北部方国进行管理的尝试遭到了失败。但是周穆王不甘心失败,还试图通过宗教活动来挽救失败的局面,伯唐父鼎铭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信息。
二、伯唐父鼎铭文中的祭礼
伯唐父鼎铭文反映周穆王获得四白鹿、四白狼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宗教祭祀活动,通过宗教方式寻求对犬戎的治理。伯唐父鼎铭文有云:
由字形观之,释为居及馆的古字都与字形、文意不合。应隶定作,读如本字,表示祭祀之义。如在吕方鼎(《殷周金文集成》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文中简称《集成》者,俱出自此书。2754)中,“王于大室”,名吕者“延于大室”,即吕“侑近”助祭周王于大室。《仪礼·特牲馈食礼》“祝 延 尸”,郑 玄《注》:“延,进 也。在 后 诏 侑 曰延。”[9]1184《说文》:“诏,告也。”则诏侑为祭祀时告而侑助即延之义也。《仪礼·特牲馈食礼》所记为诸侯公臣祝助士丧礼,告而侑助尸。吕告而侑助周王行祭礼于大室,则表明“王于大室”是王行祭礼于大室。祭于商代已有之,于省吾认为商代眢祭即是周代祭,晚商铜器戍嗣子鼎铭载戍嗣子因为侑助商王行祭之礼而受到赏赐,表明晚商时期已经有祭。
三、周穆王射白鹿、白狼的政治意义
周穆王举行此次射礼意义重大,故特地准备专用舟船,并对即将乘的舟和使用的白旗举行祓除不祥的祭祀。射的对象与以往金文所见不同,都是大的动物,如白鹿、白狼为犬戎所贡,把作为犬戎象征的白鹿、白狼当作射礼的射侯,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宗教观念。《说文》在训解“侯”字时说道“春享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诸侯射熊、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为田除害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以动物为射侯在中国上古时代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说文》谓天子射熊、虎、豹,就是以熊、虎、豹为射“侯”,其寓意是制服猛兽。诸侯射熊、虎,是以熊、虎为射“侯”,大夫射麋,以麋为射“侯”,“糜惑也”即驱除迷惑是大夫射“侯”的寓意所在。士射鹿、豕,以鹿豕为“侯”,其寓意是“为田除害也”,可能是因为鹿、豕为田害也。与《说文》“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相近的记载还见于《周礼·考工记·梓人》、《大戴礼记·投壶》,其义是那些不安顺的诸侯,不朝见于王,因此张举射侯而射他们。这里的祝辞含有诅咒的色彩,要旨表现出射礼有对朝王诸侯的拉拢、团结,以及对不朝王诸侯施以惩罚的功用。
这种诅咒实为中国古代的“厌胜”巫术的反映。《说文》:“厌,笮也。”段玉裁注:“《竹部》曰‘笮者,迫也。’此义今人字作压,乃古今字之殊。”[10]448厌胜即以巫术方式给人、物以压迫,从而达到获胜目的。“厌胜”的提法晚至汉代才出现,但在先秦时期厌胜之术的使用延绵不绝。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大经·正乱》载黄帝战胜蚩尤事,“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16]61黄帝既已战胜并擒获蚩尤,仍以蚩尤之皮做成射侯,命人射之,盖以此厌胜之术从精神上彻底打败蚩尤部族。商代晚期铜器作册般鼋铭文载,商王武丁曾弋射于洹水,商王射一箭,臣子作册般射三箭,皆中鼋身。商王命令寝职名馗者将射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并说以鼋血衅钟,不要以之为宝。晁福林断定此鼋为商王的厌胜之物,指出“商人射龟鼋所表示的盖为对于南方及东南方敌人的敌忾……射龟可能表示着对于南方的镇服。”①晁福林《作册般鼋与商代厌胜》,《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第53页。本文对作册般鼋铭文的解释也取自该文。《史记·殷本纪》载商王武乙与象征天神的人偶搏斗并获胜,以革囊盛血射之,视为射天神而出血的事件,亦是厌胜之术的表现。武乙对周人所崇拜的天的侮辱,所表现的是对周族的敌忾[17]。周武王克商后,“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之,各以[其职]来贡。”[18]卷737引《六韬》佚文,3267-3268东周灵王时,周的势力衰微,诸侯皆不朝见周王,臣子“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 依物怪欲以致诸侯。”[19]卷二十八《封禅书》,1364设射《狸首》为古 礼,见于《仪礼·大射》、《礼记·射义》、《周礼·春官·乐师》。《狸首》为逸诗,乃举行射礼时所奏乐歌,司马迁以“不来”释“狸”,汉人遂认为“狸”为“不来”之谐音,狸首即不来朝见之诸侯的头,苌弘当是以物品做成射侯,用以象征不来朝见周王的那些诸侯的头。射象征诸侯头的射侯,示意惩罚不来朝见的诸侯。这与周穆王射白鹿、白狼具有相同的政治意义,周穆王以犬戎不以宾服来朝见而征伐之,获得四白鹿、四白狼。将白鹿、白狼置于辟雍,用作射礼之侯,其乘舟为射礼,射获白鹿、白狼,以示对犬戎的惩罚,亦如《说文》所云射侯之义,因为犬戎不安顺,不朝见于周王,于是周穆王射之。伯唐父鼎铭文所载此次射礼的政治意义就是诅射犬戎,反映了中国上古时代“厌胜”的观念。
综上,周穆王时期王道衰微,欲通过征伐犬戎,改革周初确定的朝贡服制,强化对西部西北部方国的管理,来重整王朝秩序,加强周王朝对西部的影响力,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周穆王不甘心失败,以征伐犬戎所获贡物白鹿、白狼为射礼之侯,以厌胜巫术方式以示对犬戎的惩罚。将射获的白鹿、白狼作为牺牲祭祀祖先,于辟雍大室向祖先告知征服了犬戎,实以宗教方式宣示对荒服犬戎的治理。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M183西周洞室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9(6).
[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沈长云.猃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别考[J].人文杂志,1983(3).
[4]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铜器铭刻[A].古文字研究:第二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1.
[7]郭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8]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顾野王编撰.原本玉篇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刘雨.伯唐父鼎的铭文与时代[J].考古,1990(8).
[14]袁俊杰.伯唐父鼎铭通释补证[J].文物,2011(6).
[15]刘桓.甲骨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经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17]晁福林.作册般鼋与商代厌胜[J].中国历史文物,2007(6).
[18]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