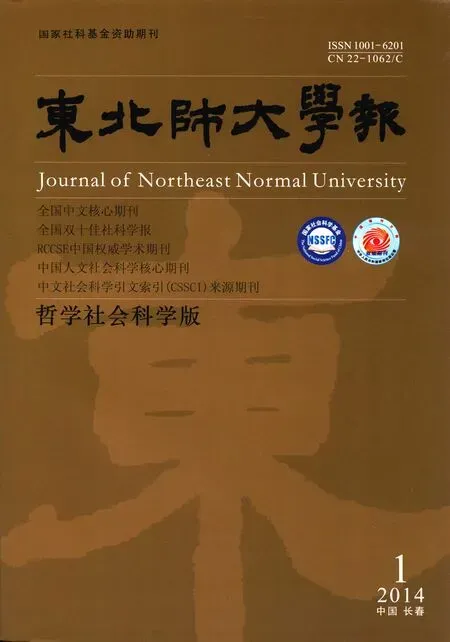马克思视野下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刘 迟,营立成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根据米勒考证,“市民社会”一词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便被西塞罗提出[1]。但是它的广泛使用与17、18世纪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剧烈的社会变迁有关。塞利格曼指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市民社会观念的出现是社会秩序危机和继承至于观念范式瓦解的结果。”[2]51基于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假定,启蒙时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带有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学者对它做出了价值色彩浓厚的阐释。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首次作为“国家”的对立概念被提出。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从法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重构了这一概念,并为“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做了基础。后来,葛兰西、哈贝马斯、J.C.亚历山大、科恩、黄宗智与吉登斯等一批学者从不同视域对“市民社会”展开分析,从“民族主义的凝聚性”视角到“文化研究视角”;从“意识形态”视角到“公域”视角,几乎将这一概念发展为无所不包的庞杂“社会乌托邦”。
为了学科把握市场社会理论意涵,笔者认为,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首先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坐标体系:这一体系应该以马克思的经典研究作为逻辑原点,将市民社会的批判理论范式作为一轴,将市民社会的建构范式作为另一轴。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的经典研究出发,将其作为参照系,在比较中讨论市民社会研究的纵横两轴,并分析多元化的市民社会理论之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启示。
一、马克思文本中“市民社会”的几种意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市民社会做了相对集中的讨论,其对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文本至少有三种维度:
第一种是最为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日常世界维度。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经典定义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3]32他强调:“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3]32而他本人的历史观在于把“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36这里我们需要关注几点:第一,这里所讲的“市民社会”与生产力发展处于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中,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第二,市民社会是一切交往形式的总和。这里提到的“交往形式”在《形态》中的解释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3]12而形成的某种模式。谈及“市民社会是一切交往形式”的总和,也就意味着市民社会是互动交往结构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此处的市民社会历史性的分析概念,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这样的“市民社会”,而且应该作为承载一切的平台和基础。可见,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最为广泛、最包罗万象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直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秉持的唯物、唯实和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分析理念是一致的。
第二种是经济市场领域维度,这一意涵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即“私人需要的体系”或“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而国家则是指社会政治领域[4]128。相应地,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包括了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3]75这里的市民社会增加了两方面的规定性:第一,它特指经济领域,或者说是市场领域;第二,它有可能排除了非市民化的,或者说农业化的经济关系,从而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第三个维度的理解奠定了基础,该维度在学界有较高的共识。许多学者将“市民社会”作为马克思“经济基础”概念的一个过渡或不成熟的用法。如郁建兴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之后“‘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之总和)、‘社会经济结构’概念取得了同义”[5],而爱德华·希尔斯也认为:“他(指马克思)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市民社会的商业或经济方面。”[2]36
第三种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维度。实际上,“市民阶级”一词本身是指中世纪“贵族”和“农民”之外的“第三等级”。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一概念指向于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 会 阶 级”[6]的 意 涵。 在 词 源 意 义 上,“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亦可翻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而产生的。”[3]75也就是说,尽管在其他历史阶段存在市民社会,但是这种“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只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才有意义,因为前所未有的分工和社会化生产为这种“社会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用韩立新的话来说,资产阶级社会与市民社会是一个社会的两面[7]。
尽管上述三个维度看似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也成为构建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一环。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的确贯穿于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弥散于一切日常生活世界中,并且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结构和组织,形成了“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但是,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得到彰显,它是异化劳动、分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作用下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中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是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8]实际上,市民社会的彰显是私有制与人的异化的彰显,但同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和自由平等交换关系的彰显,因而同时具有双重的性质。
二、“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范式及其与马克思的比较
事实上,如果分析与马克思理论有渊源的理论家——包括在其之前的黑格尔和在其之后的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家尽管视角多有不同,但是大多在市民社会研究中秉持批判视角。因此,我们可将其称之为“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范式。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成为与家庭(自然社会)、国家(政治社会)相对的概念,这里的市民社会是在“追逐一己私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相互依赖的关系。”[2]90它往往是市场因素和私人的经济利益的体现,是充满欲求、盲目、撷取的场所,往往会侵犯或阻碍公共利益。因此,只有靠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国家,这一代表公共利益和普遍精神的政治共同体对其进行秩序化才能够解决。
黑格尔的分析无疑对马克思有重大影响,然而黑格尔在“私利”层面上使用市民社会与马克思还是有较大差异:第一,马克思反复强调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点的上层建筑基础。”[3]75“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9]428很显然,国家和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与黑格尔正好颠倒,在地位上是市民社会高于国家,而不是相反。第二,对黑格尔而言,市民社会不过是一团混乱无序、无限膨胀的人的欲望的舞台和表现,马克思赋予了市民社会更加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没有将市民社会空悬于形而上的理论玄想中,而是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现实生活当然不仅仅是经济生活,马克思将描述市民社会的关键词“交往”界定为“包含最广泛的东西”,实际上,这便在唯物史观的平台上实现了多种视角(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融合。
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Gramsci.A)和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市民社会批判范式的发展上同样有巨大贡献。葛兰西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政治革命性与文化社会学意涵。他指出:“我们目前能做确定的两个上层建筑,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10]葛兰西还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高度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摧毁是一场阵地战,国家只是其外围碉堡而已,因此,无产阶级一定要努力把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哈贝马斯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在其描绘的18世纪资产阶级蓝图中明确将市民社会——“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的领域”放到私人领域中[11]35。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最近流行的“市民社会”(不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是Zivilgesellschaft,一般译作“公民社会”)与黑格尔-马克思范式的差异:“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11]序言35而这种市民社会中包含的协会(Vereinswesen)曾经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由此,哈贝马斯将“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这一任务寄托在公共领域的复兴的基础上,试图重构“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不复存在的“公域”,来建立新的合法性。
可见,葛兰西与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这也是理论界将他们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原因。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强调“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9]20他们走的是文化政治学与“亚政治”(Beck,1997)批判路径。在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上,哈贝马斯承认存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市场意义,但是更加强调其“公域”价值;葛兰西则将市民社会径直看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即使在最广泛意义上,也没有将市民社会置于上层建筑的维度加以考虑。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文化政治学转向,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也有所削弱,日益向市民社会的另一脉——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靠拢,在哈贝马斯的后期讨论中,他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已经与我们目前熟悉的“公民社会”理论无异了。
三、“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范式及其与马克思的比较
自由主义理论对“市民社会”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建构和完善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我们可以称之为“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范式。
这一范式的“市民社会”主张可以从启蒙思想中找到理论根据。洛克认为,人类原来所处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为了确保这种状态,人们自愿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赋予国家,“政权的一切和平起源都是等于人民的同意。”[2]83“人民主权论”者们对于启蒙时期国家的干涉主义不满,托马斯·潘恩甚至说:“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12]这些主张为在国家之外建构一个“市民社会”提供了根据。
秉持这一论调的学者大多同意如下观点:第一,存在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文艺的、舆论的社会自主性领域,这一领域由一系列自主性机构组成。第二,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政权和纯私人的经济领域之外,不受国家强权控制,并通过某些特定的机构和制度与国家保持互动和联系。第三,公民在市民社会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共同利益、自愿性地参与社会管理与决策,这有益于社会资本的扩展和社会信任和认同的建构。第四,市民社会呼吁公众参与,需要公众参与,并由此不断“生产”参与民主,促进民主化进程。第五,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说,市民社会同样也是一整套品德和风范,是公共精神和“市民认同”的总和[2]33-50。第六,政治民 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是市民社会努力的目标,也是市民社会真正得以存在的基础[4]230。
可以看出,尽管早期的马克思也赋予市民社会以建构意义,并认为可以通过“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但马克思理论视角与建构主义范式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根本分歧:
第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重在反思和批判,而自由主义“市民社会”思潮重在建构。对马克思而言,在宏观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层次上,“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是一切历史事件的真正舞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层次上,市民社会是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其中蕴涵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从对市民社会异化现象的揭示到对现代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统治本质的认知,无不带有浓厚的批判与反思意涵。在自由主义理论语境下“市民社会”建构意义就要大得多,该理论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后发型国家,“市民社会”是其不断推进现代性进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这种语境下要高扬“市民社会”,而不是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第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套革命实践哲学,而自由主义学者那里的“市民社会”是一套生活改良哲学。后者“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构建和发展会对公共事业发展有所推动。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套由生活改良而导向所谓现代性的某种理论。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主要是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另一个有力的统治领域,只有对其加以彻底地改造和反思,建立没有异化,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葛兰西的提法,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套革命“实践哲学”。
第三,马克思和建构论的市民社会在论证其与国家的关系上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可以清晰地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逻辑。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与之对应。而在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与其说是谁决定谁,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外在于”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应该是并行不悖,互不干涉的。
第四,马克思的分析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学,更加关注黑格尔所讨论的那个“私域”的“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社会”相联系。与此不同,虽然经济市场化是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建构市民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和不断完善的目标,但似乎更加注重社会参与政治民主建设。当然,这种所谓的“市民政治”与传统的国家政治并不完全一致。
第五,两者的理论目标大相径庭,市民社会的建构主义范式所关注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在马克思看来前者与导致人压迫人,资本统治劳动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私有制相一致;后者则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所建构出来的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应该建设真正与社会化大生产,与人的本质天性相适应的共产主义。而建构主义者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根本上是要证明一种现代性的合理,证明西方经验的可靠性。
四、反思:多元市民社会理论之于中国的启示
必须承认,无论何种范式的市民社会理论都具有西方社会的嵌入性。马克思所批判分析的市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倾向于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对中国社会的观照;建构主义者们讨论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似乎也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一批学者兴起了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市民社会的浪潮(黄宗智,2003;罗威廉,2003等),但终于得出了中国缺少“制度性舞台”(魏斐德,1993)的结论。黄宗智也认为,在中国,坚持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一种风险,而力主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2]420。情况变得复杂:进行“市民社会”的批判而找不到与之对应的靶子;进行“市民社会”的建构找不到现实依据,市民社会理论之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似乎正在削弱。
然而,否定这一理论的意义似乎言之过早,对多元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合理分析与整合,如果得当也能够为我们带来重要启示。笔者认为,将多元化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研究结合应该关注如下方面:
第一,从建构主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范式出发,在中国发现与西方完全一致的“市民社会”恐怕是徒劳,但从古代基层的士绅自治性组织到近代乡村建设运动再到当下充满想象力的各种实体和虚拟(特别是网络社区、论坛)民间团体的存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待非国家层面的管理和组织,中国社会有自己的智慧。如果我们要将这些努力归结于“市民社会”应该对其内涵和外延重新界定,特别是中国广泛的农村维权组织和利益团体及虚拟组织如何被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寻求本土化意涵是问题的核心。
第二,批判主义范式的“市民社会”有利于我们在政权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领域提出议题。如果说上层建筑应该与市民社会基础相一致,那么当国家出现了与广泛的“交往形式总和”相异化时,国家则需要反省自身。葛兰西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则告诉我们,统治阶级应该在市民社会领域,实际上也是在舆论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组织领域取得统治地位。目前来看,中国政府一方面被各方批评为文化领域的垄断者,但实际上核心价值的社会渗透力仍然不强。可喜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动,可见政府已经开始从行动上关注社会力量的作用。而如何将这种社会批判导向一种实践层面上的反思和重构,是研究者们应该特别关注的。
第三,无论哪一种市民社会理论范式,无一例外将市民社会置于国家——社会的框架内加以考虑,多数理论家都强调了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核心地位。但是正如中国学者张静所表明的,在中国基层,国家的力量的削弱并没有导致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小规模封闭的“利益阶层”(张静,2007)。梁漱溟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过是国家不统一,软弱无力的情况下的自救与积极发展之举,实际上颇有些无奈(梁漱溟,1937)。笔者认同张静的说法:“不是国家权力大小,该不该有的问题,更正确的问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权力。”[13]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凭空构建某种程度上比国家还有意义的市民社会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似乎应该对市民社会理论有一种反向思考,承认社会组织和市场发育重要性的同时,将建设更加制度化和理性化的国家社会设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市民社会”的不同语境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比较的可能,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学学者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应立足本国实际,建构本土化视角下的市民社会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和当下的社会剧烈变迁都是只有在中国自己建设的语境框架中才能得到分析和解决,而建设这种框架也是我们学者研究西方相关理论的根本目的。
[1]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G].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5.
[2]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王浩斌.市民社会的乌托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王代月.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的比较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8:18.
[6]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
[7]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8.
[8]马恩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
[9]马恩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2]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3.
[1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政治制度建设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