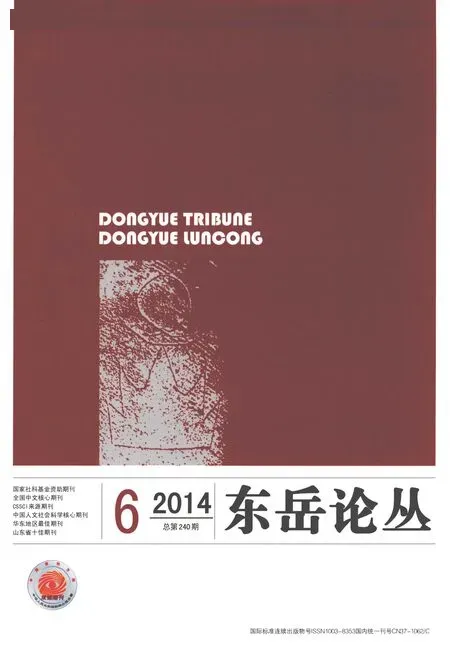历史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思辩
张 勐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4)
历史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思辩
张 勐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4)
以百年时段为基本量度单位考量,20世纪中国文学中已能发现“周期”、“循环”、“趋势”等一些规律性的因素,并已形成相对完整、持久、恒定的总体格局与方向,不应以重估为名对此肆意解构、颠覆,以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途。
“民国文学”;“十七年文学”;学科稳定性;颠覆式重估;历史虚无主义
新中国建立初始,王瑶先生以“中国新文学史”命名的那本开山性教材连同这门课程的诞生,意味着我们的学科尚且年轻①,正处于除旧立新的草创阶段,而仅仅以三十年的时限来考量文学史事件也难免有时陷入短时段的陷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其弟子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在新世纪尚未到来之前,便大梦先觉地撰文,建议将“中国新文学”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易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②,当各种以此冠名的教科书接踵出版之际,则标志着这一学科终于拥有了一百年时段为其基本量度单位,终于可以避免难能将“隔着一条杠”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些短时段历史焊接成一体的无奈,可以摆脱不断求“新”趋“变”的学科焦灼心态,终于能够应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之类的疑问,能够发现“周期”、“循环”及“趋势”等一些规律性的因素,终于得以建构一个相对持久稳定的“总体框架”,以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完整性。——恰是赖有上述“总体框架”的着意建构与渐次形成,致使我们的教学和研究衍生出一系列事关全局的观念与问题,同时也为进一步思辩、厘清问题奠定了基础。
一、学科稳定性与颠覆式重估之干扰
中国新文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及课程,它的“现在进行时”、未完成性、不确定性曾是影响学科稳定的重要原因。除却它自身内部的因素外,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频频来自外部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更使它一度沦为“政治晴雨表”。
时至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借重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科新视野,原本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我们得以重新建构学科的科学性与稳定性——这也许正是当初“重写文学史”倡导者的初衷。然而,后继者显然缺乏倡导者平和中正的襟怀气度,缺乏其运用时勉力“多分析问题,少空谈主义”的审慎③,更未能具备倡导者从一开始便意识到的“这种带有‘拨乱返正’性质的工作”是一定时期学科重建无法绕开的前提,却“并不具备长远的价值”之清醒④,以致于在其不无偏激、不无夸张、漫无边际的践行中,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观念,变形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意识形态意味十足的颠覆式重估。其中最典型的当数矮化“鲁、郭、茅”,神化胡适、张爱玲、钱钟书等倾向。
进入新世纪后,这种热衷于反弹琵琶、做翻案文章的趋势似乎并未消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方兴未艾的“民国文学史”的倡导。
因应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等契机,有学者提出了以“民国文学史”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动议。关于这门学科及课程的命名与分期,并非一个不可探讨、商榷的问题,但目的自然应以有助于教学的稳定性与科学性为宜。
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失之于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而“民国文学”的内涵则更具多元性与边界的开放性。主张“应该从意义的概念重新回到时间的概念上来”⑤,如是,当代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了,历史的分期与文学史的分期大致同步。
类似的思考实质上主张的乃是将1949年之前三十年的文学冠以“民国时期的文学”这一名称。换言之,在此概念中,“民国”只是一个物理时间。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文学”之定义,牵涉的仅仅是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自有其合理意义。而主张由“民国史视角”审视文学史的秦弓⑥、与持“民国机制”说的李怡诸先生的观点虽有可商榷之处⑦,但就总体而言,思辨甚深,启示良多;那么另一些主张者对“民国文学史”以及“民国机制”之阐说,则显然不无偏至。有学者如是诠释“民国机制”题中之要义,即“让‘民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指出:“其实,民族危机伴随了整个民国时期,如果考虑到这一层面,‘历史还原’就应该重新审视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的一切文学理论和创作。如果我们对于民国在面对民族危机时的姿态给予积极评价,那么就必然要正视其指导下的文学和创作。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因为政治原因被遮蔽了很久。”而倡导“‘民国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⑧。尽管该文每每闪烁其词,进一步,退两步,站位看似平正周致,却仍于有意无意间泄露了它其实是近二十年来继贬鲁褒胡、贬损左翼文学之后的又一次曲折表现,因应着“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作家及其文学的理想化”之思潮⑨;也暗含着以此对照、印证“共和国文学”今非昔比的观念。这便引出了下一节行将探究的问题:如何评价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十七年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无原则地容忍、迁就上述个别提倡者那厚“古”薄“今”的偏至立场之干扰,不仅将导致部分文学史内容与观点流于“翻烙饼”式的反复无常,最终颠覆的将是整个学科的既有教学格局与理论模式。
二、“了解之同情”与历史虚无主义之迷思
史家有言:治史“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此便不会流于“偏激的虚无主义”⑩;或谓:“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1)。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及教学却每每对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缺乏应有的“了解之同情”,因此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其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逻辑。例如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
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中国革命文学的尝试,乃是19、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萌生、发展及至世纪末式微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史事件与现象。新时期之前由于执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以及庸俗社会学、阶级论的思维方法,每每对其施以揠苗助长式的措施与升华。甚至不无简单化地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思维,扩展至文学领域,并迫不及待宣称战而胜之。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革命家曾有过相类的理论自信,马克思在评价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早期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威廉·魏特林的著述时便将其与所谓资产阶级的著作进行比较(12)。不容混淆的是,这种终将战而胜之的自豪与自信仅止表现在哲学范畴、政治学范畴;至于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部分国家夺取政权后,能否扩展至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马克思恩格斯自有不失清醒的思考,并认定那将是一个更其漫长、更其复杂、更其艰难的进程。
然而,彼时坚执政治标准第一、而忽视艺术标准的极左理论家们却未免过早地将无产阶级文学试验田中的萌芽视作参天大树,有失分寸地激赏、分封某些作品为“红色经典”或“革命样板”。伴随着这种波及教学领域的大树特树,一种人为地设置一个对立面——“资产阶级文学”,并由于对一些“五四”新文学著述缺乏“了解之同情”,而肆意将其归入“资产阶级文学”中,如同一并将“人性论”、“人道主义”尽数奉送给资产阶级那样的极端倾向于焉而生。
新时期以还,出于对上述过度政治化倾向的悉心反拨,学界提出了“纯文学”观念,用以纠正既往以阶级斗争叙事乃至战争话语取代文学史叙事、强调政治标准而无视艺术标准的偏至。
“纯文学”的倡导,自有其处于八十年代拨乱反正语境中的合理性,症结在于九十年代以来部分学者矫枉过正,在一些著述与教科书中刻意褒扬其所谓的“纯粹性”,神化它的“普适价值”。更成问题的是,一味以“纯文学”这一后设的标尺去衡量百年文学史,“十七年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因是难入法眼,以致彼一时期竟被视作了“一片空白”的“荒原”。其实平心思考,长篇小说领域中的“三红一歌一史”,诗歌领域中的贺敬之、郭小川、闻捷,散文领域中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纵然文学价值不高,也自有其绕不开的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一些文学史或教学却拦腰截除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史这段脉胳。恰是这种傲慢与偏见,导致其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思:无视左翼文学思潮与实践这一份不无沉重的遗产中至今仍有我们可资打捞、鉴戒、汲取的资源,故理应寻索其中未曾全然消褪、若隐若显地折射出的“革命、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等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时代风潮的投影”,以及相关辩难质询的世纪回响。具体到作品,它可以是“平常日子里的生活故事”,是激情飞扬的“青春之歌”;亦可以是仅凭“七根火柴”却点燃了困难时期人们未泯的信念的火种,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心谱写的“红旗谱”……此外,彼一时代文学中既有“特殊性格的人”,也有“来访者”;既有“清晨的凯歌”,也有非主流的“本报内部消息”。远非“荒原”一词能一言以蔽之。
三、民族精神建构与海外汉学研究之美学偏嗜
上述将“民国文学”、“十七年文学”定义刻意简化、抽象化,或藉“纯文学”之标尺厚此薄彼的倾向,溯其渊源,若隐若显可见海外汉学研究的某些影响。
上世纪60年代初,夏志清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西方学院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该著于新时期伊始引入大陆,以其别开生面的视野,救正了彼时因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教学格局褊狭所造成的遗珠之憾。然而,缘于新批评视角及方法的局限,夏著一味“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13),注重文本分析有余,而同样必要的将小说史“历史化”地叙述则明显不足,以致一部小说史俨若“顺着时代排列的某些特定作品的印象和批评”。李欧梵、王德威等又放大了其独尊“文学性”的倾向,并兼容了夏氏高抬张爱玲等的审美偏嗜,乃至蜕变为一种唯美─颓废美学。李氏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王德威的著述,无论在选题抑或美学情趣上,均透露出这种偏爱有加。
为此,李欧梵还不惜为“颓废”正名,悉心梳理、论证“颓废”的现代美学与文化意义,指出“颓废”文学的实质乃是以艺术的现代性追求来反抗启蒙的现代性(14)。以张爱玲小说为标志,上可溯及《海上花列传》、郁达夫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下可延伸至台湾朱天心、朱天文等“咏叹颓废、耽溺感伤”的作品。
因应着时近20世纪末这一特定时间节点,由海外汉学家合力营造成的张爱玲“传奇”连同“颓废”美学偏嗜竟呈一时之盛。学术界的“张爱玲热”余波未平;大学生的阅读趣味又受之影响,毕业论文选题对张爱玲趋之若骛。种种“仿汉学”末流适如东施效颦,一股颓靡之风渐次弥漫于“世纪末”。
与此相应,海外汉学家又对革命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所激扬的“崇高美学”予以针砭。80年代末方加入海外汉学阵营的王斑,受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崇高与优美的思辩之启示,将其移用于对五六十年代共和国“崇高美学”的诠解。指出:新中国文学每每藉重铸崇高以“召回主体,让主体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与动力的使命充满神圣感”,以叫人敬畏的英雄形象来激励人民(15)。
崇高美学不仅助成彼一时代对工农兵英雄崇拜的审美化,更将革命罗曼谛克情绪尽数纳入其题中之义,故此,海外汉学通过对其的剖析、批评,以反拨“十七年”时期大陆一度盛行的“高大全”、“红光亮”的美学情趣自有其合理处。问题是,这种批评不能无限扩大化,例如以张爱玲、沈从文等小说为典范,将对“颓废美学”与“崇高美学”的评析,扩展为对一切阳刚美学风格与阴柔美学风格的褒贬,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中那至今读来犹不失崇高昂扬的理想主义追求,那便显然矫枉过正了。
世纪回眸,王斑自有一番反思,在其《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中文版前言中,他如是说:“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现在人心涣散,理想空虚,民主参与冷落,公民政治瘫痪。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因此,多一点理想主义的浪漫崇高,没有什么不好。”(16)诚哉斯言!王斑不再一味淘洗、撇清“崇高美学”中可能暗含的“构建民族和政治身份的政治”元素,而难能可贵地将反省延展至新世纪民族精神建构的层面。这从或一向度提醒了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所兼负的使受教育者“精神成人”的使命。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共和国文学中所激扬的“崇高美学”之弊在于其造神之“空想”;那么,这并不能成为今天躲避崇高的理由,更不能因此听任世纪末那股“化正常为异常”的颓靡之风盛行,如是,显然无助于民族精神层面铸造“中国的脊梁”。
综上所述,“民国文学”(准确地说应理解为“民国时期的文学”)的发生发展,并不尽如某些学者所臆想的:源自于中华民国这一“新的国家体制”;究其原貌与本质,更多地还应归因于作家对彼一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抗与超越。而“十七年文学”也恰如识者所辨析的,并非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简单记录,那时作家所追求的也远不止“是与生活同步”;“而是要把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合乎情理地表现出来”。这便意味着,“文学对未来新制度、新生活必然有一个充满想像的过程”(17)。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们在其最初的构想中,便难能可贵地体现了着眼于较长时段的整体性思维,避免将百年文学史“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个螺旋给切断了”。例如注意到:二十世纪是“亚洲的觉醒”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18)。总体美感特征,“荒凉”、“颓废”毕竟只能读作新文学现代性追求中一缕颤音;而“悲壮”、“崇高”方是20世纪文学主潮之正声。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逸出了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节点仅仅视为文学史断裂的鸿沟之武断;更不认可以此后的“十七年文学”为标尺全然否定此前的民国时期的文学,抑或以此前的“民国文学”为标尺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这一类极端性思维。如是,不难发现百年文学史中的一些总体性特征。如上述识者提示的,纵然现实层面的实践一度遇到了挫折与回旋,但内蕴于文学层面的这一以贯之的“充满想像的过程”,依然连通了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百折不挠、执意追求复兴的中国梦想。——这才是不容解构、不容颠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完整、持久、恒在的方向与本质。
[注释]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②(18)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③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此语典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④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⑤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
⑥秦弓:《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⑦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⑧周维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⑨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⑩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13)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收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今天》,1993年第4期。
(15)(16)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3至191页,第2页。
(17)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至10页。
[责任编辑:曹振华]
I206
A
1003-8353(2014)06-01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