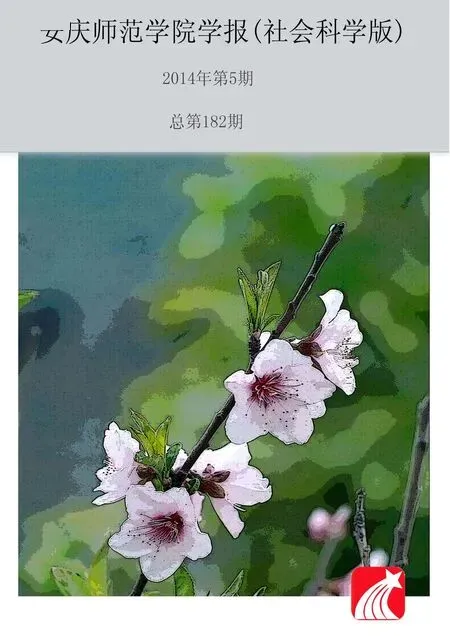论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艺术魅力
贾 莹
(兰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论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艺术魅力
贾 莹
(兰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身兼作家与批评家于一身的纳博科夫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撰写了许多批评论著。他以作家独特的眼光关注文学经典,并进行创造性解读,使文学批评呈现出另一种样貌。他的三部批评著作,有着大师批评的独特风格,蕴含深厚的美学价值、审美创造特性以及个人化色彩,展现了作为文学大师的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之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 ;纳博科夫 ;魔法师
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其迷宫般璀璨的文学创作而著称,除此之外,他还具有批评家、翻译家以及蝶类专家的多种身份。就文学领域而言,他作为作家的文学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其文学批评则相对冷落。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论著主要完成于他在美国几所高校执教期间,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经典作品,进行细致精妙的剖析,将那些长期被主流批评所忽略的文学审美价值彰显出来,提供了对经典名著的一种创造性解读,引导读者体会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之美,使文学返回自身,其批评体现出作家批评的审美创造色彩。本文以《尼古拉·果戈理》《〈堂吉诃德〉讲稿》《文学讲稿》三部著作为主,旨在发掘其批评艺术中浓郁的审美判断价值以及独特的个人化色彩,展示其文学批评的瑰丽纹章。
纳博科夫常以大魔法师来形容伟大的作家,以童话来形容伟大的作品,而他自身当之无愧是能够创造出引人入胜的童话的大魔法师。用魔法师的眼睛去观察他周围魔法般的文学世界,去感悟作家们所创制的魔法的精妙与拙劣,揭示这些魔法是如何运作、如何使得作品变成上乘的童话,最后将这些以魔法般的笔触呈现出来,这可作为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一个浓缩象征。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阐明纳博科夫文学批评艺术的风格魅力。
一、从文学性入手,维护艺术的本质
纳博科夫坚持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应该站在纯文学的立场上,他摒弃对文学的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心理分析等外部研究,主张批评应该让文学回归自身,分析作品的主题、风格、结构、文体、艺术手法等文学性问题,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形式层面。正如他在《文学讲稿》的开篇面向听课的学生所说的一句话:“我的课程是对神秘的文学结构的一种侦查。”但并非可因此断言纳博科夫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所谓的风格、结构,是包含了艺术家的品质和天才的独特诗韵。这种观念从深层来看是源于他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他认为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大作家是大魔法师,只有研究其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才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整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对七部文学作品解读的重心都是对作品主题、风格、结构、语言及修辞的详细分析,很少去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在分析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时,他首先申明他不会从社会讽刺、政治影响、法律知识的角度去读这本书,而是去赞叹犯罪主题的结构之巧妙,体会文学之美带来的震颤。接着他梳理出了三条主题线:大法官庭——雾——鸟——疯人起诉、不幸的儿童、神秘主题。然后他顺着这三条线索,将主要人物与故事衔接起来,并分析了典型的狄更斯手法,如象征性的比喻、双关语、叙述人安排上的巧妙与不足,最后总结了狄更斯能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功力,他认为最能代表狄更斯风格的艺术手法就是他善于将人物事物置于象征性环境中,例如大法官庭与伦敦的雾、戴德洛克夫人与雨、克鲁克与火等描述都是令人叹服的手法。在分析《包法利夫人》时他极力称赞福楼拜是一个具有艺术才华的大师,他靠的是艺术风格的内在力量、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法,从而将一个构想出来的里面居住着骗子、市侩、庸人、恶棍和喜怒无常的太太们的肮脏世界,“写成一部富有诗意的小说,一部最完美的作品”[1]128。他指出了福楼拜两种特殊的艺术手法:多声部配合法和叙述主题的结构式转换法,并详细举例分析他是怎样一步步地利用这些手法结构小说的。而说到《尤利西斯》每章各异的风格时,他认为这是一种变换视角的把戏,一种新的手法,为的是让人们看到不同于日常的更为鲜绿的青草和更为清新的世界。
可以看出,在面对艺术作品时,打动纳博科夫的往往不是思想内涵,而是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形式,“形式(结构+风格)=题材:为什么写+怎样写=写了什么”[1]101。以艺术批评的尺度来审视文学,从文学最本质性的问题出发,走到一部部名著活生生的心脏当中去谈论艺术,在当今文学批评被各种理论层层包裹、文化研究即将吞没文学研究、艺术价值被粗暴地简化为认识价值之时,这样的批评捍卫了艺术的审美本质,将清新的空气注入到了负重累累的文学研究领域。
二、 调动创作经验,感悟创作细节
法国学者蒂博代将作家批评称为“大师的批评”,与“职业的批评”、“自发的批评”相对比,它是一种“寻美的批评”, 是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巨大的好感,我们应该视这种好感为艺术家批评的实体”[2]122。究其原因,就在于作家在阅读欣赏作品时出于对创作过程的探究本能,会调动自身的创作体验,以行家里手的眼光对艺术做出最为直觉上的反应。作为对艺术结构形式有着极大热情的魔法师,纳博科夫常常将“诗的精确和科学的激奋”[1]111融入对文学作品的品鉴中,使阅读体验与创作经验相融合。这种“大师批评”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作者意图的推测和对创作过程的还原。典型例子是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创作过程的推敲,在这部讲稿中,他跨越几个世纪的时空距离去揣测塞万提斯的创作意图,所依据的是对艺术内部的敏锐洞察。在人物的选择和塑造上,纳博科夫推断塞万提斯之所以选择一个流浪汉作为小说主人公是为了使其卸去危险的宗教和政治责任,因为一个疯子般的流浪汉是非社会的。在分析结构时,纳博科夫认为作者原本是要写一篇较长的短篇小说以供读者娱乐,可后来被迫扩充了,在主要叙述中闯入了一系列片段和插入故事,“这是一个疲惫的作者在填充滥竽充数的东西,他此时已经没有了精力去完成他的主要创作,于是将精力分散到次要任务中去”[3]34。
其次,分析一部作品时,喜欢引入其他作家作品来比照说明。在解析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隐喻套隐喻”艺术手法时,纳博科夫插入果戈理、托尔斯泰的比喻手法进行比照,他认为普鲁斯特的比喻是展开式的、富有逻辑性和诗意地层层相套,视觉、听觉、味觉相互转换;果戈理的比喻是凌乱的怪诞和夸张,是具有美感的非理性的胡说八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隐喻则注重景物与内心感觉的密切联系。而在说明普鲁斯特表现人物的手法时,又引入乔伊斯的手法,认为乔伊斯是将一个绝对的完整艺术形象打碎,将碎片扬散到小说的时空中去,普鲁斯特则是通过它在其他人物眼中的形象来表现它,在经过一连串的棱镜印象后合成一个艺术真实体。这样的引入和对比分析,体现了纳博科夫对经典作家创作手法的稔熟,感同身受地站在作者立场上剖析作品,显露出作为作家同行的深刻洞察力。
最后,关注为人所忽略的细节。例如纳博科夫对许多作品中人物名字的象征意义的关注。《荒凉山庄》里大法官庭的办案律师的名字如“Drizzle”“Chizzle”“Mizzle”的谐音或俗语意思里都透出昏惨惨的气息,与大法官庭的昏庸联系起来;《化身博士》里海德的姓氏起源出自盎格鲁·撒克逊词hyd一字,丹麦语中是hide,即避难所,因而象征意义是海德是哲基尔医生的一个藏身之处,在海德的躯体内同时存在着医生与谋杀者,是善与恶的混合体;《尼古拉·果戈理》中纳博科夫指出果戈理赋予小人物的名字或是有奇怪的外国特征,或是表达出某种遥远的光学扭曲,或是怪异杂交的,或是噩梦般的呓语,这些怪诞的庸俗的诨名是果戈理用来揭示这些小人物的心智的独特方式。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纳博科夫所做的不仅一种批评分析更是一种“审美的创造”。套用蒂博代所言,这是一种“居于艺术最深处的批评”[2]138,是在“歌唱从根部看到的树”[2]129。纳博科夫将对创造力的感悟融入对艺术品的鉴赏中,体现出作家批评中批评与创造的不可分割的特殊性。
三、 穿插文学艺术观于批评中
通常认为,纳博科夫的文学观艺术主要在一些单篇文章中作了集中讨论,如《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文学艺术与常识》以及《独书己见》中的文论等。但同时,还有许多对文学艺术的灵感顿悟是在他解读作品时产生的,它们多是由作品中的某些文学现象引发而产生的思路,这些论述或精妙生动,或唯美诗意,或暗含着讥讽嘲弄,闪烁着纳博科夫作为艺术家的真知灼见,是他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
例如在说到《堂吉诃德》的残酷性和蒙骗的主题时,纳博科夫探讨了文学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残酷性;评述《外套》时阐明了非理性对作家的重要性以及它何以产生伟大的作品;在《尼古拉·果戈理》中大谈庸俗,从现实生活中的庸俗,联系到精神世界的庸俗,艺术领域的庸俗,庸俗的文学形象,最后回到《死魂灵》中果戈理塑造的庸俗人物形象上;解读《变形记》中“三”这个数字在故事里所起的作用时讨论了艺术中的象征问题;分析《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艾玛与包法利医生时,他从对浪漫的看法入手区分了两个人物不同性质的浪漫。还有其他关于虚构、风格、形式等等的观点,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些观点深刻地嵌在纳博科夫的头脑中,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记,因而在不同的批评论述中他会不厌其烦地变换着表达形式重复这些观念。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是他关于艺术真实与虚构的看法,其他许多论述都是以此为基点来延伸的,它们化身为不同的表述贯穿在批评中。解读《变形记》的荒诞幻想性时纳博科夫拿三类不同的人走过同一风景区为例子以阐明客观事实的不可获取性,现实在不同人的体验中是不一样的,唯一回到客观现实的办法是各取其中一份混合而成,因而现实是主观性的混合标本。而小说如果想要反映社会现实将是徒劳的,说到果戈理在他的创作低谷时期想要以搜集材料的办法弥补创造力的衰退时,纳博科夫提到了事实的存在状态,即“赤裸裸的事实并非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因为它们从不是真正赤裸裸的”[4]128。想要得到纯粹的事实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相对而言是一派胡言。从这种现实观出发,纳博科夫认为所有小说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神话。在为简·奥斯丁手法和题材的做作不真实辩护时,他认为艺术真实是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一本书取决于自成一体的天地,对于天才作家来说,“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1]7。在论及《包法利夫人》被评为是一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小说时,纳博科夫对“主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认为现实都是相对的现实,某一特定的现实,具有主观性,福楼拜的作品在他写作年代的那些熟悉描写伤感的绅士淑女作品的读者看来也许是符合现实的,但后代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他的细节过于冗长夸张,而更新一代的读者又或许会觉得描写应当更加详细。就此说来福楼拜所创造的世界是想象中的世界,有着自己的逻辑、规律和例外。主义是过时的,艺术却永远存留。沿着对艺术作品虚构本质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纳博科夫进而认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堂吉诃德》中的真正艺术是能给感官带来快感的想象,正是这部分难能可贵的东西才成就了这部书的价值。与此同时,在读书时就必须摆脱一种病态倾向,即“总要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找到‘真事’蛛丝马迹才善罢甘休”[4]44。这是天真孩童的幼稚表现。
四、 创造性的批评艺术
纳博科夫往往不是以中规中矩的理论、普遍的批评思路去阐释文学经典,而对不同的作品设计不同的批评路线和批评方式,就好像每一次阐释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解读,一种批评艺术的创新。在此基础上,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进行描述和点评,表露真实的好恶感受,使批评带有印象式的痕迹。蒂博代认为,大师的批评中“包含一种比喻的艺术”[2]128,当夏多不里昂称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拉伯雷的作品是“人类精神的矿藏和母腹”时,这不仅是一种明晰的观念,更是引起无限联想的形象比喻,它把大师内心世界与人类精神本身像静物一样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在精神现实中感受到了母腹的重量。纳博科夫的批评无疑可以借用蒂博代对夏多不里昂的文学批评所作的评价,即包含了比喻艺术的生动批评。
首先,纳博科夫常以创造性手法解读作品。在解决《堂吉诃德》中的蒙骗与残酷性主线的问题时,纳博科夫先由一个传说开始,传说中有个青年学生读《堂吉诃德》时一边使劲拍大腿一边尖声大笑,纳博科夫假以这个青年学生为对象,让他引领着我们来发现残酷性主线。纳博科夫罗列了一整套供这个快乐的青年学生挑选的使他乐不可支的事例,在第一部里他举出了所有折磨肉体的残酷性实例,数出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堂吉诃德所挨过的打,认为这会让那个青年学生笑得肚子疼。在第二部里他继续寻找了让这个青年学生哈哈大笑的造成精神上痛苦的残酷性,他把塞万提斯称为总魔法师,把书中的实施残酷的人物称为单个的魔法师,堂吉诃德所遭受的折磨即一个个魔法师手下变幻出的法术,其中扮演过魔法师的有桑丘、学士、公爵夫妇、堂吉诃德本人,公爵夫妇是一对最凶恶的魔法师,整部书的残酷性在此达到了残暴的程度,而那位青年学生看到这里可能又笑得肚子疼了。纳博科夫就这样将读者的残酷、作品的残酷以及作者的残酷都统和到了一起,清晰而生动地把残酷的魔法呈现在人们眼前。
其次,纳博科夫喜好自创新名词,而不用理论阐释作品。他将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艺术手法归纳为三种,即“马头棋步”“特殊笑靥”“警句式语调”,这些自创的名称,简明而形象地突出了奥斯丁每种艺术手法的特征。又如分析狄更斯小说中的叙述人问题时,纳博科夫并没有直接挪用叙述学理论,而是将同样的叙事现象进行了自己的创新总结。他认为小说中的叙事由三种代理人担当:第一种是“大写的‘我’”,以第一人称说话并推动故事前进;第二种是“过筛人”,其主要特点是通过作品中一个主要人物的眼睛和感官去感受事物,就像过筛子一样,让故事经过其感情和观念的筛选;第三种是“杂勤”,他存在的目的是去访问那些作者希望读者去访问的地方、遇到作者希望读者遇到的人,没有自己的身份和灵魂,相当于一个东跑西颠的打杂人,但在引导和推动故事的作用上又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生动的创新将文学理论中枯燥的问题以形象化方式阐述,体现出文学批评中艺术创造的可能性。
最后,是插图说明。往往为了说清楚一个问题,纳博科夫选择比语言更为直观的图画来帮助表达,他认为读《尤利西斯》应该准备几份都柏林的地图以弄清布鲁姆和斯蒂芬的旅行路线,读《化身博士》时头脑中应该建起一组哲基尔医生家的立体外观。为了说明海德与哲基尔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善恶混合是怎样分布的,他画了变形前后的几幅图来对照;在解释为什么堂吉诃德会将风车看作是巨人,他画了十七世纪的风车结构图;对格里高尔所变成的大甲虫,他也仔细地描画出来。
这些创造性的批评手法,共同特点都在于将批评最大限度地形象化,让它充满了文学色彩,自身具有了艺术创造的吸引力。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避免了理论批评的枯燥乏味,可看作是另一形式的文学创造。
五、颠覆文学前见,呈现魔法师眼中的魔法世界
对于一些文学史上已经有了定型的公认看法的作家作品,纳博科夫并没有一味接受前人见解,他通过细致地考察分析,以作家独特的眼光予以关照,发现了许多被人们长期忽略的细节,将作品真正的艺术价值和闪耀之处挖掘出来,为优秀作品另立丰碑。
纳博科夫为果戈理所作的评传《尼古拉·果戈理》摈弃了前人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看法,那些看法中最通俗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认识,即果戈理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旨在揭露黑暗社会、讽喻戕害人性的社会制度。纳博科夫走出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他告诉读者,如果想要从书中寻找真实信息或道德批判的人请远离果戈理,因为他的作品不是幽默故事或对社会谴责的模仿。通过对果戈理三部作品的评析,纳博科夫展示了不同于文学史上所塑造的果戈理形象和他的另类世界。
在纳博科夫眼中,果戈理不是一个幽默剧作家或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所创造的是一个梦魇的世界,他的文学属于梦幻文学。在《钦差大臣》《死魂灵》中,他发现了果戈理的次级世界,这是由一晃而过的次级人物、背景式的事物、边缘性的文字所构成的世界,然而却是果戈理的真实王国。纳博科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些次级形象的巧妙之处:在老套文学中第一幕中出现的挂在墙上的猎枪在最后一幕必须开火,而果戈理的枪挂在半空中却始终没有开火。就像这些边缘性的人物事物,在作品的转折关头蹦出来短暂地炫耀一下它们的逼真存在后再也不会出现。纳博科夫进而分析,在《钦差大臣》中,边缘性人物的塑造主要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人物对那些从未出场的人物的提及。例如第一幕中通过县长之口跃入戏剧舞台的有身上散发臭气的法官职员,爱扮鬼脸的教员,为了学问较真的历史教员等。第三幕中从赫列斯塔夫的吹嘘中跳出了一连串人物,他们轻描淡写地从两段谈话之间掠过,留下了活蹦乱跳的背影。而在《死魂灵》中,边缘性人物是由各种隐喻、比较和抒情插笔的从句生成的,即由“纯粹的言语形式直接诞生鲜活的人物”[4]78。例如以抒情插笔出现在小说开头的两个谈话的庄稼汉,他们由一辆轻便马车引出的,谈话内容就像这两个人物本身一样无关紧要。纳博科夫却认为,哲学与诗就是那样诞生于两个庄稼汉的好奇中。以隐喻和比较的手法让次级人物出场是果戈理更巧妙的招数。例如把淡灰的天色比作醉醺醺的警备队士兵身上穿的旧制服的颜色,从而在暗淡的风景中生出了一支每逢星期天便喝得醉醺醺的老兵队伍。纳博科夫认为,这些稍纵即逝的小人物所构成的次级世界就这样闯进曾经是主角们的表演舞台,构成了作品真正的情节。
在《外套》中,纳博科夫发现了另一个与次级世界同样重要、同属于果戈理的梦幻王国的场所:荒诞世界。他认为,果戈理的荒诞绝不是指古怪或喜剧性,不是某种令人发笑或耸肩的东西,是指哀怜,指人的处境,那些在正常世界里的与最崇高的志向、最彻骨的遭遇、最强烈的感情相连的东西,而某些迷失在果戈理噩梦般不负责任的世界中的可怜的人就是荒诞的,那个丢失外套的小公务员恰恰代表了果戈理荒诞世界的精神,“一个鬼魂,一个从某种悲剧性深处来的访客”[4]153。纳博科夫不认同俄国进步批评家们将主人公看作是受害者形象,将作品解读为一次社会抗议。他认为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是,“在这个徒然谦卑、徒然统治、一切都是徒然的世界,热情、欲望、创造性冲动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就是一件新的大氅,裁缝与顾客则都屈膝以求”[4]153。这才是果戈理世界迥然不同于其他文学大师世界的独特所在。
纳博科夫就这样将他所发觉的果戈理的秘密世界呈现出来,那是由次级世界和荒诞世界共同组成的梦幻王国。它是经由同样作为大魔法师的纳博科夫的眼睛观察到的世界,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纳博科夫魔法的痕迹。
结 语
纳博科夫拥有魔法师的双眼,他能洞察奇诡幻术背后的制作技巧,辨别好魔法、坏魔法以及非魔法,能体会到操控魔法的法术师们的艰辛,他目之所及之处,幻术现出了本质原型。当我们跟随着他去经历一场文学之旅的时,像是进入了不同以往的魔幻世界:这里有想博得人们残酷的笑的塞万提斯,有深谙叙事技巧的狄更斯,有普鲁斯特层层延展式的比喻,还有果戈理梦魇般的王国。同时,这场批评之旅本身也是一个魔法世界,我们在其中欣赏到了那个名为纳博科夫的法术师所制造的批评图景:他本着对文学最深处的艺术感悟,引入自己的创作经验,一步步细致地解析结构、主题、风格、修辞等纯艺术问题;他精心为每部作品设计了不同的批评模式,最为巧妙地将批评与创造结合起来;他关注为人所忽略的细节,并且深谙大师们的创作风格,对他们进行比照分析;他以诗性的文学语言为我们呈现出魔法师们别样的面孔。这是一场双重旅程,无论是在批评之内还是在批评之外,我们所获得的都是双重享受:由批评所引导的视界和批评本身的所带来的审美体验。
[1]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堂吉诃德》讲稿[M].金绍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4]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M].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校:汪孔丰
2013-09-26
贾莹,女,甘肃陇南人,兰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10-28 14:1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9.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9
I712.074
A
1003-4730(2014)05-0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