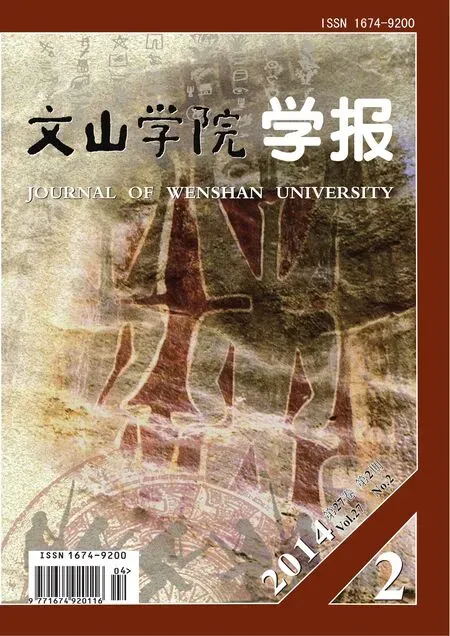欲望的缺失与表征
——从《八月之光》看福克纳
章艳萍,施应凤
(文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欲望的缺失与表征
——从《八月之光》看福克纳
章艳萍,施应凤
(文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八月之光》所展现出的黑暗、对宗教的狂热、种族迫害、暴力等社会现象,实质是作家潜意识中积极欲望缺失的一种表征。文章从社会现象入手,分析作家对南方的各种潜在欲望,以便更深层次地解读作家对南方的复杂情感。
缺失;表征;光;宗教自由;种族主义
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以多角度的模式,最为广泛地涉及到了美国重建时期南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种族、宗教、历史等问题将南方社会的腐朽全然呈现在读者面前。该小说在福克纳的创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1]216式的意义。除了对腐朽社会的批判,福克纳对南方社会的炽热情感同样也交织在字里行间。除此之外,在这部小说里,福克纳还将笔锋转向了“专制主义问题”[2]320。对南方社会的批判与赞扬共存的态度,强烈地反映了福克纳矛盾的内心。他内心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对彻底废除奴隶制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新南方的排斥及憧憬都在小说中得以表征。
一、光的缺失与表征
阴暗的人生。荒诞、绝望的人生是小说《八月之光》中人物生活的主基调。福克纳笔下的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说重建时期南方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坚守着旧南方的荣耀,恪守着旧南方的道德准则及教义条规,对于无法阻挡的现代工商业的冲击视而不见,但又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从道德准则和教义条规上看,南方人普遍信仰的加尔文主义驯化了一批又一批狂热的教徒。他们将自己甚至于别人的生活限制于条条框框之内,古板、机械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小说中的海因斯和麦克伊琴就是典型的代表;历史的根源造就了奴隶制的长存,加尔文主义的盛行更助长了种族主义的蔓延。黑人在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他们往往与暴力邪恶联系在一起。因此,像克里斯莫斯这样身上有黑人血液(只是可能)的人毫无疑问会遭到社会的排挤与迫害;美国内战以前,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繁荣使得南方人过着一种简单、固定、宁静的生活,从而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逐渐发展起比较强烈的社区观念”[3]52。南方成了社会的集合体。对于北方自由散漫的个人主义,南方人向来嗤之以鼻。他们排斥北方的任何事物,甚至排斥像乔安娜这样自小生活在南方的北方人。乔安娜因此被排挤出南方人的生活,孤独压抑地生活在远离人们视线的大房子里;南方人对骑士精神的顶礼膜拜,终日沉浸于南方同盟军昔日所取得的辉煌中,以海托华为代表的很多人将时间和空间都定格在马背上,甚至他所宣讲的教义里“充满了奔驰的骑兵,先辈的光荣与失败”[4]42。
陈旧腐烂的地理环境。尽管小说对南方地理环境的描写不多,但读者从中可以对南方人的生存环境有个大概而深刻的了解。在北方工商业的冲击下,南方在地理环境上也失去了往日的祥和与安宁。土地面积越来越少,森林资源遭到机器的过度开采。小说中多次提到伐木厂,“再过七年就会把周围一带的松木砍伐殆尽”[4]2;这里到处都是“萧杀肃静而又荒凉的田野”,经过雨水的冲刷,成了“一条条红色的堵塞的满满的沟壑”[4]2;这儿还有条铁路(工业的象征),“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飞驰而过”,“总是像个幽灵似的突然从满目荒凉的山中钻出来,像个预报噩耗的女巫尖声哭喊着”[4]2;人们生活用具和居住的房子也显得陈旧、腐烂:年久失修的马车、油漆剥落的招牌、陈旧的大房子(乔安娜的住处)、没有漆过不起眼的平房(海托华的住处)、幽暗陷塌的地面……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南方人不仅生活过得暗淡无光,就连居住环境也晦暗无光。
光的表征。在阴暗无光的生活中,南方人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福克纳在描述、反映现实的同时,也用手上的笔表达了对光的向往。他将这样一部充满暴力、极端思想与行为的小说命名为“八月之光”,是希望从天空降下一丝光亮,照亮杰弗生镇(南方)的每一个角落。另外,他设计了莉娜这个角色,一个生活积极向上,不受任何因素阻碍的待产母亲。她为着似有非有的目标永远处于行走的状态,从来都不觉得累。她如同一丝光亮穿行在杰弗生的每一条街道,驱逐了四周的黑暗。她未出生的孩子同样代表着新生的希望。福克纳自己也希望能抱着尝试的态度,像新生儿一样用全新的目光看待和迎接新南方社会。
二、宗教自由的缺失与表征
宗教强权。“南方被称为美国的‘圣经地带’,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在南方宗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5]34由于长期处于清教教条的影响与控制下,整个南方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南方人形成了宗教意义上的集体,以严苛的教条规范着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其中禁欲和女性的贞洁尤为重要。未婚先孕或偷情之类的行为更是让众人鄙视和唾骂。小说中的莉娜虽然受到乡亲们的帮助,但也免不了遭受乡亲们的非议。清教主义教条压抑了南方人的欲望,抹灭了人性。以海因斯、麦克伊琴为代表的狂热清教信徒自以为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不仅自己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以同样的要求控制着亲人的行为。海因斯恶毒地咒骂自己的女儿为“娼妇”“浪荡的女人”,在女儿难产时他拒绝请医生,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在分娩中死去;麦克伊琴对养子的教育遵循清教教义,要求8岁的孩子背诵《教义问答手册》,背不出就以鞭打和不给饭吃的方式惩罚他。他用尽一切方法让孩子明白“懒惰和胡思乱想是两大恶行,而干活和敬畏上帝则是两大美德”,尽管年幼的孩子“还不曾干活,也没有敬畏过上帝”[4]96。成年后的孩子卖掉麦克伊琴给他的小母牛为自己添置了一套新衣服,这在普通人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却让麦克伊琴将“懒惰”“忘恩负义”“傲慢无礼”“亵渎神明”“撒谎”“好色”等一连串罪名加在他身上。他抑制孩子青春期对爱情的萌动,阻止他出入有女人的场合,甚至跟踪他去舞会现场;麦克伊琴夫人在丈夫的管制下形同一个没有性格的木偶,丈夫是他的操纵杆。她不敢干涉丈夫对养子的训教,只能傻到单纯地用谎言来庇护养子,偷偷给养子送饭吃。丈夫发现后,斥责她跪下请求上帝的宽恕。作为夫妻,麦克伊琴夫妇毫无感情,只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必须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家庭,然后女人必须听从丈夫的管制。此外,牧师海托华的妻子也是清教教条的牺牲品。受到丈夫冷落的她承受不了心中的寂寞而选择偷情甚至自杀,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海托华也因此被人们认为玷污了牧师的名誉而被赶出教堂。严苛死板的清教教条让人变得没有性格,“它要求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按它的规范行事,任何偏离其准则的言论举止都会遭到公众的舆论或谴责。这样的社会必然保守封闭、对外排斥,成为产生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温床”[4]15。由此,人们对克里斯莫斯的排斥也变得不难理解了。
表征:对宗教博爱、人性自由的渴望。福克纳自己并不排斥宗教,他相信上帝,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仰望着上帝。福克纳所生活的奥克斯福镇也有浓厚的宗教氛围,“除了参加教堂活动外,对《圣经》的习读也是福克纳童年时代的必修课,他谈到他的曾祖父曾经要求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饭前先背诵一段《圣经》经文”[5]34。这样的生活在小说中也有体现:克里斯莫斯被要求背诵《教义问答手册》;乔安娜的祖父在儿子一出生便向孩子灌输祖先们所奉行的宗教,刚学会走路便要求孩子用西班牙语诵读《圣经》。
虽然福克纳信仰上帝,但他希望人们不要拘泥于形式上的条条框框。他渴望上帝将人间都洒满爱,渴望万物皆平等的精神。而现在的清教主义教条是规范、指导、训诫人们生活的僵化教条,很少关注人性。“福克纳始终强调一个梦想,就是人类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宗教结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靠历史构建物维系的,而是靠对上帝的信仰,靠精神,靠人类对自由、博爱的追求相维系。”[5]36对于清教主义博爱、自由思想的向往(缺失),福克纳借克里斯莫斯、拜伦、莉娜几个角色作出了反抗。克里斯莫斯拒绝背《教义问答手册》,甚至将书放在马厩地面,也从不祷告,更不用说上教堂了;在女性贞洁如此被看重的旧南方,拜伦竟然不顾海托华的劝阻和人们的非议,毅然决然地爱上了莉娜这个未婚先孕的妈妈;莉娜更是不顾人们的鄙视挺着大肚子行走在人们的目光下。这些行为在被清教主义驯化过的集体南方人看来有悖天理,但实际上表达了福克纳内心的呐喊与愿望。
三、种族无歧视的缺失与表征
在清教主义的纵容下,种族主义一直以来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问题。它“超越了某一个阶段的社会形态和阶级制度,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散播在人们心中”[5]62。内战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黑人奴隶的政治、经济、生活面貌。“解放宣言的发表,解放了黑人奴隶三百万人。但这不过是一种‘战时措施’,从法律上来说,奴隶制仍未废除”。[6]202南方地主阶级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奴隶)而掀起了“白人优越论”运动,采用恐怖手段迫害黑人。南方各州的民兵也任意对黑人行凶。迫害黑人的公开和秘密组织蜂拥而现,其中以“三K党”最为出名。他们在穷白人中大力散播仇恨黑人的思想,威胁那些帮助黑人的人。黑人犯罪通常被盖烙印、剪耳朵、阉割或处死。小说中的克里斯莫斯最终被种族主义者阉割致死。在人们的意识里,任何暴行都与黑人有关。小说里凶杀案发生后,人们“个个都相信这是桩黑人干的匿名凶杀案”[4]193。在调查时警察随手就抓黑人审问,并任意用鞭子抽打黑人。他们还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迫使黑人在学校、教堂、医院、饭店、商店等公共场合与白人分开,甚至连公共汽车、火车、电车都设有黑人专座。许多城市都有黑人区,如小说中的杰弗生镇弗曼雷区。政治上,黑人没有选举权,经济上,黑人奴隶依然没有拥有土地,没有任何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还被迫向前种植园主租借土地和劳动工具。很多黑人奴隶由于承受不起租金和利息而选择继续为奴。
回归到小说,主人公克里斯莫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排挤。他从生下来就被外祖父遗弃在孤儿院门口,并一直生活在外祖父的监视下。外祖父这个狂热的清教徒教唆其他孩子称克里斯莫斯为“黑鬼”,处处遭到排挤的克里斯莫斯最终被送出孤儿院由麦克伊琴夫妇收养。可是他幼小的心灵已经埋下了黑色的种子。他想追寻自己的身份,却永远无法摆脱世俗的目光。因此他一生都处于黑与白的纠结中。最终由于他无法承受情人乔安娜对他黑人身份的定位,而杀死了乔安娜,被种族主义者阉割致死。克里斯莫斯的悲剧是整个南方社会甚至是美国社会黑人处境的真实写照。
表征: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在小说中,作家对克里斯莫斯身份不确定的设置明确地表明了福克纳对种族主义的仇恨与批判。福克纳研究者肖明翰先生认为“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正是福克纳的神来之笔,它表明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一个人身上是否有黑人血统,而在于种族主义的传统观念对人的毒害与摧残”[7]335。可见,福克纳对克里斯莫斯这个人物的创造表明他内心反种族主义的强烈呼声。
四、新生活的缺失与表征
内战过后,南方人一直在其头脑中保持着昔日的荣耀。“骑士的翩翩风度与贵妇人的纯洁美丽组成了南方人的梦幻般的神话图景,南方白人以高度的荣誉感、强烈的种族和家庭的自豪感圣化了他们的生活。”[5]150南方人头脑中的非现实成分让他们保持着对旧时代社会的依恋,他们认为“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事物,而是那些应该存在,或据说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事物”[8]454。
海托华(Hightower),名字寓意为高塔。福克纳给予此人物的特殊名字,隐射出该人物的生活特征——将自己封闭在深深的高塔中,不见塔外的光明。海托华是一位过分沉湎于祖先事迹的牧师。当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就一心向往到杰弗生镇工作,为了回到祖父英勇善战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关系。遗憾的是,他辜负了牧师这一身份。他并不关心教众。他的生命一直停留在祖父的马背上,就连布道时他的教义也总是同奔驰的骑兵和光荣的战绩混合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认为“站在上帝的圣殿上所宣讲的这一切,简直近乎亵渎神明”[4]42。他对妻子也漠不关心,全然忘记自己已经结婚。无法忍受的妻子只好到孟菲斯去寻找欢乐。后来妻子从旅馆的窗户跳下自杀,偷情的丑闻也为众人所知。人们再也无法容忍亵渎圣职的人继续当牧师,迫使海托华离开教堂,离开杰弗生镇(他还受到“三K党”的武力威胁),但他拒绝离开,用自己多年攒下的积蓄在后街买了一幢小住宅,目的就是为了继续留在杰弗生镇,继续回味祖先的荣耀。
乔安娜,小说中另外一个从小生活在杰弗生镇的外来者。她继承了先辈拯救黑人的伟大使命,整日从事着黑人事务。尽管黑人接受她的帮助,但他们不愿意接近她,她独自生活在远离人们视线的大房子里。她把父辈的事业当成人生的全部,全然不在意自己是一个待嫁的需要关爱的女人。她不修边幅,打扮得像个乡村妇女,“穿着整洁宽大的印花便服,这种家用衣服她多的不可胜数”[4]156。另一方面,自小生活在杰弗生镇的乔安娜,无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文化的熏陶,因此也具有南方女性的高傲、矜持的贵妇品性,到40多岁还呆在闺中,过着节俭禁欲的生活。后来,克里斯莫斯的出现激发了她的爱,但也未能使他俩心灵交融,乔安娜自始至终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除了这两个典型人物,南方居民以集体形式呈现给读者的精神面貌也是疯疯癫癫的。他们以呆滞、毫不在意的目光观望着发生在周围的事。镇上的人们“特有的磨磨蹭蹭,不慌不忙的劲头,绕着弯子聊天……对时间毫不在意”[4]6。在围观杀人现场时,“这些人带着呆滞的孩子般的惊讶神色”,像在“端详自己的不可更改的摄像”[4]193。尸体被抬走后,人们观看大火,“带着同样呆滞惊骇的凝视目光,这目光仿佛直接来自知识起源的古老发臭的洞穴”[4]193。所有的人梦游般地过着现在的生活,头脑里都是过去的影子。
表征: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跃跃欲试。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福克纳能清醒地认识到南方所存在的弊端,他深知历史的潮流不可逆挡。因此,他希望南方人能试着接受新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深爱着这片故土的他对外来者所带来的一切感到担忧,害怕它们会毁掉旧南方的一切。在小说中乔安娜为爱情所做的努力;克里斯莫斯在临死前对黑人身份的默认(只想简单地成为某一种人),以及他对自己所犯罪恶勇敢地接受惩罚;海托华为莉娜的孩子接生而自己获得了新生,肯出去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愿意帮助克里斯莫斯;拜伦不顾乡亲们的劝告和面对莉娜的拒绝而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爱情。所有这些行为都表达了福克纳对人们试着去改变旧价值观,接受新生活的愿望。与此同时,乔安娜与克里斯莫斯的爱情失败、克里斯莫斯的死亡以及拜伦不知结果的爱情尝试则反映出福克纳内心的担忧以及产生的犹豫不决。
福克纳所成长的年代是南方正处在社会发展转折的年代,作为一个南方衰败贵族家庭的后代,他目睹了内战给南方人所造成的物质及心灵创伤。他对南方的情感极其矛盾,既深爱着这片曾经充满祥和与荣耀的故土,又对南方社会的败落深感痛苦和同情,害怕所热爱的南方会毁于南方人的偏执与冥顽不化。他渴望南方是一个充满爱,没有宗教压迫,没有种族迫害,人人平等的社会。福克纳所有潜意识欲望的缺失在《八月之光》里得到极好的表征。
[1]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杨敬仁.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3] 李杨.美国南方文学后现代时期的嬗变[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4] [美]威廉·福克纳. 八月之光[M].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 蔡勇庆.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 唐陶华.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8] [美]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M].房炜,孟昭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The Missing Desires and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An Overview of Faulkner from Light in August
ZHANG Yan-ping,SHI Yi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Social phenomena that reflected in Light in August, such as darkness, craze for Puritanism, racial persecution, and violence are factually a kind of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of William Faulkner’s subconscious desir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uthor’s subconscious desires for Southern America form the aspect of social phenomena, with the aim of getting a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author’s complex feelings for Southern America.
Missing;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light; freedom for religions; racialism
I712.074
A
1674-9200(2014)02-0075-04
(责任编辑 田景春)
2013-09-13
章艳萍(1983-),女,湖北宜昌人,文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施应凤(1977-),女,云南砚山人,文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法、基础英语教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