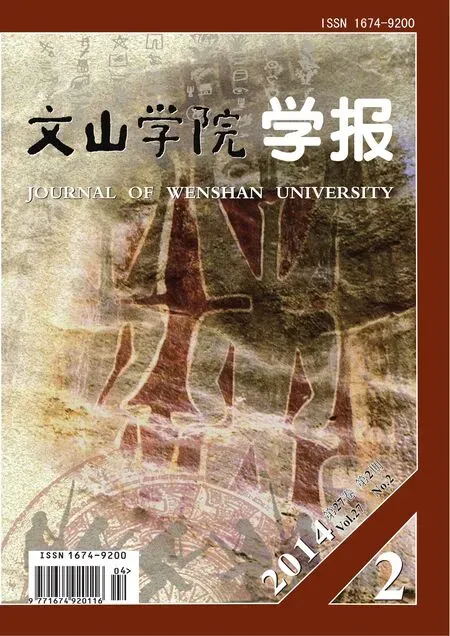“影响的焦虑”
——论范稳小说《悲悯大地》
董晓霞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云南 临沧 677000)
“影响的焦虑”
——论范稳小说《悲悯大地》
董晓霞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云南 临沧 677000)
“影响的焦虑”是哈罗德·布鲁姆用来分析诗人与先驱诗人关系的理论,它解释了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范稳在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以藏人的视角体悟藏传佛教的悲悯和大地的灵魂,创作出了体现“神灵现实主义”的《悲悯大地》,这是超越影响的创新。“英雄叙事”是作家在“反英雄”创作潮流中的逆向书写,英雄最终归于庄严、博大、静谧的大地,这是身处现代都市的作家在感性英雄崇拜的驱使下对自然的皈依。
影响;焦虑;神灵现实主义;英雄叙事;大地情结
《悲悯大地》是云南作家范稳继《水乳大地》后的又一力作,讲述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史。小说延续了作家一贯魔幻、血性、庄严、浪漫、传奇的风格,以藏地生活、历史、宗教文化为背景,以诗性的语言构建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它一改《水乳大地》集中讲述了一个民族的史诗的多重结构方式。
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分析了诗人的创作心理,认为诗人总有一种迟到的感觉,因为重要话语早已有了表达,他必须通过对前文本进行修正、重构,来为自己的创作开辟空间。布鲁姆的理论不仅适合诗歌也适合小说。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布鲁姆强调一部经典就是一份已获得的焦虑,伟大的作品不是重写即为修正。范稳渴望写出好的作品,在创作《悲悯大地》时面对经典,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神魔小说,因为有焦虑,所以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在滇藏交界处的卡瓦格博雪山及澜沧江峡谷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具体表现为以跨文化的认同的姿态,用庄严、诗性的语言直触宗教,构建起了“神灵现实主义”。范稳的焦虑当然并不只停留在创作层面,还体现在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来反思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异化;以针对“反英雄”的“英雄叙事”重拾精神信仰的神圣性;以融入大地的情结构建了类似自然文学的宁静的艺术。
一、影响:对中外经典的模仿
(一)魔幻现实主义的直接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萌芽诞生于拉丁美洲的一个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通常具有将客观现实和以某种信仰或观念意识为基点的主观真实相交融的特点,并常常运用夸张、怪诞、象征、打破时空界限等手法来进行非理性描写(但并非采用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的作品都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1]34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拉美文学的大量翻译,《百年孤独》成为很多中国作家的案头书,成为模仿和借鉴的范本。普希金曾说:“模仿可能说明作家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信心,说明他希望沿着某个天才的脚迹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说明他渴望以谦恭的态度掌握自己尊崇的范例,从而赋予它新的生命。”[2]117韩少功、扎西达娃、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都在模仿,并创作出大量带有本土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此外,云南作家范稳也坦率地承认其作品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我是非常崇拜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就放在枕头边”[3]。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滇藏交界地区有其存在的土壤,这里到处是神山、神灵,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这是一个想象力之外的世界。范稳被这片土地上的诸神“召唤”,创作出了接近魔幻现实主义本质的作品。他并没有把魔幻理解成“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知道只要披上“怪”“玄”的外衣就是“魔幻”了。拉美文学研究者赵德明说:“魔幻的真正意思,套一句中国话应该是‘诚则灵’。它是一种信仰的东西,不是魔术,不是变戏法,也不是简单的象征,就像《白鹿原》里的鹿,不是这种。”[4]可以说魔幻现实是一种感觉性的现实,要具有相应的心理思维结构。范稳虽是跨文化写作,但他深入藏区体验生活,带着敬仰之心以藏族人的视角出发对来自民间的原生态传说进行诗性挖掘,是对“诚则灵”的文学尝试。
范稳对《百年孤独》的模仿在《水乳大地》中很明显,一开篇就用“多年以后……”的句式,而且还化用一些情节,如那场持久到足以让人们失去时间感的大雨,性爱与卤水的关系,灾难与盐田出盐、女人生育的内在关联,还有江春农布倔强逃走的头颅。而这种模仿的痕迹在《悲悯大地》中很少见到,因为范稳已领略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实质并且把它融入到自己所敬仰的神山圣地。他的魔幻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根据那片神奇土地上的历史和传说来写作。在他看来,这些建立在原始意识基础上的传说并不荒诞,而且很美,透射着民间的智慧。所以在《悲悯大地》中作家带着敬畏之心精心营建着魔幻色彩的意象:打破生死界限的“回阳人”都吉和英雄扎杰会走路的骷髅;出现三个太阳昭示洛桑丹增喇嘛去找家人;天上飘下来的神的偈文;贡巴活佛与羊的对话、叶桑达娃与动物的交谈;守财奴轮回转世为蛇;会飞的神驹;央金产下蛇首人身的怪婴等等。不灭的灵魂、轮回转世、神佛显灵、动植物神奇的意象,都是范稳在《悲悯大地》中的魔幻表述,体现了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本质的把握。
(二)《西游记》的潜在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作家的创新意识外,还与中国传统的魔幻文学有关。中国的文学传统具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同空间,这种审美契合使作家创作出具有世界性文学视野又有本土特色的作品。范稳虽没明确提出过《悲悯大地》受到了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影响,但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的,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5]24。独创是建立在接受遗产和影响的基础上的,只有以传统为依托,不断借鉴他人,吸收外来营养,才可能创作出新颖的作品。《西游记》对范稳的影响具有隐含性,是一种精神渗透,虽消融于作家的创作中,但仍有迹可循。
《西游记》对《悲悯大地》的潜在影响最明显的应是“游走叙事”。这种叙事以人物的追求为情节动因,在寻找途中心性得到净化,到达终点时社会理想目标得以实现,但过程中的妖魔阻难是叙事中心,也是塑造人物的重点所在。《西游记》开篇是孙悟空的游走,目的是追求自由随性。保唐僧取经的游走是小说的重心,目的直关东土众生的劝化为善的大旨。而《悲悯大地》中两个彼此有杀父之仇的藏族青年,离乡别井踏上两条不同的寻找“藏三宝”的道路,达波多杰寻找的是宝马、好枪和快刀,阿拉西追求的是佛、法、僧,即仁慈、悲悯和爱。他们在途中经受各种磨难,遭遇各种魔怪,在佛性与人性的冲突中人物形象日益丰满,性格逐渐完善,这也像《西游记》从修身到修心的过程。此外“游走式”情节结构由于所涉空间广阔,以“找”与“遇”为机缘,所以能扩展叙事维度,形成串珠式的情节结构,《悲悯大地》就是随着人物的寻找给我们展现出神秘广阔的天地。
《西游记》是宏大的神话思维叙事作品,妖魔鬼怪齐聚各显神通,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初民的神话思维是不自觉地以想象代替事物的存在,在他们的意识中人与鬼神是可以直接交往的。西藏的神话传说也是神话思维的产物,直觉的沉迷使事物失去其自然性,转化为充满情感的直觉对象。《悲悯大地》中范稳的写作姿态是对来自民间的原生态的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神话、传说进行想象性的文学加工,这是一种对神话思维的还原:红狐变成妖艳女子魅惑土司的儿子;母狼变成罗刹女四处作孽;玉丹变成花斑豹守护朝圣者一家;都吉的灵魂寄居在名叫“勇纪武”的骡马身上,这是神话的变形思维。还有纯女人的部落、食人族、独角龙、雪人、会飞的马、飞舞的雌雄宝刀、各种神灵魔鬼,这些奇遇使《悲悯大地》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童话世界中的民族的精神世界。此外,《悲悯大地》与《西游记》的暗合还体现在创作态度上,即都认为小说家的责任就是讲好故事。中国古代小说一般以精彩的故事吸引读者,《西游记》也是由各种神妙故事串联起来的,它汲取了民俗信仰的神秘数字并展开神奇绚丽的艺术想象,使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成为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或宗教献身精神,追求真理或理想境界的精神模型。而范稳曾明确表示:“小说就是讲故事……但是现在我感觉到了今天,小说好像几乎又回到了小说最本质的东西,讲好故事,用好你的语言,塑造好人物这些基本的元素”[6]。范稳没有现代小说家先锋而孤高的姿态,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也没触及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而是注重营建极富想象力的传奇,这都是对传统小说的回顾。
范稳在《悲悯大地》中用神话思维在“游走式”的情节中,虔诚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沉重而又释然、庄严而又浪漫的故事。相对于主要叙述家族史和村史的《百年孤独》那种封闭、孤独的状态,《悲悯大地》显得开阔、明朗、大气得多。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作家所接受的这种传统文学遗产。
二、焦虑:规避的努力
(一)原创——神灵现实主义
前面已述,布鲁姆认为文学创作来自影响的焦虑。在布鲁姆看来文本不是众多符号在纸上的集合,而是作家与其先辈进行心理战的场所,先驱成为后来作家努力摆脱的渊源,是他们要修正、位移和重构的权威。所以影响推动着独创,独创受益于影响。范稳在创作时同样有影响的焦虑,有摆脱、超越的渴望,这促使他在《悲悯大地》中以诗性、庄严的语言达成了自己的原创性。
针对评论界对《水乳大地》的论说,范稳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外界很容易将我的作品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联在一起,但我更愿意称它为神灵现实主义”[7]。魔幻现实主义让范稳学会了如何去看待并学习民族民间文化,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但藏区的文化特征并不是魔幻现实的,而是神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织。因为西藏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众神之地”,是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地区,宗教文化中的神佛观念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范稳在小说中写道:“在这片土地上,传说就是现实,至少也是被艺术化了的现实。人人都是神灵世界的作家和诗人,这份才能与生俱来,与秘境一般的大地有关”[8]88。可能一般人所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技巧,但是回到这片土地上,却是一种实在。用它的创作思路、创作风格来考察藏族文化时,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风格。“神灵现实主义”是范稳自己命名的,隐含着作家的“焦虑”,想突出自己的独特性。它是在模仿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对藏区的带宗教色彩的神话和传说的虔诚书写,它的本质与魔幻现实主义相同,都强调“诚则灵”,不同之处在于它专属于西藏,属于西藏的神灵,它是对博大精深、肃穆崇高的藏传佛教的文学表达。
作为一个汉族作家,范稳并没有对少数民族抱有文化的偏见,没有强势文化的主观意志,而是走进了那片神奇的土地,触摸到了西藏的灵魂。他以诗化的语言展示了一种自在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民间文化形态。他以人类学家的姿态进行田野调查、文化考察,不是猎奇,不做故弄玄虚的呓语,而是本着藏民的诗性思维来写作,按照本然性将其敞开,对带有宗教色彩的传说进行想象性还原;诗意地讴歌兄弟共妻,因为那是家族财产永不分割的最好选择;在朝圣途中家人的逐渐死去,这不代表洛桑丹增喇嘛没有悲悯心,而是大悲悯与小悲悯的区别,作者以藏族的观点来看,死在朝圣路上是一个功德非常大的事情。此外范稳在《悲悯大地》中插入了六则田野调查和三篇读书笔记,这是一个结构上的尝试,既向读者展示了小说素材,又能和文本中的某些事件起相互印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作家融入藏族文化的努力。这些都是范稳与大地间的习与悟,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由于作者深刻地体悟了他所描写的这片土地,领会并感应到它的神韵,使他关于魔幻的笔墨不是移植,而是本土化的,富于创造性的”[9]。范稳领悟到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真谛,但并不是对它简单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神灵现实主义就是在“影响的焦虑”的创作心理驱使下的“超影响”,这种原创性是对“影响”超越的结果。
(二)反思——融于大地的英雄叙事
范稳在写作《悲悯大地》时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即描述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以诠释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底蕴。在当中达波多杰代表的是一种物质欲望,洛桑丹增喇嘛代表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作者刻意把这两种东西碰撞,宝马、好枪、快刀最后被佛、法、僧打败,以证明精神的力量是更加永恒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回答“何为英雄”的小说,作者也借洛桑丹增喇嘛的口回答了“真正的英雄要有大悲之心”,信仰、血性、刚烈、神秘、悲悯与宁静交织成了一部瑰丽恢宏的英雄传奇。范稳崇尚英雄主义,其英雄情结在《悲悯大地》中表露无遗,在他笔下英雄是豪迈血性,狭义肝胆的,他们的悲剧总是因为站在某种强大势力的面前不妥协、不屈服。联系文学中的“反英雄”叙述,《悲悯大地》就被“标出”了,显得独特而大气。
“‘反英雄’是与‘英雄’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电影、戏剧或小说中的一种角色类型。作者通过这类人物的命运变化对传统价值观进行‘证伪’,标志着个人主义思想的张扬、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微和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质疑。”[10]103“反英雄”的发展是人类崇高理想逐渐衰微的渐变过程。英雄是人类信心、力量和道德的化身,体现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反英雄”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想中“英雄”人物的解构。平民生活一旦进入艺术核心,就意味着“崇高”“远大”“宏伟”的集体理想的瓦解,以及“英雄”形象或概念的丧失。20世纪的很多作品,已不再是对某些价值观念的完整的“证伪”,而只是书写在价值观念丧失之后人们的表现。现代社会不像英雄时代那样具有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所以很多反英雄形象,由于缺乏生活的明确目标和积极的价值观,变得玩世不恭、迷惘失落,给读者带来的是滑稽、痛心、无可奈何的感觉。
面对小说从关注外部世界到关注自我之谜,再触及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的形而上的书写,或是面向世俗反映人生的低贱,记录日常生活的琐碎的形而下的写作潮流,《悲悯大地》回归传统的英雄崇拜,讲述英雄的传奇。范稳通过藏族文化来获得一个超越自己的视阈,寻找未被工业社会污染的精神遗产来反思现代文明。“作为一个被现代生活的滚滚红尘几近淹没的俗人,我渴望逃离,渴望和有信仰的人同行,从感知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学习他们的历史文化。”[11]在很多反英雄的作品中,作家对任何人都不抱希望。我们不能指望用心灵拯救自己,甚至不能使自己免受伤害。这些立志毁灭现实,把人变成阴影的作家的创作重点一直是失落:人们只会失去未曾拥有的东西。范稳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他一再强调“悲悯”,这是对众生的悲悯,对所有社会现象的一种慈悲胸怀,在宗教上则主要是对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一步步地改变和净化,最后的目的是对众生的大悲。面对范稳的作品,正如陈晓明所说:“它使我们面对一段陌生的历史时,直接叩问我们的精神深处”[12]。它展现了信心、力量和生命原初的激情,是一首讴歌少数民族生存信念和超越存在困境的史诗。
普实克在《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中指出中国史诗不发达的原因是:“中国不像欧洲人那样对个体的命运、对个体的人生经历的戏剧性变化感到浓厚的兴趣”[13]237,而是带着历史使命感整理历史史料。确实中国人的关照方式基本是散文性的,用散文形式表达历史状况。中国史学的发展,靠的是理性的伦理道德而不是感情上的英雄崇拜来作为民族凝聚力,而《悲悯大地》却以感性的英雄崇拜来烘托出史诗的氛围。范稳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一种现实,很纯粹的西藏,是一种人神未分的状态,是产生浪漫史诗和英雄传奇的时代。此外,苍凉、险峻、博大、高远的大地,展现出的是一种大境界、大写意,这构成了宏大叙事的基础和史诗的基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人和神已经分开了,范稳在小说中透露出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敬畏感的丧失:“机器造出来了,佛的位置就没有了。”[14]262“现在的天空不属于神灵了。”[14]255随着科技的进步,人被大工业社会无可奈何地异化了,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道德信念。而范稳的写作是一种在不理想的状态中尽量地表现理想的“英雄叙事”,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它只能对抗世界的进步从而实现自己的进步,因为世界的进步使人处于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他笔下的英雄在朝圣途中把心中的一切恶念去掉,直到心变得像天空一般广阔、纤尘不染。他在赎罪,作者也在反思,并希望读者也要忏悔,而所有的自省最终指向悲悯的大地,这是具有自然本身的那种恢弘,这一恢弘又让作者领受了自然的淡漠。
在有信仰的人们看来,神自然是存在的,是不可追问的。因为追问本身毫无意义。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们就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超越存在的困境,宗教使他们像孩子似的静静地被宇宙的直接影响所抓住和充满。《悲悯大地》中洛桑丹增喇嘛把自己融入大地,每一次向大地的跪拜,让他体验到大地的悲悯,“它承载着他有罪的身躯,一点点,一丝丝地消磨掉他身上的贪欲、嗔怒、愚痴、嫉妒、疑惑,让他慢慢学会谦虚、慈悲、宽容、忍耐,让他找到一颗比大地更深厚、更宽广的心灵”[14]299。作家的大地情结侧面反映了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土地伦理”,它寻找自然精神家园,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取向的文学,它激励人们去寻找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文化的完美不是反抗而是宁静。《悲悯大地》结尾以洛桑丹增喇嘛的牺牲换来峡谷的平安,建起的平安塔保佑着大地的和平与安宁,英雄的传奇变为了融入大地的宁静的艺术。
范稳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来表达宗教观念,认为宗教庇护一切,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纯粹的维系人类和平共处的精神信念,在大地中找回人性与信仰。这不是说教,而是作家美好的期望与祈祷。范稳模仿中外文学经典,在“焦虑”中用认同藏族文化的视角体悟神秘的大地,达成了自称为“神灵现实主义”的原创性,唤起了我们久违了的庄严与崇高,营建了人与神对话的诗意氛围。他的英雄叙事和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在当下文学语境中显得传统而又时尚,既是原生态的藏地文化又具有世界性的关怀,是身处物欲横流、动荡不安的现代社会的作家对“心灵净土”的美好诠释。
[1] 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转引自约瑟夫·J·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C]//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3] 田志凌.访谈范稳:被西藏的信仰[EB/OL].[2006-12-15].http://www.szdyys.com/news0001/200612/2 0061215_211447.htm.
[4] 赵德明.如果《百年孤独》是一道标杆,《水乳大地》就是一次漂亮的跳跃——北大教授赵德明谈《水乳大地》[N].北京日报,2004-03-07.
[5]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 范稳聊天实录:《悲悯大地》的创作灵感[EB/OL].[2006-11-09].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 6-11-09/1508206098.shtml.
[7] 孙小宁.范稳:我的小说不是魔幻现实[EB/OL].[2004-03-26].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54 /21861/2413022.html.
[8] 范稳.水乳大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 雷达.长篇小说笔记之二十·范稳的《水乳大地》[J].小说评论,2004(3):4-5.
[10]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1] 范稳:从慢开始,越来越慢[EB/OL].[2009-07-07].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07-07/73513. html.
[12]陈晓明.《水乳大地》: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画卷[N].中华读书报,2004-02-11.
[13]普实克.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C]//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4] 范稳.悲悯大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n Analysis on Compassion for the Earth by Fanwen
DONG XIAO-xia
(School of Chinese, Lincang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Lincang 677000, China)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is a theory that Harold Bloom used to parse the relation between poet and pioneer poet. It explains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view of Tibetan Buddhism compassion and the soul of the earth, Fanwen created Compassion for the Earth that embodies the “Gods Realism” on the basis of the magical real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 hero narration” is a reverse writing by a writer in the trend of“anti-hero”. The hero eventually returns to the dignity, greatness and quiet earth. This is modern city writer’s return to nature driven by the worship of sensible hero.
Influence; anxiety; Gods realism; hero narration; Compassion for the Earth
I207.425
A
1674-9200(2014)02-0063-05
(责任编辑 田景春)
2013-12-13
董晓霞(1987-),女,云南腾冲人,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叙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