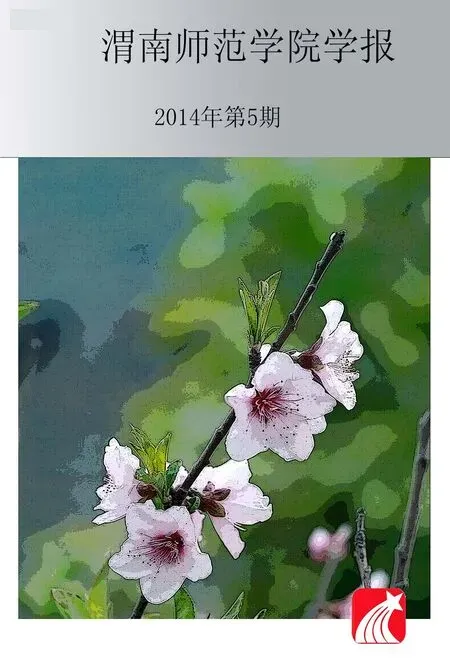探析魏晋南北朝美术貌清骨秀之风度
蒙 建 维
(保山学院 艺术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一、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主流,依然继承汉代传统,强调绘画的“鉴戒”作用。当时的壁画和卷轴画,以古圣先贤、忠臣烈女为题材者不胜枚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形式以长卷为主,构图技巧提高,绘画风格亦呈多样化。谢赫“六法论”的提出,说明这时期中国绘画的全面技巧已经被提高到条理化的高度,为画家所自觉掌握。这时期出现了“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等表现人物面貌、精神的不同风格;出现了“春蚕吐丝”“紧劲连绵”的绘画笔致,出现了其体绸叠而衣服紧窄贴体的“曹衣出水”的造型样式,出现了“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表现等绘画特征,说明画家不断丰富绘画表现技巧,不断提高人物画的表现力。
持续300多年的战乱流离虽然给社会造成破坏,但却促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落后的少数民族不断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固有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魏晋时期发展确立了士族制度,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使得士族阶层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影响了当时的文学艺术。
在思想领域,这一时期的人们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玄学思想风靡,个性得到张扬。魏晋人士不仅欣赏自然美,而且把自然美作为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人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再以自然界的美来比况人物品格的美,为生命情调的探究和人格本体的建构打下了基础,并由此开拓出魏晋风流清淡之艺术境界和生命情调,造就了魏晋人士高贵的飘逸之气。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将汉末以来社会的注重人伦品藻深化为自我对个体精神的任性适为。他们追求“道”和“自然”,并以适心随意作为一种全真养性的手段。他们认为,只有返璞归真与道合一才能享受人生的无限乐趣,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
宗白华先生在评论晋人书法之美时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表现自己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1]180魏晋南北朝兴发的审美关照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时期人的意识觉醒并得到张扬,因而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亲近。绘画和书法出现嬗变,西汉以来重在世俗功利的倾向出现削弱,对客观物象神韵性情的刻画和点染受到重视。绘画美学中心问题转移,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都要求任自然而得灵性,并由此开拓绘画美学之脉流。
二、重要画家与作品
古人有云:“晋人风采宋人道学。”汉朝人朴厚,晋代人潇洒,唯大英雄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晋代人的风雅洒脱一直是中国人“人生艺术”的高标。当时有著名画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谣等。
顾恺之(约346—407)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绘画笔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悠缓自然,将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完美境地。他审察题材和人物性格,在绘画中加以提炼,故其画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耐人寻味。顾恺之真迹未有保存下来。有三件流传下来的绘画被认为是其原作摹本,即《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
有学者认为魏晋时“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从绘画的装饰艺术性向写实性发展,尚不能熟练把握空间关系表现,并以《洛神赋图卷》为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成立的。但是,笔者同时也认为如果单从它本身还自带的装饰性而言,无疑这一作品是成功的。因为当时的绘画发展还没有出现科学的透视画法,画家只有从本身的情感去把握客观事物,这一点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所以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感官的情感性去理解这个作品。
根据资料记载《洛神赋图》是根据诗人曹植的文学作品而作。曹植以第一人称和优美动人、气脉一贯的笔法创造了人神相恋的梦幻境界,抒发了作者失恋的感伤。画家以故事发展为线索,将情节置于自然山川的环境中,描绘出洛神典雅美丽的形象和含蓄隽永的神韵。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衣带飘逸,动态委婉 ,似来又去。画面人物之间的情思不是依靠面部表情,而是靠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巧妙处理展现出来的。画中曹植欲语无言,洛神含情脉脉,表达出可望而不可即的忧伤情意,使人体验到顾恺之“悟对神通”的创作主张和绘画表现。他的这种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富有诗意地描绘了赋中的意境,并注重对人物情态的刻画,彰显了内心的丰富情感。山石、树木都富有装饰性,与同一时期的敦煌壁画有相近的风格,表现出魏晋时代特有的清秀风度。所以如果单从写实性去看待魏晋时期作品的话未免有所偏颇。
魏晋风度,在精神面貌上是风神疏逸,姿致肃朗;是内心的超然自得,行为的潇洒不群;是书法的清淡飘逸,从情挥洒;是绘画中的骨法用笔,气韵生动;更是雕塑中的超尘拔俗,秀骨清象,诗文中的冲淡平和,玄言玄意……然而这些只是魏晋风度的外貌,在超逸风度之下的,是一颗沉重的心。因而魏晋艺术的真正音响,是潇洒飘逸衬托下沉重的生命哀歌。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南北朝的艺术,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它们的价值。
其实,魏晋风度最本质的含义,是魏晋六朝人物的品藻,是此时一些极具风度的人格之美。这些才是魏晋艺术的最高成就。
以外貌反映出内在高贵的人格、内在的精神本体,是魏晋风度的特征。画家通过有限的、形象化的手段,传达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常人不可得不能至的“圣人”内在品格、精神,也就是要通过常人的五情哀乐来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人使用风度这个词,正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它的意思是指人的言谈、举止、态度、作风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美的、善的、哲理的世界。如《晋书》上称“风度宏邈,器宇高雅”的司马孚,他能具有这样的风度,是因为他“温厚谦让,博涉经史”。
三、魏晋南北朝的雕塑
虽然说魏晋南北朝在文化上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精神最解放的,文化、艺术最灿烂的时期,但在政治经济上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淡、最变幻无常的时期。不难想象一个如此持久残酷的局面会养成什么样的心境?厌世的心理,幻想的倾向,对美好的渴望自然助长了佛教的势力,也产生了石窟佛教雕塑艺术。“按照佛教说法,能够自己觉悟者得为罗汉,自己觉悟而能觉悟众生者得为菩萨,自己觉悟、觉悟众生达到圆满的程度即为佛。”[2]
秀骨清象的魏晋佛像雕塑,具有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它们富于理想色彩,具有真正的雕塑美。它最单纯,没有任何华丽繁复的装饰;它最简洁自然,没有任何装模作样;它最超脱,没有任何人间的俗颜媚态,在周围惨烈与痛苦的环境气氛下,俨如表面惊涛骇浪(壁画)而内心却依然平静的海洋(雕塑)。也正因为这样,雕塑成为了体现魏晋风度最好的艺术形式。因为雕塑最适合表现内容宽旷,寓意深长,使人产生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的正面形象。
黑格尔说:“雕塑最适合表现神。”在魏晋时期的雕塑中,常常借助一种线的艺术节奏韵律,用中国艺术中最常用的太极双鱼图式的圆形曲线,表现人体各个部分的和谐以及它们各种关系的构成。这种圆形曲线,既是同一的,又是千变万化的。因此,魏晋时期的雕塑家们装饰雕塑的衣饰、飘带,装饰雕塑的容貌、身体,是同一曲线的千变万化,具有一种富有韵律的形式美。比如,我们看到的那些大佛,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到内在欲火的燃烧,也看不到极度的恐惧,而是安闲、从容、超逸,因为雕刻它们所用的石料、处理它们的衣饰和表情的线条是那样的和谐,表现出和谐的理想化“人体”美。也许在这种残酷异常的背景之下,不想自觉受难牺牲,那么超脱是又一种无奈的选择。
因而,正如鲁迅所指出,表面看似超尘拔俗,骨子里却潜藏着巨大的苦恼、痛苦、恐惧,这是魏晋风度,也是我们从魏晋风度浸润下的佛像中该体悟到的更深一层意思。
四、结语
魏晋艺术的境界,正是以气韵生动的造型和形象,在有限的形色中,表现无限的情意;是以气之运旋来描绘一切有生命对象的生动之状。可以说,魏晋时期的艺术,是以韵律美作为艺术的魂魄。气韵生动是中国造型艺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标志。秀骨清象并不是构成超脱精神的全部,要表现出这种精神就必须“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古画品论》)。千百年来,赞赏艺术有“言外之象”,提倡艺术“言有尽而意无穷者”,要求在有限的可穷尽的外在艺术语言中,传达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精神,这正是魏晋南北朝魏晋风度所孜孜追求的,也正是魏晋南北朝魏晋风度最高成就的标志!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居阅时,翟明安.中国象征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