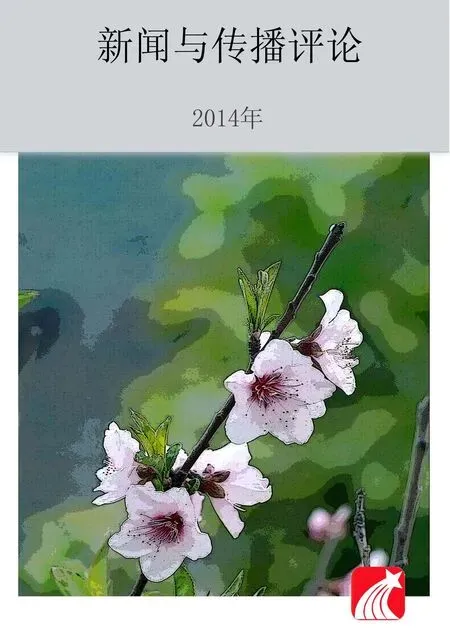谈苏报案的两个问题
□ 蔡 斐
谈苏报案的两个问题
□ 蔡 斐*
本文仔细考证了苏报案的审判过程,纠正了“章炳麟、邹容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现是革命主义的、苏报案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两个观点。指出章炳麟、邹容二人在法庭上,特别在额外公堂阶段,表现得很是“技术”,甚至有点圆滑。不但极尽推脱责任,而且否认自己的革命观点。苏报案中,尤其是审讯和判决阶段,中外双方更多的是分歧和对抗,这突出表现在对章炳麟、邹容引渡和重判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
苏报案 革命主义 勾结 革命范式
1903年的上海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富有标志性意义的个案,几乎每一本中国新闻史教材都会或详或略地提及苏报案。对于苏报案的审判,很多教科书习惯于写到,“章炳麟、邹容在法庭慷慨陈词,将法庭当成宣传革命的讲坛,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相互勾结的实质”。换言之,这样的描述强调了两点:一是章、邹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现是革命主义的;二是苏报案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
那么,历史确实如此么?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文章就上述两个问题作出考察。
章炳麟、邹容在法庭上的表现究竟怎样?
从历史资料来看,苏报案发生后,该案前后多次开庭审理,参加会审的主要有外国领事、中方谳员和上海地方官员。
1903年7月1日,按照会审公廨的司法程序,由中方谳员孙建臣、英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翟理斯进行预审对苏报案进行预审。预审程序是19世纪末会审公廨在司法程序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此前,按照中西方确立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凡是超越会审公廨裁判权限的重大案件,依章程应立即移送上海县衙,但预审程序确定后,则任何案件一定要在会审公廨“过一堂”,再由其决定是否移送上海县衙。不过,当天的预审中,先是章炳麟等人蹲踞在地,不愿意下跪,直至陪审官翟理斯喝令,才下跪参加审判。后“旋有律师博易者投案,声称陈等已延本律师声辩,请订讯案”。①对此,“华官即欲移县办理,西官以有约在先,不允。(辩护)律师亦谓订期再讯,于是中西官相商,决定还押捕房候讯”。②可见,由于辩护律师的突然出现,和中方官员要求移交审判管辖权(即更改审判机构)等因素,预审程序并未顺利进行。且邹容是7月1日当天才投案的,并没有参加预审,所以无从考证两人当天在法庭上的表现。
7月15日,苏报案第一次公开审讯,主审的依旧是中方谳员孙建臣、英国驻沪副领事翟理斯。
章炳麟是整个会审公廨中最引人注目的。据当时的《申报》记载:“章长发毵毵然被两肩,其衣不东不西,颇似僧人袈裟之状。邹剪辫,易西服,余人则穿仍用华装。”③对于清政府的指控,章炳麟回应道:“年三十六年,浙江余杭县人。《革命军》序文系我所作。”邹容则回答:“本人邹容,四川巴县人,十八岁,《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章炳麟和邹容的供认,在故宫档案馆所藏的“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亦可以证实。⑤
7月21日继续进行审理,但原告律师以本案已成为国际交涉为由,提出“此事已成交涉重案,须候北京公使与政府妥后再讯”,⑥应将案件延期审理的请求,被翟理斯批准。第二次公开庭审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短。据此,也无从考证章、邹二人当天在法庭上的表现。
该阶段,章、邹二人的表现,除了承认写作的事实外,并没有太多记载。但是从一些细节中,仍可发现蛛丝马迹。一是7月16日《中外日报》的《记苏报案第一次会讯事》一文中,谳员曾问邹容是否取得功名,邹容答曰,“我不愿进清国考场”。⑦二是英国代理驻华公使焘讷里在给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的信中,称章、邹是“狂热的殉道者”,“他们在预审时的表现使所有挽救他们的努力都变成徒劳。”⑧三是知府金鼎在给湖广总督端方的电报中指出,“章认序,并供不认野蛮政府”。⑨由此可见,章、邹二人在该阶段的表现,应该是比较直接的、一种明显的和清政府对抗的态度,但是否将法庭变成宣讲革命的舞台,无从考证。
1903年12月3日,第三次公开审理。根据清方的提议,会审公廨设立了一个名为“额外公堂”的机构负责专门审理苏报案。主持庭审的依旧是英国驻沪副领事翟理斯,谳员则更换为邓文堉,上海知县汪懋琨也参与到审判中来。
12月4日,按照司法程序,章炳麟和邹容两人单独出庭接受双方律师的讯问。根据《字林西报》1903年12月《苏报言论煽动案的审理》(The Supao Sedition Trial)(10)的记载,首先是章炳麟接受被告律师琼斯的讯问。讯问内容包括被告的基本资料、此前几年间的工作经历,在何种情况下写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何直呼皇帝的名字、何时见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印刷本以及是否采取措施制止流通等,也问到了《訄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接着由原告律师古柏讯问。琼斯的讯问比较简单,主要是表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使用的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读懂的语言,是私人之间交流政治看法的信件。
讯问章炳麟之后,双方律师讯问邹容。被告律师对邹容的讯问比较简单,只是问他是否希望看到中国改革、是否从《革命军》的印刷出版中得到报酬、现在对于《革命军》的观点等情况。原告律师主要围绕《革命军》手稿的情况、现在是否有推翻现今统治者的意图、是否认识到《革命军》具有危险性,等等。
讯问中,章炳麟甚至拒绝古柏的提问,被法庭多次警告,观审也提出这属于藐视法庭的行为。邹容也不承认自己是自首。“我与《苏报》没有关系,但是听说逮捕令中有我的名字,觉得很奇怪,就到巡捕房询问。到了之后,我碰见一名外国巡捕,便询问他我有没有被通缉,我与《苏报》有没有关系。那名巡捕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把逮捕令拿给我看,结果我在通缉名单中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并被指控撰写了煽动性的文章。”(11)
最值得关注的是,与初审时期表现出的直接对抗截然不同。章声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只是他写给康有为的私人信件,草稿被丢进了废纸篓。邹容则说《革命军》是他在日本读书期间完成的一篇作业,原稿一直留在东京。至于两书是如何印刷出版的,两人都不得而知。(12)
可以分析得出的是,章、邹二人表现的转变,显然是受辩护律师的影响。审判中,双方明确庭审必须适用中国的法律,但是原告律师并没有按照《大清律例》提出指控,而是以“煽动性的诽谤罪”(seditious libel),一个英国刑法中的罪名,来控告章、邹等人。根据英国刑法的规定,“煽动性的诽谤罪”主要是指针对英国皇室或皇家煽动仇恨和不满的一种罪行。任何人只要出版了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或者其他相关文字,一经法庭查实,都可能属于此种罪行。
对此,被告律师琼斯采取了极为高明的辩护策略。他提出,煽动性的诽谤罪中,写作、印刷和出版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罪名,即构成要件不仅要具有写作,同时还有印刷、出版这样的意图或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印刷和出版才是中国政府指控罪名的主要构成。现在当事人在法庭上已经承认有关文章是他写的,这一点我们毫不否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上述作品的印刷或出版同他们有关。”(13)且“章、邹只认著书,未认印书,今已在押数月,应请堂上开释”。(14)一下子抓住了清政府指控的漏洞。
为了配合辩护律师,章炳麟和邹容在庭审中也是极尽推脱责任。虽然两人之前都承认是自己所作,但章炳麟在法庭上称这是他写给康有为的一封私人信件,誊写稿请一个叫Tsa的人在香港通过邮局寄给康有为,草稿被丢在废纸篓,文章中“小丑”只是“小孩子”的意思,对于这封私人信件如何印刷、怎样出版、如何流通,他一无所知。以下为当时庭审的对话记录:
你知道该书在哪里印刷的吗?——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其流通?——我没有能力阻止其流通。
你不知道公开的广告每册卖10文钱吗?——那不关我的事情,应该由刊登广告的人负责。
你看到过该书的广告吗?——我看到过,不过,我没有办法阻止它。
你是在哪个报纸看见的广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苏报》。
你曾经要求苏报馆的负责人停止销售吗?——不,我根本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去过苏报馆。
难道你不希望停止该书的流通吗?——我就是希望,我也没法做到。
但是你不希望停止它的流通吗?——如果我有这个能力,那么我可能会。
那么,你知道它还在流通吗?——我不知道。(15)
邹容则声称《革命军》是东渡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时完成的一篇作业,回国前,他将文章留在东京,返回上海后,才看见市面上有《革命军》的印刷本,“杀尽满人”的观点也是他的日文老师Meidah教授的。《革命军》如何印刷、怎样出版,他也不清楚。以下为当时庭审的对话记录:
撰写《革命军》的时候,你还在日本学习吗?——是的。
是你自己出版的吗?——不是。
它是你作业的部分吗?——是的,不单单是我,许多同学都完成了这个作业。
也写文章?——是的。
是你自己出版的吗?——不是。
你要其他人帮助你出版吗?——没有。
……
你知道《革命军》一书手稿的情况吗?——原稿和我的其他书、行李等一起留在位于东京的中国学生俱乐部。
《革命军》表达了你现在的观点吗?——我己经改变了我之前的观点,我现在有新的观点。
你现在不再鼓吹推翻满族统治?——我现在鼓吹社会主义。
……
与章炳麟的手稿一样,你的文章也是未经你的同意,就被印刷的?——对于这一点,我无所谓,因为我现在认为我以前的思想是不好的,
你还有其他的书出版吗?——没有,但我准备撰写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
你给《苏报》投稿吗?——没有,《苏报》的观点与我恰恰完全相反。
你想推翻清朝政府吗?——我不想,我只想成为第二个卢梭。(16)
通过上述的庭审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章、邹二人在额外公堂阶段,都是竭力为自己作无罪辩护。他们表现得很是“技术”,甚至有点圆滑。不但极尽推脱责任,否认自己和书籍的印刷出版有关,而且否认自己的革命观点,毫无教科书中“在会审公堂上,两位革命志士,精神焕发,铁骨铮铮,据理驳斥中外反动派妄加的罪名”(17)的那种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当然,这不是说章、邹二人丧失革命气节,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自我辩护策略和自我保护措施。对此,客观的历史应当秉笔直书。
苏报案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吗?
对于“苏报案是中外反对势力勾结的产物”这一观点,学界似乎有所共识,如提出,“苏报案是中外反动派联合上演的一出丑剧,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纷纷指责”,(18)“清朝统治者费尽心机,竭力勾结租界当局制造‘苏报案’事件,其目的不仅是想把极端蔑视他们的章、邹等人凌迟处死,而且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残酷的镇压,让中国人噤口不谈革命”,(19)“英美帝国主义看到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害怕危害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就和清政府勾结起来,镇压革命党人”。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时上海“一地三制”的情境下,要在租界内抓人,并非易事。如上海道台袁树勋提出“租界之治权,彼实不得过雷池一步,而不能为非分之想、出位之谋”,两江总督魏光焘也明白,“界内拿人,最为棘手”。(22)所以,苏报案的交涉阶段如果没有外方的同意和配合,章、邹等人就不会被捕,《苏报》馆就不会被查封,但在审讯和判决阶段,中外双方更多的是分歧和对抗,特别是在引渡和重判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清政府都未能如愿,列强也很少妥协,更多的,是坚持了司法的机构、形式、过程与结果。
在引渡的问题上,按照清朝政府的打算,“(苏报案)此事关系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23)对于苏报案的被关押人员最好能够“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以免“不办首要,祸焰更炽”。(24)即将章、邹等人引渡到清政府拥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中进行审判。
所谓引渡,一般是指一国应他国的要求,将被他国指控有罪或已判刑的人移交该国的行为。租界作为中国领土,清政府要求公共租界当局移交犯罪的华人,本来不应该称为引渡,但由于租界事实上已成为清政府不能有效行使主权的特殊地域,因此租界当局视这种行为为引渡。谁知这一步却一直未能成功,特别是中外舆论哗然,新闻界开始更加深入介入后,不少国家以“政治犯不引渡”的例外原则来搪塞清朝政府,更有国家以内国法“有证据表明被引渡者在引渡国无法受到公正审判”的条款直接拒绝引渡要求。(25)
不过,清政府并未善罢甘休。为了达到引渡的目的,政府在上海和北京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经过一系列努力,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于北京公使而言,《上海泰晤士报》登载,“法公使度派尔甚愿将诸人交于华官,俄公使雷萨则又甚之,美公使康格大意亦与法公使同,惟谓当与上海道熟商,能与租界判断治罪最妙,德国署理公使莱特维芝及荷比两公使皆赞成法公使之议。意公使则独于此事有公正判决,尝谓此系公罪,而报章之言论自由久已准行于租界,无俟上海道之干预也……日本公使内田则不加可否,惟俟上海道之报告以为断。英国政务大臣汤来则待其政府之命令,而奥国公使克徐肯则并无意见也”。(26)
于驻沪领事而言,尽管各领事也存在异议,但并非全都反对引渡。美国驻沪领事古纳就主张支持清方引渡,并且致函袁树勋:“外国人之租界原非为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大义论之,当将反抗中国政府诸领袖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
但是,就在引渡问题稍有进展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沈荩案——发生了,清帝国引渡的企图便彻底夭折了。
沈荩曾为庚子年“勤王运动”的领导之一,运动失败后,寄居京城,后被告发,称“(沈荩)受康梁之命,潜藏京师,意图将皇上劫出宫去,实现保皇主张”,(27)于是,沈荩被抓。另有学者提出沈荩乃是因披露《中俄密约》惹怒慈禧被抓。(28)但无论怎样,沈荩是被抓了,而且被残忍地活活打死。(29)沈荩死讯一出,举国惊愕,中外哗然。特别是外方,一种对中国司法不信任——太后命令即为法律;审判官员屈从权势而不敢根据法律力争;刑罚的极端野蛮,不容于文明社会——在无形中得到加强。《上海泰晤士报》、《论沈荩》一文指出:“接驻各国使臣警报,谓各国执政大臣,观于此事,逆料中国居大位者,将有不得久安之势……日前英外务部大臣萨斯唐(即前文出现的蓝斯唐)曾于上议论及此事之非,而拟慎重于苏报一案,亦甚洽舆情……此次沈荩之死,实使欧美各国大臣,有异常之感触,恐本届清太后七旬之寿,各国之来庆祝者,将不复如前之踊跃矣。”(30)
这种不信任很快就弥漫到苏报案上,对引渡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原本赞成引渡的公使、领事纷纷改变立场,一致主张拒绝引渡。其中,法国反对引渡的态度转变直接瓦解了最初支持引渡的联盟。最初法国驻华公使吕班是支持引渡的,后来由于英国政府驻法公使Edmund Monson与法国交涉,向法国政府说明如果将苏报案被关押者交给清政府,就可能阻止不了他们受到最野蛮、最不人道的待遇,并且表示英国内阁相信法国政府会对英国在苏报案问题上所持观点感兴趣,两国政府将在同一战线上采取行动。(31)这一点得到了法国外交大臣M.Delcasse的完全赞同,加上沈荩案的直接示范效应,最终让法国意识到清政府的司法现状,迅速在苏报案上转变立场。这对苏报案产生了重要影响。《纽约时报》评价说,“自从法国政府一同加入反对向中国政府引渡人犯的行动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通过讨好洋人是无法达到引渡目的的,并且意识到被批捕的人犯将不会被引渡”。(32)8月5日,英国首相向驻华公使直接发出“现在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的训令。美国上议院也发来电报,拒绝引渡,命令不得将章、邹等交给清廷处置,“并将主张引渡之上海领事古纳调任”。(33)
这种转变,让清方也无可奈何,忙于引渡工作的袁树勋在给端方的电报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种沮丧,“职道承办此案,始愿未偿,以沈荩事出,变故丛生,无可补救,悚歉莫名”。(34)至此,引渡的希望彻底破灭。
在重判的问题上,严惩章、邹二人一直是清朝政府的愿望,在引渡的梦想破灭后,就一直坚持对章炳麟和邹容处以永远监禁的判决。
比如,上海道台袁树勋就认为“章、邹所犯极重,照律不但当处以极刑,且须缘坐家属。”(35)但是,早在苏报案案发之初,身处北京的张之洞就发现,“以上海索交六犯,商办维艰,属敝处商诸政府,在京设法,嗣探各使口气,皆虑交出后仍置重典,故不肯放松”。(36)也就是说,张之洞从一开始就知道对苏报案被关押者判处死刑是外人不能接受的。沈荩案发生后,张之洞为打破引渡的僵局,主动提出了“监禁免死”的动议。
不过,外人对“监禁免死”的方案并不理睬,从一开始就坚持监禁年限在三年之下,且除章炳麟、邹容之外的其余被关押者应该无罪释放。清朝的大小官吏也心知肚明,苏报案的审判权为外人所操作,并且“若依西律恐不重办”,(37)“此事仅恃沪道办理,力量较薄,非由外务部商诸公使主持,恐仅在上海监禁,多则三年,少则数月,限满释放,逆焰更凶,大局不可问矣”。(38)
1904年2月11日,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与苏报案清方最高斡旋者庆亲王奕劻进行了一次谈话。前者明确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两书的出版与章炳麟、邹容二人有关系,且两名被告都很年轻,他们所犯的罪行与判处终身监禁的决定也不相符合。即便在欧洲,这种犯罪行为也不会受到重判……并愿意尽早结束此案。(39)这也直接表达了外方在监禁年限上的立场。
2月16日,新一年的大年初一。驻沪领袖领事照会上海道台袁树勋,“各国以《苏报》馆案未断定,拟再会审一次,如再不断,将犯开释,以照驻京钦使之意”,(40)提出重新会审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清方官员的拒绝。袁树勋认为,无论是根据清朝的法律,还是中外达成的约章,会审公廨的外籍观审均无权力变更已作的判决。(41)2月21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也致电外交部,“查照前已断定之案,告知各使,请饬各领勿再翻异,盖照约照章,皆应由中国定断,既断何能复翻,如有异议,或即释放,是彼违约也”。(42)一方按照约章再次提出外方无权干涉判决结果,另一方请求外务部多作斡旋,由驻京公使向驻沪领事施压。
无奈之下,外务部只得出面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英国公使却明确表示应该酌情减免刑期,永远监禁的判决太重,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外务部也无可奈何。强下判决,本是端方和袁树勋等人的一厢情愿,外务部对这个做法并不完全支持,只能顺水推舟同意“该领既欲复讯,可再派员会审,酌照英使所请,共同定断,以期结束”,(43)答应重新会审的建议,要求魏光焘、袁树勋等地方官员妥当处理。
但此时,领事团方面却突然变卦,改变初衷,不再坚持会审,声称以往的约定有笔误,而提出只由双方派员共同协商判决。(44)不过,双方对此案判决的分歧太大,一方要求永远监禁,另一方坚持仅判三年以下,两者相差悬殊,要由双方共同作出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后,清政府做出妥协,放弃“永远监禁”的努力,转而争取尽量长的监禁年限。领事团方面对此意见纷纭,英国领事仍坚持不超过三年,但清方还是难以接受。魏光焘请求外务部“转商英使饬领事,纵不永远监禁,亦当将监禁年限从最多商定,以示儆戒”,(45)提出“能多禁一年,即可稍示一分严意”。(46)
1904年的整个3、4月,双方都在围绕章、邹所禁年限讨价还价。按照领事团坚持的司法程序,如果案件超过审判期限一直不作出判决,应当尽快释放被关押者。在这一司法程序的要求下,共同商定久拖不决,对清方十分不利。3月21日,萨道义致函驻沪领袖领事,授权可以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结束苏报案。如果双方还不能协商一致,即可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释放被关押者。(47)可是,双方的分歧仍旧很大。5月11日,领袖领事致函袁树勋,鉴于会审公堂迟迟不作判决,领事团已根据北京指示重新考虑释放在押犯的问题,并说此事有可能在两星期内得到解决。(48)
突如其来的最后期限让袁树勋十分为难,只得通过魏光焘一天内连发两封电文请求外务部出面,一方面,告知仅有十天的宽限期,“到期不定,各犯必释放”;(49)另一方面,请求外务部迅速和驻华公使联系,“询明拟减年数,磋商定案,以免释放,转行宽纵”。(50)并再与英国公使商议具体年限。同日,外务部提出至少将监禁限定在十年以内的要求。(51)这也是与英国公使磋商的结果。
然而,英国公使上述的意见,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却没有及时通知到英国驻沪领事。“查英使虽允于十年之内酌减,尚未饬知英领,致内外立意不同,”此时“晤商古领,据称两犯监禁十年,各领尚可设法照允。”(52)但英国驻沪领事仍然坚决反对清政府重判,提出“一犯禁二年,一犯即释放”的意见,并一再以审判截止期限相威胁。(53)
面临着章、邹被释放威胁的南洋大臣魏光焘,只能退而求其次。5月16日,他急电外务部,“此案展期以四月初七日为止,万不允再缓。求迅电钧处转商英使,将年限商定,急电饬英领遵办,否则英领故意以一二年为词,藉端延宕,一届限满,即行释放,诸领又不愿与英为难,非由内商定不可云。”(54)同时提出争取减至五六年监禁的建议,以免章、邹被释放。
外务部第二日(5月17日)就回电说,“苏报案犯监禁年限,并未与英使商定,现在为期已迫,如再与商,转费周折,即饬沪道与各领商定,将一犯监禁三四年,一犯监禁一年,以期结束。”(55)主动提出三四年与一年的建议,这意味着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清政府最终主动放弃了重判章炳麟与邹容的努力。恰在同一天的领事团会议上,各国一致认为翟理斯拟定的“年幼之犯拟监禁二年,年老之犯拟监禁三年”的建议是合理公正的,并提出将5月21日作为最后期限,如果清政府不接受英国观审的意见,章、邹将被释放。
最终的审判决定通过领袖领事传达给袁树勋,这是各国驻沪领事共同协商确定的结果。显然,外方的“共同商定”遗漏了重要的一方——清朝政府。同时,从时间上来看,外方的“共同商定”显然没有更多考虑外务部三四年监禁与一年监禁的建议。
5月18日,袁树勋将外方商议的结果电陈外务部,“领袖美总领古纳函复,苏报案,各领商妥,年幼之犯拟监禁二年,年老之犯拟监禁三年,均自拿获日起算,年满均驱逐出租界外,务于中历四月初七日前,会同陪审官,照以上定断,如未能照定,押犯仍开释云。查年幼犯指邹容,年老犯指章炳麟。所拟监禁年期,似可照准,乞迅赐核示遵行。”(56)第二天,外务部就同意了这个结果,也不再坚持至少最低监禁年限。
1904年5月21日,上海知县汪懋琨与谳员黄煊英、新任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复讯苏报案,并重新宣布了判决结果:“……议定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此判。”(57)至此,苏报案结案。
从上述有关监禁年限反反复复的交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清政府的要求,从力求引渡到永远监禁,到监禁十年,到监禁五六年,再到不超过三年,一降再降。在触及列强政治利益和司法底线的时候,他们丝毫不会让步。外国势力所谓的“妥协”,只能是表面的,这又何谈勾结呢?
简短的结语
可以说,本文探讨的“章、邹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现是革命主义的、苏报案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这两个观点,长期以来都是新闻史学界的“定论”与“共识”。对于此类的“定论”与“共识”,新闻史学的研究,要想深入,更应具有一种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
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大抵是由于新闻史研究长期奉行革命范式,过于强调反帝反封建因素导致的。革命范式的叙事方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确实抓住了本质,但这一指导思想显然单一化了苏报案,遮蔽了历史的真相,甚至有想当然的成分。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第一,邹容、章炳麟在法庭上的表现,更多是出于无罪辩护的庭审需要。二人的实质,是激烈的革命性质的,特别是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对当时民众的启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宣传革命的利器就是《革命军》,当时不同半年,全美洲的华侨得此书启发,不到半年,风气大开。第二,尽管清政府和外国势力在苏报案个案上显示出很大的分歧,但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上,两者相互勾结的性质也是不可改变的。
不过,个案的考察,基于个案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其背后,或许有超过宏观史学,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注释:
① 会党成擒,申报,1903年7月2日。
② 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71页。
③ 初讯革命党,申报,1903年7月16日。
④ 初讯革命党,申报,1903年7月16日。
⑤ 参见《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道员赵滨彦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25、426、465页。
⑥ 蒋慎吾.苏报案始末.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国出版社,1992,第94页。
⑦ 记苏报案第一次会讯事,中外日报,1903年7月16日。
⑧ Mr.Townley to the Marquess of Lansdowne,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1842-1937).S830 F.0.405/135,p.84.
⑨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25页。
(10) 《字林西报》从1903年12月4日至17日连续刊载的苏报案在额外公堂阶段的庭审笔录,几乎是第一时间对苏报案的庭审直播,也成为目前还原苏报案庭审的重要史料。
(11) The Supao Sedition Trial,N.C.Daily News,DEC.12,1903.
(12) 参见 The Supao Sedition Trial,N.C.Daily News,DEC.8、9、10、11、12,1903.
(13) The Supao Sedition Trial,N.C.Daily News,DEC.5,1903.
(14) 会讯革命党案,申报,1903年12月4日。
(15) The Supao Sedition Trial,N.C.Daily News,DEC.10,1903.
(16) The Supao Sedition Trial,N.C.Daily News,DEC.11、12,1903.
(17) 马模贞.中国革命史简编.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1,第34页。
(18) 汤仁泽.革命言论之枢纽《苏报》.《近代中国》第十四辑,2003,第288页。
(19) 龚德才.中国新闻事业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88-89页。
(20) 章回,包村,等.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第64页。
(21) 张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776页。
(22)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魏光焘致兼湖广总督端方江苏巡抚恩寿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13页。
(23)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77页。
(24)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十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48页。
(25)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80页。
(26) 同上。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古纳主张引渡也并非完全出于替清政府考虑,古纳主张引渡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认为《苏报》案涉案人员“疑与长江一带之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而外人之住中国者亦将罹其危难”。参见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80页。
(27) 高拜石.小心抓耙仔——苏报案的一个替死鬼.古春风楼琐记(第11集).作家出版社,2005,第98页。
(28) 参见黄中黄:“沈荩”,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这一观点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沈荩被害的原因。但是,根据彭平一在《关于沈荩与“沈荩案”若干史实的补证》一文,严洪昌在《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一书中的考察,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29) 关于沈荩惨遭酷刑的遭遇,可参见严洪昌、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45-146页。
(30) 《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外论”,第13-14页。
(31) 参见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54-56页。
(32) Shanghai Reformers are still in prison,The New York Times,Nov.5,1903.
(33)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84页。
(34)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上海道袁树勋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39页。
(35)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上海道袁树勋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39-440页。
(36)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内阁大学士张之洞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35页。
(37)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探员志赞希赵竹君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14页。
(38)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51-452页。
(39) Minute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ir E.Satow and Prince Ch'ing,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Film S830 F.O.405/142,p.75.
(40) 《警钟日报》,1904年3月30日。
(41) 《警钟日报》,1904年3月30日。
(42)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日南洋大臣魏光焘致外务部电》,见《中英等交涉苏报案当事人问题文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43)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八发南洋大臣》,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44) 1904年2月22日,领袖领事致函上海道台袁树勋,“上年备具华文照会,内载再由中西各管会审,实系笔误。本领拟再有中西判官会同商议一次,并非会审,各行更正。公廨案件,堂谕应有中西判官会同定案”。《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一日上海道袁树勋致兼湖广总督端方江苏巡抚恩寿电》,“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43页。
(45) 《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一日南洋大臣魏光焘致外务部电》,见《中英等交涉苏报案当事人问题文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46) 《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二日收两江总督》,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47) 参见 Sir E.Satow to Consul-General Sir P.Warren,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Film S830 F.O.405/143,pp.24-25.
(48) 1904年5月11日工部局会议记录,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档案》第十七卷,第83页。转引自石培华.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有关“苏报案”的资料看“苏报案”的真实情况.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6,第4期。
(49)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洋大臣魏光焘致外务部电》,见《中英等交涉苏报案当事人问题文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50)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洋大臣魏光焘致外务部电》,见《中英等交涉苏报案当事人问题文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51)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发南洋大臣》,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52)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二日收南洋大臣》,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53)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二日收南洋大臣》,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54)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二日南洋大臣魏光焘致外务部电》,见《中英等交涉苏报案当事人问题文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55)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发南洋大臣、上海道电一件》,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56)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收上海道》,见《〈点石斋画报〉案件与“苏报”案》,《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57) 《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十日南洋大臣魏光焘致外交部咨文·附照录来折》,见《中英等交涉苏报案当事人问题文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58) 台北市四川同乡会四川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邹容及其〈革命军〉》,第68页。
Research on Two Issues of Supao Case
This paper takes an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rial process of Supao case.It has corrected two viewpoints,which are“The performance of Zhang Binglin and Zou Rong in court are kind of revolutionary”and“That case is the outcome of the collusion of the sino-foreign reactionary forces”.It has pointed out that in court,especially in the extra tribunal stage,Zhang and Zou behaved quite“skillful”,even a little bit sophisticated.They tried to shrink their responsibilities,and even denied their revolutionary views.In Supao case,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es of trial and judgment,there are more divergences an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Sino-foreign parties,which are prominently embodied on these two crucial issues—the extradition and the severe judgment of Zhang and Zou.
Supao case,revolutionary,Collusion,Revolutionary model
* 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西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Cai Fei,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uthwest Politics and Law University,Post-Doctor in History,School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