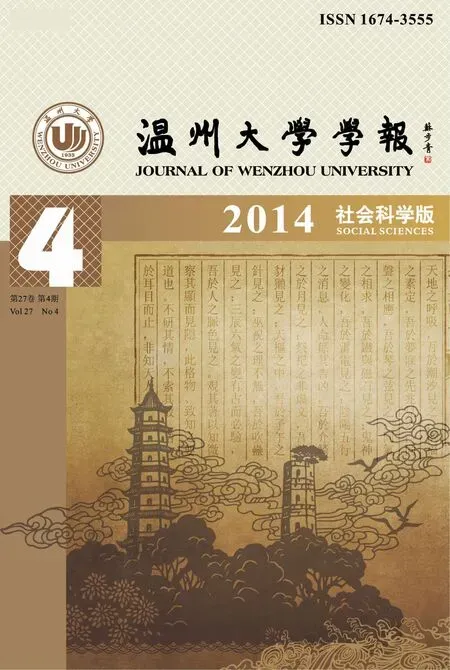电影语言本体论探析
——以麦茨第一电影符号学为讨论基点
于宏英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电影语言本体论探析
——以麦茨第一电影符号学为讨论基点
于宏英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讨论电影语言本体问题既可以从结构主义视角加深对电影本身的理解,也是以后结构主义理论阐释电影的门径和基础。电影语言本体论的核心观点是“电影即没有语言系统的语言”。电影可以被隐喻性地称为语言,但在电影中不存在天然语言中的记号系统或结构。电影是部分的和欠缺记号的系统。电影的影像充满丰富讯息,其内涵丰富但符码却很贫弱,其系统也十分简单。不同于天然语言的语法,电影语言的语法特征表现在叙事内的陈述中。电影语言能指和所指的表意功能被归为电影修辞格,同时即文化修辞。
电影语言;本体;电影符号学;没有语言系统的语言
电影语言本体论是电影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电影符号学认为电影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艺术家重新建构的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统。而这种约定性的符号系统即电影语言,亦即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语言”本体。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对电影符号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电影语言本体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麦茨第一电影符号学为讨论基点,先介绍电影语言本体论的学术背景以及麦茨两大电影符号学的关系,指出第一电影符号学的基础地位,然后主要从电影语言与天然语言的对比中说明电影语言、电影文本的特殊性,以完成在经典符号学、叙事学与电影符号学视野中探讨电影语言本体问题的任务。
一、理论背景
在电影符号学理论创立之前,电影理论还未独立,对这一艺术门类的有限分析也都依附在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中,如帕索里尼的《电影诗学》就采取了这样的研究方式。在此种情况下,电影本体研究还没有被明确提出,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之后,一些理论家把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运用于电影理论研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电影符号学。而关于电影语言本体问题的探讨就是电影符号学的重要主题之一。电影符号学是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电影理论界追求美学深度的趋向和一般美学界日益重视电影艺术分析的趋向汇合的结果,它的特殊性与含混性也就是由这一特点产生的。尼克·布朗在西方电影史经典著作《电影理论史评》中指出,电影符号学的理论贡献在于使电影符码的研究成为重要的批评或者理论范畴[1]100。从电影符号学开始,电影实体与电影语言本体才被提出并得到了规范性的描述。对电影符号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主要有符号学家艾柯,电影符号学理论家麦茨,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彼德·沃伦,对电影影像结构进行广泛研究和分析的罗纳德等,而艾柯的《电影符码的组接方式》、沃伦的《电影中的符号和含义》、麦茨的《语言与电影》等电影符号学著作都涉及了电影符号本体特征的讨论。其中以麦茨的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刻。
艾柯指出:“电影符号学是关于一种无语言在其后的言语的符号学。某种言语类型的符号学,即大组合段单元的符号学,这些单元的组合使电影语言成为现实。”①转引自: 参考文献[3].这正是麦茨电影符号学讨论的具体问题。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分为第一电影符号学和第二电影符号学两个发展阶段。在第一电影符号学阶段,麦茨以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一般语言符号学为基础明确了电影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对电影语言、电影标点符号、大组合段、镜头、光学方法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实现了对电影语言本体论的成功建构。用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电影的主要缺点是无法关注电影非物质层面的价值,因此单一的符号学是无法深入影片的精神层面来探讨的。麦茨后期电影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从而形成了第二电影符号学或电影主体符号学,它试图突破电影结构符号学的文本封闭性,转向对观众与电影文本的交流研究,进而使电影符号学理论走向开放性,从观众与电影文本的交流心理中开辟出电影符号学的另一条路径。电影主体符号学理论实现了从经典电影理论到现代电影理论的转型,开创了现代电影理论的研究路向。精神分析学与主体哲学研究的引入,使电影从技术、语言与影片情节研究走向哲学与心理学研究,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领域,使电影研究脱离青涩,进入理论的成熟期。尼克·布朗在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电影修辞学的视域中对麦茨后期电影符号学的主体理论进行了评析,指出后结构主义理论是对电影能指各类属性的精神分析学描述,前后期电影理论研究方向上的变化,代表了当代电影理论从参照物的研究到主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倾向[1]105。
然而,麦茨的第二电影符号学或电影主体符号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第一电影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不论是第一电影符号学,还是第二电影符号学,研究的主题都是电影本体。第二电影符号学将电影性概括为“想象的能指”,即电影的电影性不在于影片符号的所指意义,而在于不断滑动的能指本身。这种典型的后结构主义的电影观,在西方的电影理论研究界和文艺学、艺术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但如果没有第一电影符号学关于电影语言本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根本不可能获得第二电影符号学这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就像当年的罗兰·巴特,没有他前期的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就不会有后期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电影语言本体问题既可以从结构主义视角加深对电影本身的理解,也可以用后结构主义理论阐释电影的门径和基础。
二、作为电影本体的电影语言
电影本体即电影独立存在的依据,从符号学、语言学的角度看,电影本体就是一种具有表意符码的特殊“语言”,或者可以将之称为“影像语言”、“影像的论说”。那么,从本体论层面,我们就可以认为,电影即“没有语言系统的语言”。在电影中,除了对白、独白等自然语言之外,包括特写镜头、横摇摄影、轨道推拉摄影、平行蒙太奇和穿插蒙太奇等与电影叙述有关的技巧都是电影语言。将电影本体定义为“没有语言系统的语言”是一种隐喻性的类比。就如同西洋棋语言与电脑语言、花语与绘画语言甚至沉默的语言等,可以隐喻性地称之为语言一样,其实质是一组符号表现规则。电影符号可以被称为一种语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的叙事功能。电影与语言关系密切的原因在于电影与语言两者在思维上存在的共性,其意指要素具有相似性,意指功能的展示成为二者的本质属性。正如麦茨所说,并不是因为电影是一种语言,所以能叙述好故事,而是因为电影能叙述故事,所以电影才成为一种语言[2]44。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电影语言都是以对意指要素的意义表达为根本性任务。2013年受欢迎的《疯狂原始人》以影像语言叙述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故事,完成了人类从远古到现代历史变迁的文化性分析,成功地将人类文化转换为电影文本的哲学阐述,将自然语言的文化内容转化为电影影像语言。另外,2013年的好莱坞大片《云图》也完成了自然语言的意指功能,在电影语言中同样意指着人类文明的变迁与永恒人性的哲学主题。
电影语言不等于自然语言,但电影符号系统与语言学符号系统本质相似,电影研究应该借用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规范的工具。索绪尔认为:语言=言语+语言系统。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著名的符号学家麦茨指出电影语言是不具备语言系统的语言。电影的影像语言更类似于口头语言即言语,其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电影的影像讯息极为丰富,但其符码系统却十分简单。这正是口头语言的特征。其次,电影和口头语言一样只具有媒介的用途。通过电影发展史可以看出,电影是经历如下两大发展阶段之后才成为媒介:在早期电影阶段,电影的功能只是复制视觉感应,电影被认为是“复制的媒介”;到电影发展的成熟期,电影则突破了早期对现实物体的复制性,更多地以创造性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其突出的叙述功能使其成为表达的媒介。最后,电影像口语,是因为其“句子”在数目上没有限制。电影中的最小单位是镜头,可称为“文法特性素”,镜头不是电影中意指作用中的指示意义的最小元素单位,因为一个镜头可能传递多种讯息的要素,但镜头是电影环节中最小的元素和单位之一。
当然,将电影语言视为电影本体,不仅因为电影语言与天然语言有相似性,更在于电影语言还具有一般自然语言不具备的特殊性。或者说,在天然语言中具有电影语言并不具备的三个特征,即天然语言有分层分节结构和被系统化的模式、供互通信用的记号系统以及能够产生言语信息的特殊范围的代码。而电影语言缺乏这类语言系统,与天然语言相对应,电影语言不包含相当于语素的第一分节、第二分节的纯区分性单元,“它的一切单元,甚至像溶化和划除这类最简单的单元,都是直接有意义的和只以被实现的状态出现。”[3]17电影语言要求在大意指单元中的叙事陈述,而不要求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结构语言学中语素和音素的陈述。其次,电影是表达的媒介而语言系统是用来相互沟通的符号系统;电影属于意指领域而语言属于通信领域。电影是作为表达手段而不是作为通信手段进行意指,并不需要用一部影片去回应另一部影片,而语言却需要相互回应。最后,电影语言缺少具有特殊范围的代码,电影是部分的和欠缺记号的系统。
语言系统中的第一分节是指语言可以分解为意义词素或者语素,其作用是借以削减句子的无限制扩充以控制语汇的范围;语言系统中的第二分节是指意义词素可以分解为音素,其作用是经过内容将论说分解为表达的单位元素。语言学认为音素并非独特的最小元素单位,在其底下仍有一个隶属于同时性命令的连贯性命令。但音素是口头语上的最小要素,文字通过字典可以互译,但绝不会达到完美的状态,原因就在于语言中的第二分节是音素,音素是无法转译的,它是个别语言系统中具有固定语音意义的东西,而人类无法翻译不具意义的东西,由于语言系统中存在第二分节,使得各国语言之间的互译难度较大。而电影却不具备语言系统中的第一分节和第二分节,其原因在于电影镜头间的无尽的组合方式和电影能指和所指的距离过近。电影镜头间的组合方式没有穷尽,而语言的组合方式的数量是有范围的。在语言上,惯用语至少可以指出其最大和最小的约略的限制范围,从而有大约的估计。电影中能指呈现的单位元素是相当开放的,所有可置于镜头前的电影景观在数量上是不可限制的,不论是从摄影机和摄影对象之间的变换、摄影角度的变化、镜头焦距的变化、摄影机的运动等,还是从灯光与布景等的技巧来看,可以设想的电影影像是无法穷尽其数目的,由此,可创造出的电影镜头的数量也就是无法限制的。可见,电影镜头与语言的字汇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电影中充满太多的内在符意也是电影不具备语言系统中第一分节和第二分节的原因。电影的视觉景观必然带来能指和所指的联结,二者时刻都不能分离。“如果所指本身没有分开几个同行的段落,根本就无法解开能指,所以电影中的第二分节根本不可能。”[2]57电影内容的单位元素和表达的单位元素互相混合,电影影像“在自己的世界里塑造出所指的景观,而它自己则成为能指,也成为它自己所呈现的东西,根本就不必再去为它的所指指出意义。”[4]在对比了电影与语言系统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同距离之后,麦茨指出,在电影中,第二分节不可能出现。即使是隐喻的东西也没有第二分节。也正因为电影中没有第二分节,对于观众来说,对电影的视觉领悟要比对语言的理解少很多障碍,理解电影所需要的知识素养也比理解语言需要的知识积淀要少。电影中需要的视觉领悟比一般的语言需要的知识素养方面的领悟要少很多障碍,所以电影才可以超越文化界限、地域界限、年龄界限等障碍而为更多人所喜爱,电影比其他的艺术门类更容易在大众中普及。由此,电影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与种族,从而实现全世界的交流。
电影是表达的媒介而语言系统是用来相互沟通的符号系统。麦茨将电影称为“表达的媒介”是因为电影与其他艺术一样,其全面意义直接指向观众,无法也无需在沟通的当时立即得到语言的回应,属于一种单向沟通的现象。电影以故事的方式呈现,观众所做的只是静观。包括《公民凯恩》、《梦幻岛》、《星际之门》等电影史中极有影响力的影片,都是在电影开篇设置难题之后,并不需要观众在观影时以语言呼应的方式去解答,而是在电影故事的进程中解决影片初始的困局,因此电影是内部呼应的封闭式循环体系,无需观众在影片放映时以语言回应的符号系统。电影被称为“表达的媒介”的另一原因还在于语言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结构中,而电影存在于想象世界的结构中。《2001:太空漫游》、《哈利波特》、《黑客帝国》、《阿凡达》、《盗梦空间》等影片的成功现象皆证明了这一点。电影语言在与一般语言不同的系统中展示其意指作用,而其展示意指作用中所体现的诸多要素并不属于现实世界的结构,因为现实世界不说故事,而电影囊括的是艺术与想象世界的语言,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电影创作讲述真实或想象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电影最终以影像对现实世界的转换来完成其特有的述说。
总之,电影虽然可以被隐喻性地称为语言,但电影与自然语言有明显的区别。电影不具备语言系统,在电影中不存在语言中的记号系统或结构。电影语言缺少具有特殊范围的代码。电影是部分的和欠缺记号的系统。在电影的语言系统不足的地方,电影语言就越丰富。电影的影像充满丰富讯息,其内涵丰富但符码却很贫弱,其系统也十分简单。在索绪尔的研究中,语言系统的基础结构是对记号所指物的无理据或任意性的联系,音声陈述语的直接意义主要依赖于任意性编码原则。而电影语言的基础结构是类比性即由视觉与听觉组成的知觉类似性原则。电影的直接意义是依赖于类似性编码原则的,“电影手法把可能只是一个现实的视觉代替物的东西变成了话语。从纯类比性、连续性活动照相的意指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某些真正符号学的成分。”[3]18
三、电影本体语言的构成机制
独特的电影语言也形成了独特的电影文本。文本包括物质面、形式面与内容面三个方面。电影本身所特有的系统决定了电影文本的物质面即表达质料是胶片,电影文本的形式面是电影语法与制作技巧,电影文本的内容面是电影的故事叙事。影片文本可以被定义为“影片的全部话语,它是表现的单元,甚至于在开始时只是能被证实的单元,而且它是由影片的诸拷贝以完整的形式保持着的单元。”[3]94通过对电影的语义学辨析以及对电影语言和一般语言的细致区分,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和叙事的联系,发现电影语言的特征及电影符号学的基本修辞手段。
事实上,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并具有其自身的特征,然后才因其符码具有指示意义而成为一种语言。在电影语言本体论的讨论中,还必须找出电影语言这一本体的自身特征所在。与一般语言的语法特征相比,电影语言的语法特征表现在叙事内的陈述中,这是因为单一的语言单位有时并不构成故事,但现代电影多由故事组成,由此,必须在叙事手段与故事本身的产生过程中谈论电影语法。关于电影语言的语法特征,要“在超越影像的层次上,把影像组合成片段的过程中,在故事本身的产生中,通过广义的蒙太奇手法去寻求电影语言的特征。”[3]89也就是说,电影语言的语法特征要在叙事手段和电影符号学的基本修辞手段这两个维度中把握。而一般语言的语法是体现在陈述内的语素和语素内音素的法则中的。
要在叙事手段中寻找电影语法的根源。电影叙事手段中最著名的研究是电影叙述性的修辞法,包括能指的叙事研究和所指的叙事研究,剪接技巧分析是电影能指的叙事研究重点,而故事叙事的技巧电影则囊括在电影所指的叙事研究中。电影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与语言学中这两者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能指和所指同一性的存在及其相互转换的迅捷性,“陈述世界中某些要素构成每一电影片段之立即的所指,立即的所指通过符号学之相互作用而与片段紧密联结在一起,这形成转换原则之基础。”[2]125包括同时性的语义特征、连续性的语义特征及与陈述方式有关的语义特征等,指出这些电影语言特征都是在镜头与影像的复杂组合中,通过蒙太奇手法在叙事能指和叙事所指中产生的。
电影能指与所指转换的发生源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电影和叙述的结合是“文明发展的事实”,在电影中语言的作用很强势,电影从某种程度上被语言征服、殖民以至变形。“在电影的领域里,所有非叙述的种类——纪录片、技术影片等——皆成为次要族类,只有具有讲故事功能的剧情长片才叫作‘电影’。电影本可以有多重功能,但除了少数纪录片和教育影片的特例外,电影最后却只限定在讲故事上,并形成了剧情电影专有的符号学体系。电影与叙述的强势结合实际上限制了电影后来在符号学方面的发展,因而使得电影有点像“外在的”语言学现象影响了“内在的”惯用语功能。现代电影中的确几乎很少出现没有语言的电影,从这一实例确实可见语言在电影中的强势作用,这也是电影语言的语法特征一定要在叙事手段中呈现的重要原因。
能指和所指的表意功能被归为电影修辞格,同时也是文化修辞。电影语言的语法特征是由电影符号学的基本修辞手段呈现的,这些修辞手段包括电影的蒙太奇剪接技巧、摄影机运动和电影镜头的景位、电影的音像关系、片段切分及大组合段单元等。这些又被称为电影能指的叙事研究。将所有的电影修辞手段进行整合之后,影像的组合问题就成为电影本体符号的核心问题,进而麦茨的大组合段理论就可以为电影本体分析提供了绝对支配性的理论源泉。麦茨将电影叙事的基本单位确认为“独立语义段”。在电影文本中有八种语义段类型:独立镜头、平行语意群、括弧语意群、描述的语意群、轮替(叙述)语意群、场、插曲式的段落、一般的段落。从电影的发展来看,大多数故事片在主要组合段修辞法上彼此相似。电影叙事性由于无数影片中的习惯和重复而稳定了下来。我们对历史上大多数经典电影进行分析,发现电影文本的这八种语义段构成了绝大多数电影的文本叙述与剪辑形式。电影的标点符号概念事实上也是电影本体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语言中标点符号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是,电影的光学方法事实上成为电影的标点符号,它依赖于语境并以特技手段为标示。光学方法分离着复合的大陈述段,成为影响相互临近的诸形象的符号学标记。
[1] 尼克·布朗. 电影理论史评[M]. 徐建生,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
[2] 克里斯蒂安·麦茨. 电影的意义[M]. 刘森尧,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3] 克里斯蒂安·麦茨. 电影与方法: 符号学文选[M]. 李幼蒸,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克里斯蒂安·麦茨. 电影语言: 电影符号学导论[M]. 刘森尧, 译. 台北: 远流出版社, 1996: 92.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Movie Language——Taking Metz’s First Movie Semiotics as the Basis of Discussion
YU Hongying
(Qianjiang Colleg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18)
The discussion of the ontological question of movie language can be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ovie itself, and can be mad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interpret the approach and basis of movie as well. The core ontological view of movie language is “movie is a language without system”. Movie can be called language metaphorically, but in movie there is no sign system or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natural language. Movie is a system partial or lacking in signs. Movie images are full of rich information, rich in content but poor in symbols, and simple in system as well. Unlike the grammar in natural language, the grammar of movie language is represented by the statement in narratio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of movie language are referred to as rhetorical devices of movie, i.e., cultural rhetoric.
Movie Language; Ontology; Movie Semiotics; Language without System
I106
A
1674-3555(2014)04-002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4.00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3-11-14
于宏英(1973-),女,吉林四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电影理论,传播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