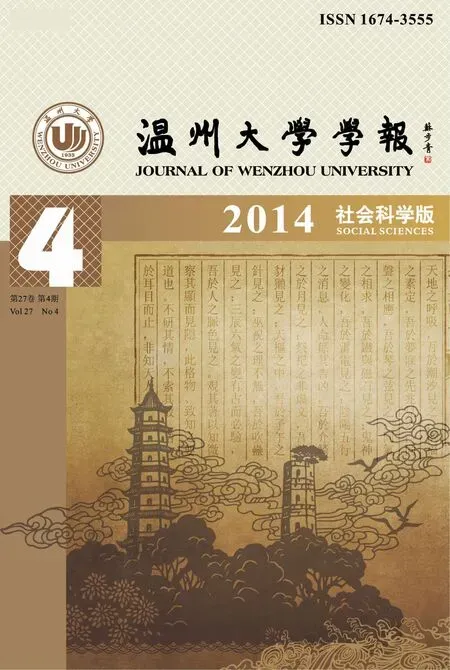宗教成为建构和平积极力量的途径和可能性
张 强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江苏南京 210003)
宗教成为建构和平积极力量的途径和可能性
张 强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江苏南京 210003)
宗教对于和平始终保持着高度关切,并通过特定的价值体系集中展现了人类的崇高愿望,推动了社会整体面貌的改善,为促成和平创造了条件。现代社会中的宗教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政治事务,但并没有完全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可以与任何社会现象混杂在一起。有鉴于此,宗教必须密切关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有效守护世界和平。
全球化;宗教;和平
从现实的角度看,宗教可被定义为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人们依靠这种体系组成社会团体,与生活中的根本难题(终极问题)展开斗争。这种斗争表明了人类的生活态度:拒绝向死亡屈服,拒绝在挫折面前沮丧气馁,拒绝恶意行为破坏社会交往[1]。约翰·希克(John Hick)认为:就当前的社会发展境况而言,迫切需要人们关注“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实践意义,也就是生活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生存在宇宙中的宗教意义。我们关注的是经验我们整体环境的宗教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意向性回应”[2]。这说明宗教确实影响人类行为,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从属性因素,而是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伴随着全球意识的抬头,宗教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再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宗教自身也越来越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分属不同意义体系的要素之间实现了相互流动。宗教几乎可以与任何社会现象或事物混杂在一起,反过来,任何事物也都能被转化成一定的宗教形式,或者与某种宗教传统进行嫁接。有鉴于此,各大宗教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向,顺势展开人文关怀,积极引导全球和平。
一、宗教关切和平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有其独特的和平指向。“主要的宗教制统都宣称,任何宗教精神的严格考验,表现在它溶入日常生活中的程度。诚如佛陀所说,大觉悟之后人应该‘回到市街去’,学习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平和、沉静与关爱的仁慈是所有真正宗教洞见的标志。”[3]许多宗教信仰者从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平和”,主要的宗教传统都鼓励祈祷、反思、冥想,强调道德行为与个人正直,宣称虔诚信仰终将达到一种和谐、愉悦、宁定的境界。尽管“会用不同的词语形容这种境界,规定不同的灵修方式,但许多人相信这种教化的本质是相同的”[4]。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道理”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人的品格会根据其信仰而得到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宗教是一种净化人内心的信仰力量。正因为如此,首要的宗教美德便是诚,一种渗透人心的诚。所以,就其教义方面而言,一种宗教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普遍的道理。只要人们笃信之、深刻领会之,这些道理便具有转变人品格的效力。”[5]虽然对于人类的解放作用一直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宗教仍在为了建设人道的社会而作着不懈的努力。宗教通过指向未来的意义体系确立起对于生活的信念,使人们真正理解并体验慷慨、宽恕、团结等社会价值,极大促进了人类精神面貌的改善,为和平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信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新天地,多种多样的媒体服务使人们能够越来越便捷地看到“他者”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需求,并与之进行比较。相比传统社会的单一与封闭,这无疑是一场触及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性问题的变革,自然会在社会各个领域掀起波澜。最为显著的就是政治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前现代社会及其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政治边缘化或者说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已成为“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民主的广泛普及,政治参与的高度发展以及政治诉求的日益多元,当然,同时还出现了社会普遍政治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变革进行得越持久、越深入,社会也就越发难以掩饰裂痕,在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认同,特别是对公义和真理的不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所有政治问题也变成了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具有一个孕育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基础。正因如此,和平共处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这个社会应如何学会自我和平相处,从而使内战不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学会文明地对待由于利益和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6]这是全球化条件下所有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和平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尽管现代文化处于混乱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期待某种宗教性解答的出现。全球社会的去中心化特点,打破了政治与宗教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随着“全球治理”思想的提出,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能够在全球性问题上扮演较之以往更加重要的角色,创造性地融合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当代的一些宗教思想已经逐步超越了个体主义的局限,提供了新的途径来思考生活世界中多元信仰体系的社会政治意义。尽管尚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但还是有助于开辟一条道路,来细致而准确地认识文化多元主义,进而充分理解宗教在世界政治中的独特地位。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7]实现和平的道路尽管曲折,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8]其中,处理不同群体之间暴力冲突的重要途径就是尽力发掘这些群体的世界观中关于和平文化的核心资源。对每种世界观来说,这些资源可能不尽相同,但都会不同程度地改善各自群体的精神氛围,甚至是整体面貌,为真正而持久的和平提供必要的舆论导向和思想基础。在这个方面,宗教可以大有作为。正像威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Smith)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人的历史正在变成自觉的历史,这也包括人的宗教史在内。而且无论是好是坏,它也正在变得更为一体化。但人们究竟如何在宗教层面上完成这种统一还远不明朗。而已经明朗的一点则是,实现这种统一的责任亦正在变成他自己的责任。不同宗教社团的人们将不得不携手合作以共同地、有意识地建构起不同宗教社团的人们能够共同赞成的而且也是他们能够共同参与其中的那种类型的世界。”[9]391又如保罗·尼特(Paul Knitter)说:“和平是一种宗教的象征,因为若不面对宗教问题并就此对话,我们就无法思考和平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而在谋求和憧憬和平之时,我们所面向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同时也是一种不可能性:人类将以一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生活、思想和存在。我们的存在与思想若不经历一场革命或转变,就不会实现和平。然而,我们怎么才能带来这样一场革命呢?这场革命必须什么条件呢?这些都是宗教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以一种新的规划将所有的宗教联合起来了,这就是共同回应和平的象征,并使之实现。”[10]不管怎样,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分析社会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时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现实生活的各大宗教也正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建构一个和平的世界,突出表现在对于某些具体目标的格外关注,比如废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止军事干预、缓解贫富分化、取消政治压迫以及对环境的无休止破坏等等。这样的过程无疑曲折漫长且充满艰辛,但并非不能到达胜利的终点。“最真实的宗教想象力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能够通过绝对的信仰部分地实现。宗教所相信的真实的东西并非是完全真实的东西,而是应当真实的东西;如果对宗教的真理坚信不疑的话,就能够去实现它。”[11]就此而言,宗教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建构和平的积极力量。
二、宗教促成和平的可能性
总体上看,宗教自现代以来一直都是被各门社会科学当作一种边缘现象来讲述的,对宗教的拒斥似乎就刻写在一些学科或理论的基因密码之中。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宗教难以继续主导人类生活,但它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之间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宗教认同冲突的存在状态之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12]正是在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交融嬗变中,宗教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和文化风貌,影响并改变了所处社会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有意识地强调“地球村”里的各大宗教传统,既能促进共同体的形成,也会激化矛盾,引起纷争;既能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诱发不同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并为某些人群的暴力行为提供辩护。就像威廉·施韦克(William Schweiker)所论述的那样,“宗教是这个星球上具有含混性的力量,它们培育彼此关爱的社群,但也在地球上的各民族之间培育暴力与仇恨。宗教以音乐、艺术、文学以及那种深化和回应了属灵的渴望的指导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们也是压制、无知和欺骗性的力量”[13]11。宗教关注的、谈论的、设想的均与人类的救赎问题有关,但却往往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给予实际的支持。尤其是“20世纪出现的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融合主义这两场危机,给许多民族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个新的宗教特征,让这些暴力斗争获得了有力的理由。多元文化融合主义促使一种宗教信仰中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冲突模式,这些冲突相互刺激,久而久之不断加剧”[14]。考虑到现代武器的毁灭能力,人们愈发感受到和平共处的紧迫性,而宗教究竟在鼓吹暴力还是赞同和平、制造对立还是增进和谐,对人类整体的生存前景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在全球化时代,足以削弱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教可信度的因素之一是关于宗教团体相互之间的对抗和敌意方面的负面消息。综观当今世界,多元信仰传统彼此遭遇、相互关联已是普遍现象。有鉴于此,人类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的发展,创造性、建设性地运用宗教资源去维护和平。不管怎样,宗教的根本价值在于和平,各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个体心灵的平和与社会环境的和平。“几乎所有宗教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它们的关切是要给人类甚至整个宇宙带来和平。”[15]在许多宗教传统中,都具有非常明确的和平观念,甚至有个别的宗教将和平提升到其教义和实践的核心位置。许多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促进和平的建设性作用,比如资助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项目等。真正的宗教从来不主张运用暴力手段解决矛盾和分歧,并致力于通过对话实现相互的理解,将暴力文化转化为和平与正义的文化,构成当今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证明,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人类文明的各宗教传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了辉煌的精神景观,突破语言、阶级、民族和国家局限的沟通交流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者”的恐惧,而且这种情绪也很容易转变为敌对与紧张,甚至演化成争斗和冲突,以宗教为名的战争充斥着人类历史,各主要文明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对比较少见。然而,如果抛开表面现象,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就不难发现,超越对立、建立联系、实现互动,向来都是不容忽视的大趋势。尤其是在文化多样性深刻发展的当今世界,人类必须学会伙伴式的和平共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与技术方面的“一体化”联合已经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政治方面的相应变革也处在积极而持续的考虑与争论之中。然而,“人类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问题则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关注,在这方面的进展也是乏善可陈;尽管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有可能被证明是极为关键的,是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所在”[9]9。除非人们能够跨越信仰的界限实现相互理解与彼此认同,除非人类真正创立起使各种信仰都能够在其中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世界,否则,全球社会的未来前景就不会一片光明。在这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历史上几乎“每一个伟大民族和宗教传统都会遇到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信念共同体。它们经常能从这种相遇中获得巨大活力。通过学习他者,某一既有传统可以大大开拓视野。例如,基督教神学便受惠于希腊哲学,伊斯兰教思想也曾经从波斯文学中获得启示”[16]。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培育一种令人憧憬的和平文化的过程中,宗教间的对话是文明对话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宗教间的和谐具有某种示范意义和先导作用。每当人类社会在某个问题上因循守旧而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时,宗教总能起到一种难以替代的作用,开辟“柳暗花明”的新局面。鉴于世界宗教产生的重大影响,完全可以将其视作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革新力量。“世界宗教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世界宗教毫无疑问构成了前现代时期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而且无论何时,的确都是如此。”[17]当前,所有宗教,包括那些正在出现的新宗教,都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那就是确认一个旨在促进共同理想与目标的行动统一体。可喜的是,“全球化”已经实质性地提高了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密度,这表明人类朝和平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宗教守护和平的途径
近代以来,随着“政教分离”原则的普遍奠立,社会“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各种宗教的和平共处,却也引发了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缺位和新形态的宗教冲突。“9·11”之后,许多社会理论学者都热衷于探究“公共领域”中的宗教问题,哈贝马斯(Habermas)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鉴于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态势,他提出了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构想。哈贝马斯认为:宗教在国家内部公共领域中日益赢得了重要性。“宗教团体在世俗政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诠释共同体的角色。宗教团体可以就有关论题发表言论来对公众意见及意愿的形成产生影响——无论这些言论是令人信服的还是有失体面的。我们世界观的多元化社会之所以要为此类干预建立一套灵敏的反馈机制,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缺乏政治规范的价值冲突中越来越多地处于分裂状态了。”[18]事实上,现代社会中那些通常相互冲突的宗教形式正通过诸如宗教自由和道德呼吁运动向公共领域渗透,甚至在个人和群体层面,这种现象也具有一定的关联意义,构成当代灵性信仰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行为与私人活动——两种范围之间的宽广领域。公共领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促进人与人之间思想观念的交流,形成一定的共识,并且使不合理的现象尽快暴露出来,以便推进社会改革。在公共领域内,人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合理明智的价值观念与健康优质的生活方式得以推广。将宗教引入公共领域,能够促成不同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加强信任,从而发挥宗教对社会和人生的积极作用。应该看到,通常情况下,宗教仅是公共领域内诸多社会力量中的一种,其独特作用在于提出意义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被其他社会力量所轻视甚至于忽略。“在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公共领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始终在场,始终发挥着作用,并没有退到幕后,销声匿迹。”[19]因此,现代社会中宗教的特殊贡献就在于通过进入公共空间,影响某些公共问题的探讨,使日益层级化的社会仍存在某种机制以反映普通民众的意见。
实际上,现实的社会中并不缺少关于和平的美好设想,每个人都希望赢得他人的尊重,并愿意通过有效的协调实现行动一致。因此,确立一种整个人类层次上的道德规范以消解那些被看得很重的只忠于和利于某个群体的行为规范,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使其深入人心,就显得尤其重要。毕竟,只有最高水平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素质才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当然,也必须承认,价值观念越一般、越抽象,也就越难唤起人们内心强烈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芸芸众生大多忙于生计,又成长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因此往往无暇顾及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一己愿望以及家族的生计与大范围的甚至全球性的问题之间即便有什么联系,也是不容易理解的,这种认识使他变为志存高远之人相对比较困难。“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利益,另一方面是地球文明和全人类文化的普遍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能够制作纽带连结这两者的,能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的,大概也只有宗教。”[20]而近些年来,各大宗教在推动诸如“全球伦理”和“文明对话”等方面的贡献和成绩可谓有目共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坚定的和平力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宗教所具有的和平属性能够将人们从公共领域中各种各样的恶势力中解放出来,并带给人们效仿宇宙无上威力的神圣渴求,有助于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格和倾向于和谐的品性。
需要关注的是,全球化条件下,在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过程中,以宗教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增长。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宗教”这个范畴本身就与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密不可分。虽然各大宗教均有程度不同的排他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已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灾难,但是,通过全然明确的提示,宗教仍然可以在全球化时代承担起维护和平的使命。历史的证据显示各大宗教传统必须对以信仰名义实施的暴力保持警惕性,制度性宗教的上层人士和普通成员必须不断努力将正义、宽恕和同情等宗教价值应用到实践之中。“宗教资源并非只是欲盖弥彰的虔诚愿望,它们能激发并储藏关于如何尽力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实在观中生活下去的思想。当然,诸宗教或者说所有宗教都还在为仇恨和无知火上加油,它们也是我们正面对的全球性天旋地转和混乱的一部分。人们必须缓和这些资源中潜在的恶意,也要消除其系统性的曲解。”[13]2这样一来,人类需要以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将宗教资源恰当融入社会力量的构成之中,由此克服当前世界和平之短促和脆弱。为此,必须深入探讨“政教分离”条件下以宗教建构和平的适当方式。可以预见,虽然当下各个层面的政治论争依然会把宗教和信仰看作必然是排外主义的,但是神学的趋向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会集中在包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上。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上,排外主义的存在固然是无法忽视的,然而宗教思想确实也反映出了相互承认、理解和宽容的趋向。当然,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尤其应当注意规定自己的活动范围,仅在这个范围之内对人类的观念和精神层面施加影响,一旦超出则要小心谨慎,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或争议。况且,宗教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所遵奉的信仰的性质、所采取的外在形式以及为信众规定的义务,而这些恰恰都是宗教与和平之关联性研究必然要涉及的论题。
[1] [美]英格. 宗教的科学研究[M]. 金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9.
[2] [英]约翰·希克. 从宗教哲学到宗教对话[M]. 王志成, 柯进华, 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51.
[3]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神的历史[M]. 蔡昌雄,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7: 317
[4] [英]阿伦·亨特. 和平与宗教[J]. 卢彦名, 译. 学海, 2004, (3): 33-41.
[5] [英]怀特海. 宗教的形成[M]. 周邦宪,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2.
[6] [德]迪特·森格哈斯. 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M]. 张文武,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6-7.
[7] [英]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M]. 朱生豪, 译.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23.
[8] [英]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96-97.
[9] [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 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 董江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0] Knitter P. One Earth Many Religions: Multifaith Dialogue & Global Responsibility [M].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6: 67.
[11] [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 蒋庆, 王守昌, 阮炜, 等.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65.
[12] [日]星野昭吉. 全球社会和平学[M]. 梁云祥, 梁海峰, 刘小林,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74.
[13] [美]威廉·席崴克. 追寻生命的整全: 多元世界时代的神学伦理学与全球化动力[M]. 孙尚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4] [美]莱斯特·库尔茨. 地球村里的诸神: 宗教社会学入门[M]. 薛品, 王旭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41.
[15] [西]雷蒙·潘尼卡. 文化裁军: 通向和平之路[M]. 思竹, 王志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28.
[16] [美]杜维明. 全球化与多样性[C] // 哈佛燕京学社.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86.
[17] [英]戴维·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 戴维·戈尔德布莱特, 等. 全球大变革: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杨雪冬, 周红云, 陈家刚,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65.
[18] [德]哈贝马斯. 世俗化的辩证法[C]. 李琲琲, 译 // 张庆熊, 林子淳. 哈贝马斯的宗教观及其反思.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53.
[19] 铁省林. 哈贝马斯宗教哲学思想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76.
[20] [日]池田大作, [英]威尔逊. 社会与宗教[M]. 梁鸿飞, 王健,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246.
Religion Becoming a Positive Power of Constructing Peace——The Possibility and Way
ZHANG Qiang
(Department of Marxist Theory,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China 210003)
Religion always has a high level of concern for the world peace, represents humankind's great wishes through specific value systems, forc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creates essential conditions for the world peace. In our modern society, religion cannot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affairs. However, instead of being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public affairs, it may be blended with all kinds of social phenomena. Therefore, religion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globaliz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world peace.
Globalization; Religion; Peace
B911
A
1674-3555(2014)04-009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4.01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3-09-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13GJ003-076)
张强(1979-),男,山西太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宗教学理论,宗教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