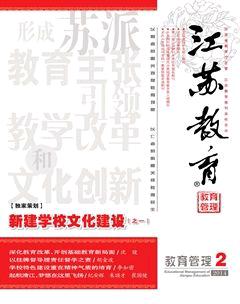每一段经历都是重要的

张菊荣,男,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校长、书记,华东师范大学教研员研修中心特聘讲座教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学校管理》编委,苏州市学科带头人(教育科研类),苏州市吴江区名校长。在省级以上教育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散文集两种《随想漫录》《随意人生》,与人共著教育文集《行走新教育》,合编《观课议课问题诊断与解决》(17册)等。办校治学,他坚信文化的价值,坚信坚持的力量,坚信专业的意义,坚信人的向善本性。他以“让每一位师生拥有成长的感觉”为使命,与一批年轻老师一起,成功地探索了新建学校的文化之路。
很多日子,很多经历,身在其中的时候,并不明白,过去了之后,才会发现其中的价值,才会知道每一段经历都是重要的。
一
1986年8月,我从新苏师范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被分配到“乡下”。一所村小,两位教师,87名学生,4个年级,2个班级。我上二、四年级复式班。
教室是泥地面,条件确乎艰苦了些。不过,回想起来,却总是觉得很有意思。没有围墙,边上是一条水泥的自行车道,横穿过去,就是一片田野,田野边上是一片浩荡的湖。春天,湖岸边开满了野蔷薇,白白的一大片。村校校长老张吹哨子告知上、下课的时间,他会跟我打个招呼:“小张老师,要不要上课?”哨子一吹,我们就上课。放学前,我们常常会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到湖边去呼吸蔷薇的馨香,去观赏很远很远的对岸湖面上塔的美丽倒影——现在最晴朗的天气都看不到这样的倒影了。我灵魂深处对于美丽教育的浪漫情怀,也许与我入职之初诗情画意的环境相关。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但我一直会怀念这段时间。在那里,我组织孩子们调查村里楼房的建造时间与背景,后来想想,这有点“综合实践活动”的味道;在那里,我发起师范同学油印“教育刊物”《青春教苑》,后来想想,这是我最初的科研启蒙;孩子们学不会一种类型数学题,我就跑到在乡中心小学工作的同学那里去交流,问她班里的情况,问她是怎样教的,后来想想,这就是我最初的教研活动……后来我喜欢琢磨真实的教育问题,喜欢办刊物以传播思想,喜欢做有创造性的事情而不喜欢重复自己,这些,都与最初的经历有关!
“老张老师”是一位极其朴素又极其认真的人,我后来也常常想,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如果我遇上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村校校长,我会不会是现在的我?
二
两年之后,我到了乡中心小学。我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那里。我不太习惯于“听话”地“线性思考”,总是有太多的想法,不愿意“大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当然,我也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我不是这种刻意求“新”的人,但可能比较“求真”。
做班主任,做语文老师,我都跟学生们相处得很好。那时候,我大概是点子特别多,班级里做的那些事儿,也总喜欢跟别人有些不一样。虽然具体做过哪些事儿,我还真的全忘了。后来做教研组长,我也和别人不一样。我的前任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我非常尊重他,他也非常爱护我,所以虽然我跟他做得不一样,但他一点儿也不生气。我们的教研活动,从来就是“轮上课”的。我“上任”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要研究一些主题,做得深入一些,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地轮着上课没有意思,必须取消“轮上制”。于是,我组织教研活动,要求大家细细讨论,积极发言。但是,这样一来,活动时间就拉长了。而学校常常会“开会”,挤占了教研活动的时间,我就去跟校长提意见,说这个不能挤占,讨论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效果一点儿也不好。幸运的是,这些“尖锐”的意见,得到了校长的表扬。之后,学校很少占用教研活动的时间了。现在年龄渐增,我的处事策略自是成熟得多了,但我那爱“做真研究”的爱好、平淡而不甘平庸的追求,丝毫没有改变,已然刻入了骨髓。
在那里,我很快成长起来。随着业务上的进步,各种小荣誉也多了起来,开始担任学校的中层干部,担任学校的副校长。当然,我依旧不喜欢重复,不喜欢平庸,总是喜欢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出彩”一点。现在想来,这些“出彩”多半来自于外界的肯定,还没有使自己的内心真正强大起来。更遗憾的是,很多的“出彩”只是花在了怎样让学校在考核中排在前面一些。
我在那里一切都顺顺当当,没有压力,也没有挑战。业余,我读些闲书——哲学、散文、小说、文史,只要不深奥的,都读。当然,也读些教育书——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但读得不深。我喜欢写作,写些“轻便”的随笔。离开那里前,我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算是对这种“优哉”生活的总结。我甚至不愿走出这个小镇,觉得这种日子很惬意,也很自得。如果2002年我没有终于走出这个小镇的话,也许,至今我还在像井底之蛙一样快乐地生活着。
三
人也许只有在回忆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我在回首这段小镇生活的时候,明显地发现那时的生活的确类似于“井蛙”。2002年暑假,我走了出来,来到吴江市教科室。说实话,我来到教科室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人才的,但是很快,我就像跳出井口的青蛙一样,发现原来天有这么大!我那一点点写小散文的功夫,我那一篇篇毫无深度的“论文”,能算什么啊?
吴江的教育科研在全省是有地位的,我坐在那里,面对的几乎是“大山”。我所能够选择的,只有努力!幸运的是,在2002年的暑假,我结识了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老师,并一时相交甚密,成为“新教育实验”早期的热情推动者。“新教育实验”给我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我因此看到了一片更广阔的世界。尽管后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所转移,但“新教育实验”带给我的教育情怀,也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一直到今天,我们汾湖实小把“恒”作为学校的校训,把“土书”作为学校文化的奠基石,还是带有浓郁的“新教育”色彩的。
但是日子很快也变得平凡起来。如果没有2006年10月份开始深度卷入的“课堂观察研究”,也许我也会像全国很多科研部门的专家一样,坐在办公室编辑杂志,蜻蜓点水般地访问学校,提供不痛不痒的咨询,发表不痛不痒的文章。但深度参与课堂观察研究,改变了我。2006年10月,我与一线老师走入课堂,用沈正元副局长的话来说,“吴江的课堂观察揭开了帷幕”。此后的两年间,白天,我走进学校,与老师们一起观察课堂,研究课堂,每有所得,辄欣欣然;晚间,在书桌前,记述我能够记得的每一点故事,梳理我的思考。我起码留下了30万字的关于课堂观察的笔记,在《中国教育学刊》发表了《课堂观察的基本理念与初步理念》《基于教师主体的课堂观察的有效开展》,在《江苏教育》《江苏教育研究》等刊物井喷式地发表了关于课堂观察的实践思考。吴江的课堂观察在一定的区域内颇具影响,我也算立下汗马功劳。
白天,我在学校现场;夜晚,我用文字的方式,对这个现场进行省思。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带我离开教科室,带我来到城区的一所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带我来到今天我所任职的汾湖实验小学。
市教科室的6年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我可以走进那么多的学校,与那么多的学校结成关系;我可以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的高人,与那么多有学问、有精神追求的高人交往;我可以那么静心地阅读着各种教育书籍,那么静心地写着自己喜欢的文字。这是多么难得的6年啊。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也许几年之后,我会变成一个地道的“学人”。但在2008年的暑假,我又换工作了。
四
当时,我想不到那个我并不情愿去的地方,会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驿站;也想不到这短暂的一年,会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经历。如果没有这一年在那里的探索,也许我也未必有勇气走进汾湖实验小学,与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开创一所学校的历史。
我来到的是城区的一所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那是一所发展水平相对薄弱的学校。虽然我并不情愿去那里,但一去,马上就与校长并肩奋斗。
我知道,我去那里是担任书记,分管的是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一些老教师,非常努力,朴实无华,默默耕耘;我也看到一些老教师,传播着并不十分积极的言论。我能够理解,当一个人感觉发展的黄金期行将过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组织党员开会,和大家交流:“我们不要求每个老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能够走多远,但你们决不能劝别人跟着消极!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回顾一事无成的一生时会说‘幸亏那时候,某某某,劝我消极。没有人会感谢一个曾经劝他消极的人。我的要求很低,哪怕我自己不算努力,但决不劝说别人消极!”现在,我离开那里已经五年多了,我知道他们中间至今还有人与我的这个观点共鸣着。
学校发展需要建立正能量的场。我们确定新的一年为“教师发展年”。我们组建了“小团队”,结果发现这个“小团队”对学校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个“教育沙龙”后来让没有报名参加的教师“后悔当初没有报名”。我们为每一个青年教师建立“小课题”,结果发现,“小课题”解决了大问题,老师们开始走上了研究之路。我一个一个地与老师商量选题,又一个一个地帮助他们提炼总结。我们主张走“小步子”,结果发现,我们跨出的每一个小步子,对于一所学校的发展很可能就是“大步子”!
我的教育信仰,就是在那里明晰并坚定起来的。我的两个“坚信”后来慢慢地演变为汾湖实验小学的“学校信仰”:坚信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欲望,坚信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标识。因为在这里,老师们用无数的事实,告诉了我!
作为一个“事业人”,工作岗位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态度”。你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工作,你就会收获怎样的回报。在那里所经历的困难,在那里所获得的体验,虽然只是一年时间,却胜过很多很多个年头。面对困难,该怎么看,该怎么做,困难中蕴藏着怎样的机遇,这一年,我收获良多。
五
2009年暑假,我来到了汾湖实验小学。每次离开,我总是犹豫的,更何况,从城区到这里,来回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汾湖的领导几次三番地邀我前去,我感动了!自己何德何能,让人如此看重?他们如此看重我,他们又为了什么?
这是值得骄傲的四年,我们创造了太多的故事。也许,这些故事,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对于我们每一个创造故事的人来说,却又是那么的重要,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至少对我来说,已经沉浸在教育思考与教育实践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了!
第一个开学,我与老师们约定:“我们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每一个人,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出一本书!在这本书里,记下我们的成长。至少,等到我们做爷爷奶奶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着它告诉孩子们:我们曾经这样努力过!”想不到这个相约,竟成为了我们的“土书文化”。到今天,51位老师,已经创造了令人惊叹的204本书!这些,是我们图书馆的无价珍品,那是用生命编织的风景啊!更令人自豪的是,土书故事,没有终止时。
我实在没有办法在很短的篇幅内表述这四年的巨大收获,老师们的成长故事常常让我热泪盈眶,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也常常让我怦然心动,学校文化的魅力更是常常让我惊叹不已。四年里,年轻的老师们竟然能够在《中小学管理》《江苏教育》集束性地推出专题成果,而这些成果,便是在课堂上“做出来的”!四年里,我们埋头努力,几乎“拒绝”媒体报道;四年后,《教师博览》(2013年第9期)推出深度报道《过一种饶有兴致的专业生活》,《江苏教育》选择这里举办“苏派校长高层论坛”,主题便是“新建学校的文化建设”,并将发表学校文化发展的完整案例《站在学校文化的源头上》……当然,也必须深深感谢那些关心与帮助我们的领导与专家,特别是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如果没有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三年的悉心付出,我们不知要多走多少弯路!
我发现在这里,会有永不疲倦的精力,源源不断的思想,我甚至感觉自己的“想法”几乎到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境地。我知道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时期,而这一切的到来并不突然,人生每个阶段所经历的,似乎都是为了今天而做的准备。
一路走来,不经意中,已经走出了一片片风景,只是走出这风景的人并不一定知道。入职期初的生活带给我教育的浪漫主义色彩,乡镇中心小学十余年的广泛涉猎与优哉游哉的生活带给我别样的视野,“新教育实验”让我拥有了笃厚的教育情怀,“课堂观察”让我完成了科研入门;“书记生活”让我学会了如何认识困难,如何挑战困难,然后才有了2009年至今汾小四年多来我与同事们的共同创造!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重要的,都是可贵的,真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