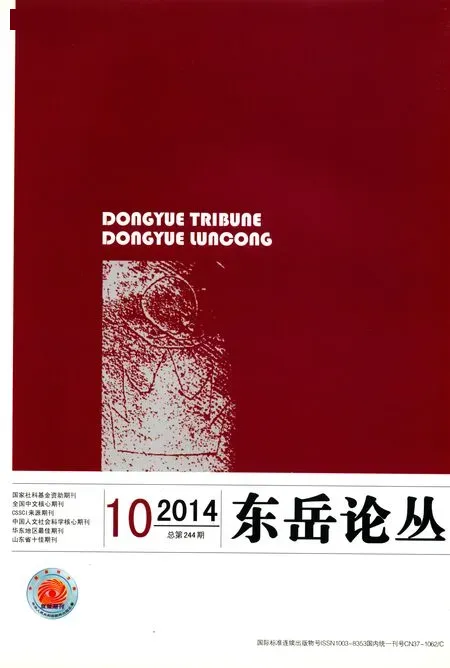家庭变革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吗?——对布达佩斯学派家庭变革理论的反思
颜 岩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上海20043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3)
布达佩斯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在布达佩斯围绕卢卡奇形成的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核心成员有赫勒(Agnes Heller)、费赫尔(Ferenc Feher)、马尔库什(Georg Markus)和瓦伊达(Mihaly Vajda)。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一危急时刻,布达佩斯学派举起了“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从家庭变革出发探讨了社会主义人道化的路径,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家庭变革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辨析布达佩斯学派家庭变革理论的得与失,不仅有利于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国内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有助于保障我国民主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全面构建新型社区提供有益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布达佩斯学派成立之初卢卡奇便拟定了“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但对如何“复兴”他也心存困惑。如果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卢卡奇得出了阶级意识先于阶级革命的结论,那么四十年后,面对阶级意识迟迟未现的尴尬局面,他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关于阶级革命的理论预设,并渐渐意识到“阶级”不能代替“类”,要实现类本质的复归,就必须摆脱拜物教的束缚,走向某种终极的东西——艺术。通过提出一种审美救赎论,卢卡奇试图在个体与类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寄希望于个体通过享受和理解艺术品擢升到“类本质”的水平。该转变标志着卢卡奇的理论重心由宏观的阶级革命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变革。照此思路往下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一场政治革命虽然可以建立一个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却不足以改变人自身,尤其当新社会的主体(新人)缺位时,人道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们姑且假定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随之而来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蜕变为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语),新人又何以能够产生?无奈之下,卢卡奇诉诸于教育、启蒙和艺术品的净化作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教育者一定是受教育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又何来“纯净”的教育者呢?既然整个社会已经被物化意识所浸染,又何来知识分子的启蒙呢?今天,仿制品大行其道,赝品与真品实现了“内爆”(鲍德里亚语),还能有真正的艺术品存在吗?即便有,还有欣赏它们的人存在吗?卢卡奇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走出悖论,布达佩斯学派将目光转向家庭,主张通过变革资产阶级旧家庭,建立共产主义新家庭,实现人的丰富个性,塑造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其理论逻辑是:“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①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这就喻示着,社会变革将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人的态度的改变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关键。于是,如何在家庭内部完成个体的再生产,令家庭沿着人道主义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得以改变就成为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理论关切。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描绘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细节,他们深知,刻画得越具体就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布达佩斯学派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指向,即消除私有财产、异化和集体权威。因此,革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用新的社会形式取代现存的社会形式,而是更充分地实现人类个体和社会关系。消除:(1)人的关系变为物的关系的拜物教;(2)人从属于他人;(3)人与他人的关系仅仅表现为手段。”②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7.p.43.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把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把它看成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这一过程的前提条件。”③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7.p.43.这就预示着,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消除了异化,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沿着这一人道主义的思路往下走,布达佩斯学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总体的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一种真正的人类关系的实现吗?单凭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能够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吗?一方面,按照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的分析思路,他们更愿意相信只有日常生活朝着人道化的方向改变了,社会变革才能发生,共产主义才会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卢卡奇的审美救赎论,主张寻找一个中介或切入点,这就是家庭。
二、资产阶级家庭批判:社会革命的起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绘了三种婚姻形式: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制。在他看来,私有财产的废除以及国家的消亡同资产阶级专偶制家庭的瓦解紧密相连。一方面,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专偶制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标志,由于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第75页,第77页,第95页。,确立财产继承人的身份,为财产的继承奠定基础,因此这种婚姻关系要比以往所有的婚姻关系更加牢固。另一方面,专偶制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第75页,第77页,第95页。专偶制下决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约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第75页,第77页,第95页。不难想象,专偶制下定会出现如下情形:男子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则会出于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专偶制还是一种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妇女家务奴隶制之上的家庭形式,这就使得丈夫占据了一种特权统治地位。在谈到未来的家庭形式时,恩格斯指出,专偶制并不会消亡,而是会真正的实现,但“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第75页,第77页,第95页。这就表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废除私有制之后,资产阶级的专偶制家庭将自行瓦解,共产主义的家庭形式(真正的专偶制)将自行出现,“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布达佩斯学派对这种乐观的姿态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培养出拒斥私有制的个体,资产阶级的专偶制家庭是不可能瓦解的。因此,恩格斯的逻辑必须被颠倒过来,即首先从家庭出发,弱化和废除资产阶级专偶制的家庭结构,建立共产主义特征的家庭模式,然后以此为基础再生产出具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新人,由他们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革命从家庭出发这一观点是否合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马克思那个时代而言,工人每天基本上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他们“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在这种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人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管理家庭事务,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大街上和工厂里长大。因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较少涉及家庭变革,这是有情可原的。后来,马克思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转而研究人类学和家庭问题,恩格斯更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足以表明,家庭始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产阶级家庭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具体说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具有四个特征:(1)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已经终结。离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被普遍接受,尤其在瑞典和丹麦,人们认为婚姻制度应该在法律上被废止。(2)在法律上,男性在婚姻中的权威几乎被彻底清除,事实上的确也削弱了,这与“妇女解放”、妇女工作范围的扩展、妇女政治平等的实现等有关。(3)与性有关的道德规范发生了转变,这既改善了妇女的境况,也令离婚率不断攀升。(4)大家庭在事实上正逐渐被核心家庭取代③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0.。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的离婚率确有走高趋势,人们追求自由性爱的意识也越来越强,闪婚闪离、非婚同居、独身丁克等现象已不再罕见。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勃兴,妇女越来越意识到家庭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争取平等地位的同时,她们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生产力水平日渐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三口之家逐渐成为基本的家庭结构模式,独生子女性格的培养以及老人晚年孤独等问题也随之出现。这表明,家庭问题决不可小觑。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布达佩斯学派描述的这些特征并不具有典型性,尤其对我国而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要素交错共生,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家庭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前文曾提到,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家庭能否塑造出具有共产主义潜质的个体,将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按照他们的判断,目前实现家庭变革的形势并不乐观,这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仍然是压迫的、权威主义的和剥削的,其基本功能仍是确保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一种迎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性格机制。要实现资产阶级家庭的变革,首先必须对这种家庭关系进行颠覆性的批判,这就需要注意两点:首先,资产阶级家庭并非共同体(community),而是独裁主义的,这就使得它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尤其在告知他们如何在共同体中生活和行动时明显乏力。即使在一个妇女享有平等权力、家庭民主气氛浓厚的家庭,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观。因为孩子仍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一切事务仍然受到父母的干涉,最重要的是,由孩子自由结合且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是不存在的。按照福柯的理论,规训与惩罚来自一种权力的压迫,在现代家庭中,年龄的大小通常会形成一个自然的等级序列,年长的孩子相对于年幼的孩子拥有一种特权,压迫就在这里滋生出来。试想,在这样一种等级森严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成年后必然会具有一种权力欲和压迫欲,这对于塑造共产主义的新人来说极为不利。其次,资产阶级家庭是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必然会产生一种自私的自我保护本能,为争夺物质财产而出现内部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还会蔓延到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之间。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有意拒斥私有观念的家庭里,这种境况也不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因为无论父母心胸多么宽广,他们也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把所有的玩具都拱手送人,而是一定会强调这些玩具是“你的”。在这个意义上,赫勒认为“正是现代家庭再生产出所有权意识和自然共同体重要的‘我们意识’”①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
布达佩斯学派关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批判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确与马克思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恩格斯曾对无产阶级的家庭寄予厚望,认为“无产者的家庭……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86页。布达佩斯学派认为,这一论断忽视了现代社会无产阶级家庭结构资产阶级化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也不是说无产阶级开始认同资产阶级,而是表明,在无产阶级的家庭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特征。试问,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家庭,有可能培养出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体(共产主义的新人)吗?笔者认为,正是时代的局限性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详尽阐明家庭变革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而这一理论“缺陷”又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被进一步放大,后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继续对家庭变革保持缄默,“将总体社会进程和个体心理特征的塑造看成是直接关联的,并坚信前者的转变将自动引发后者的变革。”③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与这种理论路向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反复强调,“‘新人’的塑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其目标也不是社会结构转变的机械应答,而是瞄准一种与社会生产单位的民主转变相关的心理特征的培育。”④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这就开启了一条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道化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个问题上,布达佩斯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是一致的。
总之,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物质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阐释并不足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他们坚信:(1)社会越发达,个体进入生产领域的阶段就越滞后,年轻人就越容易以一种固定的心理道德特征开始他们的工作生涯。(2)社会越发达,人们用于生产的时间就越少,减少工作时间成为社会的目标,单纯在生产领域形成全面的关系是不可想象的。(3)即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和技术,从个体的立场看,他们却不能决定生产⑤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一言以蔽之,只要人们的心理特征没有发生质的转变,任何政治民主和社会变革都是无效的,而任何心理特征的转变必须通过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激进变革才能实现。
三、公社: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形式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全新的家庭形式,其基本特征有四个方面:(1)必须是一个民主结构的共同体,个体早期可以在里面习得民主倾向。(2)必须确保全面的人际关系,包括成人与孩子的关系。(3)必须确保个体的发展和实现,其基本前提是,甚至在孩童时代,人际关系也可以自由反复地选择。(4)必须消除专偶制以及专偶制废除后所引发的冲突⑥Andras Hegedüs[et al.]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这种新的家庭形式就是“公社”(commune)。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公社作为资产阶级家庭的替代者,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政治)细胞,而是集体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因此,整体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独立于公社的。公社与共产主义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说来,一方面,“由于公社仅仅是作为一个家庭发挥作用,它的实现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状况,独立于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⑦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具有共产主义需要的人,公社将有助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转变。”⑧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在谈到社会转变(共产主义革命)和家庭变革(建立公社)的先后关系时,布达佩斯学派强调了后者的优先性:“这绝不意味着公社的组织必须‘等到’共产主义转变开始后才可以出现,恰恰相反,这两个进程必须同时启动,并且如果形势喜人,家庭向公社的转变可能在整个进程实现之前就会到来。”⑨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15.pp.16-17.p.18.p.18.pp.18-19.p.20.p.20.p.20.更进一步,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公社的运行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工作是强制性的,公社中所有健全的成员必须工作,参与社会劳动分工。(2)任何人不能免除公社的集体任务。(3)公社中的每位成员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孩子们的共同体,无论该共同体中是否有“自己的”孩子。(4)公社不能干涉成员的生活、工作、自由时间和人际交往,公社范围也不能太大,要保证内部能够实行直接民主。
布达佩斯学派对公社寄予了厚望,他们坚信现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形式无法让人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公社却可以彻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我们知道,大家庭要比核心家庭运行起来更经济,因为人们可以同时照看多个孩子,年长的孩子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同理,公社要比大家庭更经济,因为在孩子组成的共同体中,他们可以互相照顾,只需少量成人在旁边指导即可。当然,人们也可以在公社中普遍使用大机器,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的传统家庭中,人们在空闲时间只能围坐在电视机旁,或徜徉在商品世界中,那么在公社中人们则可以自由发展自己和孩子们的个性,从事一些更积极、更有文化内涵的活动。
公社最明显的优势体现在对孩子的护理上。在公社中,孩子并不是被集体带大的,而是属于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并不是说,公社中成人和孩子的关系不可能是亲密的、广泛的,而是说他们的关系决不能是独裁的。孩子在共同体中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可以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在公社中,传统的家庭亲情关系被打破,父母对子女固定的感情偏爱被彻底消除。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将会倾向于选择更具魅力、与他们内在相关的成人作为“榜样”,成人也会自由地选择中意的孩子。这是一个没有强制和胁迫的双向选择过程,如果该过程顺利可行,那么公社成员的个性将沿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私有制也将被扬弃,“我的”和“你的”的二分将不复存在,一种真正的和谐社会将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理特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将会支持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绝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境况:即认为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是正常的。”①Andras Hegedüs[et al.],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6,p.24.
四、简 评
论述至此,人们或许会顿生疑惑,既然布达佩斯学派描述的公社具有如此多的优点,是否表明这是一条社会革命现实可行的道路呢?换言之,是否意味着家庭变革的星星之火足以能够燎燃共产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呢?做出这样的论断还为时过早。首先,公社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形式的论述存在根本性差别。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认为私有制的废除是未来家庭形式生成的基本前提。布达佩斯学派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也可以让家庭成为非经济单位,让私人家务成为公共事业,让孩子的抚养成为公共的事务,让一切孩子平等受到关爱,不受任何歧视。这明显忽视了资本逻辑对家庭的渗透和殖民!人们不禁会问,公社运行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如何保证公社成员在分配财产时做到公平公正?如何保证公社中拥有权威的人能够避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干扰,做到大公无私?当布达佩斯学派强调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公社时,如何保证公社成员一定是道德高尚的好人?在一个由道德水平低下的坏人组成的公社中,如何保证孩子健康成长呢?当人们自由选择一个公社过自己喜爱的生活时,如何保证人们不会变心,进而始终对自己的配偶保持忠诚呢?当孩子可以自由选择公社中的成人作为“家长”时,如何保证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呢?这会不会危及原有的伦理亲情关系?其次,布达佩斯学派所谓的“公社”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特征,并且在描述时充满矛盾。如其所述,公社中所有健全的成员必须工作和参与社会劳动分工,因此工作是强制性的。这一点颇让人费解。人们在公社中从事着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劳动,又如何保证个性的全面实现呢?如果个体的个性和能力无法全面发展,又怎么能够说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工厂还是家庭,人们的工作都应该是自愿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驾驭这种力量。”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第557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第557页。可见,强制劳动(分工)与私有制是紧密相连的,任何试图保留前者除去后者的做法均不可能实现。最后,在对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形式的理解上,布达佩斯学派更多地停留于一种理想(理论)层面,即将之视为一种应当确立的状况,他们恰恰忽略了,这种状况是需要现实的运动才能实现和改变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仍然在解释世界,而没有改变世界。
当然,提出问题通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布达佩斯学派对未来家庭形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与那些强调宏大叙事、革命的必然性和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相比,布达佩斯学派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和家庭变革,强调社会运动的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无疑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革命理论,尤其对我们反思宏观政治革命与微观日常生活变革的辩证关系,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偏宏观、轻微观的社会历史表述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实践层面看,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布达佩斯学派对未来家庭形式的诸多设想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拿来就用,而是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民情,在逐渐探索的基础上展开试点。例如,布达佩斯学派对家庭内部平等、自由、民主原则的强调,就对我国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形式,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形式进行了勾画,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他们对家庭变革作用的过分倚重陷入了乌托邦,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变成了误读,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