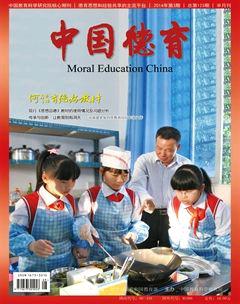民国德育教材言说论
摘 要 民国德育教材编写者凭借丰厚的语言修养使德育教材言说出语典雅,而赤诚的德育情怀又促使教材的言说呈现出清新晓畅特质。另外,无论是言说者角色的确定,还是言说者与倾听者关系的处理以及德育行为导引的方式,均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教材建设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 键 词 民国;德育教材;言说
作者简介 冯铁山,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教材是教育教学开展的凭借,也是教师、学生和作者、编者进行交流对话的媒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教材就是一种言说。民国教材先是语文教材忽然走红,然后修身、公民等德育教材也成为热捧之物。针对这种现象,倘若从言说方式的角度去审视其言说的性质、类型,进而探究其存在的意义,也许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生动的解答。
一、民国德育教材言说的特点
1. 言说者“我”的角色定位
民国德育教材分为修身与公民训练两个类型。修身科重在培养个人的私德,公民训练则是培养健全公民的基础。无论是私德的培养,还是公德的训练,为了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的兴趣,激发他们道德学习的主动性,民国先贤教材编写首先淡化了教材语言的训导者角色,打破了道德教材长期“无我”的状态,注重采用第一人称,模拟儿童的口吻,让教材的受众—学生成为主体,从而变道德说教为道德自省。比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世界书局中华印行“公民训练小册”之《模范公民》(第八册)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以“我”的视角审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每一课的导引语均采取“我看见新事物,要常常留心研究”“我发生了疑问,就想法去解决我要仔细地观察事物”“我使用公共器具,一定依照先后的次序”诸如此类的言说方式,这样“我”就成为了教材带动受教育者修身、健德、明理的发起者与导引者。教材涉及的德目、德行均听从“我”的召唤和推动,其实就是忠实于学生德性自觉的自然性与自觉性,增添了道德修养的无穷乐趣。
2. 言者听者“比德”的关系协调
教材的言说是德育信息的发出者,而读者则是言说者的倾听者。言者和听者是什么关系,自然也就反映在言说语言的运用上。自古以来,受伦理文化的制约,大凡德育教材,编写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为道德至高无上者,导致教材的“言者”与“听者”成为教与受教的主客体对立的关系,为了保证德育言说的权威性,典型的话语表达就变成“诗云子曰”。民国时期,言者的功能逐步向劝解、劝导等方面转化,言者与听者不是“上—下”对立的关系,也不是“下—上”的谄媚关系,而是“我—你”的对话关系。这就决定教材编写者需要利用一种恰当的言说手段或方法改变道德说教的言说方式。教材编写者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学寓言式的以物“比德”的言说方式,通过动物、植物以及其他人物类似的故事、现象以引起听者的心灵感应,从而达到自觉认同、理解直至实际践履的目的。比如“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一课借猫犬忠于职守的现象引导学生建立职业理想,涵养职业操守。文字诙谐活泼,德育修养的要点简洁明快。除此之外,言者还善于借助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口吻来言说道德规则。比如《会场规则》,编写者就以王生父亲的口吻讲述了小公民会的会场规则,如按时到会、不要打断别人发言,对于提案要少数服从多数等。这样更增添了言说的生活意味和普适价值。
3. 言说行为“图景”的生动描述
言说即做事,做事意在合乎道德规则。民国教材编写者善于展示生活的图景,让听者自然而然经受生活乃至生命的感动接受德育信息并自觉生发有意义的德育行为。比如,1912年由范源廉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修身教科书第三册就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种种生活图景。但就第一课而论,图景描述的是一位父亲右手拿收束的雨伞,左手拿着礼帽,左脚朝向家外,稍作停顿,右脚稍微抬起,侧身回头用关爱的眼神注视着妻儿。母亲携儿相送,母亲一手牵儿,一手微微上扬,口里念念叨叨,依依不舍。与图景相配合的言说词为“父远行,儿随母,出门送父”。贾丰臻用简要的笔触记载了当时教师教学的要点:“其一,父母长者外出时,须出大门送之;其二,帽子及携带物须注意。如忘记携带,则代为取之;其三,须述‘慢慢走‘早些归等相当之辞,而行敬礼。其四,送出门时,行普通之敬礼。”[1]
二、民国德育教材言说的性质
1. 德育是以“言说”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
德育教材是德育言说的载体,言说的优势就是德育的优势,言说的局限就是德育的局限。因此,德育教材的言说本质而言就是有效地处理言说者的角色定位、把握言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进而采取合乎德育规律性与目的性统一的方式,导引德育行为的言语交往活动。德育知识的言说主要表现为采取陈述句的方式,将善恶知识寓于故事与现象描述之中,使人明辨善恶;德育情感的言说主要表现为言说者采取感叹句句式表明对有关事务、事情、人物等肯定性或否定性的态度,这种有关褒扬贬斥的情感使听者好恶分明;德育意志的言说主要表现在言说者通常采取祈使、命令的句式或内在地包含祈使、命令语气的词句促使听者趋善弃恶;德育行为的言说体现在言说者对言说对象的认知和把握上,或规训,或隐喻,不一而足。
2. 德育思想决定德育教材的言说方式
德育言说的知情意终归要体现在导引德育行为上,如何有效地导引听者的德育行为成为德育教材编写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考察德育行为与德育言说的关系有两种语言观值得关注:其一,语言“工具论”,语言是人们交往交际的工具,作为工具,德育教材的言说应该做到“明白如话”和“以词达意”;其二,语言“人文论”,语言不仅是交往交际的工具,还是人类文明文化成果的载体,是人类精神滋长的助产士,德育教材的言说应该挣脱工具论的束缚达到“纯文”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德育言说是德育思想的表现形式。在德育活动中,有什么样的德育主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德育言说,这又促使德育言说者自觉不自觉将自己之置身为道德的至圣地位,德育言说成为“诗云子曰”的圣人或代圣人的言说,听者接受德育言说的人文熏陶,往往是限于言说者或言说内容代言者的权威、地位、学识、身份等种种压力。
3. 典雅而诗意的民国德育教材言说性质
民国德育教材编写者把握了文言向白话文转化、白话还没有来得及独立的现状,寄望挣脱文言的束缚又传承文言典雅的神韵,使德育教材言说既具有德育工具功能,又具有德育人文的味道。教材编写者丰厚的语言修养使他们出语典雅,而赤诚的德育情怀又促使他们力求教材言说表达清新晓畅。于是民国教材的言说既体现白话的“明白清楚”“平易近人”,又传承了文言在音律上的铿锵、形式上的精美、图景的意象鲜明、意境的含蓄悠远以及德育行为导引的隐喻比德。比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之《秋天早上好》:“秋天早上好:白云飞,红叶飘,月光淡淡星光小,只有早起的人,才能看得到。秋天早上好:墙角边,树枝梢,虫声唧唧鸟声闹,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听得到。”这种言说浅显中蕴含典雅,平和中包涵情趣,清幽中隐藏玄机,因而读起来和谐婉转、抑扬顿挫,不仅容易触发听者的内心感动,更容易激发道德行为—做一个早起的人,领略自然的秋天之美,修养人生的德行之美。语言是存在的家,典雅的言说是家的灵魂。民国教材的言说本质上是一种尊重民族语言典雅特质的诗意言说,自然具有恒久的魅力。
三、民国德育教材言说的启示
民国德育教材的言说既借助白话文体又传承文言神韵,唤起听者的道德自发性、自主性与想象力,将语言工具与人文性融为一体的艺术,对当前改进德育教材编写,尤其改进德育言说有突出的借鉴意义。
1. 德育教材言说处理好“语言”和“精神”的关系
如果说德育言说是一个富有主观思想的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集合,那么,德育教材所要传到、产生的功能就消融或建构在语言编码、解码的言语实践之中。“人具有意识,但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2]马克思认为人的意识与精神是与语言的理解、表达同构共生的。“精神在语言中扎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它们所造就的肉体”[3]。洪堡特更进一步将语言与精神活动联系起来,认为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从这个角度审视德育教材的言说,德育虽然离不开行为,但行为总是由意识与精神支配的。所以与其说德育是一种精神现象,不如说德育是一种运用蕴含德性语言的言说活动。德育教材的言说不仅是指称“什么”,不仅表达某种意义,更主要的功能还在于让倾听者自启其智、自致其知、自建其德。审视当前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政治》等系列德育教材,受新课程改革影响,这些教材不乏德育目标的三维性、德育内容的生活性、德育教学的探究性等亮点和创新点,但受德育“传教”“训导”思想的影响,语言的选择和运用的价值取向侧重“约束”“控制”“听话”的为中心,因而教材言说侧重的是“道德规则的解释”而不是“道德精神的培育”。
2. 德育教材言说要处理好“问理”与“问心”的关系
德育教材不仅要传授德育知识,还要兼顾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之于德育的目的。这就导致我们今天的德育教材言说基本特征是“规训化”的,即言说者习惯于凭借纯理性的态势审视和规范具有情景化、生活化的学校德育问题,传递、灌输抽象的德育理论、规则。但我们也要看到“问理”德育言说尽管在学科体系化、知识系统化、说理逻辑化等方面取得突出的功效,与此同时,由于这种言说是通过强制性的道德命令和道德规则灌输方式进行,因而规训道德知识的同时也规训学生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个性。民国德育教材较多地考虑到“问心”,力避用纯理性、确定性的言说对学生道德现象、道德行为给予普遍性的解释,而是以他们的生活体验作为言说的起点,注意对儿童当下乃至将来的道德生活予以图景式展示。
3. 德育教材言说要处理好“通俗”与“典雅”的关系
如前所述,民国德育教材言说产生于文言向白话转化特殊的时代。尽管“五四”新文化“反文言,倡白话”旌旗猎猎,但时代使然,言说者浸润文言已久,这使得教材言说处处烙上了“通俗而不粗俗,典雅而不文言”的特别色彩。中国的语言文字原本“典贵疏达”,汉语是天底下最完美的文字。[4]然而,媚外的文化心态和日渐衰微的母语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使得汉语本身出现了“粗俗化”的危机。另外,德育教材言说也存在一个悖论:以语言的通俗化推进德育的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也许能够使德育理念变得“明白如话”,但难以激发倾听者的诗意冥想与道德境界上的要求。德育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语言也不是外在于是德育存在的。凭借且依靠中华民族典雅语言而演绎的德育教材言说,德育言说者与德育倾听者能够实现主体间性的解构与建构,实现德育应然境界与实然境界的沟通与融合。
参考文献:
[1]贾丰臻.修身作法教授谈(续)[J].教育杂志,1912(4):1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81.
[3]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1.
[4]李乾明.近代教学论学术思想的中国气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17.
责任编辑/杨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