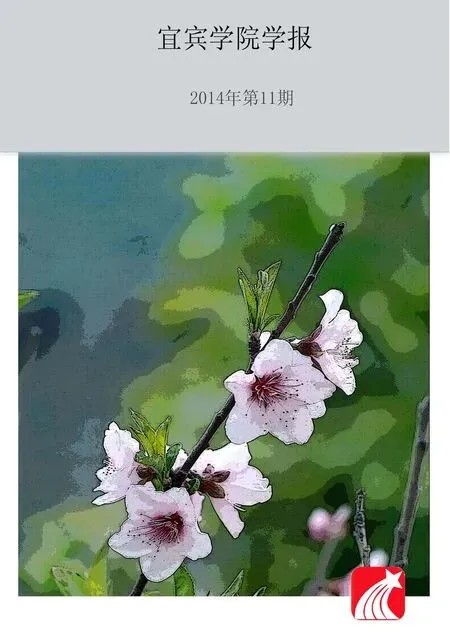唐君毅先生《哲学概论》价值论之要旨
朱建民
(华梵大学,台湾)
唐君毅先生《哲学概论》价值论之要旨
朱建民
(华梵大学,台湾)
《哲学概论》为唐君毅于1974年出版的专著,初衷为哲学教科书而作,但绝非简单的教科书式写法。该书述及伦理学较少,于价值论着墨甚多。唐君毅由易而难,陈述价值论之存在地位之各种说法,层层推进,以儒家致中和之价值论为归趋;明辨价值之本末与选择之原则,提出“心灵、生命、物质”之价值等差原则;最终落实于人道之实践功夫。《哲学概论》体现了唐先生要旨,显示出中国儒家思想的独特洞见。
唐君毅;价值论;《哲学概论》;致中和;价值等差;实践之功夫
哲学概论是近代中国大学哲学系或通识课程中常见之科目,内容主要依循西方哲学的架构、问题和概念语词,顺此而下,哲学概论往往成为西方哲学的概论,而忽略了西方以外的文明。这种现象至今犹存,长此以往,不免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只有西方哲学的那种形态,才算是哲学。因此,回到中国学术界的场域,居然也会出现中国是否有哲学、中国是否有知识论这类的论辩。
唐君毅先生之《哲学概论》原为当作一般哲学教科书而写,于1961年出版。当然,他对上述偏颇现象早有深刻省察。在初版自序中,唐先生说,尽管教过多年哲学概论,并试过多种教法,“然迄今吾仍唯有坦白自承,尚未知何为此课程最基本之教材,为一切学哲学者,所首当学习者。亦不知何种教法,为最易导初学以入于哲学之门者。①吾今所唯一能有之结论,即真为中国人而编之哲学概论,其体裁与内容,尚有待于吾人之创造。”由此可见,唐先生此书有意为中国人而写,体裁与内容不循前例,必有重新之抉择。
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思想家所谈之哲学问题不完全等同西方思想家所谈之哲学问题。因此,为了避免独尊一方而排除另一方,唐先生尝试对哲学作了较概括的界定,以期能够包含中西印三大文明于内,其中一种说法是:“哲学是一种求关联贯通人之各种学问或销除其可能有之冲突矛盾之一种学问。”[1]18其中更强调贯通知行,这点显然较为偏显中国哲学之特色。
如此,唐先生的哲学概论在西方之外,自然也包括中国和印度要素。此所以唐先生在论述西方哲学理论之后,必继以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名理论部分,述及印度之因明和中国之名学及知识问题;在天道论部分,述及印度与中国的形上学思想;在人道论部分,述及印度与中国的人生哲学。如此,三大文明皆有哲学,且各具特色。但整体而言,分量仍以西方为主。唐先生在1974年第三版序中提到,此书不同以往之哲学概论,在于“开始用中国哲学的数据,以讲一般哲学问题”。唐先生回顾,此书的遗憾是用得仍嫌太少,但后来陆续出版的六卷《中国哲学原论》已补此不足。
在架构上,本书有意跳脱西方一贯的方式,而试图以天道论涵盖西方之形上学,以名理论涵盖西方之逻辑与知识论,以人道论涵盖西方之伦理学、人生哲学、美学、价值哲学等。不过,唐先生并未以中国哲学常见之架构完全取代西方惯用之方式,例如代之以天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这样的分类。由此,或亦唐先生“圣之和者”生命情调之表现。《哲学概论》一书在分量上,知识论最多,形上学次之,价值论最少。不过,就中西哲学之比重而言,中国哲学在知识论部分着墨较少,反而在价值论部分着墨甚多。唐先生在初版自序说,价值论的部分,“其分别讨论问题之方式,亦为西方式的。然贯于此部之一精神,及每讨论一问题,最后所归向之结论,则为中国通天地、和阴阳以立人道、树人极之儒家思想。此以儒家思想为归宗之趋向,在本书之第一、二部(导论与知识论)已隐涵,第三部(形上学)乃显出,于本部则彰着。”由此可见,本书价值论的部分最能看出唐先生哲学的归趋所在。
唐君毅先生是当代新儒家主要开创者之一,对于道德哲学用力之深,众所周知,其本身之生命亦为道德人格之展现,践履之功,盎然面背。其著作由书名即可明白表示者,如《道德自我之建立》《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其余如《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莫不奠基于此。以道德实践为主要关怀而建立之道德哲学,颇异近代以来之西方伦理学。或许由于这个缘故,唐先生虽于西方伦理学著作涉猎甚多,但于其《哲学概论》一书却未深入铺陈。当代一般之哲学概论,在形上学和知识论之外,必以西方古今伦理学说为主要篇章,如此,英国效益主义、康德义务论等乃必备重点。但是,唐先生之《哲学概论》述及伦理学甚少,反而多所着墨于一般较少深入论述的价值论。
唐先生指出,依中国哲学,伦理即“人与人之间之所以相待之当然之道与理”。
伦理之学“兼指人之如何成为君子,免于小人,以敦品励行,或由知圣人与之同类,而求学圣人之为人伦之至之学也。”[1]1042依西方哲学,伦理学“指研究道德根本原理,与道德之意志行为之目标及善恶及正当不正当之标准之学,而初无特重人与人之伦理关系之义。”人生哲学“以整个人生之意义、价值、理想,为反省之所对之学。”价值哲学以一切价值(包括人生价值和其他自然价值)为研究对象。以上皆可括而统称为“人道论”,皆涉及“人之所当知、当行,以成其为人之道。”[1]1042唐先生之价值论,始于价值之存在地位、价值之分类与次序、价值选择之原则,旁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意志自由之问题,最后归结于中国哲学最关注之问题:人道之实践。若于人道之实践继续探究下去,即属中国意义之伦理学,而更远离西方意义之伦理学。如此,唐先生前述道德哲学之著作亦可视为中哲伦理学之补充。在《哲学概论》结尾处,唐先生说:“人欲成为圣贤人格所经之工夫之历程,即种种修为之道,与所成人格在宇宙之地位毕竟如何,其气象如何?具体人格在人伦关系中之品德如何?具体行为之善恶是非如何判断?人如何具体实现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则吾人于本书之始,已说明此乃属于圣贤之学、专门之伦理学及文化哲学?非此所及。”[1]1219换言之,唐先生之《哲学概论》未深究西哲之伦理学,亦未深究中国意义之伦理学(此处甚多丰富论述见诸唐先生其他著作),而唯于价值论多有论述。这些篇章呈现唐先生对价值论最完整的论述,而且显露最多唐先生个人创见与主张,绝非其第三版序言所称《哲学概论》“乃一通俗性的哲学教科用书”,故本文针对此一部分展示其中要旨。
一 价值之名义与存在地位
首先,依照一般西方哲学的方式,唐先生区分价值、反价值、非价值。价值意指“吾人今所谓价值或好或善,乃指知识上之真,情感感觉上之美,道德的意志行为上之善,及实用生活之利等。”反价值意指“凡与价值或好或善相对者,则我们可名之为反价值,或负价值,或不好,不善。”非价值意指价值中立,无善无不善。[1]1043
唐先生指出,一切价值皆涉及人之好恶,而人之好恶有不同涵义:实际上之好恶,能有之好恶,当有之好恶。“如果我们以此广义之好恶为好恶,可说一切价值,即可好的,一切负价值,即可恶。好与恶,同于欲与不欲。则我们可一切价值,皆可欲,一切负价值,皆不可欲。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即可暂作为善或价值之定义。”[1]1051唐先生此处没有明确地把“可欲”视为当有之好恶,以对比于“所欲”之为实际上之好恶。他将可欲之谓善视为一种“指示之定义。即指示我们去发现种种善或价值之所在之定义。”[1]1051不过,唐先生这种说法只是借用孟子的语词,未必合孟子原意;唐先生本人对此了然于胸,故用“暂作为”一词。
关于价值之存在地位,唐先生由易而难,陈述各种说法。这种做法基于唐先生的哲学观,同样的论述方式也不断出现在他其余的著作中。唐先生说:“吾人若将一哲学问题之答案,置于一哲学系统之内部看,则每一哲学系统,对各哲学问题之分别答案,即可互组成一在大体上定然无疑之全体。此全体,要为一人类思想之一表现,一创造。即其根本不合事实,而只是其中之思想之各方面之依逻辑的秩序,如是如是的配合,亦即有一价值。吾人如真能以此观点,去看一哲学问题之不同答案,则我们亦可说,此不同答案在不同之哲学系统中,可各有其价值。以至可说相对于不同之哲学系统言,此不同之答案,皆有一意义上之真。而每一哲学系统之为一包涵逻辑秩序之全体,即其内部为有某一种贯通关联,而可满足人之自一种观点出发,以了解世界之贯通关联之哲学要求者。”[1]221-222依此,唐先生好于每一问题上尽可能周全地列举各种说法,设法给予每一种说法一个恰当的位置而予以肯定,有时甚至费心为某些不易成立的主张曲成其说。这点在当代新儒家中,对照牟宗三先生的风格,更显不同。不过,在价值论的部分,唐先生自身的立场更为明确。他列举关于价值之存在地位的说法共十三种,而以儒家致中和之理论为终;他对前十二种西方哲学的价值论,一一分析,层层推进,一说故有进于一说处,但皆有其缺点或不尽处,或难以成立,或仅能显现真理之某一面向。唐先生最后以儒家致中和之价值论为归趋,论述亦最为精彩。以下依序来看唐先生对这十三种价值论的解析。
(一)将价值直接等同事物之存在
唐先生指出,这种说法有悖常识,因为我们不会把任何事物之存在皆视为有价值。[1]1053
(二)以实际欲望者为有价值
如此,事物是否有价值,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人之欲望。在此,唐先生进一步分析此说法之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张有价值者与实际所欲者在内涵与外延皆同;另一种是主张有价值者与实际所欲者内涵不一,外延相同。唐先生认为第一种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有二:一是,欲求食物乃一事实,但说食物有价值则是对此食物存在之评价;二是,说个人之欲求乃一主观面,说欲求对象之有价值乃就对象之客观面说。第二种主张是将有价值者与实际所欲者视为内涵不一而外延相同,在此,唐先生更进一步分析其中的三种类型:快乐论,得其所欲,令人快乐,而快乐即价值,故所欲者即连带而有价值;主观论,一物为人实际所欲,即使此物获得价值;客观论,本身有价值者,必定为人所欲求。[1]1055
(三)快乐之所在即价值之所在
依快乐论,乃以快乐为唯一具有“本身价值者”,而其他事物则因可带来快乐而具有“工具价值”。唐先生认为,快乐论无法成立。一则,“如快乐与善,乃外延上之同义语,则当说一切快乐皆为善的,一切善的皆为快乐的。然此乃不合事实者。”[1]1059例如,偷窃或害人亦可得快乐,但吾人不以为善。二则,“快乐并非唯一有价值之物,而有价值一名之所指,与快乐一名之所指,在外延上并不全然相同。快乐至多只为有本身价值之事物中之一种。”[1]1060
(四)价值为客观事物本身所具之性质
唐先生认为,“此说重在指出以事物之价值性质之来原为主观的之说,首与吾人之主观的心理经验不合。”但问题是,“我们如必欲依于具此价值性之客观对象,以界定此价值性,吾人又恒苦于难指出,此价值性之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何部份。”[1]1060
(五)价值为自存的
针对这种形态的客观论,唐先生批评,“价值性之自存之说之一根本困难,即在我们离已有之现实存在事物,而思维其价值性时,是否真能不同时假想一具价值性之形相或境界,或不假想一具价值性之存在事物?”[1]1063
(六)价值依附于完全之存在
对这种形态的客观论,唐先生问难:“此说之一最大之困难,是:当完全之存在视如一客观存在的已成之事实时,是否尚可说其为善……上帝为完全之存在,而无不实现之目的或善,则其本身岂不亦可无所谓善,或超于善之上,而其为善,唯是对吾人之不完全而向往完全者为善?吾人岂不可说上帝之善,非其本身之性质,而说此只为其对一切向往上帝之吾人,所显之性质?”[1]1065
(七)价值存在于事物之发展历程中
对此,唐先生批评:“吾人易据之以说明动的价值,然不必能说明静的价值。”[1]1066再则,“心灵活动之价值性,不只在其自身之为动的,而在其自身与‘静’或‘事物之静的关系’或‘已成过去之静的世界’,所构成之关系全体之中。”[1]1067
(八)以价值为关系性质
关系性质乃对比于本身性质而说,“一物之有长度,为其本身之性质。而其为大为小,则为其关系之性质。一物之关系性质,乃因其与他物有关系,然后表现之性质。”[1]1068唐先生举西哲培黎之主张:“以价值为由于吾人对某一对象产生兴趣时,对象所具之性质。”这种主张并不容易了解,唐先生也作了相当精微的分析与说明。他指出,“此说并不以一物本身之具价值性,与‘吾人欲望之’或‘得之之时可生快乐’为同义语,亦非以‘一物之具价值’与‘吾人对之有兴趣’为同义语。而唯是谓:当吾人之兴趣在于一物,或一物能引起吾人之兴趣,而构成‘一为发生兴趣之主体,一为兴趣之对象’之关系全体时,则此对象,即具备一价值性。”[1]1068
此间区分甚为微妙,跳出唐先生的说明,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哲学的词语来说,培黎的主张即是将评价视为一种三元关系的活动,而价值即是这种三元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性质。只有主体或客体,不足以形成评价活动,必须再加上主体对客体之兴趣。若用唐先生的说法,“此种理论之长处,在一方可说价值性之为客观对象之所具有,而另一方又说其所以能具有之根据,在主观之生命心灵,对之发生兴趣之关系。”[1]1068
唐先生认为这种主张颇多长处,但仍有不尽处。“然此说之以事物之价值性原于兴趣,则最后必归至兴趣自身之是否具有价值之问题。在此,培氏则主张一兴趣本身之价值,由其与其他兴趣之关系决定之说。即一兴趣愈能促进更多的兴趣之和谐的满足者,其价值愈高。而此价值即一狭义之善之价值,或道德之价值。于是此说最后应归至:以‘求兴趣之和谐的满足’之道德心灵,为一价值之根原。”[1]1069最后这句话是唐先生本人的主张,也是他认为培黎之说未尽之处。
(九)以事物之和谐关系为价值所在
唐先生认为,这种价值论表现在西方莱布尼兹、怀德海等人的哲学中,也表现在中国易传及中庸的中和之教中。[1]1071唐先生对这种主张作了很细密的分析,但未加以批评。
(十)心灵之理性的道德意志具有本身价值
“康德分善为无条件之善,与有条件之善。有条件之善,为相对于一时之目的者。而无条件之善,则为一绝对之善,而内在于心灵之本身活动之中者,此即由吾人之心灵,依理性而生之意志活动中之善。”[1]1077唐先生指出,“康德之所谓善意志,乃一超越之意志。所谓超越,即言其与一般之意志,不在一层级,而一般之意志中之价值,皆为其所肯定者;一般之意志欲望中之反价值者,则为其所欲加以化除,否定者。因此而依康德之哲学,吾人亦可说,吾人之欲实现此一善意志,必须超越并限制吾人日常生活之种种一般意志欲望。此即康德之严肃主义所由生。尼采则以为此乃康德哲学中之虚无主义之成份。”[1]1078
(十一)不存在为价值实现之条件
唐先生指出,以黑格尔之辩证法为例,“否定原则”乃一切存在事物变化之原则。“黑格尔视各存在事物之互相否定其存在,所发生之矛盾冲突,及一一存在事物之各为一有限与片面性之存在之事,皆为合以实现一全体或绝对之理念,或绝对精神之善或价值者。然在黑格尔之哲学中,又以‘能由矛盾冲突之逐渐化除,片面性之逐渐被补足,以进于全体’之存在事物,其价值较高。由此而其哲学,遂又非只重否定矛盾之原则,而亦重肯定与和谐之原则者。”[1]1083仅偏否定原则,非唐先生同意者;但后面这种更高层次之融和与整全,则唐先生本人较为赞同者。
(十二)具负价值者能由超化而成为表现正价值者
唐先生指出,“人之能于反价值之事物,同时看出其能超化,而成为表现正价值之事物,因而能于烦恼中见菩提,人欲中见天理,一切罪恶中见神圣;此乃代表人对价值之存在地位之一最深之认识。而为古今东西之大哲所共有。然此中仍有一问题,即烦恼中虽有菩提,然菩提未显,烦恼仍是烦恼。[1]1085
(十三)儒家致中和之理论
唐先生说:“中国儒家与黑格尔,同重视自然事物之变化。然黑氏视变化,为一种自然事物内在矛盾之展开,而中国儒家则恒视之为事物之求和,而为其内在之中和性之表现。”[1]1087一阴一阳相继相生,为中和之表现;一阴一阳相待相济,亦为中和之表现。唐先生指出,依儒家,“在此二种中和中,亦皆有一价值之表现。此价值之表现,亦即事物内部之善德或内部之价值之表现。”[1]1087
唐先生认为,儒家致中和之理论可以包涵前述十二种说法中若干有道理的部分。其一,儒家致中和之理论亦是主张价值存在于事物之和谐关系。由此显现三项理论优点:在和谐关系中,常以价值在客观之对方,故可涵客观论之说法;整体而言,价值在和谐关系中,故可涵价值存于整体情境之说;和谐关系乃依于求中和之性,则价值之原即在事物之主观存在内部,如此可涵主观论之说法。[1]1088
其二,儒家致中和之理论可以包涵肯定不存在为表现价值之说。例如,改过迁善;过是负价值,能将此负价值改除而不存在,亦即正价值。唐先生指出,依儒家,不像西方或印度把罪过视为先天之罪或累世之业,而是认为,一切罪过最初只是源于过度,开头皆是轻微之过,放纵之则成大过。人对自己之好恶过于重视而忽略他人之好恶,即成自私与我执。“人欲去其自私我执之心,在开始一步,遂只须在其喜怒哀乐上用工夫,而去其过度之处,同时亦即补其所不足之处,此之谓致中和。此致中和之工夫,虽至切近至平常,然充极其意义之所至,以使其喜怒哀乐之情,皆无过不及而生之私蔽。”[1]1089唐先生说明,致中和的中,不只是指两端之中间,更指“喜怒哀乐之未发”,亦即“一切喜怒哀乐所自发之本原之内心之隐微处”。而所谓致中和,在反面工夫上即是:“吾人于发现喜怒哀乐过当而节制之,以使之不存在,亦即将其再收回去,以归于其本原之内心之隐微处。”经此超越、否定之工夫,方能进一步求得中和目标之实现,以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1090。
其三,唐先生认为,若以太极阴阳之论来看致中和之价值说,更显其高明之处。“在此太极阴阳之论下,言价值之存在地位,又必言价值与存在之根底上之合一,与一切存在事物,无不直接间接实现价值,表现价值之义。而其立说,又大有高明过于上述诸说者在。”[1]1091例如,可以对生死问题有一高明之看法。阴阳不完全等同于存在之有无,而是由隐而显或由显而隐。由隐而显固然表现价值,而由显而隐亦表现价值。如此看待生与死,即不如他方之以死亡与消灭为大患。[1]1092依此,如高攀龙死时曰“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则中国先哲“唯是其信一生之始终之事,乃表现宇宙之太极阴阳之理之一显一隐、或一动一静、一往一来相应成和,以生化不穷之历程……在中国思想,则我之生为阳之事。此阳之事原非由宇宙之无中生有,而只是宇宙间在理上,原可有之如此如此之我之一生,由隐而显,由静而动;则其死,亦只是由显而隐,由动而静,以相应成和。生无憾,则死无憾……在中国儒家思想,以人物之完成其由始至终之一历程而无憾者,亦即能尽其性者。能尽其性,则无论其存亡生死,皆表现价值。[1]1093
在价值论上,唐先生以太极阴阳理论诠释儒家致中和的价值论,并以此为最完备且具启发性之理论。整体而言,唐先生此阶段对太极阴阳理论之深刻体会,表现在《哲学概论》的许多篇章中,除了价值论之外,亦表现在形上学的部分;除了表现在上述价值之存在地位的问题上,亦表现在下述价值之分类与次序的问题上。
二 价值之分类与次序
唐先生指出,价值之分类有两种类型:形式分类与内容分类。区分正价值、负价值、非价值,即为一种价值之形式分类。本身价值与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无条件之善与有条件之善、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根本价值与衍生价值,皆为价值之形式分类。[1]1098-1103
就价值之内容分类而言,唐先生指出,希腊哲学区分真、善、美三种根本价值,中世哲学又增加圣,这是以信、望、爱等宗教性道德而成就的高尚人格价值。近世德国哲学家施普朗格于《人生之形式》,“以真、美、爱、利、权力、神圣为六基本价值。并以科学求真,艺术求美,经济求利,政治求权,教育实现爱,宗教实现神圣,而善则为此各种价值之和谐配合,所实现之普遍价值。”[1]1104
在中国哲学方面,唐先生指出,“所谓价值之分类,实即善德之分类。中国先哲所谓善德,初不限于人生之善德。自然,宇宙,及万物,亦同可有其善德,然要以人生之善德为主。此种善德之分类,盖多为内容上分类……而近似于西哲对价值之形式的分类者,则一为善德之阴阳之分,一为善德之本末之分。”[1]1105在这部分,唐先生提出原创性的阐述。
就阴阳之分而言,唐先生指出,固然可有阳善阴恶之说,而将阳视为正价值,阴视为负价值。不过,就阴阳相依相生的观点,更一般的说法是把阴阳皆视为正价值,阴有阴德,阳有阳德;如此,唯有孤阴孤阳方为负价值。依此,中国阴阳之分不必对应西方负正之别。不过,唐先生将阴阳之分与西方内在外在之分相对应。他说:“阴德从事物之静处说,当一事物既静且终,则其所实现之价值,皆暂涵于事物之内,若与他物无关。故西哲所谓事物之内在价值、本身价值,即近于中国所谓阴德。阴德所以成己。阳德从事物之动处始处说,当事物正发动开始时,则其所表现之价值,必如及于其自身之外,而别有所成。而西哲所谓事物之外在价值,工具价值,则近于中国所谓阳德。阳德所以成物。”[1]1106
至此,唐先生只是单纯地将中西分类对应。接着,唐先生更进一步提出阴德与阳德的辩证关系,而指出二者之相涵。
如成己为阴德,成物为阳德,则阴德,乃接受他物之阳德之阴德;而阳德,亦即使他物能接受其所施发,而有其阴德之阳德。是又见阳德阴德之相涵。至于由时间历程中观之,一物于成己后,恒必归于再成他物;而此再成他物,即所以重彰显其所具之德于外,而亦所以成其为“有成物之德之己”者。故一事物之内在价值,又终必显为外在价值。而一事物之外在价值,既所以成就他物之己,亦即所以使此物成为“有成物之德之己”;而其有此德,又为表现一内在价值者。如以我之善意志为具内在价值,则此善意志之表为善行,而贡献于他人,人受其益,即其外在价值。纵一事物表面上只有外在价值者,吾人亦未尝不可视此外在价值,为其本身原所具有之内在价值之表现。如吾人饮水止渴,此水似只有止渴之外在价值。然可说天地间之水,自始即有能止渴之本性,而自始具能止渴之内在价值。其止我渴,即其内在价值之表现。反之,一切似只具内在价值之事物,如一人在深夜时内心之忏悔,吾人亦未尝不可视之为有引发以后之无数之善行之外在价值。故真正之价值,真正之善德,皆当为合内外之道者。由是而凡内在价值之不能表现为外在价值,外在价值之无所根于内在价值者,皆非真正之价值也。[1]1106-1107
唐先生上述之阐述甚为精彩,展现他不止于单纯地静态分析,而多进至动态的辩证观点。而且,唐先生更由中哲阴阳相依、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观点,对西哲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分不止于静态之别异,而进一步点出其间相涵相依之可能。同样,唐先生对西哲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之分亦求其间之会通。他说:“如从一切内在价值之表现于外在价值处说,则一切价值皆可说为相对。此所谓相对,即对一客观对象或对一客观情境,而显其价值。于是所对之对象或情境异,则同一之行为,并不必表现同一之价值。故对父母之孝行,为有价值,以同一之孝行,对路人,则不必有价值。则此非谓价值纯为主观而无客观普遍性者之谓。因一切人在同类之对象与情境前,某一类之行为仍可皆同为有价值者。如一切人在父母前之孝行,皆同为有价值者。而其有价值,即为绝对的有价值,并不以此外之其他情形之变化而变化,亦为可不以古往来今,东西南北之时间空间之异而异者。由是而此价值,亦即兼有绝对,普遍永恒之性质者。此即会通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之道。”[1]1107
唐先生此处之阐述颇类程伊川回应弟子杨时之问。杨时怀疑张载《西铭》民胞物与之说近似墨家兼爱之说,程伊川答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等差本二也,分殊之藏,殊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当代新儒家刘述先特别用力于理一分殊之说。
唐先生指出,西哲强调价值内在外在之分、相对绝对之分,但依中哲之见,其间皆可会通,此类区别并不重要。反之,西哲未强调之根本与衍生价值之别,中哲对价值本末之分却极重视。在此,亦中哲在价值论有可进于西方者。首先,唐先生分辨本末之意义,并指出此一分别与阴阳之分不相对应,与西方根本衍生之别也不完全相同。“本是先生,末是后生;本是开始,末是完成;本是能生,末是所生;本是一,末是多;本是总持,末是散殊;本是植根地下,而有不可见者,末是上升于天,而可见者。本末之范畴,与阴阳之范畴,不必相对应……本末之分,涵此多义,故亦不必与西方之根本价值与衍生价值之分,全然同义。”[1]1108-1109
唐先生指出,中哲言善德之本末之分,均涉及价值内容。而中哲谈到的价值内容,主要指的是各种善德。唐先生强调,“此似唯以道德之价值为主,然其余之价值,亦可涵摄于其中。”例如,孔子说的智,“即多少涵摄西哲之知识上所求之真”;孟子说仁义礼智四德,依五伦而说五德,“则西哲之真善美,皆统于孟子所论之人格成就历程中。”[1]1109此处固见唐先生圆融会通之性格展现,然其间仍有差异,必须加以注意。例如,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②由此可见,孟子言智乃就道德实践而言,与西方近代理性知识仍有甚大差异。
唐先生指出,中哲之言善德,不止于人伦,而常通于宇宙人生。例如,《易传》言仁义礼智之人德,又言元亨利贞之天德;其间,“人之仁即天之元,人之礼即天之亨,人之义即天之利,人之智即天之贞。”这种天人相通的看法至汉儒,“又依五行以言天之五德,与人之仁义礼智信之五德,并与各种物之五德相配。其中虽不无种种穿凿附会之论,然其根底,则为以一切事物,无不表现一价值,而亦皆至少可表现五德之一,或于其生化历程中,依序表现五德之思想。”[1]1110中哲重视价值之本末,反对把一切价值平列。其中,最常被视为本者,如孔子之标举仁,大体皆为后贤承袭。例如,程明道说义礼智信皆仁,朱熹说仁统四德。[1]1111此外,本末之说亦涉及实践次第。唐先生说:“大率中国先哲皆以人之一切德行事业,或一切实现价值之事,应由最切近处开始。[1]1112此所以《大学》必由诚意、正心开始,必先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西哲人对价值分类有基本的差异,西哲价值分类多属“依相斥而异范围之关系而分”,中哲价值分类多属“依相生而异次第之秩序而分”。虽然,唐先生本身偏后者,但他也愿意承认“相斥之价值分类法”与“相生之价值分类法”皆可成立。[1]1113
何以两种分类皆有价值?唐先生提出他的说明。“吾人须承认,从现实上看,人之各种文化活动,人之在社会之各种职业,及人之人格之形态,明各有不同,而各有其所实现之价值,然在实际上,亦常有不能兼备之情形。”[1]113此所以有孤立分别之价值分类。“然在另一方面,人所欲实现之各种价值,恒有一次序之相生之现象,亦为不能否认。此种相生,乃此未终即有彼之始,而始终相涵。如中国《礼记·祭义》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然,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此中有善德之次序相生,亦未尝不可分别言之。然分别言之,非谓其相异而相斥,其间仍为一贯之善德之流行。”[1]1114此所以有相生相依之价值分类。
唐先生进一步分析,相生之价值分类仍可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由外而内、先知后行的观点,依此,“则吾人恒倾向于以所知之外界事物之价值,为第一序之价值之所在。此可推至以自然界之物质事物,与其所在之时空,为一切价值之根原所在……又人之一切对物质事物之知识,皆依于人之对物质之数量、时空地位之数学几何学之知识,此知识中之真理,亦即为一切真理中有最基本之价值者。此对物质事物真理之知识之价值,亦即为人所当求之第一序之价值……利、快乐、与美感等之价值,即属于第二序之价值。再由人与人皆能在外界之自然界生存,人乃有余力,以从事内心之反省,然后人有其内心之道德,宗教之生活;此种生活所实现之善与神圣等价值,则宜属第三序。”[1]115
另一观点则与上述相反,乃是由内而外、先行后知。“我们如从行开始,则行之始,是我们之抱一目的,有一志愿。此目的志愿之合理与否,善与否,即是我们可首先体验到的价值……由人之本天理良心行事,而后形成人格内部之一贯与和谐,及行为之和谐,乃有人格之真诚与人格之美。此即孟子之所以由‘可欲之谓善’,以言‘有诸己之谓信’(真诚),及‘充实之谓美’。而此充实之美,亦即人之德行及于他人之善之表现,由此,人乃有礼乐艺术之文化之生活上之美。天君泰然,乃能知自然界之天地万物之美;神智清明,乃能进而原察于天地万物之理,而有真正之知识,以利用厚生。此即中国先哲之所以置智德于仁义礼之后之故。人有真正之知识,以利用厚生,人乃知自然界之万物之皆足以养人,于是视无生之自然,如金木水火土等,皆可以润泽生命,而皆各有其德。”[1]1116
在上述两种观点中,唐先生清楚地采取以心灵为本、以物质为末的立场。他的理由是,由于心灵之能自觉,而肯定各种活动与存在之价值;唯心灵而能知万事万物之价值。另一方面,“心灵以外之事物,虽可实现价值,然因其不能自觉,则其所实现之价值,即不能真存在于其自身之内部。”[1]1118
进一步,唐先生指出,心灵的活动涵摄了仁德、智德和审美之德,而且,仁德为其余二者之本。何以如此?唐先生说:“此中之理由甚多,吾人今姑只举一种,即:吾人如承认人之心灵为在自然界中具最高价值者,则人能爱敬人,而与人之心灵通情通德,亦即为有更高价值者……人之爱人而与他人心灵通情通德之心之德非他,亦即人之仁心仁德。人依此仁心仁德,而与他人一切喜怒哀乐之心情,与他人之一切刚柔之相感通,亦与人之欣赏美境,勤求真理之心情相感通,复与他人之仁心仁德本身相感通。由此而人之仁心仁德,即为一‘肯定尊重一切人之心德,一切人之人格价值’之一种心德。此心德即必然为一在人类社会中具最高价值者。”[1]1120-1121
此外,在谈到价值选择之原则时,在质之原则、量之原则、本身价值较高之原则、适合原则、次第原则、理性原则之外,唐先生亦提出“心灵、生命、物质之价值之等差原则”。依此,而有杀生以成仁之说。“生命之价值之高于物质之价值之理由,在物质之本身纵有一价值,然其不能生殖,则不能由其自身以引生出同类之价值之实现。而心灵之价值之高于生命之价值,则以唯心灵乃能认识一切有价值之事物,而涵容之。由此涵容,则可进而了解此一切事物之价值,而加以肯定,加以欣赏,加以爱护。而此能爱护一切有价值之事物之心,即吾人前所谓仁心之充量发展,乃一切事物之价值之依恃,因而为宇宙间最有价值之事物,亦人生之一切价值之根原。”[1]1192这是他的价值论最根本的主张。
三 中国哲学最关注之问题:人道之实践
明辨价值之本末与选择之原则,接下来应属实践工夫。唐先生最后指出一些入手之处。首先是,自觉自己是人,而且是有异于禽兽之人。“实践人道自何处始?则我们之答案实亦无他,即随处就人性之真实表现处,加以自觉,而充量的加以表现。此即实践人道之始也……实践人道之始,并不待远求,并不待对人性有穷尽之研究与分析,而唯待人之就此日常生活中,人之异于禽兽之自然表现处,而加以自觉,以知其所以为人。此即实践人道之开始,此之谓‘道不远人’。”[1]1210这点是孔孟成德之教的立论基础,也是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从其大体为大人”的实践工夫。
实践人道的第二步即是“自觉我是人之一”,也就是肯定我之外还有他人,“此其他之人,与我同为人,而外在于我,一方与我发生种种人伦关系,一方亦为我之一外在的限制。”[1]1211“由自觉我是人之一,知在我之外还有无数的人,则人对人之最根本的道德,即为一方自尊自敬,一方尊人敬人。自尊自敬,是原于自肯定其自己之人性之无上尊严;尊人敬人,是原于肯定他人之人性之无上尊严。”[1]1213在此,唐先生用的虽是现代的表述方式,阐述的其实即是孔子说的忠恕之道以及《大学》说的絜矩之道。
再进一步,“自觉我是一定之伦理关系中之人”。唐先生指出,“我们说我是人之一,则我对我以外之一切人,皆应有一平等相待之相尊相敬之道,与忠恕之道。但是我们还不能否认一事实:即我虽可与一切人发生关系,但实际上我只能与少数的人,有一定之伦理关系。”[1]1214唐先生在此的阐述亦甚精彩。他说:“在确定的伦理关系中,人与我乃相互成为内在于他人之心灵之存在……而吾人亦唯在直接之伦理关系中,方能以吾人之各为一具体特殊之唯一无二的人之资格,以互成为内在对方之心灵中之存在。至在其他种种人与人之关系中,则我与人恒至多只以抽象的人之一之资格,互存于对方心中,或我与人只以其人格之一方面互存于对方心中。”[1]1215依唐先生这段话,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区分具体的或抽象的伦理关系、直接的或间接的伦理关系、确定的或不确定的伦理关系。如此,在面临抉择之时,不致出现只爱抽象的人类却忘了照顾身边的邻人,也不致出现墨家兼爱之说。另外,正面来看,依此自觉,即应行入孝出悌之事。
更进一步,自觉自己之职分以及自身所处群体之公共目的。唐先生指出,人的心灵有无限的价值理想,但事实上不可能实现,而个人必须自限于某一职分。此一限制亦有应当之理,因须让他人亦有其当尽之职分。“人与人由其事业活动所尽之责任职分之互相配合,而有种种成就社会事业之团体结合。每一团体中人,即以成就某一社会事业,为其共同之目的。由各种社会团体之结合,即组成国家。国家之强盛,即为国家中之公民之公共目的。由此而我欲使我所尽之责任、职分,与人相配合,以成就种种社会事业,我即必须求自觉我所在之社会团体之公共目的,及国家中之公民之公共目的,而使我之一切活动,皆能与此目的之达到,不相违悖。由此而我有当实践之种种对所在之社会团体及所在国家之道德。”[1]1217
最后一步,我之唯一性之自觉。“我们如果真了解我们之每一人,乃一特殊而唯一无二之具体人格之义,则不难了解我在不同时,于不同情境之不同行为,皆为一特殊而唯一无二之行为。由此而其所实现之价值,亦当为一特殊而唯一无二之价值……而其价值,亦即无他人之生心动念与行为,或我之另一时之生心动念与行为,所能加以代替……人之一切生心动念言语行为,是则是,非则非,当其既发,即为一已成之事实而不可挽。然人之能知及此义,则所以使人能谨言慎行于事先,研几慎独于心念之未动,以更忧勤惕厉者也。[1]1218-1219
就个人的存在处境而言,唐先生分解其中的重要层面:作为具有人性的个人,作为群体关系中的个人,作为家庭中的个人,作为具有诸种特定社会角色的个人。唐先生以儒家思想为根底,对于个人如何在上述身分中尽其分,提出说明。更在最后点出人存在过程中每一时刻或事件的独特性,由此而抱持珍贵慎重之情。就社会之公共目的而言,唐先生举国家为范围最大之例,也显示某种时代背景。若于今日,必推至全球。然虽未明白言及,但就儒家推恩及于四海来看,唐先生亦不限于国家为止。
注释:
①此当属唐先生自谦之语,因为是否有所谓唯一之最佳选项亦难说。1975年,唐先生至台湾大学哲学系讲学,我曾当面请益,读哲学应由何处入手。唐先生回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并详加指点此中路径。可见,唐先生于此必有独到之见解。
②参见《孟子·离娄上》。
[1]唐君毅.哲学概论[M].第三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
[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李 青〕
OntheKeyAxiologiesofTangJunyi’sA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
ZHU Jianmin
(HuafanUniversity,Taiwan)
A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is a monograph of Tang Junyi’s published in 1974.Although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meant to be used as a textbook, it didn’t follow the set models of a textbook.The book dabbled only a bit in ethnics, while more attention was given to axiology.Proceeding from the shallower to the deeper, Tang Junyi expounded different ideas on the existence and status of axiology until it ended with the Confucian axiology of “Zhizhonghe”; he also discriminated the important values from those unimportant and advanced the principles upon personal selection of values, placing in descending orders the value of mind, life and substance; and finally, the book stated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e.A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offered a comprehension overview of Mr Tang’s ideas on axiology, providing an insight into the key idea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Tang Junyi; axiology;A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 Zhizhonghe; descending order; practice
2014-10-15
朱建民(1952-),男,台湾高雄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B261
:A
:1671-5365(2014)11-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