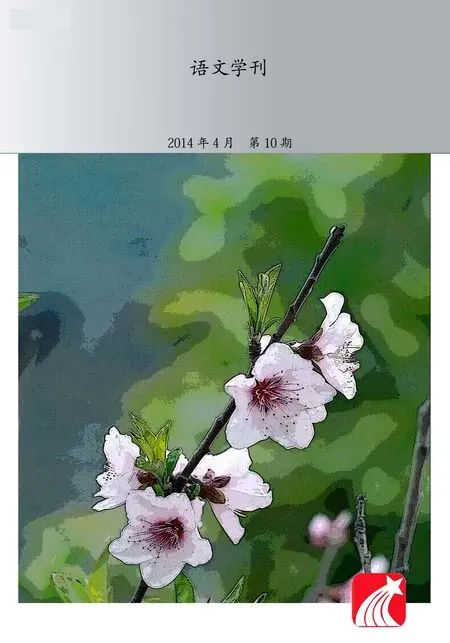论庐隐对五四男性叙事的超越与局限
○代廷杰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一、退守边缘的女性叙事
茅盾说“庐隐,她是被‘五四’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1]。但庐隐很快从“五四”怒潮的中心移至边缘,并且自守于主流话语的边缘。纵观庐隐的所有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庐隐之所以是庐隐,主要不在于她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而主要在于她对两性关系域的特别专注,并且这种关注已使她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中心视野。所以,尽管我们也能看到庐隐笔下的女性曾参与到五四“逆子”们的反封建同盟,但很快她们就从中游离出来,告别了“父权之战”的战场,进入到“性别之战”的纠缠中。站在女性的立场,在两性关系域中,她展开了对男性的审视和批判。所以,“神圣情爱之旗帜”一旦抽离反封建的所指,在庐隐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就是爱情的虚无、男人的虚伪、女人的伤害。
兰田就是这样一个“正是出了火坑又沉溺水坑了”的五四女性。在《兰田的忏悔录》中,兰田正是“被‘五四’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她接受了新思潮,打破了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寻求个人的幸福和妇女解放的出路。她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契合了“五四”时代主潮。但庐隐的独特与尖锐之处就在于她越过了男性作家们妇女解放的社会经济层面,而进入了两性关系层面,揭示了妇女解放的最大障碍不是经济而是道貌岸然的男性——作为有经济来源且妇女运动的先锋,兰田的悲剧就是毁在这种男人手里的,一方面他们在兰田受到迫害的时候,用“高雅”的同情轻而易举地诱惑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子”,但另一方面这种“高雅”的同情与“高超”的伎俩不过是为了骗取兰田的信任进而骗取兰田的钱罢了,他们没有尊重和真正的爱情,结果受害的总是无辜的女子:“受他的愚弄,终至作他的牺牲品……误信了不纯正的爱情,作了兽欲的牺牲。”
《兰田的忏悔录》实质是兰田对道貌岸然的男性的血泪控诉。庐隐站在女性的立场对男权社会作了彻底的否定和猛烈的抨击。所以庐隐歇斯底里一般地绝叫道:“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求乞恩惠,如果男人的心胸,能如你们所想象的,伟大无私,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切梦幻,都将成为事实了!而且男人们的故示宽大,正足使你们毁灭。”(《花瓶时代》)表面上这是庐隐对女性的警示,而实质是对男性的抨击。她洞穿了一些新时代“革命的青年”的虚伪与自私,他们满口新思想新道德,而“羊皮”遮掩下的卑劣行径给刚刚觉醒走上社会的新女性以巨大的诱惑和深深的伤害。
与五四男性大师们的战场在“父权之战”不同,庐隐的战场在“性别之战”。她把潜伏在父子冲突下的几乎被遗忘的两性矛盾挖掘出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时代产儿的两性解剖图”(白薇语)。这正是庐隐在女性视角下更为深厚的思想覆盖面和尖锐的思想穿透力之所在。
二、“性别之战”的图景
庐隐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觉使她看出了被男性大师们“鼓吹”的妇女解放的虚妄。所以就在胡适《终身大事》发表的第二年(1920年),她颇为清醒地指出:“妇女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妇女解放的事实,大半都是失望的。”[2]P31924年,她又说:“拿我们妇女运动过去的事实,和人家欧美对照看,我们简直是耍猴戏,模仿人家的样子,耍耍罢了。”[2]P23由此可见,庐隐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有着自己清醒独立的见解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种怀疑、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她以女性的视角切入到两性关系时,她戳穿了所谓“革命的青年”的男性乌托邦神话的虚妄,“像你们这种脑筋、这种思想的男人,才真是恶魔呢,怎么配做革命的青年!”[2]P329这正是庐隐与同时代的男性大师们不同的地方:她不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父权,更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给女性带来深深伤害的男权/夫权。
清醒的庐隐告别“父权之战”,奔赴“性别之战”。但游离出五四的时代怒潮不仅意味着失去同道和同盟,也意味着失去曾经拥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庇护被排斥在历史之外,更意味着女性从此成为一个孤立的群体,并将陷入双重的宰制:封建礼教的父权压迫与主流意识的性别/男权压迫。在对女性的压迫中,两者实现了合流与共谋,即共同以男性身份与女性对立。所以在庐隐的叙事中,我们看到压迫与反压迫、背叛与反背叛、抛弃与反抛弃等这些二元对立项都不是以阶级身份为界限,而是以性别身份为界限。女性的性别再一次成为其不幸的根源。所以在庐隐的叙事中,我们也看到展现在前景的“只有儿女/少女和少女样的妇人”,“男人们,永远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过客”,他们“来而复去,留下了爱恋、憧憬、痛悔,甚至死亡”。[3]P30
庐隐从女性经验出发,发现即便是自由恋爱这一现代爱情规则也会被利用,蜕变为男子欺骗、诱惑女子的幌子,从而失去它应有的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涵。在《或人的悲哀》中,KY决绝地说,“人事是做戏,就是神圣的爱情,也是靠不住的”。在女性叙事者“我”的眼中,甚至男人也是令人憎恶的。好朋友叔和就是那种“我生平最恨见异思迁的人”。“我”痛痛地拒绝了他的追求。但是他仍纠缠不休,常常以自杀来威胁“我”,使“我”脆弱的心灵,受了非常的打击。同样的,孙成和继梓是一样的“虚伪的可怕”。他们两个为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倾轧,而“我现在是被钓的鱼,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在这里,叙事者“我”从女性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发现在两性关系中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渔夫和鱼的关系,就是“钓”和“被钓”的关系,这就不仅看到了男人的虚伪和贪心,而且感受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人的被“物化”,以及女人作为“物”被男人抢从而成为胜利男人的“战利品”的可怕的生存状态。
在庐隐的叙事文本中,“性别之战”为我们呈现的是女性对男性泣血的控诉,她敏感地发现“爱情”在这个男权社会的虚幻存在和男性的虚伪本质以及性别压迫的实质,所以庐隐笔下的女儿们对男性的排斥和抨击不仅是对男性个体的宣战,她是把对男性个体的批判和对整个社会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男权封建意识的清算与反抗。庐隐对两性矛盾的特别关注和深入挖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中心视野,与男性大师们的分野使她的尖锐的思想穿透力再一次抵达男性大师们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盲点。
三、放逐男性
有人称庐隐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这头衔她“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庐隐自传》)。其实,尽管庐隐对两性领域特别关注,但严格说来,她写的不是男女“恋爱”,而是男女两性的矛盾与冲突,恋爱/爱情只不过是虚设的场域。所以在庐隐的叙事文本中,看不到两性间微妙复杂的心理回合,也看不到女性自身的内在情爱体验,更看不到女性通过恋爱可能获得的性爱冲动,能看到的只是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伤害和由此带来的女性对人生的怀疑。恋爱/爱情这个本来只关涉两性性情场域的话语被庐隐抽空了所指,成了一个空洞的无所指的能指符号。同样的,庐隐笔下的男性只不过是虚设的幻象,他们并不构成爱情关系中的男女双方的主体之一,并未真正对象化,他们只是在普泛的意义上象征性地呈现在女性叙事者的文本中,并成为庐隐探索女性问题的载体。作为被讲述者,他们只是被提及而不是被塑造的形象,他们处于沉默状态,他们话语权的被剥夺来自女性叙事者“我”,既是由于第一人称自我表述的限制性叙事视角所限也是由于“我”宣泄对社会人生的愤懑、谴责、抨击的所需。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女性叙事者的“叙事话语场”,而是被女性叙事者放逐在文本之外。
贬抑男性是庐隐放逐男性的又一叙事策略。在庐隐的叙事文本中,男性不是被虚化就是被贬抑,与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相比,男性往往是苍白而虚弱的,黯然失色,令人可鄙。《或人的悲哀》中的唯逸、《海滨故人》中的蔚然、《彷徨》中的秋心、《秦教授的失败》中的秦教授等,在庐隐的叙事文本中,我们再也看不到《终身大事》中那个未“出场”的陈先生的身影,他们胆怯、懦弱,缺乏与命运抗争、追求幸福的勇气、能力和力量。按露沙的话说“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倘若“失了感情的慰藉”,有的“竟抑抑病了”,有的“竟至于死了”,如此胆怯懦弱的男人怎能不让女性失望!显然,这些男性形象是作者在女性视角下观察所得,并站在女性立场上对男性做出的或讽刺或不满,细腻的刻画中流露出觉醒女性对男性的深深失望,在客观上也构成了对男性大师们建构的男性乌托邦神话的质疑与拆解:他们不仅无法救赎女性,就连他们自身也陷入了难以自救甚至需要借助女性的“情感的慰藉”来“安慰他灵魂的枯寂”的困境。
构建姐妹之邦是庐隐放逐男性的又一叙事策略。庐隐这种贬抑男性的叙事策略固然拆解了男性作家们建构的男性乌托邦神话,把男性在社会和两性关系中无能虚弱的本质暴露出来,对男性进行了彻底的去势,但这种拆解和去势带给女性的是一种无所依傍的失落感。既然女性在男人那里找不到幸福而陷入孤独和悲哀之中,那么在女性之间寻求友谊也就成为自然了。所以在庐隐的叙事文本中,涉及女性友谊的篇章比比皆是,《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们、《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们、《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们、《兰田的忏悔录》中的兰田们,等等。这是暂时剔除了男性和对男性欲望的姐妹之邦。她们用同性联盟建立起来与男性世界的壁垒使她们暂时避开了因男性引起的恐惧与焦虑,从而使她们在同性那里获得了精神慰藉和心理补偿。“这是一种以自虐的方式完成的施虐行为”,庐隐通过对女性自身欲望的否定完成了对男性欲望的否定与拒绝,“将男人置于一种无所适从地性焦虑之中,从而完成了一种对男性的阉割形式”,从而彻底把男性放逐在文本之外。[3]P42
四、“处身性”叙事的局限
当庐隐彻底把男性放逐在文本之外时,她建构的姐妹之邦也被自行放逐于男权社会之外。这种社会性的自我放逐最终把庐隐笔下的姐妹们围困在男权社会的孤岛中。狭小的天空,幽闭的心灵,封闭的女性自我天地,乌托邦式的虚幻壁垒最终使她们过着一种自我囚禁般的生活,并在男权社会的不断挤压和吞噬下或自行瓦解或陷入悲哀不能自拔或逼上死路。《海滨故人》中,露沙的姐妹们最后一个个被男性们瓦解,莲裳结婚,露沙不到完婚就悄悄地走了;宗莹结婚,露沙亦是“涕泪交加”“肝肠裂碎”;设想中的“海滨故人”留给她们的是“屋迩人远”。《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兰田的忏悔录》中的兰田,她们无不带着愁苦倦容,陷入悲哀中不能自拔。《丽石的日记》中,丽石最终因为阮青与表哥结婚发出“抑郁而死吧!抑郁而死吧!”的绝望哀叫,不久果真因为心脏病辞世。这一切都昭示着庐隐为她笔下的人物设计的“姐妹之邦”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女性救赎之路。这首先是时代、社会、男权给女性带来的重压造成的;其次是觉醒的知识女性难以摆脱对男性的身心“依赖感”,难以冲破自身战胜自我;当然这也不能不与庐隐“处身性”[4]叙事的局限有关。
庐隐的一生太不幸了。她自幼就缺少家庭的温暖;成年后,母丧,夫亡,友逝,特别是爱情上遭受到的严重创伤,使她对人生的体验悲多乐少。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她“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但“在文章中”,她却“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她说“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庐隐自传》)所以庐隐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在悲哀中呻吟,或是在痛苦中彷徨的,她们艰难的处境和忧郁的心境也无一不是作者的心声;但庐隐这种“处身性”的叙事束缚了自己,不仅造成了所谓的“庐隐的停滞”(茅盾语),更重要的是使得庐隐和她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思想高度思考问题,她只能对她笔下的人物采取一种平视视角,而无力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对人物的处境、体验、情绪作出深刻的理性把握。所以庐隐的小说是一种典型的宣泄性的文本,它弥漫着浓重的挥之不去的哀伤、幽怨,以至于庐隐自己也承认“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但她是以放弃作家的理性反思和思想力度为代价的。庐隐的“处身性”叙事使得她沉浸在宣泄的畅快中,“只是为了表现我自己的生命而创作”(《文学家的使命》),从而拘囿于一己的哀怨中。在无节制的情感表达中,庐隐常常顾不上对题材进行艺术提炼和对思想进行升华,作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倡导者,庐隐的创作失去的不仅是作品的艺术蕴藉,更重要的还是探讨妇女问题理应达到的思想深度。所以,尽管庐隐倡导妇女“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做人”(《今后妇女的出路》),并对男性作家们建构的男性乌托邦进行了质疑和拆解,对男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放逐,但妇女解放的时代命题,连同她笔下的女性一起被淹没在因“处身性”叙事而带来的浓重的悲哀中;妇女的解放和救赎也因“处身性”叙事的局限而成为毫无希望的“痴想”——这不能不说是庐隐小说文本中女性叙事的一大缺陷。
[1]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C].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2]庐隐.庐隐选集(上、下册)[C].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即德国生命哲学的“Befindilichheit”,指“处于……的心理状态”,译作“处身性”。这里用来指称庐隐小说文本的叙事特点。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