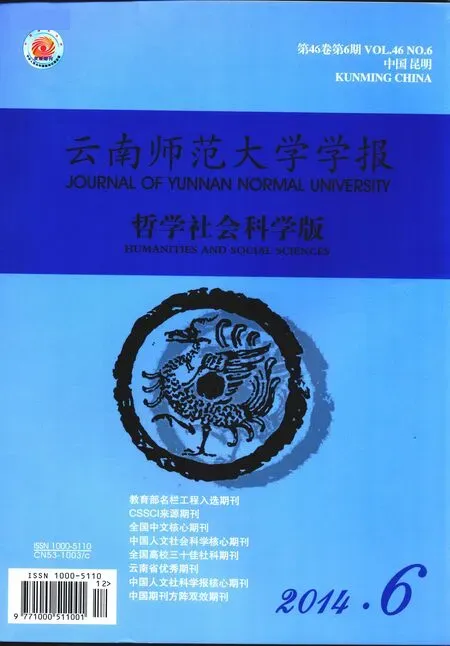中国社会结构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基于妙峰山香会的田野调查*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中国社会结构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基于妙峰山香会的田野调查*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以亲属关系比拟人神关系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前往妙峰山进香的信众们认为,神灵的灵验是基于彼此关系的阶序等级而呈现效力差别的差序的灵验。信众们通过对神灵的亲属称谓以及用亲属交往比拟宗教实践,试图与神灵建立起拟亲属的关系,进而用亲属关系的道德约束神灵的灵验。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支配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践逻辑,形塑了信众的神灵观及其基础上的仪式实践。就这一意义而言,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中国民间信仰具有比较宗教研究基点的意义。
中国社会结构;民间信仰;差序互惠
在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杨庆堃对于中国民间信仰“弥漫性”的定性最具学术影响力。杨庆堃准确指出了中国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紧为一体的事实,强调这种宗教“无论是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结构的一部分,它自身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1][p.10]然而,杨庆堃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分析仅仅指出其“弥漫性”的外在特征,并未回答中国民间信仰赖以依存的社会结构对其精神内核的影响。
众所周知,乡土中国因其差序格局从而有别于西方社会。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p.30]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差序关系是由父系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来表征的,而地缘关系也是差序格局的重要维度,在这两者之上形成了传统中国相对封闭的家族体系与村落社区。显然,杨庆堃注意到中国民间信仰对社会结构的紧密依存,强调“宗族构成了宗教的场合,祖先崇拜作为家庭生活的首要方面,从宗教信仰、仪式象征和仪式活动以及其组织等,都深深地融入了家庭之中”。[1][p.271]此外,“社区保护神的信仰是传统社区基本观念整体的一部分,是社区共有基本生活方式的象征”。[1][p.271]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生性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格局,[3][p.169-170]在这些社会和经济团体中也同样表现出了宗教的面向。[1][p.271]那么,在外在结构之外,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精神内核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人类学实践论的引入为分析中国民间信仰的内核特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惯习与场域是布迪厄实践论的核心概念。在实践论中,惯习产生实践,实践修正惯习。正是惯习产生的行为实践建构着社会,但这一惯习却并非仅是实践者个人的目的,而是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是“内在的外在化”的过程。[4][p.80]布迪厄实践论打破了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他试图重建一种社会嵌入的论点,将文化视为一个不断进行中的过程,认为文化是主体立足于既有的文化范型,不断更新创造的过程,强调作为系统的文化与作为实践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借助于“实践论”分析范式,立足于笔者对京郊妙峰山香会组织的普查,本文以前往妙峰山进香香会群体的宗教实践为分析对象,对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对信众宗教实践内核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田野对象:妙峰山庙会与香会
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是京畿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主祭神为碧霞元君。在对碧霞元君的神格演变进行考察后,罗香林认为,民间对碧霞元君的来源有着四种来历,即东岳大帝的女儿、民间凡女得道成仙、黄帝七女之一和华山玉女。[5]尽管民间对于碧霞元君出身的说法并不一致,但却普遍认为碧霞元君是我国女神信仰的突出代表。碧霞元君主人间的生育,是生殖女神在北方,尤其是在华北地区的地方性表现。
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山东。相传宋真宗东封泰山,一玉女石在真宗面前显圣,宋真宗为此玉女石重建雕像,修建“昭真祠”加以供奉。[6][p.121]此后,民间便逐渐兴起供奉碧霞元君。大约到了元代,碧霞元君信仰传到北京,北京民众开始建庙供奉。
由于碧霞元君与泰山之间的关系,北京民众通常把供奉碧霞元君的寺庙称为“顶”。明代年间,北京城内已经形成祭祀碧霞元君的“五顶之内,城郭环绕”的格局。这五顶中,中顶在右安门外,草桥北,明代在唐代万福寺遗址上兴建。东顶在西直门外小关。西顶在西直门外蓝靛厂,麦庄桥北,明代万历年间初建。南顶在左安门外东南马驹桥,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又称“大南顶”。与之相对的“小南顶”指永定门外南苑大红门的碧霞元君庙,始建于明德化年间。北顶在安定门外,北极寺之东,即朝阳区大屯乡北顶村。[7][p.356]在这五顶之外,在北京郊区,还有三处供奉碧霞元君的山峰,即为“三山”,分别指称门头沟妙峰山、平谷丫髻山和石景山天台山。在供奉碧霞元君的诸多信仰地中,以妙峰山最为灵验,故被称为“金顶”。
妙峰山的香火肇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当时便已形成了四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月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妙峰山在清末年间最为兴盛,其香火超越了城内其他供奉碧霞元君的寺庙,成为远近闻名的“金顶”。在这浩浩荡荡的进香队伍中,有组织香会的进香是妙峰山庙会最为突出的特点。康熙二年,保福寺引善圣会在此进香立碑。在顾颉刚先生调查的1925年,更是有着114档香会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的轰炸,妙峰山庙会不得不中断。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妙峰山庙会才得以恢复。如今的妙峰山庙会,虽不及清末年间那般兴盛,但每年庙会,仍然有数百档香会朝顶进香。
二、香会群体的神灵观:差序的灵验
与其他供奉碧霞元君的圣地相比,妙峰山上的碧霞元君以“灵验”闻名。“灵验”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概念。神灵的灵验通常与信众的许愿相关。“许愿就是在神灵面前表达愿望乞求帮助,如果愿望实现了,许愿者就会再次进香并供奉祭品。还愿是愿望实现后向神表达感恩之情,无论是病愈还是家财兴旺,或是生育男孩等,人们都不会食言,一定会来还愿。”[1][p.92]如愿意味着神灵灵验,诚如王斯福所言,灵验是一个神灵信仰在地方社区兴起的基础条件,并成为信众笃信神灵的关键。[8][p.143]神灵的灵验与信众的仪式实践之间形成一种互惠的关系。对于灵验的乞求,使得中国民间信仰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神灵体系,而是更多体现出以灵验为本位、以情境为取向的特征。
如前所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灵验是信众个人宗教经验的起点。然而,信众对于神灵的灵验却有着完全个人化的感知。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的会头刘鑫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拜神并不是说你拜多少就给多少,灵不灵是有她自己的打量。你心里有娘娘,跟娘娘亲,娘娘自然跟你也亲,你心里没有娘娘,庙会的时候,花得再多,也没用,娘娘不灵。①访谈人:张青仁,访谈对象:刘鑫,访谈时间:2011年5月7日,访谈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
在刘鑫看来,尽管人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惠关系,但作为神灵庇佑的灵验并非平等地面向所有的信众,而是呈现出一定等级的差序。这种灵验的差序并非仅是建立在信众在仪式现场上的表现,而是根植于日常生活,取决于人神关系的亲密程度。简言之,在朝顶进香的信众们看来,作为神灵回报的灵验是建立在人神关系亲疏远近的基础上,是基于彼此关系而呈现出阶序等级的差序的灵验。
神灵的灵验不仅取决于人神关系的亲疏远近,两者之间更是具有相互建构和转化的可能。狮子会会头郑伟的经历颇具典型性。2005年,由于父母双亲身患重疾,加上自己身患糖尿病,郑伟家里捉襟见肘。万般无奈之下,他前往妙峰山进香。在身体好转之后,他将此归因于娘娘的灵验。他在家里为碧霞元君设坛供驾,碧霞元君成为“他们家的老娘娘”。此后,村里赶上拆迁,得到补偿款后,郑伟家庭的危机迅速解决。他越发地认为,家里状况改善的根源在于“我们家的老娘娘”对他的庇佑。对家里的老娘娘,他越发恭敬。每逢初一、十五,他都在家里上香供奉。狮子会出局时,他更是提前在神案面前向娘娘汇报。在他看来,灵验的娘娘就如同他的家人一般。正因为如此,娘娘才能灵验地庇佑着一家的平安。
信众们对于神灵的不同信仰取决于神灵的个性以及他们对神灵的个人体验。[9][p.66]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万神”和“有意义的神集”两组概念。[9][p.66]个人的万神是指个体的信仰者所了解的神的集合,有意义的神集指的是在个人的万神中处于核心位置的神灵,它包含那些对于信仰者而言有着特殊含义的神灵,对于个人有着个人的意义和突出的特点。在妙峰山香会的个案中,个人的万神及其基础上的有意义的神集是建立在人神之间的差序关系及其差序灵验的基础之上。
会头们对于神灵灵验的说法反映出他们的神灵观,在他们看来,尽管人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惠关系,但是人神之间的互惠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等价交换,作为回报的神灵的灵验是基于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呈现等级差别的差序的灵验。信众们的这一神灵观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仪式实践。
三、仪式实践:与神灵建立亲属关系的表征
信众们对于灵验的认知形塑了他们的仪式实践。这一形塑首先表现在对妙峰山主祭神碧霞元君的称呼上。尽管妙峰山“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名号很早就出现在文人笔记中,但在顾颉刚的调查中,前去进香的民众均称碧霞元君为“老娘娘”。如今,“老娘娘”仍然是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的信众们对碧霞元君的唯一指称。每逢香会进香,在会头们向碧霞元君呈起表文、宣告来到的时候,他们口口声声地向着这位“老娘娘”表虔心。在介绍碧霞元君灵验的故事时,“老娘娘”亦是他们对待碧霞元君的唯一指称。
称呼碧霞元君为“老娘娘”,显然是与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女性神的神格特征有关。在对碧霞元君神灵演变过程的分析中,彭慕兰发现从泰山神中诞生、并获得神灵特征的碧霞元君最初是作为繁育神的角色出现。信众们称呼其为“老娘娘”,一方面是出于对碧霞元君的尊重,突出碧霞元君在神灵众多的妙峰山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老娘娘”意味着子孙繁盛,是信众对其超凡生育能力的肯定。[10][p.193]此外,信众们使用“老娘娘”这一拟亲属称谓指称碧霞元君,无疑拉近了人神之间的距离,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具生活化特征。
事实上,即便至今,在碧霞元君信仰兴起的山东地区,信众们仍然执着地称呼碧霞元君为“老奶奶”。[11][p.123]京郊的怀柔农村也是如此,按照只走一股香道的规矩,怀柔区的信众一般前往东山的丫髻山进香朝拜碧霞元君,“东山奶奶”是他们对丫髻山上碧霞元君唯一的称谓。与“老奶奶”相比,“老娘娘”的称谓在表达亲属意味的同时多了一层皇权等级的色彩。这种政治隐喻的叠加是与清廷对妙峰山庙会的参与有关。尽管如此,却依然不能掩盖“老娘娘”这一称谓背后亲属关系的含蕴。
信众们不仅亲切地称呼碧霞元君为“老娘娘”,他们更是用多样的仪式实践“伺候老娘娘”。朝顶进香是妙峰山香会最为重要的仪式实践。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的香会分为文会和武会两种。文会是指在庙会期间搭棚设驾,为香客、碧霞元君服务的会档。谈及文会朝顶进香的意义时,会头赵凤岭说到:
文会就是吃喝拉撒睡,什么会都有。吃饭有馒头会,喝水有茶会,给娘娘扫灰有掸尘会,给娘娘献花有白纸献花会,这些都是伺候娘娘的。还有些修道会、缝绽会、燃灯会,这些会是让香客上山好走道,给过往香客服务的,虽然这些会不是直接服务于娘娘的,但也是为了给娘娘催香火,也是给娘娘服务的。①访谈人:张青仁,访谈对象:赵凤岭,访谈时间:2010年5月22日,访谈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赵凤岭家。
尽管武会是“练技术之会”,但会头们认为,与文会一样,旧时京城的十三档武会,也都是“伺候老娘娘”的。与文会不同的是,武会的伺候有着多层次的含义。首先,行香走会的武会通过朝顶进香,给老娘娘催香火,这是最为直接的伺候。此外,武会还要在娘娘驾前献档表演,为娘娘献艺。最为重要的是,旧时京城十三档武会都有着深层次的象征意义,他们通过营造一个象征的庙宇空间,伺候着位于正中的碧霞元君。
开路(会)打先锋,五虎(棍会)紧跟行。门前摆设侠客木(高跷会),中幡(会)抖威风。狮子(会)蹲门分左右,双石(会)门下行。掷子石锁(会)把门挡,杠子(会)把门横。花坛(会)盛美酒,吵子(会)响连声。扛箱(会)来进贡,天平(会)称一称。神胆(大鼓会)来蹲底,幡鼓齐动响太平。[12][p.85]
在这十三档香会中,
“狮子”象征庙门前的石狮,所以有守驾的责任,行香时狮子守驾,各会由狮子前经过,狮子殿后起行。“中幡”像庙前旗杆,所以先行(以下略按次第),“自行车”会像五路催讨钱粮使者,“开路”像神驾前开路使者,所以练杖,“打路”、“五虎棍”、“少林棍”皆为引路使者。“天平”(什不闲)像称神钱者。“挎鼓”像神乐。“杠箱”像贮神钱粮者,所以更有杠箱官。以外“秧歌”(俗称高跷会)、“小车”像逛庙游人。“双石”、“杠子”、“花坛”……等,既像神前执事,又像赶庙玩意档子。[13][p.155]
民国年间,当踏车会、小车会和旱船会想要加入到进香武会的行列时,新增的踏车会声称自己是为娘娘催讨钱粮,为各会档跑腿送信的,小车会说自己是为老娘娘从陆地运送钱粮的,旱船会则称自己是为老娘娘从水路运送钱粮的。因为只有是“伺候老娘娘”的,才能加入朝顶进香的香会名录。
除了朝顶进香外,不少会首会员家中更是供奉着碧霞元君的神案,他们将自己供奉神案的行为也称为“伺候老娘娘”。供奉茶案的亲友同乐清茶圣会的会首老卢每逢初一、十五,都会给娘娘上香。家里有了什么新鲜的水果,也会及时给娘娘驾前上供。茶会出局朝顶前,老卢也会给娘娘上香,请求得到老娘娘的庇佑。在他的眼中,他天天伺候的老娘娘更像是他的长辈,庇佑着全家的安康。与老卢一样,前述聚义同善天缘狮会的会首郑伟也在家中“伺候老娘娘”。娘娘驾所在的客厅是家里的圣地,在这里的一言一行都有着一定的讲究。每天早上,郑伟先要给娘娘请安,初一、十五要给娘娘上香上供。每逢狮子会出局,郑伟更是早起叩拜娘娘,心里默念,祈求得到娘娘的保佑。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之前,郑亦要要率领会众,在娘娘驾前磕头叩拜。
朝顶进香、燃香供奉,这些颇具象征意义的宗教实践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为常见的仪式活动。但在香会群体的陈述中,他们并不关注仪式本身的象征属性,而是关注仪式活动具有表达与建构人神关系的属性,强调宗教实践作为“伺候老娘娘”的方式。信众们用“伺候老娘娘”来指称自己的仪式活动,用晚辈对长辈的孝敬来比拟自己的仪式实践进而强调宗教实践义务性的特征,其实质是用亲属之间的交往来比拟宗教实践并试图以此与碧霞元君建立起拟亲属的关系。
用亲属称谓指称神灵、用亲属交往比拟宗教实践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碧霞元君信仰兴起的山东,女性香客们认为自己前往泰山碧霞元君祠进香是“回娘家”。如同出嫁的女子,进香的妇女们要自己制作食物为义务,对娘家的老奶奶做出贡献。[11][p.123-145]在河北赵县范庄,每年农历二月二龙牌会,信众们认为自己是在“伺候龙牌老人家”;在河北宁晋,信众们平时在家中“伺候三皇姑奶奶”,每逢农历三月初一到十五的苍岩山庙会,信众们更是不远数百里,前去苍岩山“探望三皇姑奶奶”。在对马来西亚一个华人社区民间信仰活动的调查中,白晋(Jean DeBernardi)也发现中国人更倾向于用父母与子女而非政治等级来隐喻人神之间的关系[14][p.60-61],信众们如同对待长辈一样对待着神灵,对其毕恭毕敬。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仪式实践表达着信众们对于人神关系的理解与建构。他们试图通过对亲属交往的比拟,将神灵纳入亲属关系的序列中,[14][p.61]进而与神灵建立起拟亲属的关系。
信众的宗教实践与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民间信仰是以灵验为本位,作为神灵回报的灵验是建立在人神关系的基础之上,是依据彼此亲疏远近呈现出效力差别的“差序的灵验”。想要确保神灵的灵验,信众们必须与神灵建立起各自的联系。因此,信众才会通过对神灵的拟亲属称谓以及用亲属交往比拟仪式实践,与神灵建立起拟亲属的关系,进而用亲属交往的道德确保着作为回报的神灵的灵验。
四、差序格局的宗教图景
无论是信众们关于神灵灵验的差序认知,抑或是他们试图与神灵建立亲属关系的仪式实践,信众的宗教实践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深刻影响。费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本质上是在强调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它的基本起点是自我,是自我由己外推、与他人建立多重关系的过程,不同的关系存在着一种“有等差的次序”。在这一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方式亦是服从于彼此等差次序基础上的差序人伦。费先生对差序格局在道德领域内的运作做了分析。在道德领域内,社会道德与私人关系发生了联系。“传统的道德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所有的附着标准不能脱离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2][p.36]同样,在人际交往的互惠中,彼此的收益也是服从于相互之间差序关系而呈现出大小的差别,这便是“差序的互惠”。[15][p.303]
诚如涂尔干所言,社会构成了个体认知世界的基本模型,而个体的经验就是在社会的模型中得以形塑的。[16][p.605]个人所熟知的世界必然是社会的世界,恰恰不是社会反映世界,而是世界就在社会之中。涂尔干的分析强调着作为文化范型的社会对个体实践的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观点与布迪厄对于场域与惯习的认知是不谋而合的。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是外在于个体,并通过支配人类的实践从而在人类中获得了主导的地位。这也意味着,人类的实践作为历时性存在的社会事实,是依赖于既有的文化范式。
涂尔干与布迪厄的论述在对中国民间信仰信众实践逻辑的分析中得到了深刻的验证。正是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形塑了中国民间信仰完全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神灵观与仪式实践,并支配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践逻辑。如同人际关系中“有等差的次序”一样,在信众眼中,人神关系并非是平等的、均质的,神灵的庇佑是依据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呈现出效力大小的差别。因此,他们通过对神灵的拟亲属称谓以及用亲属交往来比拟仪式实践,试图与神灵建立拟亲属的关系,进而用附着在亲属关系上的道德约束并维系着作为神灵回报的灵验。对于信众们而言,亲属关系的道德属性不仅从根源上确保了神灵的灵验,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神交往的功利性。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尽管人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惠关系,但简单地运用商品交易的原理对人神之间的关系做出功利性的评价,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人神之间互惠关系背后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及其背后的社会隐喻。
信众的实践逻辑反映出原生性的差序格局的重要影响力。在乡土中国,人们通常是遵循着血缘关系的亲疏确定交往的取向与模式,这种按照血缘关系表征的差序格局即为原生的差序。[3][p.167]尽管在现代化的当下,原生性的差序格局面临着基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利益格局的冲击,但其仍然在当下的社会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并成为影响和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如此,即便在利益关系冲击的今天,信众们仍然会通过多样化的、在地化的仪式实践试图与神灵之间建立起拟亲属的关系,其根源则在于儒家思想主导下原生性差序格局在当前社会中仍然起着的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差序格局支配着的中国民间信仰实践逻辑对于信众们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乡土中国的大多数信众们而言,神灵灵验的回报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他们在缺乏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可供诉求的唯一资源,是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支撑他们维系生活的重要源泉。信众们通过仪式实践与神灵攀交情、拉关系,进而用亲属关系的道德约束并保障着作为回报的神灵的灵验。信众们仪式行为的实质是为自己不确定的生活加上了一份保险,并为他们在经历苦难时提供精神支柱,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主要支撑。正因为如此,朝山进香、日常供奉,这些民间信仰的实践已经内化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如同亲戚之间的走动一样,他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仪式,并且每一次仪式实践都充满着期望。
杨庆堃对于中国宗教的分析,本质上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下,以西方宗教为参照,从外在形式化的特征中把握中国民间信仰不同于制度性宗教的特征。诚如杨念群所言,杨庆堃的这一分析范式并没有注意到东西方宗教的比较分析并非是一个功能结构的问题,其本质是观念的问题。[17]进言之,这种东西方宗教观念差异的核心则在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其表征便在于根植于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的神灵观及其基础上的仪式实践。包括杨庆堃在内的诸多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与西方宗教外在特征的对比中,做出了中国宗教弥散性、功利性的判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判断本身隐喻着东西方宗教之间的阶序等级。然而,无视社会结构的差异,单纯地在与西方宗教形制的对比中把握中国宗教的外在特征,显然只是一种文化偏见。
结 语
对亲属关系的模拟是中国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信众们通过对神灵的亲属称呼以及用亲属交往比拟的仪式实践,试图与神灵之间建立起拟亲属关系,进而用亲属关系的道德约束着作为神灵回报的灵验。信众们的这一实践逻辑体现出差序格局的强大影响。
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形式,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18]尤其是在现代化之前的中国社会,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原生性的差序格局更是起到了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基本准则。既往的研究指出了基于差序格局在经济生活、政治领域的强大影响。[3][p.139-163]事实上,差序格局的阐释力不仅局限于此,其更是形塑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践逻辑与仪式表征。当然,这再一次验证了涂尔干关于“宗教即是社会”的论证。
差序格局形塑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践逻辑,这使得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的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独立于西方宗教之外的存在而显现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在比较宗教研究中,“作为文明组成的基督教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宗教研究的唯一基点。”[19]就这一意义而言,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中国民间信仰具有比较宗教研究基点的意义。以中国民间信仰作为基点,并以此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或许能够丰富比较宗教研究的话语,开拓出比较宗教研究新的图景。
[1] 杨庆堃.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谢立中.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译林出版社, 2009.
[5] 罗香林.碧霞元君[J].民俗,1929,(69-70).
[6] 顾颉刚.妙峰山[C].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
[7]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 Stephan Feuchtwang.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M].London:Routledge, 2001.
[9] Adam Yuet Chau.Miraculous Response: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 Redwo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0] Roy Bin Wong,Pauline Yu,Culture&State in Chinese History:Conventions,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C].Redwood:Stanford Unversity Press,1997.
[11] Brian R.Dott.Identity Reflections:Pilgrimages to Mount Tai in Late Imperial China[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5.
[12] 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3] 金受申.北京通[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
[14] DeBernardi,Jean.Heaven,Earth,and Man:A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Spirit Medium Cults[D].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6.
[15] 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16] (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7] 杨念群.宗教功能的本土化阐释——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读后[EB/OL].http://www. 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11/494. html.
[18] 王昉.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结构特征:比较视野的讨论[J].贵州社会科学,2012,(2).
[19] Yongyi Yue.Holding Temple Festivals at Home of Doing-gooders:Temple Festivals and Rural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J].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4,(1).
Impacts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on Chinese folk religion:A study of the Pilgrims Society of Miaofeng Mount
ZHANG Qing-Ren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a that believers of a popular religion compare some kinship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s and believers.The pilgrims heading for Miaofeng Mount believe that the efficacy of the goddess varies,depending on the hierarc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ddess and the believers.The believers try to establish an intimate kinship with the goddess by addressing her with the terms of kinship as well as a connection to some religious practice like relatives'communication.They expect to use the moral obligation between relatives to ensure the goddess'efficacy.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of Chinese society shapes the logic of the Chinese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s,and helps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and ritual practices.In this sense,the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based on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a basic point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folk religion;difference sequence in mutual benefit
B91
A
1000-5110(2014)06-0107-07
[责任编辑: 黄龙光]
2014-08-20
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北京香会研究”(14WYC063)阶段性成果。
张青仁(1987—),男,苗族,湖南麻阳人,中央民族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间信仰、海外民族志。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