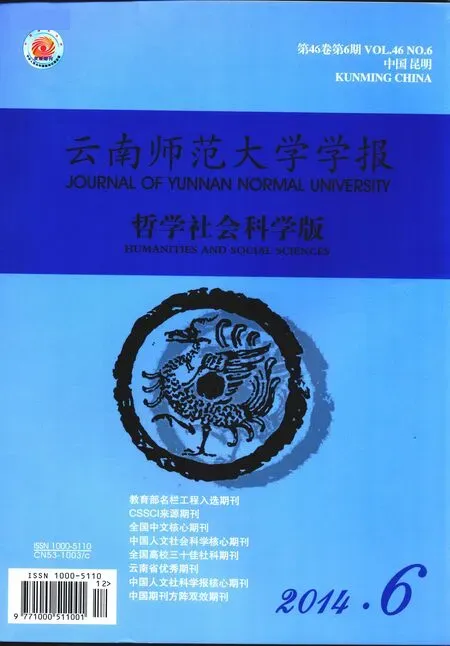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潘链钰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潘链钰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唐代因政治开明、文化多元以及经学本身的“式微”给了诗学良好的发展契机。初唐经学一转六朝浮迷虚华之气而重刚健致用之姿,文坛则强烈呼唤风骨之体。盛唐之际三教鼎立而儒学边缘,诗风则儒道禅层色皆染,颇重“意境”之论。中唐经学新变再加晚唐经学衰敝,直接导致诗论向内转的发展趋势,因而“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诗境成为风尚。唐之经学与诗学之关系给予宋明理学及后世文论极大的借鉴意义。
唐代;经学;诗学;关系
一、前贤研究回顾
诗的国度再加上初盛唐隆盛的世景使得历代对唐代诗学与经学之关系做了诸多研究。此处择要概说之。首先是对唐代经学与诗学有着宏观性把握的文章,如高林广的《试论初唐史家、政治家的诗学思想》。[1]这篇文章从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初唐诗本体、审美特性、南北诗歌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唐诗本体涉及到经学思想中的尊体意识及天道思想对诗学和诗歌的影响;审美特性则是秉持经学(尤其是《诗经》的风格)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功用意识;南北诗歌则是经学倡导的文质问题的延伸,是把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诗歌风格推向更高层面的诗学思想。高先生的文章大致代表了从宏观角度研究唐代诗学与经学关系的文章的观点。其他从宏观角度把握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之文章,其研究与高先生的观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或从社会演变之角度做了深入的挖掘,或从帝王对经学及诗学之影响上做了补充,但大致都是高先生观点的延伸,此不赘述。
其次是从五经中的单个经典对于诗学的影响这个视阈的研究。这类文章数量较多,其中尤以《毛诗》对诗学的影响这类主题为最。这大致是因为《毛诗》与唐诗都属于诗歌的苑囿,有着相似的体性与审美观照,因而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比如谢建忠《〈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与唐诗文学价值》[2]、黄贞权《〈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3]等等,都从《毛诗》的角度出发,对唐代诗歌与诗学之关系做了解析。其中谢建忠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谢先生认为“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复杂、庞大的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就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情艺术再创辉煌的唐代诗歌成就。”[2]谢先生此言言简意赅,正好将他文章的全部意思表述出来。所谓“人文情怀”乃是唐诗书写的普遍的人伦情怀,“现实精神”则是借助了诗歌“怨刺”的古老话题,“抒情艺术”则是与前两个方面紧密联系的比兴之法。它们三者都是经学阐释视域下的诗学理论,都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现实感的诗学价值观念。谢先生论述得比较清晰,唯一不足的是他把《毛诗》与唐诗进行比较说明的时候,有把唐诗推向《毛诗》特性的嫌疑。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再看黄贞权先生的《〈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就会明显地发现,首先,这篇文章是对谢建忠先生观点的延伸。黄先生直接从“情志论”、“诗缘政论”、“兴象论”三个方面将《毛诗正义》所具之思想嫁接在唐代诗学之树上。除了“兴象论”乃是唐代(尤其是盛唐)诗学的独特命题以外,试问“情志论”和“诗缘政论”放在两汉、六朝或者两宋难道不能成立吗?诗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体验,本来就具有广泛性和共通性,《毛诗正义》会标举,六朝与两宋的诗学同样标举。这样一来,用他来比附经学对诗学的影响就会显得意义不大。其次,这篇文章也犯了以上说到的拿《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简单比较的毛病。文章还认为孔颖达提出的“兴象论”对唐代诗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兴象论”本身并非孔颖达提出,且作为诗学的理论又对唐代诗学产生影响,这种看法有待商榷。
除了《毛诗》这个主题外,还有学者从《周易正义》的角度阐述经学对唐代诗学的影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且论述较为深入的是刘顺的《〈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4]此文认为作为孔颖达版的《周易正义》在唐代得到了官方的指定和认可,使得孔颖达有关“象”论的说法对唐代诗学中的“意境”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促发作用。同时,《周易正义》里强调对“易”的解释乃是“变易”,这也对唐代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致而言,这篇文章的确从《周易正义》的角度阐述了经学对诗学的影响。但孔颖达提出的象论思想并非是一种创新,早在《周易·易传》里便有了“象”的论述。更为关键的是,孔颖达的象论只是对唐代的“意象说”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至于“意境”,似乎关联不上。
从刘顺的文章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还是《毛诗正义》,作为一种经学的规范和模板,给予当时士人一种教科书式的阐述,其出发点和目的还是归因于现实和政治。这跟诗学理论提倡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经学对于诗学的影响,表面上看是经学在规范指导着诗学,但是实际上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现实指导着诗学的发展。经学只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正式的思想指导而存在。正是这种存在,才是经学对诗学的真正影响。因而在梳理唐代经学对诗学影响的过程中,首先要明晰社会现实政治以及文化的大致脉络,这种政治文化的大环境造就了怎么样的经学思想,然后再辨别经学中的哪些思想对诗学产生的影响。其逻辑应该是:
二、唐代经学和诗学略述
(一)唐代经学略说:唐初《五经正义》与中唐新经学
放在中国经学史这个大的环境里,唐代经学并不算是经学的辉煌与显赫的时代。汉至唐几百年的乱世瓦解了大汉朝苦心经营的意识形态和经学体系。因而在唐初想要建立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再加上唐代三教并立的局面,进一步加速了传统经学的意识危机。虽然“隋唐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在三教鼎立的三教关系新局面下展开的”,[5]但儒家处于释道二家的下风会带来政治统治的不稳定性。唐朝的经学家们为了缓解经学的不利局面,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唐太宗直接表示对三教的态度:“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6]“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7][p.656]“而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6]无论道释二家如何发展壮大,作为跟政治统治连接紧密的儒家思想是不会轻易被磨灭的。儒家基于与统治之紧密,其经学只会缓而不衰,不会衰而至绝。统治者的意识表现出救弊儒家经学式微的坚决,于是面对唐初现实,太宗要求统一经学文本。孔颖达《五经正义》应运而生。《五经正义》乃是一个经学文本的定本,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需要这种经学的定本,是因为当时的士人对于经学没有统一的认识。《隋书》记载隋朝“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8][p.506]可见隋代士人没有对经学的统一认识,而是各各自疑,这对于朝廷取士以及官吏选拔无疑十分棘手。《五经正义》的出现,给了士人学习的一个范本,也给科举考试一个统一的而规范的文本,这对于政权的稳定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五经正义》实际上还标志着古文经学的胜利,更意味着南学的胜利。“隋统一天下后,经学之所以统一于南学,其根本原因乃是南学代表了经学的发展和进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顺应了这一经学的发展趋势。”[9][p.730]皮锡瑞说唐代的经学乃是“大统一的时代”,还说《五经正义》乃是“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0][p.198]皮锡瑞盛赞《五经正义》的功劳,可是人们忽略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大一统的经学时代意味着没有突破和创新,只有守成和沿袭。从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并非是好事。“以疏不驳注为特色的五经正义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因此他虽然实现了对经学的统一,但同时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系统的终结。”[11][p.24]《五经正义》反映出唐初渴求经学统一的心愿,但此书编撰完毕后不久就遭到唐人的诸多非议。于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详定是非,事竟不就。”[7][p.962]唐人这种对一统与尊汉的经学思维已经表示反感,这已经展露出唐人欲寻其他经学路径的端倪,同时也标明唐初义理经学和理性主义思潮的逐渐兴盛。
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以外,唐代还能提及的便是中唐的新经学。新经学形成之原因首先是唐代社会因为安史之乱而发生了的巨大变化亟须重新建立经学体系。其次是中唐经历了魏晋几百年的动乱、盛唐的兴隆和安史之乱的残酷,唐人的心灵亟须安慰和满足。恰好此时禅宗应运而生,给予了士人“禅式抚慰”,随之而来的便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为代表的新经学迅速发展起来。新经学对当时的社会价值和经学发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唐代这种处于经学转向理学阶段的新经学自然会遭到后世的种种评论。我认为,新经学促进了经学由汉学转向宋学,促进了经学中“理”的阐发和认识。新经学之“新”义正在于此。但是今天看来,他的不利因素则是压制了原本春秋学中所含有的“遵从史实”的精神,导致史学只言义理和尊王重天,这是在侧面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实体。
要而言之,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和唐代统治的特性导致了唐代经学偏重经学文本的统一,也促发了唐朝后期义理经学的发展。这些特点对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唐代诗学理论特色总览
唐朝是诗的国度,诗坛苑囿里的诗学理论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唐代诗学理论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诗学理论远滞后于诗歌创作,但诗学尤有建树。这是唐代诗学的不幸,却是唐代尤其是盛唐诗歌的大幸。“盛唐之所以令诗歌恰逢其时,又因为这是一个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盛唐诗人对于诗歌虽有自觉地追求,却没有系统理论的约束;对于时代虽有认真的思考,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盛唐诗人所有的这些性格,乃是属于纯诗的品质,因而最高的诗必然出现在盛唐。”[12][p.1]二是诗学理论形式多样,且别具诗性。唐代诗学理论形式只有四种:诗学专著、诗选、序跋书信以及论诗诗。诗学专著比如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的《诗髓脑》、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等。这些作品重在对声律、作家、作法、创作等做出论述,即使没有成体系,但客观而言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至于诗选,则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点评精到,多重兴象,较有建树。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因提出“风骨说”而极有影响,则是序跋书信类的杰出代表。论诗诗则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堪称佳作。尤其是论诗诗“这种将理性思维借助感性形式加以表现,利用或叙或议的诗境扩大读者想象空间的形式,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信息”[13][p.4]三是创造性的把握诗学范畴与核心价值。唐代主要诗学范畴有“风骨”、“意象”、“意境”、“韵味”、“属对”、“声律”等等。“风骨说”最早由刘勰提出,它作为一种诗风则由陈子昂及初唐四杰引领,着重诗歌与作者生命力的关系,意在一扫六朝的浮华淫靡诗风;“意象”是盛唐诗坛中别具特色的诗学理论,讲求诗歌意融于象的创作高度;“意境”是王昌龄首倡且被盛唐诗人发挥到极致的诗美理论,讲求诗歌意在言外的审美空间;“韵味”是司空图对唐代诗学的特殊贡献;“属对”和“声律”则是唐人对近体诗做出的总结性探索。这些诗学范畴是唐代诗人学者几代人辛苦总结的诗学理论,直接为六朝诗学向两宋诗学过渡搭建了一条特色桥梁。
三、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新论
中国经学自古就有着“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14]“通经致用”之经学精神跟现实政治和文化策略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在论述唐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时,我们会紧密结合唐代政治与文化之大致情况,力求圆照经学对诗学之影响。大致而言,唐代经学对诗学之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唐初致用救弊之思推动了风骨说的发展;二是中唐经学新变引动诗学思维向内转的态势,催生出“象”与“境”的之诗学视阈的内向追求;三是《五经正义》之修辞观对唐代韵律说的影响。前二者为宏观上的把握,第三者为个案的推演,下面分别述说之。
(一)“经”之致用与“风骨”救弊
唐代统治者有着少数民族的血统,思想上并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限制。正因如此,他们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力度没有汉代那么大,整个社会显得开明而通融,跟汉代知识分子明显感觉到的压抑和逼迫感截然不同。从经学领域可以看出,整个唐代并没有极力强调经学的建设和思想的控制。除了唐初为了救治隋代乃至六朝遗留下的科举问题因而命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以外,唐代在初、盛两个阶段,几乎没有具有影响力的经学著作或者经学大家出现。唐初《五经正义》只是为了人才选拔,且实际上并未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且中唐和晚唐的经学新变只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于经学史而言,意义也不大。正是唐代统治者宽松的文化控制力,因而唐代诗人可以随意地发挥想象和热情,创造出举世辉煌的诗歌气象。
唐初政治文化的宽松,导致经学思想控制的宽松,诗学领域的限制渐少,没有力求歌功颂德之政治要求,而诗坛面对六朝以来的浮靡之风则可以有力地呼唤新的诗学风尚。再加上唐初太宗及君臣提出融合六朝以来南北诗风之政策,[15][p.38]给了“风骨说”良好的萌发土壤。唐初诗学中的“风骨”理论正是在此种态势下产生。正如毕万忱所言:“(陈子昂)立足初唐诗歌创作的实际,回顾诗歌发展的历史,肯定以《诗经》、汉、魏古诗为代表的优良传统,批判晋宋以降,尤其是以齐梁体诗为标志的浮艳柔弱诗风,继承前人的某些诗歌理论主张,顺应唐代社会发展的需要。”[16]“风骨”说自刘勰始,其内涵有二:一是求作品刚健有力,二是反对文辞浮华藻饰。至陈子昂则在此内涵中,又明确呼唤文质兼备的诗学新风。陈子昂此说明显针对六朝文风而言,但我们仔细回想孔子之文学审美标准就会发现,陈子昂所谓之“风骨”的内涵竟与孔子之审美标准极为相似。孔子提倡“辞达而已矣”,无须过分装饰,儒家“天行健”之人格精神则是众所周知,而孔子“文质彬彬”之诗学理念也正合陈子昂之诗学旨归。如果说陈子昂之“风骨论”只是在唐初包括四杰在内的少数群体的呼喊的话,那么到了殷璠之“风骨论”,则成为一种全局的共识和诗学理论上的自觉总结。殷璠之“风骨论”相较陈子昂“风骨论”中之济世救民、以身许国的志向,更多的乃是一种朝气蓬勃、新鲜生动的“青春的歌唱。”这正是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的本质。不仅陈子昂之“风骨论”,其“兴寄说”也是经学致用的另一种表现。以诗言志与以文兴寄向来是儒家文士内表情外书愤的普遍方式。这种兴寄,超越了传统比兴内涵之范围,更多的带有一种致用性的兴寄,是要有托于事与有为于世的儒家担当精神的化身。这跟前文所谓“风骨”大体乃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不赘言。
由上述可见即使唐初《五经正义》之编撰并未直接对唐初诗学产生效用,儒家及经学内在的影响还是一直存在。表面看来,唐代诗人可以因为统治者文化控制力的减弱而随意发挥,但是我们看到有识之士并未因此而“离经叛道”,一改儒者风范而重堕六朝淫靡诗风,而是强烈地倡导儒家刚正之风,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经学的影响力,或者说是儒家“通经致用”这一思想的影响力,是经学“经营”之根本大旨的潜在作用给予了历代士人无限的动力去构建儒家勾勒的蓝图。这一点,是以前学者没有提到和关注的。无论唐代统治者如何不重视经学的建设或者思想的掌控,他们无法抹去自先秦以来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加上唐代士族是不同于汉代平民的阶层,他们了解儒家文化,又具有一定的言论权力,“通经致用”的文化传统与“学优则仕”的进取精神潜在地激励着他们勇敢地对现实加以干预和支配,尤其是在唐代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加促进他们发挥不断致用的儒家精神。儒家文化这种先天的暗合性始终浸透于华夏民族的文化之根里,不会轻易被替换掉,战国风云汹涌没有灭绝儒家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六朝淫靡没有抹杀儒家的进取精神,唐代更加不可能,即使唐代是三教并立的时代,儒家也不会因此而消沉。
(二)“经”之新变与诗学内转
唐有初盛中晚之分,这已是共识。其实简单说,唐之分期只有两端:前之隆盛,后之衰颓。自安史之乱,唐王朝国力急剧下滑,中央与藩镇,唐与周边矛盾重重。大一统之世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悲凉与衰落。这是政治上中唐的大致景象。文化上,初唐《五经正义》的撰毕给了士人经学的典范,但随着《五经正义》之缺弊逐渐显露,盛唐后期一股疑经思潮悄然涌动。纵观整个盛唐,惟则天朝一直强调的忠孝之道被玄宗继承而发扬,但忠孝之倡导实则带有封建统治愚民之嫌。且中唐之现实击碎了经学的典范形象,士人意图挣脱汉代以来经学之束缚的举措越发明显。三教并立的局面虽给了唐代社会多元的价值体系以及开明的统治策略,但道释二家对儒家的“排挤”,一方面使得经学式微而诗学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也给中唐诗学的内转做好了铺垫。
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对《三传》之驳斥,掀起一股冲决经学藩篱的浪潮。虽然遭到四库官臣的严厉批评,但是可以想见这三人者确有新变之果敢。他们注重从经书中去阐发义理,已经是宋学显露的征兆。中唐韩愈“道统”之论与李翱“复性”之言,对批驳社会之黑暗无甚作用,二人之思想却抬高了《大学》、《孟子》、《中庸》于儒家经典中之地位。尤其是李翱之援佛入儒之心性论,直接是宋代理学心性的先河。当然,这些所谓“开宋代理学之先河”云云须至宋方能缕析明了。在中唐这个时段里,经学的此种发展态势,造就了中唐诗学向内转的明显特性。
世风变则经学变,经学变则诗学变。经学与诗学作为同是主导儒家致用精神的文化载体,自然会对世风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至死不渝的救赎意识。中晚唐国力的锐减,导致社会矛盾丛生,经学无力统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而释道二家之道已经渗透到士人内心,酝酿出有别唐前期清刚雅健的“风骨”之论的新的诗学风尚。
1.经学式微与“象”、“境”凸显——诗阈内转
士人心态在中国三教文化里总是做着“儒——释道”两种模式的转化。政治清明则士人欲行致用,政治黑暗则士人归隐内心。中晚唐之社会现实,造成经学分崩离析的局面,这种理性的丧失,导致中晚唐经学的疑经、改经行为比比皆是。既然经学整体无力自救,而现实分明不再需求风骨之诗学,中晚唐之诗人们普遍“顺应”现实境遇将重心放在了非现实的内心世界。在诗学视阈上,他们由外向的追寻诗气的风骨清峻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诗歌内在的“象”与“境”之上。“象”是《周易》就有的言说,“境”则自佛理中来。盛唐王昌龄“意象”、“意境”的发现,本是承刘勰、钟嵘之情景交融之理论而来。盛唐山水诗,是在六朝山水诗发展基础上的更大的突破,融情于景的诗学境界超越了六朝模山范水的单面思维。这本是诗人对诗歌描写自然风景时融情入景的正常视阈。可到了中晚唐,“象”与“境”不再单独表征诗人之现实世界,而是有着现实之外的诗境空间,也就是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境外之境”。意象之本义在诗意层面而言,本来就具有双重意思,“词义是一层意思,词义之外还有一种意思,而这种意思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17]“‘境’是对于时间上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境’当然也是‘象’,但他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趋于无限的‘象’,也就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常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境’是‘象’和‘象’外虚空的统一”。[18]这种“意外之意”其实就是中晚唐诗人追求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而这种象外求象、境外寻境的思维模式,不得不说乃是受佛教三生三境的宗教思维的影响。盛唐诗人是没有主动构建诗歌意象之外的世界的,他们或豪放或清丽,主要着眼于眼见之物,而对内心细腻的诗境没有太多关注。而中晚唐诗人却对内心世界有着极为深入地挖掘。晚唐诗人李商隐,那种朦胧哀戚的诗歌,让诗本身的现实层面变得迷离,也正是诗境外之境的诗学追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诗阈内转及诗学对“境”“象”之追求的直接原因乃由佛道而非儒学(经学),但其根本与底色却仍然是儒家经学。孔子有“绘事后素”之言。无论诗家如何深入释道二家探其艺旨,其诗心之根仍深埋于儒家之壤。因而纵然司空图有《诗品》妙言境外之境,象外之象,其文仍以足具儒家刚健之风的《雄浑》为首则足以证明,其“境”“象”诗心仍是儒家经学之心,只是此刻经学与诗学之心,已有了明显向宋明理学与心学转变之痕迹。
2.以道济儒与“味”的强调——诗美内转
中晚唐政治衰敝,经学式微,诗人身心双隐,诗人因社会动乱而无致用之思,规避内心的无奈之举使得他们将目光投向任性虚无的道家,这是中晚唐诗人的普遍倾向。韩愈以佶屈聱牙之言辞入诗,实际在潜意识里就是对儒家“文质彬彬”之诗美标准的消解。白居易诗歌浅显易懂,已经脱离了典雅神韵的盛唐风范,为走向诗歌“平淡”的美学风格做了铺垫。皎然的诗歌与诗学充满着佛家理、格与境的追求,标志着诗人们规避内心之旨归已然刻骨,而晚唐司空图“四外”之说,直接纳儒家天地境界、道家自然虚空之旨与佛家杳渺之思于一身。赵德坤先生言道:“‘韵味’的内涵当与‘滋味’相近,指向文本的语言形式之美,显然这已经不是司空图关注的主要方面,他将兴趣投注到语言之外更为辽阔广远的意义视域。这一境界已然超越了人的理性的逻辑思维,进入不可思议的地段,实际上与道家的本体境界儒家的天地境界和禅宗的真如境界接壤了。”[19]这种三教合一的境界旨归,显然是儒家审美之柔婉的一面无限地接近这释道二家的美学宗旨。晚唐儒家经学的凋敝可见一斑。经学的“致用”荡然无存,儒家的“兴寄”之途闭塞,而“风骨”、“刚健”流于无用,正是晚唐文化格局的真实写照。
儒家经学提倡之雅健与风骨,被道家“味”的追寻代替。这种明显的“以道济儒”的思维表现在诗之审美标准上,则是“韵味说”的出现。钟嵘曾提“滋味说”,但司空图之“味”已经不是“滋味”了,而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种“言外实内”的味觉诗韵,明显有别于钟嵘之说。他不是眼前的诗歌的味道或者风格,而是一种恍惚朦胧的抽象表征,是由鲜活之象通往无限之“道”的,是老子所谓无味乃是大味的至味之旨。“味外之味,景外之景,象外之象,都是‘道’的表现,同出而异名。”[20][p.277]司空图“韵味说”的道家意蕴不言自明,而这种韵外之味,则是侧重于视听之外的更为虚化的空间。但这并不代表道家消解了儒家的审美标准,晚唐道家审美标准的泛化只是士人“借道补儒”的暂时性策略,儒家融刚健婉柔于一体的美学思维并非轻易能被释道二家取代,正相反,道家这种对“韵外之味”的追求在晚唐之后渐渐被儒家审美吸收,与宋代偏于“筋骨思理”之诗风融合,苏轼承袭而提出“至味说”。而从大局而言,则是宋人由此创造出平淡自然、雅理深健的宋诗气象。
3.经注义理与“理”的萌发——诗情内转
中晚唐经学注疏一反唐初《五经正义》“疏不破注”的原则而主张注入义理的阐发。这种一反《五经正义》尊崇汉本的经学思路最开始又是从疑经疑传的举动开始的。啖助曾直言“左传非丘明所作,《汉书》丘明授陆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亦皆附会。”[21][p.210]赵匡亦疑此,曰“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22][p.406]这些疑经疑传的言论标明汉学的松动,而韩愈提升《大学》《中庸》之地位,且对之采用寻求义理的阐释方式,其实正是义理学之雏形。韩愈论道德修养,则谓“圣人抱神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不善之心,无自入焉。”[23][p.189]还说“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7][p.2864]这些言论很明显充满着义理阐述的口吻,而不再是汉学字句训诂考释的模式,连李翱的《复性书》都充满着心性之学的论述,可见汉学向宋学之转化已经势在必行,也可见宋学之端倪在中唐人那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身影。
正是解经思维的转换,中唐以后之诗人也逐渐转化了诗情的要求。风情神韵不再是他们的追求,“以理入诗”则成为诗情新的创作焦点。当然,这个“理”有着儒家济民的不平之“理”,也有道家虚空尚任的自然之“理”,还有禅家自性了悟的佛缘之“理”。诗情诗格的内转趋向以及以“理”为重的现象比比皆是。杜甫论诗诗就有着诗情转变的趋向,他直接将议论、批评带入诗中,全然不用神韵意境的营构而直接点出心中之理。皎然极重诗格之“情”与“格”,而对诗体诗风的细致分类本身就是一种对诗情与诗格掺入理的思考与辨析的表现。何况皎然擅长以玄虚微妙之言论诗,一如禅言偈语,正是开了后来以禅理论诗的先河。韩愈弟子李翱,极其强调文章与诗歌内容的纯正和词章之工整,更推崇义理和文词兼善的诗学主张,“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必能传也。”[24][p.2840]
“理”的“泛滥”,也直接标志着诗格的转化。而这一转化,当然自韩愈开始。[25]韩愈诗中理的成分的增加标志着诗格之转化的趋势已不言自明。唐人声韵格调的创作技巧,不再需要随意性的抒情表达,而转向诗中理与趣之相协带来的厚重的美感。而这层厚重的美感却又在晚唐及宋人那里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平淡”的外衣。在这样几个方面的改造中,“理”的愈发壮大成为诗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唐代经学的相对式微加上佛教及时提供的优秀的学理思维,都直接促进了唐代由诗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化。这也是为什么跳出唐代的时代圈子,站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学者会将唐代的经学作为一个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化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假想,如果唐朝没有灭亡,如果没有宋朝,那么唐代经学就不存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历史和时间会给唐朝充分的转变时间,诗歌的领域为了寻求新的体裁和境界,则会自觉地向理性、议论的方面发展,那么宋朝才会出现的议论诗、说理诗,早在杜甫及韩愈之后大放异彩。而“唐代”的经学则会明显地走上理学的道路,不必等到宋朝才得以完成。当然了,历史不容许任何的假想,唐代只是完成了经学的一统局面和诗学的境界开阔,诗歌造就了盛唐的气象和向理学转化的过度。这种诗学格局,说到底还是唐代政治与经学的直接影响。要而言之,唐代经学的这种“不自觉的式微”,带给了诗歌和诗学“道释化”的机会,又给唐代诗人极大的审美自由,这不仅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唐诗气象,而且造就了唐代专有的诗学特色。
(三)《五经正义》修辞观与唐诗韵律说
《五经正义》之修辞观早已被学者注意,石云孙先生有《孔颖达修辞理论探》一文专门研究《五经正义》之主要编撰者孔颖达的修辞观。[26]石先生分二十项对孔颖达之修辞观做了梳理,确有草创之功。我认为,作为五经正义的主要编撰者,孔颖达之修辞观很大程度上就蕴含在《五经正义》里面,这种统筹的经典编著必须是统一的思想认知才能做到,因而五经正义之修辞观等同于孔颖达之修辞观应该无疑义。《五经正义》从官方指导思想的层面对文化界进行了规范。对于诗歌和诗学而言,唐人的“规范”更多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声律、对偶、句法、结构和语义的要求上。”[27]本节主要论述的是《五经正义》之修辞观对唐代诗歌韵律之影响。
《五经正义》之修辞观大致有20个方面:变文、便文、对文、省文、互文、重言、倒文、足句、协句、韵句、配文、篇章句、文势、文次、张本、发文、覆说、结之、蒙上文、通下文、作文之体、随事为文、甚言、假言、比兴,一共20项。其中涉及对唐诗韵律的主要有:变文、对文、倒文、韵句、甚言、比兴等6个方面。当然,这6个方面或许会因研究角度的差异而在不同学者那里显示出不同的认识。这是学术角度的差异,不妨碍本节之研究。要而言之,变文、对文和倒文乃是对诗体的论述,而韵句、甚言、比兴则是对诗法之研究。
变文、对文和倒文对唐诗格律说之诗体规范有重要指导意义。变文是说文章诗歌之中不宜有相同一字的重复出现,若须用字,则应变而用之。南朝沈约已有“八病”之言,其中的触绝病即与此类,因而在作诗之时,须严格避开同字或同韵。我们看在唐代诗歌中很少有一首诗里同用二字的例证,即使崔颢之《黄鹤楼》前三句用三次“黄鹤”却不妨碍其成为名诗,但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诗词忌用同字乃诗家诗体之法则,六朝至唐之诗人对之多有研究,因而影响到唐人诗学格律之说,不算新奇。对文,则是中国诗性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六朝骈文的对仗直接给了唐诗以工对的经验,而唐之工对不同于六朝则在于唐之工对无六朝有意为之之痕迹,且诗之对文绝少于骈文之对,因而能有一二争奇之句,则能锦上添花,倍增全诗精神。唐人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之《诗髓脑》对属对颇有研究。至于倒文,自《诗经》即有,诗经之言说自然也给后世诗体起到借鉴作用,但唐人之倒文运用的娴熟,以至于在不破坏整体诗美的同时还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杜甫对中唐之诗歌格律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而唐人倒句中又以杜甫倒文之手法高妙,至宋则王安石偶有天然之句。
韵句、甚言和比兴也是《五经正义》之修辞观对诗学之诗法产生影响的重要部分。韵句之研究,早在明杨慎和胡应麟则有研究。韵句在六朝已见端倪,且六朝之韵句多似后来唐之韵句,可见其影响。东汉佛学之传入,翻译之间偶见汉字韵律已是共识,《五经正义》于此重视,乃是因为诗文不同史志,协律可歌方得韵味无穷,因而“正义”之特别强调无疑也推动了韵律之发展。唐初以沈宋二人之韵律研究为上,对律体之成型贡献极大,赵翼《瓯北诗话》云:“汉魏以来,尚多散行,不尚对偶。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已为律诗开端,沈约辈又分别四声,创为蜂腰、鹤膝诸说,而律体始备。至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于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28][p.502]甚言者,夸甚之言也,亦即夸张。格律诗之创作中夸张的运用很大,大致是因为唐人有着想落天外的丰富情感,李白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李白式的夸张给了唐代近体诗一种修辞的范本,其融合儒之刚健与道之缥缈的夸张方式赢得诗歌史之赞誉。至于比兴,则是自《诗经》始早有的诗法,此处之所以提及,乃是想要点明五经之重视比兴跟唐初经学建设和世风转变有极大的关系,唐初经学建设和世风之变,呼唤的是有“风骨”与“兴寄”之诗歌,而风骨与兴寄往往跟比兴之手法紧密相连,正是“经营”之需要,比兴之手法在中国诗学历史长河中才永不衰绝。
四、唐代经学对诗论的影响对后世文学文论之意义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隆盛之世的唐代,其具有一代之特色的文论必然受到经学之影响。而此种影响在唐后仍有余波。对后世文学文论的规范与发展有极大的意义。
首先,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压迫的文化政策是唐代经学与文论关系良性发展的温床。对于后世文论而言,经学的制约性始终还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而经学制约性的力量来源还是政治的指引。唐代开明的政治氛围、宽松的文化管制以及多元的文化影响造就了唐代诗歌与诗学的独特魅力。这种范式虽然没有在包括两宋在内的王朝获得生命的延续,但是他的典范性还是在文论史与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其次,唐代文化的影响力比政治的直接干预更能对经学与文论产生效用。唐代统治者表面推崇释道二家的背后,仍然是儒家思想占据社会的主流。这里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更是华夏民族特殊的环境造就的民族性格。儒家文化潜在的影响力绝对胜过讲求隐逸自然之风的道家,也胜过四大皆空、无为无治的佛家。但是佛道二家并非对政治统治一无是处,佛家的“空”与“善”的思想能够减少社会矛盾,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则能宽慰士人的心胸。唐代三教鼎立的多元文化恰好是在统治者的有意识的管理之下呈现出开明开放、多元交融的局面。这种局面虽然表面上削弱了经学的影响力,但是经学思想在释道二家融合中也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诗论上则产生了心灵之境的新领域的阐释理论。这些都是唐代文化影响的结果。宋及明清没有这种文化环境,因而与唐代的经学特色和诗学个性不太相似。
第三,中唐社会的巨变带来的经学及文论的转变再一次印证了经学直接受到政治影响的事实,也再一次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经学发展来说的重要性,也说明文论对于政治和经学发生变化的敏感。通过文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原本通达开明、风骨硬朗的外向式诗学阐述,经过安史之乱的搅扰及政治的衰敝,变成内心狭小委暗、愁怨哀思的内向式诗学探索。中唐韩柳的“道统论”充满了重建稳定经学与道学的迫切感,元白的平易诗风没有了盛唐的华美气象,晚唐司空图的韵味探索以及象外之象的论说充满了对现实逃避、渴求境外之境的嫌疑,而“郊寒岛瘦”的凄美更是说明了盛世之后经学诗学与文论的种种怨伤性格。唐代社会越往后发展,经学讨论的气度就越小,诗学阐述的口吻就越悲悯,连诗歌都充满了惋惜和哀怜,唐代社会的晚景正好被李商隐委婉地说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第四,唐代逐渐走向理学化的经学直接影响了诗论走向理学化的诗论。关于经学理学化的源头,其实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六朝时期玄学的理化思维加剧了儒释二家的融合。玄学本来就有着说理性的特点,这种说理性的思维一旦运用到儒家经学层面,自然会对经学的阐述方式和思维模式产生影响。唐代孔颖达融合南北经学而编纂的《五经正义》就继承了六朝玄学化思维的理学套路,这种官方修订的大一统经学的模板更能促进理学的不断壮大。经学的理学化直接影响了诗论的理学化。中唐以后诗论都有着理学的影子。皎然、司空图所谓“境”、“韵”、“味”等,皆虚由义理阐述而直通诗论内涵,若以寻常考据析之,何能领悟文旨。至两宋随着传统章句之学的逐渐衰退和理学的不断壮大,经学表现出明显的义理的特点,而大量诗话的出现又正好是经学理学化影响诗学理学化的证据。诗话这种体裁具有的自我阐发观点的方式正是随着理学家可以随意阐述经典义理的不断完备而快速发展的。不过正如六朝经学有南北之分、又有南北融合的特点,理学在暂时战胜传统经学之后,一定会反过来重新吸收传统章句之学的特色,也会走向一条融合的道路。这种轨迹恰好在经学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印证。
[1] 高林广.试论初唐史家、政治家的诗学思想[J].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5).
[2] 谢建忠.《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与唐诗文学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2007,(3).
[3] 黄贞权.《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J].船山学刊, 2010,(2).
[4] 刘顺.《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J].江淮论坛, 2007,(5).
[5] 洪修平.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2003,(6).
[6] 吴兢.贞观政要·慎所好(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刘昫.旧唐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8] 魏征.隋书卷七十五[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9] 姜光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吴雁南.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12] 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14] 汪高鑫.论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J].安徽大学学报,(2).
[15]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6] 毕万忱.论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传统特质[J].文学遗产,1990,(8).
[17] 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8] 叶朗.说意境[J].文艺研究,1998,(1).
[19] 赵德坤.韵味说疏正[J].文艺评论.2013,(2).
[20]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21]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22] 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23] 韩愈著,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24]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5] 刘崇德.诗格之变自韩愈始[J].大连大学学报, 1991,(1).
[26] 石云孙.孔颖达修辞理论探[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5,(7).
[27] 张伯伟.论唐代的规范诗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28]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s and Confucianism of the Tang dynasty
PAN Lian-yu
(School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Because the Tang dynasty advocated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nfucianism was on the decline,poetics enjoyed good development.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xperienced a shift from the florid style of the Six Dynasties to a vigorous and practical style.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saw the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three religions though Confucianism was somewhat marginalized.The poetics in this perio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mages.This shift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directly led poetics to turn inwardly.Thus,emphasis on the rich implications of poetry was in vogue.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etics and Confucianism of the Tang dynasty shed much light on Neo-Confucianism and later literary criticisms.
Tang dynasty;Confucianism;poetics;relationship
I22
A
1000-5110(2014)06-0090-09
[责任编辑: 杨育彬]
2014-05-23
2012年度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阶段性成果。
潘链钰(1988—),男,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