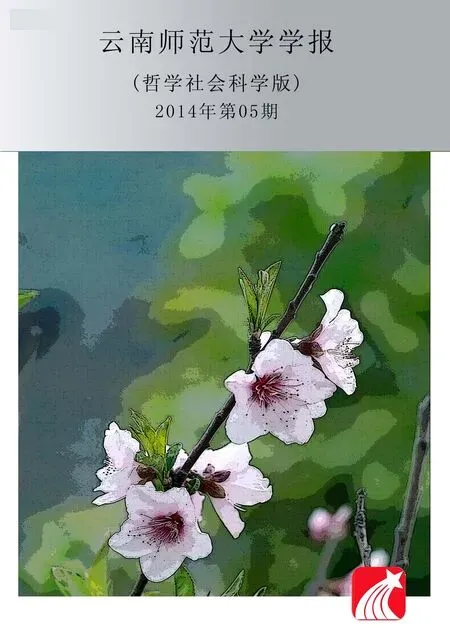旅游吸引物权的表达与实践*
辛纪元, 曹务坤, 吴大华
(1.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2. 贵州师范大学 团委,贵州 贵阳 550001; 3. 贵州财经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之提出
近年来我国各地旅游纠纷频发,有些旅游纠纷甚至演化为群体突发事件,如湖南凤凰门票事件、甘肃黄河石林景区村民围堵游客入口事件、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景区村民与景区工作人员打架事件、广西桂林“龙胜脊梯田案件”、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件”等等。旅游纠纷问题已成为旅游学界、社会学界及法学界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如倪家宁(2013)[1]等调研和分析了湖南凤凰门票事件,旅游管理学界的学者保继刚、左冰(2012)[2]从旅游吸引物权的维度反思旅游纠纷产生的原因,探讨旅游纠纷的解决,试图为旅游资源开发扫除障碍,从而推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其根源在于旅游吸引物权——这种由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旅游吸引价值转化而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及其权利——至今尚未被大众所认识、被法律认可。”“本文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指出旅游吸引物权存在的现实性以及对其确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进一步厘清农村土地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的角色和权利,提出可能的土地制度改进方案来突破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以助于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保继刚和左冰所提出的“旅游吸引物权的立法”的一些观点,如保继刚和左冰主张在《物权法》的第二篇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直接补充以下条款:“物之旅游吸引孳息(即本文所称旅游吸引物权),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张琼,张德淼分别在《旅游学刊》和《法治研究》对“保文”进行了批判,并提出解决旅游纠纷的一些建议。“本文将以物权法为视角,论证旅游吸引物权的复杂性与统一立法保护的不合理性,并就‘保文’作者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商榷,同时主张运用《合同法》、《旅游法》等现有法律与解释、分析、解决农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冲突。”“通过分析旅游吸引物权属性可知,现有《物权法》对‘保文’所提旅游吸引物权皆有相应规定,再为此单独特征法律或设立新的法律概念实属立法资源浪费”。
他们的观点为什么截然相反呢?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相左的根源乃是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乃是对旅游吸引物权的表达不同,对旅游吸引物权的实践之理解和诠释不同。保继刚、左冰是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解构“旅游纠纷与旅游吸引物权”内在关联性,重构农村社区的旅游吸引物权在《土地法》和《物权法》中的地位,他们认为,确认农村社区的旅游吸引物权,修改《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扩大农村社区财产权。张琼,张德淼(2013)[3]却是从概念法学、规则法学及物权法理论等视角检讨和反思旅游吸引物权的统一立法和整体立法问题,认为解决景区冲突问题的法律建议并非是设立旅游吸引物权而应保障旅游开发合同,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对合法“旅游吸引物”类型化,并明确旅游吸引物的权属,以便更好地保障相应主体的合法权益。
虽然他们的观点相左,但是他们对解决旅游纠纷的路径——旅游吸引物的确权和旅游吸引物权的类型化形成了共识。张琼、张德淼在《“旅游吸引物权”整体立法保护质疑》一文中改变了《旅游吸引物权不可统一立法之辨析》一文中不赞同保继刚和左冰所倡导的解决旅游纠纷的路径——旅游吸引物的确权。由此可见,从旅游吸引物权的视角探讨旅游纠纷解决,这已成为旅游学和法学共同研究的课题。旅游吸引物和旅游吸引物权是什么?如何在法律中表达旅游吸引物权呢?旅游吸引物权如何在法律实践中运行呢?本文拟从法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作尝试性探析。
二、旅游吸引物
(一)旅游吸引物的概念
纵观旅游学术界,对旅游吸引物的概念的界定和诠释,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西方学者从系统论的视角界定和诠释了旅游吸引物的概念,他们认为,旅游吸引物是一个建构的系统,它由旅游者、核心吸引物和标识物三要素构成,包括吸引物本身、人为建构的信息和符号。“西方的研究表明:旅游吸引物不仅是天生的或历史的遗产,也不仅仅是指旅游吸引物本身,它更是一个建构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旅游者、核心吸引物和标识物。”[4]“而Leiper(1990)则从构成要素的角度把吸引物定义为包括三要素的体系:游客或人的要素、中心或核心要素、信息或标识要素,当这三要素相结合,就形成了旅游吸引物。”[5]Law ton从管理者和旅游者的视角界定了旅游吸引物的概念。“Law ton(2005)指出吸引物是吸引管理者和旅游者的注意力的,有特殊的人类或自然界特征的知名事件、遗址、区域或相关现象。”马凌(2009)[6]从文化学的视角界定和诠释了旅游吸引物的概念。“旅游吸引物符号的3种形态(标志符号、文化符号和群体符号)在旅游活动中常常同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首先,文化符号是标志符号的源泉,后者由前者抽取部分信息后社会建构而成;其次,标志符号作为‘能指’,指代相应的文化符号(所指);最后,富含情感能量的标志符号或文化符号被投射到旅游群体之上,形成群体符号。”林红,王湘(1998)[7]从心理学的角度界定了旅游吸引物的概念。“在现实条件下,能为旅游业所利用,并且能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吸引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一切自然客体与人文因素的总和,统称为旅游吸引物。”胥兴安、田里定义列举的视角界定了旅游吸引物的概念。“胥兴安、田里结合旅游三要素认为,旅游吸引物是一种能吸引旅游者的综合体,它不仅包括了旅游活动的客体——旅游资源以及以此为中心开发出来的核心旅游产品,还包括了旅游活动的媒体——旅游业以及与核心旅游产品一起构成的组合旅游产品”。
秉着“求同存异”的理念,在吸收以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法人类学的维度,运用归纳法重新界定和诠释旅游吸引物的概念。虽然以上学者界定和诠释旅游吸引物的视角不同,对旅游吸引物的概念的界定不同,但是他们对旅游吸引物的界定和诠释的目的具有趋同性,即界定和诠释旅游吸引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业,而旅游纠纷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子,旅游发展成果的分享问题是旅游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法律制度是旅游发展成果分享和解决旅游纠纷的根据,因此,从此意义上说,很有必要从法学的维度界定和诠释旅游吸引物。物的控制性、价值性、物的主体特定化、人格化等法律意义上的特质,所以从法学的维度界定和诠释旅游吸引物的概念时,应该融入它的特质。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对旅游吸引物的概念作如下界定。所谓旅游吸引物是指旅游景区、景点为游客所提供的需求。
(二)旅游吸引物的本质属性
旅游学界的一些学者探讨了旅游吸引物的本质属性,在此仅列举一二例,并不对其评述,只是试图从法学的维度思考旅游吸引物的本质属性。“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旅游吸引物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旅游吸引物是相对于游客而言的吸引力课题,其吸引力可以分为绝对吸引力和相对吸引力。绝对吸引力来源于旅游吸引物的某种特殊的客观属性;而相对吸引力则来源于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属性,即该客体成为旅游者价值认同的符号”。[8]
众所周知,旅游吸引物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而按照传统民法理论,民法调整财产和人身关系,依据排斥法原理,旅游吸引物要么属于财产,要么属于人身关系,显然,旅游吸引物不是人身关系,既然不属于人身关系,就应该属于财产,进而言之,旅游吸引物的本质是民法领域的财产,是集合财产,即旅游吸引物是由不同性质的有形物和无形物构成。
(三)旅游吸引物的特征
事物特征是来自比较,比较就必须要有参照物,根据“就近原理”,选择我国民法中的“物”作为参照物。与我国民法中的“物”比较而言,旅游吸引物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具有无形性。我国民法中的“物”仅是有形物,而旅游吸引物包括旅游吸引有形物和旅游吸引无形物,所以说旅游吸引物具有无形性。第二,具有复杂性。由于旅游吸引物由旅游吸引有形物和旅游无形物构成,有些旅游吸引物的主体属于集合主体,有些旅游吸引物的主体不明确,所以说旅游吸引物具有复杂性。第三,具有集合性。旅游吸引物的集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旅游吸引物不是单个的物,而是由N单个的物抽象而来;另一方面是旅游吸引物的主体是共有主体。
三、旅游吸引物权
(一)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
张琼、张德淼等学者虽然探讨了旅游吸引物权的立法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界定和诠释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对旅游吸引物的认识并没有形成共识,旅游吸引物和旅游吸引物权极其复杂等。而保继刚、左冰(2012)[2]对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的理解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旅游吸引物权的外延太窄,仅把旅游吸引物权界定为:旅游吸引由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旅游吸引价值转化而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及其权利。这种主观和客观二元是权利本位的理论基础。“人与物”关系的协调是权利本位的要旨,因此确定旅游吸引物权主体是旅游吸引物权概念的要素之一。由于旅游吸引物权主体具有集合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以在界定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处理,一种方式是省略旅游吸引物权的主体,另一种方式扩大和抽象旅游吸引物权的主体,本文拟采用第一种方式。笔者认为,所谓旅游吸引物权是指对旅游吸引物所享有的权利。
(二)旅游吸引物权的本质属性
张琼,张德淼(2013)[3]根据相关原则,探讨了旅游吸引物权本质属性,他们介绍3种观点,即准物权说、自然资源物权说和资源权说。“法学研究中以往关于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的直接研究成果很少,但间接的研究成果有一些。根据最相关原则,关联性最大的当属资源权的研究。关于该权利性质的研究现存3种主流观点:准物权说、自然资源物权说、资源权说。”“基于以上观点,旅游吸引物权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似乎符合准物权的特征。”固然,以上3种观点具有合理性,但是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旅游吸引物权的外延被缩小了。如有形物或传统知识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被排除在外。旅游吸引物权的本质属性是财产权,不是人格权或身份权。
(三)旅游吸引物权的特征
与土地权比较,保继刚、左冰(2012)[2]认为,旅游吸引物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性,此观点具有合理性。“旅游吸引物作为附着在土地或某物品之上的旅游吸引价值的权益体现,是与土地或物品的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性。”与民法中的“物权”比较而言,旅游吸引物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人格性。民法中的“物权”的指向对象是有形物,有形物没有人格性,而旅游吸引物权的指向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有些无形物具有人格性,如景区或景点的民族歌舞表演。第二,复杂性。旅游吸引物权的复杂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旅游吸引物权的主体复杂;(2)旅游吸引物权的客体的复杂性,既包含了有形物,又包含了无形物;第三,集合性。旅游吸引物权不是单一的财产权,而是一组财产权。
四、旅游吸引物权立法模式
保继刚、左冰(2012)[2]与张琼、张德淼(2013)[3]从官方法的视角分析了旅游吸引物权立法模式。保继刚、左冰赞同旅游吸引物权的统一立法模式,而张琼、张德淼则不赞同旅游吸引物权的统一立法模式。“其弊端正是本文之所以提出将对旅游吸引物的用益‘债权物权化’的现实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在《物权法》第二篇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将旅游吸引用益(旅游吸引物权)的对价,明确列入法定孳息,或直接补充以下条款:物之旅游吸引孳息(即本文所称旅游吸引物权),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笔者建议对《物权法》中地役权的定义进行调整,同时直接用地役权的名义设立‘旅游(用益)地役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之旅游吸引物供自己使用的权利’,将旅游吸引物之利用形式及有关权利义务纳入地役权之中,以协调和处理旅游吸引物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在利用这一资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吸引价值无法独立,不宜修改《物权法》之‘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用益物权中不宜设定‘旅游(用益)地役权’,解决景区冲突问题的法律建议:非设立旅游吸引物权而应保障旅游开发合同”,“总之,旅游吸引物作为一个包括众多不同类型事物的集合体,其性质与内容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其权利主体与客体在某些方面也不甚明确,所以无法对其进行整体立法保护。因此,笔者建议,不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各类合法的旅游吸引物进行有意义的清理归类,进一步明确其权属,以更好地保障相应主体的合法权益”。
保继刚、左冰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张琼、张德淼的观点值得商榷。由于保继刚、左冰对旅游吸引物和旅游吸引物权的认识存在局限性,所以导致他们的旅游吸引物权仅是在《物权法》一些条款中补充或修订旅游吸引物权。另外,保继刚、左冰所提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内容不符合物权法理论和物权立法实践。张琼、张德淼在《旅游吸引物权不可统一立法之辨析》一文中论述了旅游吸引物权的不可统一立法之缘由,提出了解决景区冲突问题的法律建议:并非是设立旅游吸引物权而应保障旅游开发合同。笔者认为,张琼、张德淼关于“旅游吸引物权不可统一立法”的一些缘由是合理的,但是完全否定旅游吸引物权的立法的观点是片面的。不过,他们在《“旅游吸引物权”整体立法保护质疑》一文中纠正了此观点,而认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模式应该采用分散立法模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关于“解决景区冲突问题的法律建议:非设立旅游吸引物权而应保障旅游开发合同”的观点并不令人心悦诚服。一方面,保障旅游开发合同是解决景区冲突问题的一种方法,并非全部;另一方面,旅游吸引物权是旅游吸引物权人与旅游开发商谈判的基础,若本属于旅游吸引物权人的旅游吸引物,而法律并没有对其确权,则有可能的结果是:在旅游开发谈判中,旅游吸引物权人处于弱势群体。众所周知,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是我国旅游发展的重头戏,民族地区是我国扶贫的重要对象,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而民族地区旅游吸引物权人拥有的旅游吸引物是能分享应得的旅游开发成果的影响因子。另外,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应该符合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目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是指通过对民族村寨进行旅游开发,从而提高民族村寨的生产力,提高民族村寨居民的生活质量,即民族村寨旅游是民族村寨扶贫的手段,民族村寨扶贫是民族村寨旅游的目的,所以从此意义上说,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制度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从法治维度看,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所存在的原因是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制度的价值目标缺位,即不是定位为“公平为主,兼顾效率”,而是定位为“效率为主,兼顾公平”。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最大的不公平是民族村寨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是民族村寨的无形财产并未得到法律和市场的认可,或被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低价或无偿索取,是民族村寨和民族村寨居民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没有话语权,是民族村寨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低,民族村寨居民的财产权利缺失。
对于旅游吸引物权立法模式的建构,笔者提两点不成熟的构想。第一,不能仅仅局限于官方法的层面反思和建构旅游吸引物权立法模式,因为仅仅局限于旅游吸引物权立法模式与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实践不符,也与法律多元理论相左。第二,根据著名法人类学家千叶正士[9][p.11]的法律多元理论和格尔茨[10][p.2]地方性知识理论,应该把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建构为官方立法模式和非官方立法模式。旅游吸引物权官方立法模式又细化为两个统一立法子模式和分散立法子模式,根据旅游吸引物权的特质,结合我国法律体系,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应该采用分散立法子模式。[11]
五、结 语
旅游吸引物是旅游学中一个关键词,虽然对于旅游吸引物的表达不一,但是他们都从不同路径探讨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和利用,有些学者也开始从法律的维度思考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尤其是保继刚、左冰等学者在物权范畴中努力寻找旅游吸引物权建构,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景区旅游纠纷,促进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期望唤起法学界人士关注和研究旅游吸引物权立法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张琼、张德淼等法学界人士作了相应的回应,运用物权法理论批判了保继刚、左冰关于“旅游吸引物权统一立法”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建构性的建议,但是在法学界并没有更多的声音,与“一石激起千层浪”预期目标相距甚远。由于旅游吸引物权既涉及旅游学中的旅游吸引物理论,又牵涉法学中财产法和立法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研究旅游吸引物权的表达和实践需要了解旅游学中有关旅游吸引物方面的前沿理论,也需要对财产法和立法学有所研究,因此,笔者对旅游吸引物权的表达和实践只是作了尝试性地初探,并不一定蕴含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际价值,只是期望激起更多的学者关注和深入而系统地研究旅游吸引物权立法理论和实践问题。
[1] 倪家宁.凤凰政府就门票事件向商户道歉 坚称收费不会变[N].北京青年报,2013-5-2.
[2] 保继刚,左冰.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J].旅游学刊,2012,(7).
[3] 张琼,张德淼.旅游吸引物权不可统一立法之辨析[J].旅游学刊,2013,(12).
[4] 陈岗.旅游吸引物符号的三种形态及其研究展望[J].旅游科学,2013,(6).
[5] 李亚娟,陈田,王婧.黔东南州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研究[J].资源科学,2013,(4).
[6] 马凌.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J].旅游学刊,2009,(3).
[7] 林红,王湘.旅游吸引物的系统论再分析[J].旅游学刊,1998,(2).
[8] 赵玉燕.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1,(2).
[9] 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0] 朱晓阳,侯猛.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 田里,杨懿.旅游后现象理论体系构建研究[J].思想战线,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