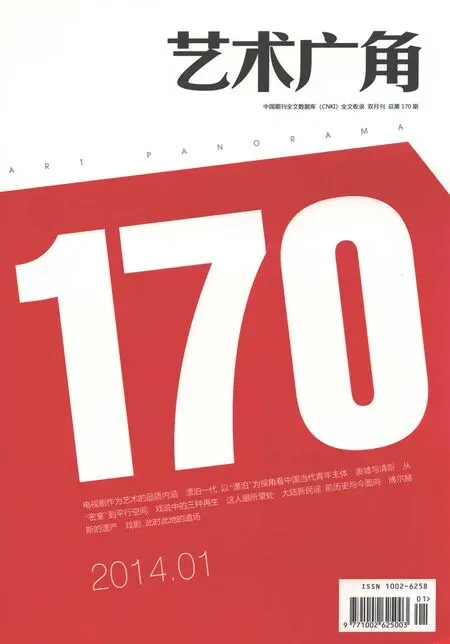这人眼所望处
——关于一些文学问题
黄孝阳 郭洪雷
这人眼所望处
——关于一些文学问题
黄孝阳 郭洪雷
郭洪雷:最近读了你几本小说,知道你也会下围棋,论年龄,你喜欢上围棋也应当是在“擂台赛”时代吧?
黄孝阳:1990年在学校念书时迷上围棋,通宵达旦地下。那时正是“中日擂台赛”如日中天的时候,若谁不知道聂马两者的,是要被排除在雄性生物这个种群外的。这种对智性的崇拜与当下年轻人对郭敬明的追捧,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反差。1997年,这项比赛改成仍然是NEC冠名赞助的三番棋,不再是“打擂”这种更富有话题性与观赏性的形式,逐步退出公众视野。
郭洪雷:其实老一点儿的棋迷都会有一种感觉,时下90后一代下出的棋,与聂马等上世纪80年代棋手有很大不同,好像人们对棋的理解和认识有了很大变化。那时讲棋形、讲美学,现在棋盘上充满暴力,一切决定于计算;那时输赢一目半目的棋很常见,现在挺过中盘收官的棋明显减少。我觉得先锋小说仿佛也有一个类似的变化。现在读你和七格等先锋新锐的作品,感觉在心智结构上与马原一代先锋小说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按理人类的心智结构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三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这种变化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不知你是否产生过类似感觉?你觉得产生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黄孝阳:我们这一代人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很可能就是另一个马原、格非。这并非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不够。对于文学这个星空而言,已有的星辰总是不够。互联网,以及它背后的现代性浪潮,从根本上塑造着青年一代的心灵,它有种种的好,亦有许多的弊。不管大家对利弊有什么样的争论,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又或者说,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多半是启蒙者的形象,一副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是等级社会的产物。随着技术进步推动的转型,社会结构日趋扁平,启蒙转而为“一个人与世界的互相生成”,是个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觉醒与自我进化。权威的声音在于指引,而非服从。若说作家还有什么特权的话,是他比普通人更能清晰地意识到边界所在。边界的确定需要技术含量、德性,以及更多的智性。
您说,“按理人类的心智结构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个理是什么呢?人要有常情、常识、常理;也要警惕其陷阱。一个成语“朝三暮四”,大家都知道其最初的本意,那些猴子太笨;但在今天,早给的那颗核桃是能产生利息等财产性收入的。事实上这二百年来,整个人类知识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之前三千年的累积总和。随着互联网对知识传播的加速、生产方式的重组等,今天的三十年就其知识生产的效率而言,极可能超过大清三百年。从古至今,一直有两种人:一种是生活在经验与秩序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另外一小撮渴望改变,往往头破血流,他们的出现是小概率,但决定人类进程的,总是他们创造的那些小概率事件。
郭洪雷:的确,马原、格非一代先锋小说家起步时,BP机还未出现,而你们这批人以先锋姿态出现于文坛时,BP机早已无影无踪了。网络技术、现代传媒大大改变了人们感受时空的方式,也会改变人类想象和理解的方式。但我对你说到的“启蒙”问题另有想法,找机会我们再聊。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心智结构的变化在你自己的写作中也有体现,在你的作品中,读者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蜕变的轨迹。
黄孝阳:我喜欢蜕变这个词,犹如蝉蜕去壳,这是一个有着异乎寻常的痛感与美感的奇异过程。对我而言,每一部长篇小说,相对于前一部,至少在结构、主题上要有变化,甚至于语言。至于写作技艺,作者总是渴望能一部比一部写得更好,但起伏不可避免。山峰尚有重峦叠嶂,何况肉身皮囊。不管我的写作过程是不是一条阳线,我都不喜欢在平面上滑动。滑动有惯性,是会上瘾的。要改变。我说“我是我的敌人”,这话是什么意思?人需要自我否定,因为他不是上帝。人极易沉溺于把他装起来的那个现实,因为安全感的匮乏。唯有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关系,才可能不断进化。这不是唆使小说家不与人为善,动辄与人瞪鼻子上脸。小说就是脑子里的暴风骤雨。不要满足于人名、地名与叙事手法的改变。一个小说文本是不是好,一是呈现,二是追问。它呈现了哪些可能性,若有必要,是不是可以用十倍的篇幅阐释它,不仅是评论与解析(如《微暗之火》),还有对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的呈现。至于追问,就不要满足于“人性”这种不动脑筋的说法。如果把世界比喻成河流,人类的已知顶多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水滴,而当代一个中国写作者的经验大概也就是这个小水滴中的几纳米吧。我相信是这样。
郭洪雷:你这里所说的“呈现”“追问”,对于先锋写作而言非常重要。有很多人,包括许多先锋小说作者都把对先锋小说的理解指向写作技艺层面、形式技巧层面,很少有人能在追问的能力方面反思自己的写作。我有一个极端而又粗浅的看法:形式技巧问题对中国小说家而言不是问题,只要假以时日,我们强大的“山寨”能力足以使任何舶来的、先进的、新鲜的、独创的技巧、手法落满灰尘。中国先锋作家往往是独创性技巧、手法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中国是这些技巧与方法的旅游目的地而不是出发地。当然,这里原因很复杂,但归根结底与我们思想和思维能力的低下有直接关系。而思想和思维能力的低下往往表现为回避呈现的可能性问题,拒绝或者说没有能力对“人”与“世界”的基本问题进行追问。看到一些先锋小说家得意地拍着自己装满零碎儿的“百宝囊”的样子,真是让人起急。你所提倡的“量子文学”及你的小说对佛学的借鉴,使我看到了你在提高思想、思维能力方面的努力,让我看到了新世纪先锋小说发展的一种可能的方向。你对“量子文学”的兑现,让我看到了形式技巧之上的东西。
黄孝阳:谢谢您的鼓励。人都喜欢听好话,我也不会例外,但要自省,尤其要面对批评。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哪怕他的文章已然不朽,他也是小的、卑微的、极其有限的。“不朽”是别人给出的,是外来之物,不是一个生命内部的秩序,不会成为勇气与智慧的源泉。一个写作者要敢于挑战常情,像堂吉诃德挑战风车那样,滑稽、愚蠢、笨拙、可笑,在这一时刻,他被一切障碍粉碎;在下一刻,他又能粉碎一切障碍。而所有的批评,都可视为自己文本的某种延伸,再激烈的苛责与再匪夷所思的误读也是自己某个对立面的呈现——把文本看成光,它照在不同物体上,便有了各种形状的影子。
在小说中,我追求难度。小说的难度在哪?在于你的每一次言说,都推开了一扇门,门后有把你吓一跳的狮子与雪山;在于你说尽了世间词语,却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说,而你又不得不说。难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价值观。世界的起源(意志)应该是简单的,但它的表象极其复杂,且日趋复杂。我觉得对复杂性的追求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社会,作为文学艺术,乃至于宇宙本身最根本的追求。唯有这种渴望,才能解释所有的过往及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复杂性不是简单的H2O的累加,它要有构成河流、湖泊与海洋的愿望。世界由各系统构成,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H2O是其中一种),且呈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是开放的,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它们却在这个下午构成了这株树所有的形象。一个真正具有复杂性意味的文本(或者人),绝不可能适用于“奥姆剃刀”;能被简化的,即是伪复杂。简笔画可以勾勒出人的轮廓,但它毕竟原始。艺术永无终结之时,除非人类历史终结。
你提到了我的小说中的佛学意味。我妈妈是信菩萨的。小时候再穷,也会隔三差五去庙里捐点香油钱。对佛学,我打小就充满好奇与兴趣。成人后,阅读甚多。它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生智慧,是“觉悟”。但总的来说,佛学是厌世的,讲的是一个“空”字,入了佛门,连亲情血缘都要一并斩断。现代物理学根源于理性,相信世界可以被理解,相信人类的认知并未就此结束,基调是乐观的。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都在以它们的方式渗透、改造“我”——这个不可捉摸的魂灵;虽然我对它们都只能算略懂皮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当然,它们在某一方面都是统一的。比如“信”,宗教上的“信”就不多做解释;科学上,比如,搞物理研究,目前,你必须相信光速不变。
郭洪雷:对于现代物理学、佛学对你的小说的影响,我不想从“科学”和“信”的角度来认识,毕竟人的肉眼是看不到一只网球以时速数百公里飞出的不确定性。我更看重你把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套叠在一起对你的写作产生的影响。用老话说那会产生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意味着一套相应的方法论,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种启悟,一种属己的生命哲学。这些一旦映射到你的写作中,就会产生一种令人惊异的美学风貌:它的轻盈、简洁、空灵——但不会让有经验的读者将它们直接归因于卡尔维诺、卡佛、博尔赫斯等中国先锋小说的那几位外籍大神——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它是从你的那套生命哲学里滋生出来的。我前面说,你的写作对新世纪先锋小说意味着一种可能的方向,就是这个意思:机杼自出而又圆融无碍。
黄孝阳:宏观与微观的重叠,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产生……您说得真好。在我的内心里,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深情,有种种“古怪而又悲伤”的爱,对它总是抱有最天真的幻想(并不是奢望它会更好);所以一直在胼手胝足地去做事,一头汗,一些烦躁,许多欢喜,以及无数感伤。我想这些都源于您说的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时,觉得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湍流。湍流,物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是对复杂与秩序的同时概括,犹如暴雨将至。应该说,我现在写的小说,个人风格极其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叫黄孝阳的汉人写的。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郭洪雷:我想问孝阳兄一个不大该问的问题: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的写作影响比较大,或者说比较直接?对一位作家特别是一位先锋小说家,问这样的问题不大礼貌,就像问人家一个月挣多少钱一样,有掏家底儿的意思。
黄孝阳:我不大喜欢中国文化里“留一手”的传统。当然,在一个匮乏时代,教会徒弟确实有可能饿死师傅。但在这个现代性的开放社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说,人的透明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不管他多么渴望捍卫隐私)。哪些作家(作品)对我影响比较大?太多了,最早是唐诗宋词,现代诗;后来是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作家;接着是拉美欧洲的一批;再后来就少读作家的作品,改读人文思想历史时政科普等。这倒不是一个“望尽千帆皆不是”的心态,而是说,我想跑到外面来看看“小说”。在它内部呆久了,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尤其是现在,这种“从外面看”的视角特别重要,它会给当代小说注入新的血肉。
对小说而言,最好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尚未来临(当它进化成更与个人心灵息息相关的当代小说)。现代性正在把人打碎,时间、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等都碎片化。要回到作为人的整体,作为“一”的自洽,只能是求诸于上帝,或者在某些时刻去阅读文学,而不能指望理性与逻辑——没有比它所导致的傲慢更糟糕的事情了。
在我看来,至少对于新一代的批评家而言,要有能力区分小说与当代小说,就像区分长城与埃菲尔铁塔(这个比喻过于陈旧);或许应该这样说,就像区分亡灵与生者的容貌。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发现生命,在众多一闪即逝的脸庞上瞥见天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小说的任务不再是对永恒与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再是对那些结构工整、旋律优美之物的渴望;也不再迷恋对道德及所谓人性的反复拷问。那些已被发现的,已经被盖成楼堂馆所的,不再具有重复建设的必要。在由故事构成的肌理之下,那些少有读者光临的小说深处,世间万有都在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而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件。
郭洪雷:不管一个人的写作属于什么性质,书总是要读的,但对中国先锋小说而言,阅读尤其重要,它涉及到中国先锋写作的筋骨。8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你只要读在前面,写在前面,用在前面,你就是先锋。一个人的阅读路径决定着他写作的走向。陈希我在先锋小说家中比较另类,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支援和背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等日本作家。他的尖锐、阴狠,他对人性中黑暗的专注,与他的阅读有直接关系。一个人调整了阅读路径,他的创作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格非自己就曾说过,他能拿出“江南三部曲”与他阅读范围的扩大不无关系。但我总觉得中国先锋小说作家在阅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早就存在,现今也没有多少改观。一是太爱读小说;二是就读那么几个人的小说。时间一长,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都是一窝生的,都是一奶同胞。只要读读先锋小说家们记述自己成长的文字就会发现,总是那十来个人十几本小说在那里晃来晃去。记得顾炎武《日知录》曾举过一个铸钱的例子,铸钱有两种方式:一是取铜于山;二是毁旧钱铸新钱。当下先锋写作走前一条路的太少,走后一条路的太多。刚才你的回答印证了我的一些想法:阅读视野要开阔,多读杂书,也就是你说的“要跑到外边来看看‘小说’”,要学会“取铜于山”。成天泡在那么几本小说里,经典倒是熟了,可你的创造力可能无形中也就枯萎了。前些日子看了一个电视节目,那些用来抽取胆汁的狗熊被解救出来,管子拔掉了,伤口愈合了,被放到动物园里。可是它们总是在原地打转转儿,连一步也迈不出去。有形的铁笼子被打开了,长期的囚禁、无形的铁笼子仿佛已经镶进它们的身体。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些先锋小说家:左转半圈撞上卡夫卡,右转半圈碰上马尔克斯,迈前半步和博尔赫斯撞个满怀,退后半步又被卡尔维诺绊了个跟头,就是原地不动,睡觉做梦也还是昆德拉式的。那情形,真让人心疼!
再有,阅读的重要还在于它会帮助一位小说家建立两套谱系:一是技术的谱系;一是精神的谱系。当下先锋小说作家经营前者的很多,构建后者的寥寥无几。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先锋写作如果真的有所谓神谱的话,八九十年代的大神肯定是马原。但在你们这些先锋新锐眼里,王小波地位可能更高一些。
黄孝阳:我的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替他人做嫁衣裳。前些天,太阳很大,我在马路上走着,走在朝九晚五的上班途中,突然深感厌烦,就问自己想去干什么,蓦然想起王小波说的一句话——以后活不下去,改行去当货车司机。今天的我已经不好意思说“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也不愿意说,“我也能这样写”。但我必须得说,王小波是我的精神源泉之一。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深刻,他也不深刻;不是因为他的幽默与诙谐,郭德刚更幽默与诙谐;不是因为他对常识的不遗余力地推广;也不是因为他在文坛外默默奉献出汉语小说的一种美学(尽管是有限的)——而是因为他的不服从。简单说,对传统的颠覆。这种颠覆,首先是思想层面的。
再经典的作品与作者相遇,皆需要缘。不仅是初见时的缘,还有重逢时的缘。你要有缘进入它的体内,才能感觉到它的心跳与温度。王小波的笔在反讽中有惨烈,在黑色幽默中有沉痛,在戏拟中有愤激。在惨烈、沉痛、愤激的背后又是那个生命的荒原。要想读透这三层,需要智慧,还需要阅历。它对读者所提出的要求是苛刻的,否则只能是“淫者见淫”。它只适合对现实不满的人看,只适合那些不甘心被朝九晚五的笼子囚禁的人看,只适合那些趋害避利、作为一个反熵存在的人看,只适合那些渴望着形而上的人看,只适合那些有勇气摘下傲慢与偏见之有色眼镜的人。它也只适合年轻人看。事实上,我现在已经不读王小波了。他是一个必须经过、也必须遗忘的过程。
郭洪雷:一般而言,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要经过模仿、摆脱、自成一家三个阶段,我觉得你的可能性还远没有完全释放干净。博兰霓、殷海光、林毓生一系的思想里,非常强调对原创性思想和经典揣摩和模仿,只有经过这一段,你才能拿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谙熟传统,才谈得上创造性转化。王小波颠覆传统的前提是他对传统的熟悉,包括留美期间他与历史学家许倬云之间的闲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复思考等等,都能使他的颠覆认穴精准,力道强劲。其实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而言,在王小波身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孔融、阮籍、李贽、金圣叹等人的精神脉息。传统的强大在于它的内部好像有一个装置,它一方面能把反叛者、颠覆者设置成自我维系的“他者”;另一方面又能把反传统、颠覆传统者纳入到传统中来,使他们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反抗传统、颠覆传统几乎是中国先锋小说作者的“袖标”,但只要对他们的小说进行文本细读,传统的筋脉也就露出来了。在我看来,中国先锋小说作家对传统的认识过于狭窄,过于模糊。其实他们所说的传统往往指向“现实主义”或文学史,他们的“弑父”冲动远远大于他们思考、分析、触摸传统的欲望。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和王小波比较显得轻浅的主要原因。
黄孝阳:您说的是。怎么说呢,以反抗之名行的事,多半还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当然,所有的反抗都是有意义的,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里。反抗,意味着挣脱,对自由的渴望。这是一个生命哲学的问题。但反抗未必就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增加。它是浪漫主义最极端的表达。我热爱传统,一个关于人的传统。我只是说“传统虽好,已然匮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所能唯一必须去捍卫的,就是形成他的那个传统。”所以,在很多夜里,我总会去想那个能让人把自己献祭出去的东西,它应该包括了:权力、恐惧、性、爱情、对上帝的沉思、口腹之欲、公平与正义,以及星辰等等。这些词语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让人“心甘情愿”的维度上,它们取得惊人的一致。我总是在沉思天堂(它至少有一千零一种形式),当我还待在人间的时候;我很好奇,等我来到天堂,我将沉思的是什么。是那一千种我已经看见过的形式么?肯定不是,若是,就有悖论,有种种纠结与痛苦,天堂也将摔落于地。那么,一直让我沉溺其中的究竟是什么?
我把这个问号放在这里。在一些时候,问号或许即答案。
郭洪雷:你用“献祭”这个词,让我感到了一种悲凉。我想这种悲凉感受既是形而上的也是现实的。说句俗话,现时代做小说家难,做先锋小说家更难,做一个客观上拒绝了电影、电视剧的先锋小说家尤其难。你那一串串的小故事,你对量子文学的经营,你对“当代小说”的强调,让我看到了一种拒绝,也看到了先锋小说生存的艰难。不过我觉得一个没在先锋写作里边“打过滚儿”,上来就写顺滑故事的小说家未见得有太大的出息。莫言、贾平凹、张炜、王安忆、韩少功、刘震云这些被认为写得好的人,不同程度都曾与先锋小说有过染,或“偷”过先锋小说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看到莫言现在“收麦子”,就忘了他“挖垄沟”的日子。
黄孝阳:被认为“写得好不好”其实不重要,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人哪,就是太在意名利了。名利是门,要进去,更要能出来。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写小说,为的不是“出息”,而是我开始说的“与世界的互相生成”,是自我教育、自我进化,是为了德性与智性,是对“我”的好奇与上下探索,是为了理解少女唇上的笑与老者额上的皱纹。我很喜欢殷海光说的一段话:“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据我所知,道德标准、正义感、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二次大战以后,这些可贵的品质已受到严重的考验,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但这些心性不曾消失,有些人继续珍惜着它们,这也许就是人类希望的幼芽”。您说的先锋小说的生存困境,这是一个现实,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不是一定要屈服于现实。人,完全可以成为艺术的尺度,所谓诗意地栖居。我们说时代潮流,逆之者亡顺之者昌,其实,对于人的心灵生活来说,一个时代若太“弱”了,就有理由绕道而行。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并非就一定是人必须拥有的。这倒不是暗示我是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或者投胎技术好。而是这个消费社会对先锋文学完全不屑一顾。既然我热爱这样一种富有智性与德性(我可以潜入文本,成为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本身已经是对我最丰厚的回馈,我又何必在意它能换来多少银两?宋徽宗写瘦金体,也不是为了卖钱。我不是宋徽宗,但我可以做别的工作养活自己。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而所谓的先锋与传统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只是一个叙事策略。宋词相对于唐诗,是先锋;几百年后,它们都是传统。
郭洪雷:我曾经写过批评《牛鬼蛇神》的文章,批评马原在这部长篇里玩“旧作接龙”。不过我打心眼里还是喜欢马原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小说写得如何好,喜欢的是他谈起自己小说时那股牛逼哄哄、舍我其谁的劲头儿。那劲头儿里有一种尊严,有对文学的雄心在。由于是同事,平时和陈希我接触多些,一次闲聊时我问他:“除了形式技巧之外,80年代先锋小说的主要遗产是什么?”他说:“形式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对文学的雄心。”不知孝阳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孝阳:陈希我答得巧妙。但这个“文学的雄心”还是在文学的内部,是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写作技艺的信心与期待。“文学的雄心”还可以从另一层面阐释,比如我刚才说,在现代性把人打碎的一个历史潮流中,它对人整体性的还原,把碎片黏合,对深埋于技术人、理性人深处的“作为人的情感”的挖掘。文学在这里是可以像上帝一样让人得到安慰的。
我们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是在“求真、审美,止于至善”。一个常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事实是,真善美并不互相兼容,且互相为敌。而在它们各自的内部,也同样可能互不兼容。美的不兼容,这个最好理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善的不兼容,这个也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有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命题。善是一个极复杂的道德范畴,我们把它搁在一边,谈论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我说真也是不互相兼容的?桌子不是桌子,难免是鬼不成?大家都知道,宇宙是加速膨胀的,这是十五年前美国宇宙学家的发现。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失效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把肉眼所察觉的牛顿力学体系里的种种现象命名为常识。但宇宙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不断阐述着常识之误。这种启示是否适用于人文学科?若适用,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深度与广度?今天的中国,人们太喜欢用常识两字打人了,好像不附和一声苹果是会落地的,就不配为人。常识究竟是谁的常识?如何证伪?或者说如何去求解公约数?要证伪,只能指望事实与逻辑。但事实从来就是主观的事实,是罗生门,是薜定鄂的猫,是一个被利益、本能、人固有的缺陷等所决定的波函数。我们说要求真,这个真随着人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是随机的,由概率支配,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观察者的意愿而呈现出他们乐于见到的结果,所谓人择原理。而逻辑这座“不可能的楼梯”也常把人引入歧途。事实上,由于公众语境里叙述技巧的需要,所有人都在设法强调观点与结论,忽略前提与条件,甚至是选择性忽略。
换句话说,要证伪,光有科学与理性是不够的,还要诉之于一种作为人的基本情感,要有慈悲,感同身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警惕理性的自负,要谦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常识的捍卫者、良知的践行者,在这个飞速膨胀的宇宙里,以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去追寻那无尽的谜与那无限的美,而其中的某一刻停顿、某一个难以言喻的呈现,即是文学。
黄孝阳:作家,编辑。著有《旅人书》《乱世》《人间世》等。郭洪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小说修辞研究,兼及当下小说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