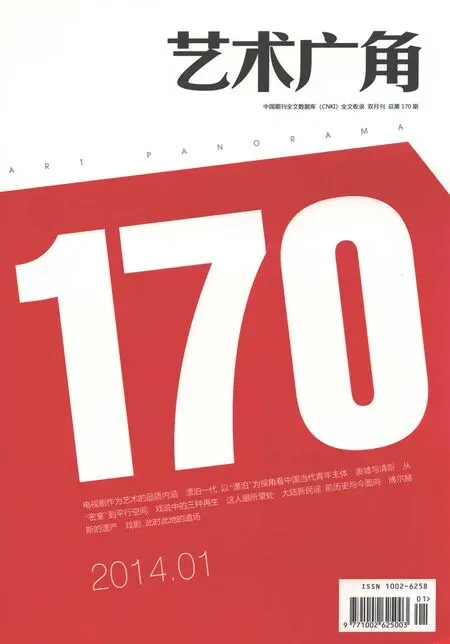当代中国作家论书法
李徽昭
当代中国作家论书法
李徽昭
书法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一种美学与文化的亲缘关系,作家天然地亲近书法。唐代书论家张怀瓘一再指出: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书议》);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文字论》)。可见,文学与书法从来就是交相互用的,中国作家善书法、懂书法具有天然的文化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亲缘关系受到破坏,书法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便转为隐形的文化基因,存活在中国文化血液中,并主要为作家所承袭。现代作家多曾受过书法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他们没有放弃毛笔书写,成了中国古今文学和文化之变上的桥梁式人物,他们与书法文化的血脉关联比较自然,也印证了书法与文学难以割裂的文化关联。当代作家有着大不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建国后,中国作家、书法家一并被体制接收和规训。建国初及20世纪80年代分别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使作家和书法家相继职业化。书法教育的文化环境逐渐封闭,文学和书法应有的文化联系为职业化所区隔。
20世纪末,中国经济崛起,传统文化复兴,具有文化自觉的部分当代作家开始主动介入书法艺术活动。这也证明,文学与书法的亲缘关系,确是中国文化的隐形基因,中国作家选择书法与书法选择中国作家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随后,在与西方各种文化艺术思潮不断碰撞磨合中,传统文化渐被中国社会所体认,当代作家的书法活动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2006年以来,西安与广州相继举办了作家或文人书画展,引起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当代作家介入书法文化的主体有两批:分别于民国时期与建国前后出生和成长的。周而复、姚雪垠、汪曾祺等前辈作家出生成长于民国时期,接受过一定的旧式教育,具有较为自觉的书法文化意识。贾平凹、熊召政、余秋雨、陈忠实、高建群、张贤亮、王祥夫等作家多出生成长于建国前后,书法自觉意识稍弱于前辈作家。总体上,由于出生成长时间的差别,民国时期与建国前后出生成长的两批作家,教育与书法文化修养的差异使得他们论及书法的文字也稍有不同。
一
周而复是当代著名作家、书法家,曾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副主席。其书法艺术和文学作品,珠联璧合,相互辉映。周而复生于1914年,幼承庭训,学习古文、诗词,练习写字,受过临帖、默帖和读帖训练,具有深厚的书法功底及修养。周而复的书法“结构严谨,欹侧面取其姿美,笔法方折纤劲而达清秀;骨力洞达,肌腴筋健,刚劲蕴藉”,郭沫若认为其书法“逼近二王”。尤为重要的是,周而复以深厚的文化修养认识到书法艺术的当代价值,体会到书法传承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初,他联合其他书家倡议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为书法的当代传承、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周而复认为,字如其人,自然流露。字不但表现每个人的特性,还能表现每个人的思想感情(周而复:《略谈书法美学》,《中国书法》,1987年4期)。有关具体创作,周而复认为,笔法借点画以显,点画借结字以显。字的点画相当于绘画的线条。线条要有粗细、浓淡、强弱等不同,用毛笔书写,可以表现出多姿多态而又和谐统一的情调。关于书法创新,周而复认为“要植根于前代书法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基础之中,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继承优秀的传统,不断努力发展和创新”。在具体继承上,又应区别对待,因为“历代名家书法,不是每一幅作品都好,每一个字都好,每一笔都好,应该分析其优、缺点,扬长避短”。周而复对书法艺术的表现性及其影响有独到见解。他说,中国书法艺术“具有与一般艺术门类不同的艺术品格,成为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正是对书法表现特征的体认,使他说出,“中国书法艺术对欧美一些国家也有深远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传统艺术基本都是以模拟再现为主的具象艺术,到了现代才出现抽象艺术。现代抽象派绘画,受到中国书法艺术影响以后,才提高了它的艺术素质”(周而复:《敏而好学 勤于笔耕》,《书画艺术》,1994年2期)。
和周而复一样,姚雪垠、汪曾祺生于民国时期,解放前即参加了文学活动。姚雪垠出版有历史小说《李自成》五卷,书法颇具文人情趣。姚雪垠指出了书写内容于书法的重要性,他说,常常看见有不少条幅出自不同书法家之手,书法风格各有独到,但内容都是几首常见诗词,毫无新鲜感。内容的千篇一律影响对书法艺术的欣赏。(姚雪垠:《书法门外谈》,《书法》,1980年8期)这一看法关涉书法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应该说,姚雪垠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书法艺术的美不在书写内容,但无法脱离书写内容,内容与形式协调统一才能提升书法的价值。书写内容主要与文学相关,对书写内容文学性的关注反映了书法欣赏者的文化期待。
汪曾祺从小受过较为正规的书法训练,其书法与小说一样,极富清淡幽远空灵的趣味。汪曾祺对书法体会颇深。在书法章法上,他认为:“‘侵让’二字最为精到,谈书法者似未有人拈出。此实是结体布行之要诀。有侵,有让,互相位置,互相照应,则字字如亲骨肉,字与字之关系出。‘侵让’说可用于一切书法家。——如字字安分守己,互不干涉,即成算子”(汪曾祺:《徐文长论书画》,《中国文化》,1992年6期)。有关文人书法,他说“这种文人书法的‘味’,常常不是职业书法家所能达到的”。对电脑写作换笔问题,他觉得“电脑写作是机器在写作而不是我在写作”(汪曾祺:《文人与书法》,《中国书法》,1994年5期)。对于街头牌匾中的书法文字,他认为“字少一点,小一点,写得好一点,使人有安定感,从容感。这问题的重要性不下于加强绿化”(汪曾祺:《字的灾难》,《光明日报》1988年6月5日)。
秦牧、刘白羽、邓拓、杨朔等作家也出生成长于民国时期,多受过较系统的书法教育,有较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基。他们在民国时期养成的毛笔书写习惯形成了日常书写风格,作为审美艺术的书法,又超越了日常书写,具有独特的法度、技巧与审美情趣,在书法内容和形式结合中,涵纳了文学文化与精神的多种情趣。或许正是较系统的国学及书法教育形成了他们近乎无意识的书法行为,他们留下来的论及书法的文字较少。同时,他们经历了建国后一段历史时期,作为革命对象的“传统文化”,书法显然不能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80年代书法热开始时,他们又相继离世或疏远文坛,其书法活动也就未能引起社会关注。所以当代前辈作家的书法与当代职业书法可谓是一种断裂式的弥合。不过,应予肯定的是,周而复、姚雪垠、汪曾祺等部分前辈当代作家的书法活动推动了书法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与发展,引领了当代书法的文化风向,他们的书法见解应该是当代书论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笔。总体来看,他们生活成长的环境形成了较为自觉的书法意识,多能清楚地认识到书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主体性价值,对书法的形式与内容均有较高的要求。他们的书论见解有深厚的传统书论、国学支撑,因此,能深刻地触及书法时弊。
二
与周而复、姚雪垠、汪曾祺等前辈作家不同,贾平凹是建国后在中国农村出生成长的新一代作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投入书法艺术活动。长期的书法艺术活动中,贾平凹形成了朴拙其外、内美其中的书法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特的贾平凹书法艺术思想。他认为,过分强调书法艺术,即更多的唯美性、趣味性和装饰性,会影响天才的发展,以致最后沦为小家。因此,在他看来,“技巧,都以精神构形,似妙作之妙出”。“若呼名是念咒,写字是画符,这经某一人书写的形而上的符号是可透泄出天地宇宙的独特体征”。书法应该“本份书写,以书体道”,在当下,现代人已经“很难从书法里去体验天地自然了,很难潜下心修炼自己技艺了”。所以,他申明,“我为我而作”,“我是在造我心中的境,借其境抒我的意”。贾平凹充分表达了书法艺术的个人精神表现特性,显示其书法艺术思想的个性,也是对古代书法理念的回归。东晋王羲之早已说过,“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技巧显然从属于书写者的文化精神与思想。所以,他强调书法家精神修养历练。他说,“如果想成为大家,都是要扫糜丽去陈腐,以真诚、朴素、大气和力量来出现的”。“在掌握了一定的技法之后,艺术的高低优劣深浅厚薄,全然取决于作者的修养。人道与艺道往往是一统的,妙微而精深”。这不啻击中了当下中国职业书法家的软肋,对书法家思想、精神与文化修养的强调,对才艺背后“人”的呼唤,显然是作家贾平凹文学的“人学”意识向书法领域的延伸。
在作家书法上,与贾平凹齐名、被称为“北贾南熊”的“熊”,是以长篇小说《张居正》知名的湖北作家熊召政。熊召政的书法灵秀儒雅,富情趣韵味,显出文学修为与书法艺术的沟通互动。他认为,书法由造形而体会里面的含义,由表及里,由形式而达精神,就是书法和文学最高的境界。由此,他批评当下的书法创作,使书法从文学中脱离出来,变成一种单纯的形式美,实际上违背了中国书法最早的本义。熊召政重视书法艺术技巧。他认为书法是一种身心投入的活动,它有技术因素在里面起作用,“书法不能有书无法,法是书本身的规律”。尽管重视技巧与法度,但他更强调,技术并非书法的唯一,书法有形式,仅追求形式,远远不够。重点应关注形式与技巧背后的学养。“一个人的字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经历、学养、生存和精神状态”,这是作家熊召政深深体味到的书法艺术境界。在小说《张居正》中,熊召政对书法“从气度上来评判,没有去讲求笔画与流派,是把书法作为反映一个人的素养、气度来加以评述。气度与法度,气是境界,法是学养”。他批评当下一些书家缺乏学养支撑:字非常好,可是笔法太甜,气度偏弱(李霁宇:《“北贾南熊”猜想》,《文学自由谈》,2007年2期)。可见,熊召政与贾平凹一样,十分关注书法背后的文化精神内涵,注重人生经历、身世、学养在书法中所起的作用。由此,熊召政对当下书法艺术做出了严肃的思考。他问询:有没有一个书法大家,通过简体字能把书法表现得很美?他期待:总有一天简体书法也会从风雅变成风俗的。他重申:书法家应该首先是文人,文化复兴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文人自身的精神状态与品格追求的问题。
学者余秋雨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转型为散文作家,其《笔墨祭》引起诸多关注与批评。《笔墨祭》中,余秋雨祭奠了“作为一个完整世界的毛笔文化”的消失,他指出书法文化“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它应该淡隐了”。但他又说,“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抚慰,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作为一位学养颇深的作家、学者,《笔墨祭》中的余秋雨是矛盾纠结的,作为文化研究学者,他爱书法,深知其中的文化重负,显然无法断绝书法中的中国文化基因。所以后来,这位“笔墨”的“祭奠者”不仅亲身投入书法艺术活动,并到迷恋的境地。他认为,从书法的“满纸烟云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文化人格”,“毛笔字写到一定程度,需要超越技术,而获得一种神秘的‘气’”,他呼吁要“保护书法与拯救公共书法”。余秋雨对书法文化悖反式的认同,反映出书法在当代文化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矛盾特征。
其他一些著名作家也从不同角度对书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陈忠实充分体悟到文人书法的价值。他认为作家用毛笔写字,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维护传统文化背后,陈忠实也重视提高书法家的文化与精神修养。他说,不能“只是临摹某大家的笔法技巧墨色浓淡,而不得大家的思维和精神”,单纯临摹“终究走不出大家大师的阴影,无法形成独立艺术个性的自己这一家”(陈忠实:《气象万千的艺术峡谷——高峡印象》,《金秋》,2007年 1期)。作家高建群觉得,当下书法得以兴隆,应该从民族心理深层上找原因。当中国人在传统书写工具毛笔先是被钢笔、圆珠笔取代,随后被电脑取代时,面对的是传统断裂、国粹丢失的危险,这是中国人怕失去传统,继而失去自己(高建群:《掀起一波大浪来》,《陕西教育》,2006年1期)。这昭示我们要从民族文化根源上维护书法文化。文学评论家白描认为,在黑白对比的审美感受里,首要的是书法意蕴提供给观赏者的审美愉悦。对当代书家剑走偏锋,追求诡异奇怪,他说这是大妄(白描:《习书感言》,《四川文学》,2006年8期)。作家王祥夫对中国书法、绘画均有研修。他认为,书法之“法”是书法的性命与灵魂。书法作品的面目可以有俊丑不同,法却是一样的,离了法只能说是写字。因此,“技法到死都重要”,“点和线是中国书画的舍利子”。作家张贤亮从书法中体悟到了新的乐趣,他从研习书法中享受到了类似手工操作的乐趣,而且练习书法也不会失去手写汉字的本领(张贤亮:《电脑写作及其他》,《朔方》,1996年1期)。
三
给予书法以律动的根源是书写者的生命,书法线条律动节奏形成的书法形象显示了书写者的精神文化修养和生命意识([日]平山观月著,喻建十译:《书法艺术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没有书写者生命力的投入,就无法在点画构形中赋予有意味的形态。中国当代作家的书法观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书法以及中国文人在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建构中的责任担当问题,强烈的文化生命意识使得他们真诚地视书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他们不约而同地体味到书法独特而有意味的表现功能,重申了诗书画同源或字如其人等看法,提出了重视书法背后的“人”及其文化修养问题。通过对书法家个“人”及其文化修养的重视,他们肯定书法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对当下职业书法文化与精神缺失的现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实际是对当下中国书法“唯形式化”的警戒。他们对书法家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期待,实际是希望能够以书法家的文化、精神修养实现书法表现的“再功能化”,重新赋予当代书法以新的文化意识。他们以深厚的文学修养体悟到书法欣赏对书写内容的审美期待,由作家文化修养而触及书法家书写内容的文化意识。在书法法度与技巧上,尽管他们有不同看法,但技巧为人及其精神所“用”是他们大致相同的理念。他们期待的是能够回归书法文化的源头,即生命意识、精神性等。
当代作家论及书法的文字具有深刻的文化与思想价值,对当代中国书法发展有着更深层的意义。他们的书法观指向了职业书法中渐渐失落的生命意识及文化精神,着重处理的是文化、文学与书法的关系。他们强调书法传承中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担当,强调书写背后的精神文化修养、人格精神,这与当下书法教育虚热(各高校纷纷开设书法专业,但书法专业高考文化分远低于其他专业)、过于重视书法的市场价值、艺术形式背后精神文化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诚如王岳川所说,中国书法界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现象,书法消费主义导致书法本体迷失不彰,书法创新也失去了明确方向(王岳川:《书法时代症候与书法命运》,《中国书画》,2009年3期)。作家的书法观重新彰显了被现代艺术遮蔽的书法文化身份。可以说,当代作家书法观是中国文化观念在当代的合理顺变,在全球化审美语境中突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本土身份,显示出古今通变、克服当代书法艺术变形的本土意识。他们也提出了当代书法理论的一些新范畴,如“精神构形”“本分书写,以书体道”“气度与法度”等,值得书法理论界深入体会与思考。总而言之,当代中国作家的书法观是当代作家在书写中体味沉思出的艺术感觉与理念,体现了中国书法本身应有的生命意识及人文精神,这些阐述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审美主体身份的确认具有一定的意义。
作家书艺活动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作家书法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呼唤,社会需要具有真正精神文化内涵的名流引导日常文化生活。作家书法形成的新表现、新风格、新精神,是当代作家主体精神的需求,释放了作家文学创作中对自由的渴望,提升了作家的文化精神境界,促进了当代作家的文化主体性认知与建构。由此,作家书法与主流文化和社会风潮形成了某种契合。作为一种客观文化存在,当代作家书法理念或将对中国文化心理更新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我们又应看到,在日常书写丧失造成书法文化危机的情况下,当代文人作家亲近和创化书法文化与疏离书法文化构成了当代文化发展的矛盾(李继凯:《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4期)。这种矛盾警醒我们应该呼吁更多作家关心、参与书法艺术活动,共同推动并实现中国书法文化内部更新。值得欣慰的是,当下已经有一批60、70后实力派作家开始参与到书法研修中,如雷平阳、徐则臣等,他们正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文化观,这也许是中国当代作家书法乐观的未来。
当然,当代作家的书法创作也存在不少问题,章法、布局、点画线条处理等仍欠法度,在技巧上确实有着一些缺憾。但当代作家的书法观及其书法实践可以弥补职业书法的某种不足,比如职业书法只知道如何“造型”而不知道如何“造人”([日]平山观月著,喻建十译:《书法艺术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他们不乐意谈书文关系,很少谈所书写的文字内容,甚至有时还对这些“书外之物”不屑一顾,完全忽视书法艺术中人的修为与完善。面对作家书法这一文化存在及其书法观,职业书法家理应深入思考,支撑书法家书写的“法”的深层内涵应该是什么;职业书法过分重视的“纸上因素”是否暗含某种危机;作家书法中包蕴的情操意趣、审美观念和文化素养等“纸外因素”对职业书法家是否应有深刻启示(金开诚:《再谈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书法艺术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当代作家书法观的文化刺激下,职业书法家应该充分反观自身书法理念及实践,这将为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源泉与动力。
李徽昭:任职于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