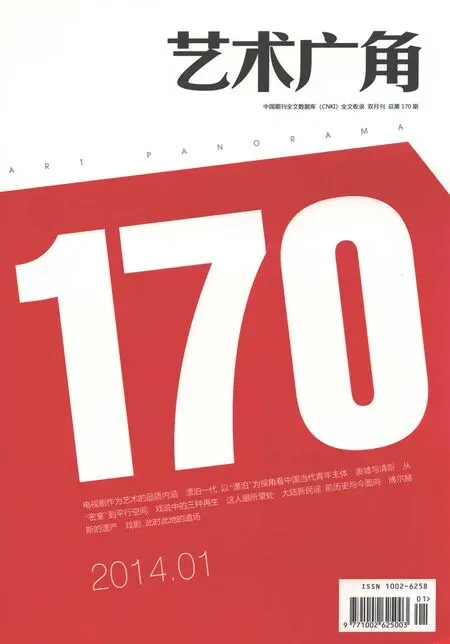从“密室”到平行空间
——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社会空间的想象
张慧瑜
从“密室”到平行空间
——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社会空间的想象
张慧瑜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二战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宣告结束。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短促的20世纪”来描述1914年到1991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后冷战的开启意味着人类又回到“漫长的19世纪”。针对这种历史大转型有两种代表性的论述,分别是美国理论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借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认为冷战中不战而胜的美国意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或终结形态,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与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亨廷顿不同意这种乐观的“全球合家欢”式的看法,他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后冷战的冲突将发生在西方文明和其他多极的非西方文明之间。虽然亨廷顿反对福山“一个世界”的看法,但他却也分享着政治、历史终结的现状,为90年代流行的文化差异政治、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亨廷顿所指出的这种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的前提在于,非西方文明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如东亚经济的崛起会挑战西方所支配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文明冲突不是19世纪的文明/西方与野蛮/非西方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一种类似于近代以来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文明”国家主导的鏖战。这种用“历史终结”和新“文明论”来描述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恰好使用的是19世纪的社会政治语言,这本身可以看成是19世纪的“归来”。本文并非要纠缠于这些既理论又服务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后冷战现实国际战略的说法,而是想通过以电影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文本讲述全球化时代的两个故事:一个是90年代后期浮现的“一个世界”或“密室”的故事,如《楚门的世界》(1998年)、《骇客帝国》(1999年)等;二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所讲述的“两个世界”或平行空间的故事,如《逆世界》(2013年)、《极乐空间》(2013年)等。如果说前者是对9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呈现,后者则是对二战后出现的后工业化/工业化的双重结构的反思。
一、“同一个世界”与影像的“牢笼”
借用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全球化的时代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种“普天同庆”的氛围又被90年代以美国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所强化,让“小小寰球”变成畅通无阻的“地球村”,实现了撒切尔的名言“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与这种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体化,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高,信息/数字改变了人类的时空感受。从社会管理到个人生存已经数字化,就连货币/金融也越来越虚拟化,这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全球流动的速度以及金融资本化的程度,以至于2008年从美国蔓延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感觉到疼痛,可谓,“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新世纪之交,这种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快乐的90年代”的幻想被打破,后工业、消费主义大都市景观让人们陷入一种无可逃脱的影像“牢笼”之中,特别是数码影像所带来的拟真化使得人们沉浸在“失真”的焦虑状态。正如许多惊悚片/科幻片中的末日场景,一觉醒来那些繁华大都市中只有闪烁的数字大屏幕依然反复播放着广告,而人类已经灭亡或逃离地球,就像《机器人瓦力》(2008年)中所呈现的地球变成了城市垃圾所堆积的工业废墟。
1998年美国导演彼得·威尔拍摄了《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借楚门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被摄影棚所构造、操控的现实世界,楚门从出生到成长到工作、结婚这种美国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不过是一场大型的电视真人秀。尽管楚门逐渐找出破绽,并最终尝试走出这间巨大的现实摄影棚;但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摄影机以及楚门始终处在被看/被监视的位置上,恰好成为生活在后现代的都市消费者的最佳隐喻。影片也呈现了那些每天都在欣喜若狂地“观看”《楚门的世界》电视节目的观众们,一种充满了围观/偷窥快感的消费者。这样一部带有自反性的关于电影的元电影,引发了“是否每个人都是楚门”的反思。这种真实/虚拟、现实/拟像的界限的消失,在1999年的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骇客帝国》中得到更加充分地体现。如果说《楚门的世界》再现了60年代西方进入消费主义社会之后,大众传媒生产的影像成为个人生存的现实拟像,那么《骇客帝国》则呈现了数字化时代个人身陷数码海洋中无处逃遁的焦虑。
这部影片更加绝望地把世界呈现为一个完全数码化的世界,主角在先知的指引下才明白自己所身处的现实生活是一种电脑程序。不管是操控世界的邪恶势力,还是拯救世界的“新神”,都是数码化的产物。悖论在于,影片对于数字世界的反省和批判恰好是借助数码技术来完成的,比如最为著名的镜头是用数字技术第一次创造了“子弹时间”。同样的主题在2012年夏季热映的好莱坞大片《饥饿游戏》中再次浮现。这部电影把故事放在未来世界,人类已经放弃以战争来解决争端,按照阶级和工种区分为不同的生存区域,每年要从各自的区选出两名“幸运儿”参加全国性的荒岛生存游戏,以避免各区之间的冲突。影片的有趣之处不在于选手们之间的“大逃杀”(日本知名影片《大逃杀》),而在于游戏设计者或者说庄家随时根据战况增加游戏者的难度和情节,甚至一度为了增加观众的娱乐效果而修改游戏规则,让一对“不抛弃、不放弃”的恋人可以幸存下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处在双重位置上:一方面是后现代世界的影像消费者/观看者,另一方面又是这种影像世界的囚徒/楚门或尼奥。那些参加“饥饿游戏”的选手,谁是游戏者?谁是被游戏者?谁又是赢家?这恐怕是每一个看电影或玩游戏的观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种影像的“牢笼”从上世纪6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进入消费主义、后工业社会,就已经成为理论家们思考的主题。
二、中国电影中的“密室”想象
这种支配性的空间秩序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浮现出来的新故事。中国从80年代开启改革开放,经历90年代的双轨制,到2001年加入WTO,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单一的社会制度和空间秩序,使一种同质化的“密室”想象也出现了,下面仅举两个例证。
第一是“从江湖到宫廷(后宫)”的故事。新世纪之初,国产武侠大片成为带动中国电影产业崛起的电影类型。武侠片作为一种中国电影史中源远流长的叙事类型,经常会处理双重空间的故事——江湖侠客与庙堂权贵的纠结。2001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依然在讲述玉娇龙从官宦之家逃离、奔向自由爱情的江湖故事,很像“五四”时期反对封建大家庭追求个人解放的启蒙叙事,这种朝廷与江湖的二元对立也是90年代式的“禁锢”的官方与“自由”的民间的想象。而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则开始讲述侠客从江湖自废武功、归顺朝廷的故事,至此中国新世纪以来的古装武侠大片中江湖消失了,一种在90年代对民间的自由想象也消失了,只剩下尔虞我诈的宫廷和永无休止的宫斗,比如陈凯歌的《无极》(2005年)、冯小刚的《夜宴》(2006年)、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年)、长影集团推出的《铜雀台》(2012年)等。
这种大银幕上的宫廷大片近些年又进一步“传染”给小荧屏的青春后宫(穿越)剧中,这些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后宫剧把你死我活的“宫斗文”发挥到极致。如热播的《后宫·甄嬛传》(2012年)就讲述大家闺秀甄嬛一旦选秀入宫就只能在闭锁的后宫中选择“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生存方式。宫廷、后宫里没有真爱、没有友情,只能时刻准备参加“饥饿游戏”充当祭品。就像改编为电影的《宫锁沉香》,“笼中雀”(囚禁的金丝雀)再次成为重要的意象出现在剧情和海报中,“笼中雀”是“五四”以来启蒙知识分子用来描述个人处境的比喻。《后宫·甄嬛传》本身也是一种职场剧的后宫版,甄嬛的晋级之路与都市白领在外企公司中的“升职记”是相似的。个人进入社会,就得像甄嬛那样变成奋斗、拼搏的腹黑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人们只能有“同一个梦想”,一个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逆袭之梦。
第二是“密室”中的人质。2006年谍战剧《暗算》成为最火的电视剧,后来又被拍摄为电影《风声》(2009年)。这两部作品把新中国电影史中地下工作者潜伏的故事改写为“捉内鬼”的故事,不是写地下工作者如何有勇有谋地从敌人那里获取情报,而是敌人如何使各种伎俩挖出潜伏者,这就把反特片中从人民内部抓特务的故事变成了敌人抓地下党的故事。这种倒置本身呈现了一种历史叙事和文化想象的反转,也就是说一种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变成了被囚禁在密室中被怀疑、被虐杀的老鼠。谍战故事变成密室杀人游戏,反特片中所包含的敌我对立的冷战逻辑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与封闭空间的对抗。密室杀人游戏正是对这种没有外部空间的内在恐惧,而密室杀人也成为近些年恐怖片的主题。
第六代导演管虎2012年的文艺片《杀生》同样讲述了封闭边远的西南小镇村民合计杀死一个异类分子的故事。一群人或庸庸大众与一个异类或个体的故事,是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典型叙事。如果说这种个人与封闭空间的二元逻辑是“五四”到80年代的文化原型,讲述着无法撼动的老中国与绝望的启蒙者(个人主义)的故事,那么《杀生》则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长寿镇与其说是愚昧封建的老中国,不如说更是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的理性化的“牢笼”,一种卡夫卡式的现代城堡。《杀生》不再相信个体拥有突破牢笼、束缚的启蒙主义神话,反而呈现了个人作为理性机器的祭品的事实,牛结实所能做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命运的安排。这种密室空间在2013年管虎的新片《厨子·戏子·痞子》中也存在,其重要的造型空间就是那间机关重重、密室迭出、暗道密布的日本料理店。如果说《风声》讲述了被日军囚禁在密室之中的地下党老鬼如何牺牲自己把情报传递出去的故事,那么《厨子·戏子·痞子》则是一个倒置的《风声》。日本细菌专家被劫持在一个密室之中,轮番上场的痞子、厨子和戏子通过诱导细菌专家传递情报而获得治愈瘟疫的配方,这些燕京大学毕业的有为青年变成了蝙蝠侠式的超级英雄。
不管是古装武侠大片、后宫剧,还是谍战片、小成本艺术片等,都呈现了一种个人身陷权力、历史迷局的状态,个人再次被书写为历史的人质——一种只能在既定游戏、既定权力格局下成为牺牲品或者赢家的故事。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话语赋予个人反抗、走出去的勇气和希望,那么30年之后个人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和解放,反而深陷“现代”的牢笼之中。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个世界”的想象,其实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后现代“幻想”,从二战以来全球秩序就被区分为去工业化的后工业社会和再工业化的工业社会这样两重空间。
三、“两个世界”与19世纪的归来
消费主义时代也被称为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其背景是二战后欧美经济迅速恢复,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高福利的政策。正如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用“消费社会”来描述处在50-7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法国社会,“黄金时代”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的说法。这是一个蓝领工人白领化、知识精英成为职业经理人、制造业工人开始从事第三产业的时代。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并没有消失,先是转移到日本(五六十年代),随后是韩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地区(六七十年代),最后转移到中国最先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八十年代开始)。这种新的全球产业分工在冷战终结之后以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名义被再次强化,直到新世纪之交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中国过度生产、欧美过度消费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地理学形成。
如果说欧美社会通过不断地产业转移逐步进入去工业化的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实体经济升级为去实体化的金融经济),那么中国则在产业转移中完成新一轮的工业化;换句话说欧美世界的去工业化与中国80年代以来依靠外资和廉价劳动力所完成的工业化是一体两面。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图景下,中产阶级取代了19世纪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二分法成为社会的主体,尤其是以消费者的身份成为大众文化景观中可见的主体。随着产业转移而制造出来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则成为不可见的他者。那些基于西方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也由建立在以生产者/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变成对消费社会、符号经济的批判。这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批评视野同样看不见全球化时代里的双重生产者:分别是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所制造出来的新劳动力大军以及隐匿在第一世界内部的多由非法劳工组成的体力劳动者。这种欧美消费者与第三世界生产者的主体分裂,一方面使得都市中产阶级所从事的旅游经济、文化产业、高科技术、信息产业、金融产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体产业类型,另一方面工业化时代的无产阶级、工业厂房在消费空间主导的都市景观中变成消失的主体和废墟化的空间。这种全球产业的“乾坤大挪移”,造成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中空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化相伴随的是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化。
有趣的是,同样的产业及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内部被复制再生产。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城市化加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崛起,在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对外出口的世界加工厂的同时,中国都市尤其是大都市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消费社会及其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新中产的命名方式出现于新世纪之交,这既呼应着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所催生的脱离体制的弄潮儿、民营企业家,又被想象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以美国为样板的后工业社会的主体与中坚。这种八九十年代以来持续的工业化与新世纪以来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的去工业化,就是农民工和新中产在当下中国登场的历史缘由。如果说新中产与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激进市场化、新世纪加入WTO以来新出现的社会群体,那么相比从事第三产业的新中产被作为主流价值观及样板人生,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则处在匿名、失声的状态。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再现逻辑相似,在中国的文化景观中,能够出场的依然是形形色色的消费者,农民工/生产者隐匿在消费主义景观背后。这种消费者/生产者的身份断裂,不仅使得从事工业劳动的生产者在消费空间中被屏蔽(正如城市建筑工地被绿色帷幔所包裹,而作为消费空间的高档酒店却要用透明玻璃有意暴露厨房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流连/留恋于购物广场的消费者自身作为生产者的身份也被遗忘了。
2012年有一部好莱坞科幻重拍片《全面回忆》,这部影片把未来世界呈现为由两个空间组成:一个是机器保安、戒备森严的后现代大都会,一个是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唐人街式的殖民地空间。技术工人居住在殖民地,每天乘坐穿越地心的高速地铁到大都会工作。这样两个空间不仅是金融危机时代美国与中国的隐喻,而且也代表着消费与生产空间的分裂。不仅如此,近两年来还出现了一种19世纪的经典名著重新改编为电影的热潮,如2011年的《简·爱》《呼啸山庄》,2012年的《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同样讲述了贫富分化的二元世界。在金融危机的时代,这些作品把人们重新带回风起云涌的20世纪之前的岁月。
四、平行世界的故事
近些年,与《全面回忆》相似,有多部好莱坞科幻片讲述双重空间的故事,世界被区分为上层和下层或者被遗弃的地球和漂浮在外太空的大都会,如《机器人瓦力》(2008年)、《阿童木》(2009年)等。这种双重空间并非新出现的文化想象,可以说是科幻叙事的经典主题。1895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创作的《时间机器》就呈现了未来世界中地上被奴役、地下高度发达的故事;1927年德国导演弗里茨·朗执导的黑白默片《大都会》第一次在影像上讲述了这种机器人在底层提供劳动、人类居住在上层的世界图景。如果说这些作品用两极化的社会图景来隐喻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悲惨世界”,那么这些看似相似的表述再度出现,却呈现了全球化时代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分裂与对抗。
2013年初法国与加拿大联合拍摄的《逆世界》就呈现了这样两重空间,繁华富丽的上层空间和肮脏贫困的下层空间是两个彼此平行、相向而立的世界,连接两个世界的是一处叫通天塔的跨国公司,来自下层的屌丝男爱上了上层的白富美。当然,结尾也采用了逆袭成功的大团圆结局,这符合商业电影充当白日梦的功能。无独有偶,2013年9月份在中国上映的《极乐空间》同样讲述了两重世界的故事。这部大量使用手提摄影的科幻片,是执导科幻片《第九区》的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在未来世界地球变成了人口过剩、垃圾成堆的贫民窟,而富人们则逃离地球在外太空建立了一个“极乐空间”。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绿荫婆娑、高度发达的世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无不向往那样一个遥不可及的天堂。一个在给极乐空间生产机器人的工厂里上班的工人马克,因工伤被感染只剩下五天的生命,他发起了“偷渡”极乐空间的逆袭之旅,结尾处马克献出自己的生命格式化极乐空间的操作系统,从此极乐空间向地球人敞开了大门。这确实很像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值得关注的不在于好莱坞个人主义英雄再一次拯救了世界,而是世界被想象为富裕和贫穷的两极化世界,一个19世纪的社会寓言被重述。
与这样两部西方人拍摄的科幻片不同,近期还有两部亚洲电影用现实题材的方式也处理了相似的主题:一部是韩国暑期上映的讲述恐怖袭击的电影《恐怖直播》;一部是2012年在印度上映的以纳萨尔派游击队为原型的影片《无法避免的战争》。《恐怖直播》也采用手提摄影营造紧张气氛,场景基本上就是一间狭小的演播室。工作失意、与妻子离婚的男主播意外地与汉江大桥爆炸案的恐怖分子电话连线,于是,一场与恐怖分子对话的现场直播成为最引人关注的媒体事件。就像布洛姆坎普的《第九区》中人类管理员在身体变异中理解了被囚禁的外星人的悲惨境遇,这个以为拿到独家新闻即将升职的主持人尹荣华,在与扬言要继续制造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周旋的过程中,逐渐从不顾民众死活的总统、飞扬跋扈的警察局长、只关心收视率的媒体上司的世界中清醒过来,最终认同这个替作为工地工人的父亲索要总统道歉的恐怖分子。这同样是两个世界的故事,对于30年生计没有改善的工人来说,想引起媒体、公众以及政府的关注,除了极端的恐怖袭击外别无他途,而尹荣华的绝望在于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的把恐怖分子的“要挟”当回事。
如果说《恐怖直播》呈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达社会依然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弱势群体找回尊严的问题,那么《无法避免的战争》则讲述了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的反政府游击队的故事。影片以警察安插在游击队里的卧底卡比尔从为警察卖命到认同于游击队理念为线索,正面阐释了为何游击队与警察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这部影片很像科幻巨片《阿凡达》中美国士兵杰克倒戈纳威人打败武装到牙齿的人类开发商的故事,只是《阿凡达》中美轮美奂的潘多拉星球是一种对原始部落、前现代文明的浪漫想象,而《无法避免的战争》中的“潘多拉”则是贫穷、不断遭受政府和大企业剥夺的、活不下去的地方。影片也反思了政府与企业联手推动的工业化项目及其发展主义逻辑,不仅无法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反而使他们变成失地农民,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发展困境。
这样四部影片虽然风格各异、题材类型也不同,但它们却讲述了平行世界的故事。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两种泾渭分明的世界不仅存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而且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就像《无法避免的战争》一样,以政府、企业、警察所代表的城市文明和以暴力、贫穷、落后所代表的乡村世界的对峙,是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样两重空间的出现,与上世纪下半叶全球产业分工有着密切关系。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世界把制造加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随之在欧美世界出现了一个去工业化的消费主义时代;正如《极乐空间》《逆世界》《恐怖直播》中所呈现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既绿色又环保的上层世界,而这些承接工业化产能的第三世界则变成污染严重的代工工厂,工人成为下层世界的代表。如果说上层世界是消费的、物质丰裕的世界,那么下层则是生产性的、被忽视的空间。尽管两个平行的世界借助通天塔来沟通,但是两个世界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却充满了偏见和怨怼。就像《恐怖直播》中,没有谁会认真对待一个工厂工人的威胁,没有谁真正关心大桥上人质的安危,包括电视主播在内都想从这样一次“电视真人秀”中捞到好处。
这四部电影的启示在于提供了平行世界之间的几种可能关系:第一种是最乐观的,《逆世界》中屌丝通过努力在上层世界与心爱的女孩喜结良缘;第二种是最有想象力的,重新改变《极乐空间》的操作系统,让两个世界融为一体;第三种是最恐怖的,在《恐怖直播》中无助的弱势者发动个人恐怖袭击;第四种是最绝望的,就是无法避免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没有走出19世纪的幽灵,而且正处在从个人恐怖袭击向平行世界的战争过渡的时期。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和大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