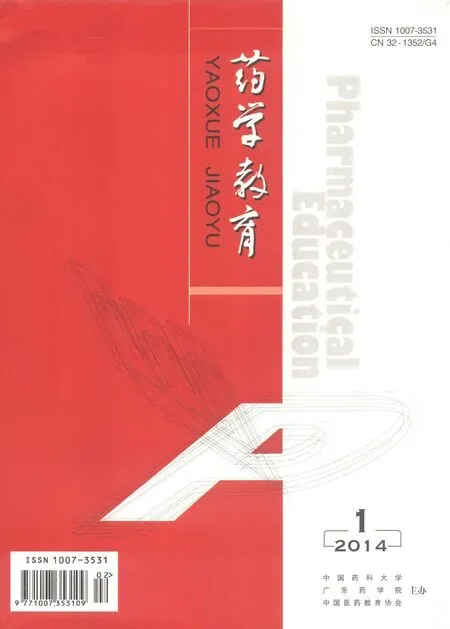药剂学课程渗透通识教育理念的实践*
沈腾 张奇志 方晓玲
复旦大学药学院 (上海 201203)
通识教育是对自由教育、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才教育等教育理念进行或继承或融合后而被广为接受和实践的一种大学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1]。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和复旦大学的复旦书院是近年探索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不仅能够给学生以严谨的专业知识和严格的专业技能训练,还能让学生分享深入人类某一精神活动和智力领域的经验,在思考和探索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学术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养成。美国大学院校联合会研究表明,21世纪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将走向新的融合,鼓励专业课教师承担通识教育的责任[2]。
药剂学是将原型药物制备成用于治疗、诊断、预防疾病所需形式的一门学科,即以药物剂型和制剂为对象,研究其基本理论、处方设计、生产工艺、质量控制和合理应用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其宗旨是制备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顺应性的药物制剂[3]。药剂学是一门在其产生、演化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散发着浓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气息的学科。因此笔者在药剂学课程中充分挖掘和提取通识教育的精神并渗透至专业内容的教学实践当中,使通识教育与专业课程融会贯通,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通过追溯历史激发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每种剂型的发展历史,重大发现的产生、变革和科学家的奉献精神等,都蕴含了通识教育的精神。中国剂型发展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对药品就有“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谚语。夏商周时期的医学《五十二病方》、《甲乙经》、《山海经》,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中都有关于药物剂型和疗效关系的记载。西方药剂学起始于公元一世纪前后,被欧洲各国誉为药剂学鼻祖的格林对植物制剂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专著中著录了散剂、丸剂、浸膏剂、溶液剂、酊剂、酒剂,人们称之为格林制剂。随着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机械文明的发展,药物制剂的生产工艺发生巨大的变化,药剂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从原来的药物学中独立出来,同时药剂学的研究范围也突破了格林制剂的范围,不断地扩展。现代药物制剂已从普通制剂进入到药物传输系统时代,包括缓释制剂、控释制剂和靶向制剂等。
除了在总论中介绍中外药剂学的总体发展历史外,各剂型的历史追溯可以引导学生把握技术发展的脉络,感受人类锲而不舍的实践精神。例如,现代注射剂最早来源于古代用毒箭治疗毒蛇和昆虫咬伤,而后采用粗针穿刺技术进行天花病毒和牛痘的接种,19世纪后半期在微生物理论依据下发展了皮下注射器和安瓿;1875年发明了灭菌和防腐技术;1911年确定溶液中的“热原”会致热,必须采用无菌蒸馏水配置注射液;直至1930年Radmaker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无菌防范措施和规章制度,奠定了现代注射制剂的基础。
在药剂总论或各论中将剂型的中西方沿革历史介绍给学生,这些与学科有关的历史铺垫渗透了科学和人文精神,让他们感受到药剂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生动丰富的学科,加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激发学生对药剂学这门课程的兴趣,促进对专业的认同感,为将来大力发展祖国的药学事业贡献力量。药剂学历史素材的提取要善于利用中外文不同版本的教材或者参考书籍,笔者在教学中经常利用的参考资料有《Encyclopedia of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Ansel's Pharmaceutical Dosage Forms and Drug Delivery Systems》、维基百科网站等。
二、利用普遍联系原理掌握交叉学科的学习方法
与其他药学专业课程不同,药剂学科涉及到非常庞大和具体的知识基础,具有实践性强、应用面广、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其内容与许多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化学、高分子材料学、基因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在科学研究上存在大量的交叉与渗透,每个学科的发展对药剂学科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教授教授Robert Langer教授利用聚酸酐的不稳定性,开发出可生物降解的高分子材料,并成功地应用于药物控制释放领域。利用生物降解材料聚乳酸-羟基乙酸开发的亮丙瑞林缓释微球注射剂在肌肉注射后可在体内稳定释放长达一个月,大大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治疗效果。又如,美国肯萨斯大学教授Ronald T.Borchardt经常关注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他最早注意到人克隆结肠腺癌细胞(Caco-2细胞),在结构和功能类似于分化的小肠上皮细胞,可以用来进行模拟体内肠转运的实验。由此开发的Caco-2细胞模型是十几年来国内外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药物小肠吸收的体外模型,具有相对简单、重复性较好、应用范围较广的特点。在历史上,药剂学的重大发现往往是由交叉学科中产生并推动的,将这种科学发现的普遍原理告知学生,使他们有意识积累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有朝一日能够运用到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增强解决问题的创造力。
药剂学大厦是由众多的分支学科如工业药剂学、生物药剂学、药物动力学等和基础学科如生理病理学、解剖学、物理化学等共同支撑建立的[4],所涉及的知识面必然广博繁杂,内在的逻辑联系也必然千丝万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药剂学的知识点分散零碎、不够系统透彻。教师可以采用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来组织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善于采用归纳总结、启发联想、逻辑推理、考察调研等学习方式。例如,在讲授片剂的各分类剂型时,可以安排学生去网络上检索或者去药店调研泡腾片、口含片、缓释片等剂型的常见品种,分析剂型的选择与药物自身理化性质、生物药剂学性质、临床病理生理、商业策略等等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充分掌握不同片剂剂型的丰富内涵。对同一种辅料在不同剂型上的应用可以让学生归纳总结并讨论。总之,针对药剂学的学科特点,应用普遍联系的原理,善于变换不同的教学方式,多角度启发学生的思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也是通识教育的要义。
三、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在一项对药剂学人才需求的调查结果表明,运用传统模式培养的药剂学人才,其思维方式以模仿、验证为主,缺乏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不强,其知识运用能力已与制药行业的发展不相适应。通识教育的真实目标是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创造性人才奠定独立思想和精神感悟的基础。在教学中有意识地采用以问题为中心,通过设定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培养创新意识,拓展创新思维。例如,选定一个模型药物,让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其临床应用情况以及有关理化性质与生物学性质,据此选择合理的剂型,并对处方与工艺进行设计。这样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一种探索精神。此外,将药剂学中目前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引入课堂教学,如探讨难溶性药物的增溶问题,除了教科书上提供的标准答案外,鼓励学生进行思考和质疑;最后再与学生分享文献报道在该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情况,开阔学生的思维和眼界,无形之中就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另外,可将教研室的科研成果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教研室的科研成果往往是药剂学科最前沿的研究内容,并代表了教研室的学科特色和水平,也是教师们多年的科研积累和总结。
例如,在讲解靶向制剂这一章节时,笔者以复旦大学药剂学科的两项“973”项目为例介绍脑靶向的最新研究进展,让学生近距离的感受知识产生的起因和过程,近距离体验教师解决问题的历程和思路,从而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原动力,增强自身参与知识构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培养研究与创新意识。教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渗透入教学内容的同时,学生可以感受和学习教师的治学态度、学术修养和人文精神,对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培育职业精神,增强责任意识
药物制剂,作为药物的最终给药形式直接供患者使用而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药品安全事件频发,涉及到药品生产管理的各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在教学时以此为反面教材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在教学中重点分析安徽某公司克林霉素膦酸酯葡萄糖注射液,该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利润,未按批准的工艺参数灭菌,擅自降低灭菌温度、缩短灭菌时间等工艺指标,导致无菌与热源检查均未达标,2006年因注射欣弗死亡11人恶性事故,造成重大社会负面影响。通过“欣弗”事件能使学生明白灭菌操作的严格性,丝毫不能马虎,并可进一步引导学生从中吸取教训,即未经验证、审批,不得随意改变药品的生产工艺,否则有可能酿成严重后果。2011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在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力百汀)中检出塑化剂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由于长期摄入高剂量的塑化剂可影响肝脏和肾脏,或可能致癌,因此决定立即停止销售和使用,此事件提示在制剂制备时对辅料的安全性不容忽视。此外,中药注射剂鱼腥草事件,“齐二药”的亮菌甲素注射剂、有毒明胶等安全事件都令人发醒。
在药剂学教材中也包含了一些法规的内容,例如对一些剂型的定义、质量要求、质检方法等的描述可以还原它的出处,并根据这些法规的修订情况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从而将教材与法规联系起来,引起学生对法规的重视。将《中国药典》、《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物研究指导原则》等法规作为专业参考资料推荐给学生,并布置一些课后习题,如统计《中国药典》中栓剂的种类与数量,让学生通过查阅了解、熟悉这些法规,逐渐形成一种规范意识,树立药品安全生产和管理的责任意识。
在通识教育背景下,要在专业教育中融入通识教育的精神,笔者的体会是教师自身首先要确立通识教育的理念,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建立培养“完整的人”的信念。其次要打破原先教学中建立的仅限于专业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训练的“条条框框”,勇于尝试和实践通识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和提取专业知识中具有体验性、实践性和讨论性的元素[5],进行课程的有效构建和整合,从而有意识地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唤起学生对专业的传承与创新。总之,渗透通识教育精神的专业教学是大有可为的。
[1]张慧洁,孙中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综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81.
[2]闫晓天,胡鸿毅,林勋.高等中医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9,9:40.
[3]方晓玲主编.药剂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4]鲁莹,钟延强,樊莉.药剂学课程群建设与实验教学改革和探索[J].药学教育,2012,28(2):20.
[5]王德峰.从大学理念看通识教育的方向与道路[J].复旦教育论坛,2006,4(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