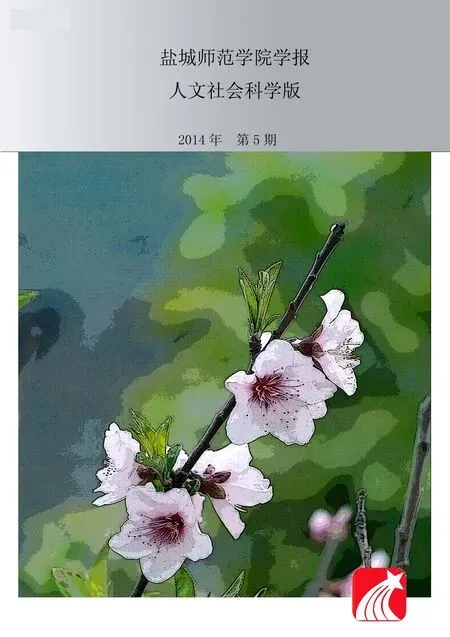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张金环
(中国石油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吴伟业词作数量较少,主要以其“梅村体”诗史而并非以词名世,故长期以来,学界对梅村词所论较多的是其反映“诗人”人格心态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吴伟业的词学观念及梅村词本身在词史上的贡献并无足够重视。事实上,梅村词在清代曾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其词学观念与创作实践,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与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深远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变。本文拟从吴伟业的词学观念、创作实践、影响与传播三个方面,论述他在清代“词史”观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对后世“词史”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 吴伟业“词史”观内涵
在明朝灭亡以前,吴伟业与当时多数词人一样,以词为“艳科”,创作了大量缠绵悱恻的艳情词。但随着明清鼎革的时代巨变,他与云间派等“词以婉约为正”的词学宗尚开始渐行渐远,自云:“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摹秦、柳。中岁悲歌诧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喑噫不能出声……”(《评余怀秋雪词》)[1]1233,创作观念明显转变。认为词不应该只写“香奁艳情”,也应如诗一样发“悲歌诧傺之响”,甚至应该比诗歌的表现功能更广:
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阙。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且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传奇、杂剧,体虽不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杂剧三集序》)[1]1211
认为词、曲与诗的源头、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言长”还是“言短”的区别,当然也就无所谓“诗庄词媚”。与诗相比,词的价值正在于其篇幅更长,更能“纵发欲言”,承载诗歌所无法承载的内容与情感。在实践中,其本人词创作也由早期以小令为主,变而为中调,又变而为长调居多,亦印证了此一观点。尤侗曾这样描述梅村诗与词、曲之间的关系:“今读其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盖先生之遇为之也。词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为词,词可为曲,然而诗之格不坠,词、曲之格不抗者,则下笔之妙,古人所不及也。”[2]316指出其诗与词、曲相通的一面:都以抒写兴亡盛衰为主题,皆合乎风雅之旨。梅村诗、词、曲三种不同文体之所以会呈现出相似的风貌特征,显然是词、曲向诗靠拢的结果。那么词与诗的区别,即吴伟业所谓须借词才能“纵发欲言”的具体内容指的是什么呢?《倡和诗馀序》云:
余影结梅村,兴颓药圃。鹤城仙去,时逢怆笛山阳;鸥渚舟横,久绝献环洛浦。属瑶函之寄,掳委婉于四愁;看锦字之贻,写缠绵于七辨。铜丸应手,音节沉雄;玉管调心,宫商窈眇。爰题尺素,随托双鱼。弟兄胥掩张、刘,恨乏卢谌之叙;童子亦跨辛、陆,惭非永叔之褒。须知碧草粘天,秦楼可赋;黄尘匝地,梁苑难言。惨角悲笳,非春院咒花之客,啼香怨粉,尽秋江酬月之人尔。[3]1
谓国亡后自己“影结梅村,兴颓药圃”,得宋氏《倡和诗馀》而觉其“掳委婉于四愁”、“写缠绵于七辨”,于心境独合。认为宋氏等词虽写“碧草粘天”、“啼香怨粉”,而实乃伤时感世,因“秦楼可赋”而“梁苑难言”。事实上,《倡和诗馀》词包括向来为人所称道的陈子龙《湘真阁存稿》29首,绝大多数仍然只是写“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4],与所谓“梁苑难言”的家国兴亡并无多大关涉。宋征璧《倡和诗馀再序》即自谓 :“相订为斗词之戏,以代博弈……挹子晋之风流,人人玉管;揽广陵之烟月,树树琼花者矣。”[3]3由此可见,梅村此序乃曲为之说,实为个人主张张本:词当写诗所不能畅所欲言的兴亡盛衰之“事”与“情”,实质即“诗史”观的延伸。孙枝蔚称其“以史料为词料,是梅村长技”。[1]537可谓知言。
词比诗更能“纵发欲言”的原因,除“其言益长”等体式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吴伟业没有明言,即在“诗祸”、“史祸”频发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有些敏感的话题,用词这种在当时仍被普遍目为“小道”的文体来表现,显然比用诗歌更合适。因此,他突破明末盛行的“诗庄词媚”观念,认为词与诗同源同质,既然诗可纪史、传心,那么词亦可纪史、传心,且能写“诗史”所不能“纵发欲言”之情、事,极大地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吴伟业尽管尚未明确提出“词史”概念,但显然已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词史”意识。
二、“词史”观之实践:比“诗史”更能“纵发欲言”的“词史”创作
基于自觉的“词史”意识,梅村词于“倚红偎翠”之外,首开清代“词史”创作的先河。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史”入词,使词亦具有史料价值。纪录易代史实,反思兴亡原因,抒发故国之感,表现“诗史”所不能畅所欲言的史事,是后期梅村词最突出的题材特征。如长调《满江红·蒜山怀古》:
焦页42号平台是涪陵工区首次“井工厂”同步压裂施工,也是张相权参与的该工区规模最大、设备使用最多、施工工序最复杂的一次超大型施工作业。作为队长,张相权丝毫不敢马虎。那段时间,每天的施工运行都达到饱和状态,每个工具都得详细检查才入井,每个工序都得亲自确认才放心,最轻松的一天睡6小时,最晚的只有不到4小时。
沽酒南徐,听夜雨、江声千尺。记当年、阿童东下,佛狸深入。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笑风流、北府好谈兵,参军客。 人事改,寒云白,旧垒废,神鸦集。尽沙沉浪洗,断戈残戟。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任黄芦苦竹打荒潮,渔樵笛。
此词乃顺治十年秋,作者被迫应征北上途经镇江时所作。写词人沽酒京口旧战地南徐,在萧瑟凄凉的夜雨江声中吊古伤今,回忆反思南明的亡国痛史。上阙以古喻今,借西晋大将王濬(小字阿童)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狒狸),写当年清兵南下,迅疾攻下镇江、扬州之事。指出马士英、阮大铖把持下南明小朝庭的荒唐可笑,大敌当前,国家军队竟不如一介“白面书生”。下阙化用辛弃疾、杜牧、刘禹锡、李白等人诗词成句,抒发蔓草铜驼、人事全非的黍离之痛,将吊古伤今的诗词意象重叠溶合,不仅曲折地传达了欲言难言的亡国之痛,而且将明清易代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使一己的亡国之痛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反思。又如《满江红》其他调亦复如此:《白门感旧》写弘光南渡、明朝灭亡;《感旧》“满目山川”写弘光君臣荒淫误国,葬送南明半壁江山;《重阳感旧》写“故宫非,江山换”的兴亡历史;《过虎丘申文定公祠》写“三公旧事”与“今古恨,兴亡迹”……正如范汝受所云:“(《满江红》十三调)其中具全部史料,兴会相赴,遂成大观。”[1]571杜于皇所谓“江山如梦,不减一声河满”。[1]564曹尔堪则直以“词史”称之:“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1]564再如《望江南》十八首,靳荣藩以为“有明兴亡,俱在江南,固声名文物之地,财赋政事之区也。梅村追言其好,宜举远者大者,而十八首中止及嬉戏之具、市肆之盛、声色之娱,皆所谓足供儿女之戏者,何欤?盖南渡之时,上下嬉游,陈卧子谓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梅村亲见其事,故直笔书之,以代长歌咏叹。十八首皆诗史也,可当《东京梦华录》一部,可抵《板桥杂记》三卷,或认作烟花账簿,恐没作者苦心矣”。[1]538看重的正是梅村词与“诗史”并行,“直笔书之”的史料价值。而以史事入词,正是清代“词史”观的一个重要内涵。
第二,以词传“心”,使词亦具有“心史”价值。抒发失节之恨,写“诗史”所不能“纵发欲言”的心迹,是后期梅村词的又一重要主题。如名作《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词中虽有“脱屐妻孥非易事”苦衷的诉说,但更多的却是对自己“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的悔恨自责。“剖却心肝今置地”,丝毫不掩饰失节辱志的“罪孽”,词人对自己一生作出“一钱不值何须说”的结论,可谓字字血泪。如此真切沉痛的悔恨与刻骨铭心的自责,是总不忘重塑诗人形象的“梅村体”诗史所罕见的,正如靳荣藩所言“为平生心血所寄,而发其诗之所未发”[5],比其真正的绝笔《临终诗四首》更加酣畅淋漓、情真意切。正因如此,此词被后世许多论者误以为梅村绝笔,如比梅村稍后且与之有过交往的尤侗即云:“及临终一词云……其恨恨可知矣。论者略其迹,谅其心可也。”[6]陈廷焯亦云:“此梅村绝笔也。悲感万端,自怨自艾。千载下读其词,思其人,悲其志,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有别。”[7]再比如《满江红·重阳感旧》在感怀国事的同时,表白“富贵本浮云,非吾愿”的心迹;《木兰花慢·过济南》、《金人捧露盘·观演〈秣陵春〉》、《满江红·感旧》等则传达出“叹鲍叔无人,鲁连未死,憔悴南归”、“庾信哀时惟涕泪,登高却向西风洒”、“无限恨,断人肠”的失节之恨……可见,与赋予“诗史”以“史外传心之史”的“诗史”观一致,梅村亦赋予词以抒写“心史”的功能,是梅村词对清初“词史”创作的独特贡献。
第三,以史笔写词,开创了“词史”的特定形式。如上所述,“词史”观念引起内容的变化,而内容的变化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引起形式的变化。梅村“词史”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以个人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以小见大,叙述史实,抒发兴亡之感。如《风流子·掖门感旧》:
咸阳三月火,新宫起、傍锁旧莓墙。见残甓废砖,何王遗构;荒荠衰草,一片斜阳。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执经横卷,奏对明光。 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
上阕写在甲申国变的彻天烽火之后,清朝已建起新的宫殿,但宫旁仍可见明故宫的旧墙废垒、残砖遗瓦,长满荒荠衰草,勾起词人无限伤心往事。于是紧接着回述自己十八年前于文华殿为太子讲经,“左相按班,百官陪从”的隆重礼仪和盛大场面,以及词人“执经横卷,奏对明光”的情形。下阕接着叙述崇祯帝含笑垂问《尚书》大义、“共退东厢”,又“忽命紫貂重召”、赐以“龙团月片,甘瓜脆李”的特殊恩遇与君臣言笑晏晏的欢洽情景,当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风光荣耀!最后却以一句“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陡然作结,身世之悲,亡国之恨,沧桑之叹……无限伤心沉痛尽在其中!故沈雄云“余读其‘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几使唾壶欲碎”[1]580。通过对个人身世遭际的叙述,反映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详略开阖,擒纵起束,正如梅村体“诗史”一样:“以龙门之笔行之韵语。”[1]259故程穆倩评曰:“一气奔放,直是唐人叙事之文。”[1]580又如《满江红·题画寿总宪龚芝麓》“数十年事,以前半阕数语叙尽”[1]564,《满江红·寿顾吏部松交五十》“前段写其脱险,后段是园居之趣”,《木兰花慢·寿汲古阁主人毛子晋》、《烛影摇红·山塘即事》、《沁园春·赠柳敬亭》、《贺新郎·送杜将军弢武》、《风流子·为鹿城李三一寿》、《风流子·题画寿总宪龚芝麓》等虽是应酬之作,但均以个人命运映照历史变迁,如一篇小传,且如王士祯所云“娄东长句,驱使南、北史,妥帖流丽,为体中独创,不意填词亦复如是”[1]567,体现出以史法写词的创作倾向,开创了“词史”的特定形式。“将词法与史法相结合,以对写史方法的比附作为创作价值的某种重要体认。这些,当然也就构成‘词史’说的重要内涵”[8],故在这一方面,梅村词亦为“词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借鉴。
总之,梅村词正因其既传“史”又传“心”,形成了“意气遒上,感慨苍凉”的独特风貌[9],“在国初实开宗风”[10]3428,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及后世“词史”创作影响深远。
三、梅村“词史”的传播与接受
的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明清之际,很多词人笔下都有堪称“词史”的作品,并非只有梅村词独具“词史”特质。但梅村“词史”创作不仅自觉、集中,而且因其风雅领袖的身份,对清初“词史”观的形成影响颇大。这一点,通过梅村词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可得直接证明。
第一,从吴伟业与明末清初词人的交往来看。在“词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陈维崧无疑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其《词选序》“选词即在存经存史”的论断被公认为清代“词史”观确立的标志。陈维崧正是以“词史”为重要衡量标准,将梅村词选入其《今词苑》与《箧衍集》的。他在《酬许元锡》一诗中自述学诗词经历云:“嘉隆以后论文笔,天下健者陈华亭。梅村先生住娄上,斟酌元化追精灵。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华亭叹我骨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二十以外出入愁,飘然竟从梅村游。先生呼我老龙子,半醉披我赤霜裘。”[1]1704言其早年师承陈子龙,可谓登堂入室。但鼎革后,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转而受教于梅村,并深得梅村赏识。吴伟业是维崧父执辈,在明朝即与其父陈贞慧交好,故维崧自幼便从其游。吴伟业对这位晚辈也称赏有加,将其与另外两位友人之子彭师度、吴兆骞一起誉为“江左三凤凰”,有《读陈其年邗江白下新词四首》盛赞其词其人,其中“长头大鼻陈惊坐,白袷诸郎总不如”之句传诵一时[1]524。正是由于相似的命运变迁,二十岁后的陈维崧转而更加认同吴伟业,始终与之过从甚密。如顺治十年,梅村被清廷强征北上,遇陈维崧于镇江,召其饮于舟中,陈维崧《吴骏公先生招饮京口舟中,时先生将渡江北上》诗曰:“……先生顾盼饶大略,旌旗猎猎弓弦拓。夜深铺叙声琳琅,玉箫金管江上作。十年风调羽扇轻,耻与田窦相纵横。玄圃著书意不怿,后湖论兵功未成。自言海内烽烟蔽,白首词臣念遭际。故将终思灞浐隈,新恩不羡清漳第。陈生慷慨弹云和,双鬟倚瑟为之歌。朱雀公卿谁健在?青溪子弟奈愁何!横江祖饯明星湿,白牙樯上乌啼急。君不见枯树谁怜庾信哀,玉关终望班超入。”[11]1707对梅村诗词才华赞赏不已,以庾信方之,对其遭遇深表同情。顺治十五年,陈维崧过娄上,梅村设宴款待,并介绍弟子许九日与之相识[11]19;顺治十七年,陈维崧至太仓、昆山,访梅村并为冒襄五十请寿言[1]773。又如陈氏《寄云间宋子建并令嗣楚鸿》诗以“为梅村太史所赏”为赞扬“楚鸿工词曲”的依据:“君不见娄东太史青门宅,爱度新声劝宾客。就中令子词最多,四弦鹍鸡声裂帛。”[11]1694《念奴娇》词赞梅村曰“祭酒能为解散髻,下语千人都伏”[11]1331,甚至以“斯世之纪纲”[11]1669誉之。可见陈氏受梅村影响之深,“心慕手追”谅非虚言[11]90。维崧四弟陈宗石评其鼎革之后所作词曰:“或孤蓬夜雨,轗轲历落;或风廊月榭,酒枪茶董;或逆旅饥驱,或河梁赋别;或千里怀人,或一堂燕乐;或须髯奋张,酒旗歌板,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11]1830正同梅村词一样,惯用长调,通过个体命运写家国兴衰,溶身世之感于时事之慨。康熙十年前后“词史”观的提出,正是其入清以来创作观念的理论总结,而在此过程中吴伟业的影响显然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不止陈维崧,明末清初大部分词人都对梅村词评价极高。比如同是陈维崧父执辈、且与吴伟业交往密切的龚鼎孳、冒襄、曹溶等人;稍晚与陈维崧同时且过从甚密的众多词人,除吴伟业笼罩下的娄东诸子及前文已提到过的孙枝蔚、曹尔堪、范汝受、程穆倩等人外,又如孙默、邓汉仪、邹祗谟、董以宁、董俞、杜于皇、袁于令、李渔等人,都对梅村词有极高的评价,其中如吴绮、尤侗、余怀、王士祯等著名词人,甚至视之为师。由此可见,吴伟业在清初词坛的地位和影响,可见其在“词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清人所辑清词总集或选集对待梅村词的态度来看。较早如孙默《国朝名家诗余》39卷(康熙初留松阁刻本),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当代词总集。孙氏以《梅村词》2卷编首,并请尤侗评次、作序,尤侗序云:
若推当代之隽,擅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见梅村先生耳。先生文章彷佛班史,然犹谦让未遑。尝谓予曰:‘若文,则吾岂敢?于诗或庶几焉。’今读其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及所制《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盖先生之遇为之也。词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为词,词可为曲,然而诗之格不坠,词曲之格不抗者,则下笔之妙古人所不及也……予于先生琴樽风月未?平生,故谬附知言,序其本末如此。予观先生遗命于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词人吴某之墓’,盖先生退然以词人自居矣。夫使先生终于词人,则先生之遇为之也,悲夫![12]
可见孙氏与尤侗对梅村词推崇备至,正是有取于其“诗可为词”,即与其“诗史”相通的“词史”价值。正如许多学人所言,此集对清初词坛尤其是广陵词坛及由广陵词派分出的倡导“词史”观的阳羡词派影响甚巨,其中吴伟业的开山之功于此可见。又如康熙间顾贞观、纳兰性德《今词初集》,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钞》,同样以梅村词编首,聂先序曰:“有欲合刻梅村、香岩、棠村三大家词者。以梅村骀宕,香岩惊挺,棠村有柳欹花亸之致。或谓河北河南,代为雄视,未若三公之旨之一也。意气遒上,感慨苍凉,当以梅村为冠。”[9]推重之意不言而喻。另外如康熙间陈维崧《箧衍集》和《今词苑》、邹祗谟《倚声初集》、蒋景祁《瑶华集》、王士祯《感旧集》、尤侗《鹧鸪斑》、沈雄《古今词选》,乾隆间夏秉衡《清绮轩词选》,嘉庆间王昶《国朝词综》等著名清词选集无不推尊梅村词。当然,否定者亦有之,如乾隆间蒋重光《昭代词选》便不选梅村词,谢章铤对此极为不满:
蒋子宣曰:“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梁苍岩诸人,词俱名家。然取冠本朝,殊乖教忠之道,一概置而不录,于体为宜。”其说甚正。然谈艺非讲学比也。诸公在国初实开宗风,不独提倡之功不可忘,而流派之考更不可没。夫钱文僖词载于宋,赵文敏词登于元,昔人不以为非,编次之例应尔。信如子宣之言,则诸公之作将附于胜国乎?抑另编一集乎?况五代十国,词家率多身更两姓,非付之秦火不可。西河、西堂辈名挂前朝学籍,推类至尽,亦不宜选矣。进退之间,动多窒碍,乃至高论非通例也。……子宣采取,亦殊失真。至梅村,“淮南鸡犬”,眷恋故君,其《贺新郎·病中有感》云云,不作一毫矫饰,足见此老良心,读之鼻涕下一尺。述庵奈何竟置此词于不选乎?此词关系于梅村大矣。述庵其未讲知人论世之学哉。[10]3428
梅村词在清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其可供“知人论世”的“词史”价值,信如谢氏所言“不独提倡之功不可忘,而流派之考更不可没”。
第三,从清代词论家对梅村词的评价来看。梅村词在清代屡被目为诸家之冠,在此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梅村词,亦艺林所称引,谓其婉靡雄放,兼有周柳苏辛之长,本朝词家推为冠冕。(程穆衡《吴梅村先生诗余序》)
吴梅村诗名盖代,词亦工绝。以易代之时,欲言难言,发为诗词,秋月春花,满眼皆泪。若作香奁词读,失其旨矣。(陈廷焯《词坛丛话》)
吴梅村祭酒,为本朝词家之领袖。其出处绝类元之许衡,慢声诸词,吟叹颓息,苍莽无尽,盖所谓有为言之者也。(张德瀛《词征》)
明崇祯之季,诗余盛行,人沿竟陵一派。入国朝,合肥龚鼎孳、真定梁清标,皆负盛名。而太仓吴伟业尤为之冠。(徐珂《近词丛话》)
透过这些评价,不难看出吴伟业对清词创作的影响。吴衡照云:
太仓自梅村祭酒以后,风雅之道不绝。王小山[时翔]与同里毛鹤汀[张健]、顾玉停[陈噀]倡词社。又有王汉舒[策]、素威[辂]、颍山[嵩]、存素[愫]、徐冏怀[庾]辈起而应之,几於人人有集。……洵乎与浙西六家,异曲同工矣。[13]
其实,梅村词的影响远不止娄东一地。正是由于吴伟业榜样于前,陈维崧等阐扬于后,“词史”观才渐渐深入人心,至晚清“在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历史环境中,成为不少作家创作的指导思想”[14]。如邓廷桢、林则徐、龚自珍、蒋春霖、薛时雨、张景祁、王鹏运等人都无愧“词史”之称,书写了清词史上璀璨的一页,其中不少人受吴伟业直接影响,如龚自珍“明知其非文章之极,而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15],又如薛时雨:“祭酒风流俨若存,一丛香草伴吟魂。”[16]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吴伟业虽非以词名世,在清代词史上甚至算不上特别重要的大家,但其“词史”观与成功的创作实践,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清代“词史”创作却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为明清之际词风转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尤侗.尤西堂全集:西堂杂俎三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29.
[3] 陈子龙,等.倡和诗馀[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4] 彭宾.彭燕又先生文集[M].清康熙六十一年隆略堂刻本:18.
[5] 靳荣藩.吴诗集览[M].清乾隆年间苏州埽叶山房刻本.
[6] 尤侗.艮斋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2:99.
[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济南:齐鲁书社,1983:251.
[8] 张宏生.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J].南京大学学报,2008(1):101—107.
[9] 聂先.百名家词钞序[M].四库全书本.
[10]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M].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陈维崧.陈维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 孙默.国朝名家诗余[M].四库全书本.
[13]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M].词话丛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6:2474.
[14] 傅璇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93.
[15]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66.
[16]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M].宣统三年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