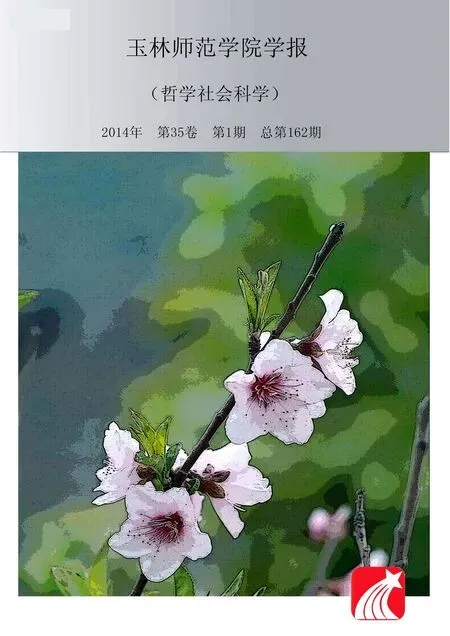正义视域下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分配标准评析
□彭本利
(玉林师范学院 法商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正义视域下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分配标准评析
□彭本利
(玉林师范学院 法商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如何分配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是国际气候谈判争论的焦点,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义务的分配标准不能达成一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分析了目前国际社会认定温室气体排放权和分配减排义务的标准,然后对这些标准从正义的角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最后就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可采取的立场和对策提出了建议。
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标准
温室气体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如何分配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也就成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议题。由于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设置,关系到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分配,关系到各国的发展空间,所以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谁承担减排义务、如何减排、减排多少的问题始终是各国激烈争论的焦点,对温室气体排放权和减排义务的分配标准不能达成一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主要的原因便是各国对气候变化正义的不同理解。每个国家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张对本国最为有利的标准确定自身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减排义务。那么哪些标准才是真正合符正义的呢?今后国际气候制度该如何公正地确立减排义务呢?
一、确定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的标准
以什么标准来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权和分配减排义务,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有以下一些标准:
(一)人均排放量标准
即按人口比例分配排放权和减排义务。人均排放量标准又可细化为人均累积排放量和未来人均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1900年至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累积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12倍,1990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7.4倍,2005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排放量仍高达发展中国家的4.8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2009年的统计,2007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38吨,其中附件一缔约方国家(发达国家)平均为11.21吨,非附件一缔约方(发展中国家)只有2.56吨,仅为附件一缔约方的22.8%。”[1]由于印度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印度首相气候变化特使Shyam Saran在丹麦的赫尔辛格气候变化会议上主张人均排放量标准。澳大利亚实行积极移民政策,人口呈增长趋势,也曾提出以“人均排放权”为谈判制订减排目标的基础。2008年4月30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爵士领导的研究小组推出的《气候变化全球协定的关键要素》报告提出了人均排放
紧缩趋同的方法。该报告“根据205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限以及2050年全球总人口预测数据,进一步推算出人均2tCO2当量的减排目标,并采用紧缩趋同的原则,要求205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都降到2tCO2当量左右,实现人均排放的趋同。”[2]中国有学者提出“工业化累计人均排放量”方法和全球碳预算方案。“工业化累计人均排放量”方法认为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工业化全过程,它们早已透支了“工业化累计人均排放量”的指标限额,而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或即将步入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求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达到“工业化累计人均排放量”的指标限额。根据这一指标,G8国家的工业化累计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倍,是中国的11.3倍。[3]全球碳预算方案是首先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和全球长期碳减排目标来确定全球碳预算总量,然后对全球碳预算初始分配进行全球人均核定。[4]另有中国学者提出“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案。“一个标准”指碳排放权分配应以各国人均排放量相等作为标准。“两个趋同”指到目标年(如2010年),各国人均碳排放量趋于相等(如1.33吨碳/人),同时从基准年到目标年的过渡期内(如1991年-2100年),人均累积总排放量也趋于相同。[5]
(二)历史排放标准
即根据各国温室气体历史累计排放量按比例分配排放权和配置减排义务。排放量多的国家分配多的减排义务。如巴西方案提出根据各国历史上形成的累积排放量确定各国的义务分担。
(三)实际排放标准
是指按当前各国实际产生的温室气体来确定减排的义务。实际排放标准又可以分为产品生产标准和产品消费标准,前者是根据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或者根据产品来源地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来确定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后者是根据产品的最终消费主体或消费地来确定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和责任主体。
(四)GDP标准
GDP标准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与一国的经济产出进行联系起来确定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GDP标准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GDP总量模式,即按国家GDP总量大小分配减排义务,GDP总量大的国家分配多的减排义务;另一种是单位GDP强度模式,即计算出单位GDP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各国通过逐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而不是机械地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我国目前主张采取单位GDP强度模式。
二、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分配标准的正义审视
(一)人均排放量标准
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实际上是一种发展权,因而也是一种生存权。作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而也有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利。人均排放量标准肯定了地球上每一个人不论其所处国家和经济状况等的不同都享有平等的利用气候容量资源的权利。因而该标准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标准,容易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但是人均排放量标准不能准确考虑人口增长以及历史排放等复杂因素,并且有鼓励人口增长的缺陷。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在人均排放量标准中,人均累积排放量优于未来人均排放量。斯特恩报告所主张的紧缩趋同的方法属于未来人均排放量标准,并没有考虑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排放需求。如中国目前人均排放是5tCO2当量,按照2050年要降到2CO2当量的趋同标准,中国相对于目前要减排60%,即使在短期内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已几乎没有发展空间。[6]因而斯特恩报告所主张的紧缩趋同的方法客观上是不公平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工业化累计人均排放量”方法和全球碳预算方案以及“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案则不仅考虑了人生存和发展的碳排放需求,也考虑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和全球长期碳减排的目标,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方法。
(二)历史排放标准
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而非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带来的。从190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以不到全球总数20%的人口,产生了占世界排放总量80%的温室气体。1950年以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而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去,短则50年,最长约200年不会消失。”[7]历史排放累积量标准要求温室气体排放量多的国家分配多的减排义务,具有污染者负担原则
所包含的公平价值,体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要求,是当前分配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需要考量的标准。但是,其不足之处是承认既成的排放现实,导致排放量多而对大气现状危害大的国家同样也获得了多的排放权。而且,这种基于历史责任的减排义务分配标准,考量的是国家的排放总量,而没有考虑人均排放量;只强调污染者要为历史排放负责,而没有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当前及未来发展需求给予必要的考虑。
(三)实际排放标准
实际排放标准的提出,是“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产要素早已跨越国界,资本、产品、技术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的商品的生产。伴随国际产业的转移相应地产生了污染的跨国转移,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也形成了跨国“碳源”转移。根据生产者或产品来源地对碳负责的方法来确定减排义务,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国内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但最终消费却在国外。“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有1/3的碳排放量来自为外国消费者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有资料显示,“美国进口产品中所谓的碳内含排放量在1997—2004年间差不多翻了一番。2004年,美国进口产品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18亿吨,相当于该国2004年碳排放量的30%”。如果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美国本土生产,“那么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3%~6%。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7%~14%是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产品而产生的。”[8]
相比较而言,产品消费标准优于产品生产标准,前者较公平地反映了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主体,避免隐性碳排放被忽视。但是根据产品的最终消费来确定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是一种末端治理的方法,也与由相应主体从源头上承担责任的精神不符。
(四)GDP标准
GDP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状况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GDP总量模式确定各国的减排份额,实质上是一些发达国家试图用大国责任替代公约附件一国家的责任,用当前排放责任和未来潜在排放责任替代历史排放和高人均排放责任,明显对大国和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单位GDP强度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各国的减排能力,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国的减排动力,加大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开发应用上等方面的投入。单位GDP强度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一个相对宽缓的减排过渡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但是单位GDP强度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它不能充分反映各国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没有直接体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总量目标。
三、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分配标准上可采取的立场和对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被《京都议定书》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中,不用承担强制的减排义务。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却越来越大。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高调要求中国和印度为减排作出实质努力;2007年12月,“巴厘岛路线图”要求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都要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2008年12月,在波兰的工业城市波茨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会议(COP14)暨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COP/MOP4)上更是以高度认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减排计划行动的方式促使中国接受温室气体减排 “硬法”指标的约束。2011年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美欧提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应接受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加拿大更是以《京都议定书》没有包括美国和中国为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今后中国承担国际减排义务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也主动承诺自主减排。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时建立统一的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要分别下降 16%和 17%。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已耽误太多。切实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抓紧采取实质的行动,世界各国将要付出的国防和安全成本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冲突成本远远大于
减排成本。2008年6月27日,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但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会越高。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9]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的利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国际社会需尽快就温室气体排放国际义务分配的标准达成一致,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在今后的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采取如下立场和对策。
(一)遵循合作、公平的原则
气候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对气候资源的利用,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需要各国开展气候合作,共同采取应对措施。当前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争论,正表明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陷入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气候合作中要消除“囚徒困境”,需要各国都拿出真正的诚意,积极打破非合作的纳什均衡。公平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是采取国际合作行动的动力源泉。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哲学家尼采提出:“给平等者以平等,不平等者以不平等,才是正义的真正呼声;由此可以推出,永远不要平等对待不平等”。[10]温室气体排放国际义务的设置实际上是一种排放权分配,在坚持“给平等者以平等”分配正义原则的同时,还要遵循“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纠正正义原则,即不并是平均分配温室气体排放义务,而是应该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根据各国的现实能力。
(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公平原则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体现。1992年的《里约宣言》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括“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两个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共同责任”是指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需要各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采取积极的减缓措施。“区别责任”是需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历史形成、当前各国的能力和水平。因而根据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承担量化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承担相应义务。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家所主张的如果只是发达国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相应安排,那么会出现所谓“碳泄漏”,而导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无法实现的观点,实际是发达国家在推卸责任,不愿承担与自己历史责任以及现实能力相称的减排义务以及不愿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应对能力寻找说辞而已。
(三)综合现有的标准合理确定国际减排义务
以上分析表明温室气体减排国际义务的分配标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单一的标准都存在不足之处,应该综合现有的标准,既需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历史原因也需要考虑到现实因素,既要考虑国际共同的行动也要考虑各国的发展需要,公平合理地确定。如人均排放量标准方面,需综合历史人均排放量和未来人均排放量。在历史排放标准方面需要合理确定计算减排比例的基准年。如《京都议定书》规定计算发达国家减排比例的基准年统一为1990年,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长短各不相同,过去累积的排放总量也不同。况且发达国家到1990年大多已完成工业化,此后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趋于稳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水平则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巨大滑坡,其后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已大幅减少,很多国家甚至到2012年也未必能恢复至其1990年的水平,这些国家实际上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就能实现《京都议定书》为其设定的减排指标,还能超额完成任务。[1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此时才刚刚发展起步,排放量的基数很低,排放增长的速度却非常快。因而,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要求在确定减排的基准年上不能实行一刀切,应该根据历史排放情况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选取不同的年份。如发达国家可以选取1990年甚至更早的年份作为基准年,而发展中国家可选取2005年甚至更后的年份作为减排的基准年。在实际排放标准中,排放量的衡量需要考虑产品的生产全过程,直至消费的各个环节所产生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并按照公平原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产品来源地和消费地之间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分担。 ■
[1]《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358.
[2]陈迎,潘家华.对斯特恩新报告的要点评述和解读[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5).
[3]陈泮勤,曲建什.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之国别研究[M].气象出版社,2010:140.
[4]潘家华.满足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及其国际公平与可持续含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
[5]何建坤,刘滨,陈文颖.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平性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6).
[6]陈迎,潘家华.对斯特恩新报告的要点评述和解读[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5).
[7]程平.环境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评哥本哈根峰会中的博弈[J].理论与改革,2010,(4).
[8]李丽平,任勇,田春秀.国际贸易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责任分析[J].环境保护,2008,(3).
[9]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9、26、27.
[10]王小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哥本哈根协议》和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J].社会科学,2010,(7).
[11]郭冬梅.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实证分析——从国际公约到国内法的转化[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3).
【责任编辑 谢明俊】
Comment on Allocation Criteria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PENG Ben-li
(Law and Business College,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How to allocate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of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s the focus of debate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the crux of the issue is failure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 standards for allo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obligations of reduction emission.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ndards of allo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obligations of reduction emis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n makes objective assessment on these standards, finally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what posi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should China take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greenhouse gases; obligations of reduction emission; standard
D912.6
A
1004-4671(2014)01-0048-05
2013-09-01
玉林师范学院2013年重点研究项目《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广西为例》(2013YJZD06);玉林师范学院2013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G20130005)。
彭本利(1979~),男,汉族,玉林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