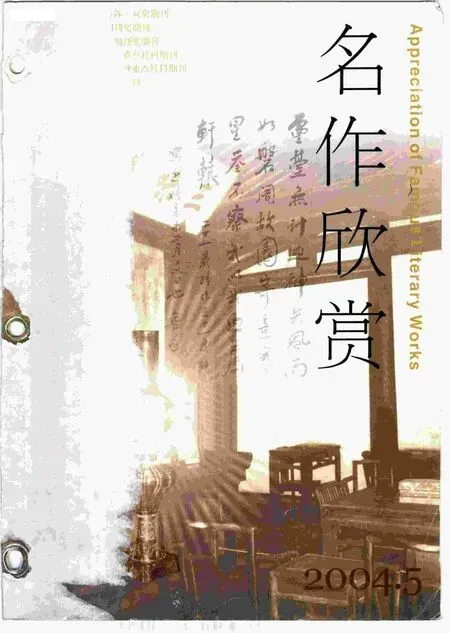评元杂剧《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形象
⊙王睿君[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 成县 742500]
作 者:王睿君,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秋胡戏妻”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历代文人对这一题材不断加工改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元杂剧作家石君宝独具慧眼,将这一故事中女主人公罗梅英自尽的悲剧改为大团圆的喜剧,他以遭遇变故的婚姻家庭生活为突破口,深刻揭示了在崇尚金钱与权势的社会中所导致的人性丧失和道德败坏的陋习。而剧中女主人公罗梅英身处污浊环境且能在诸多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情怀,不能不值得人们称道。
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元蒙民族入主中原,蒙古贵族当政,原本高居“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族地位一落千丈,虽然蒙古贵族没有用法律条文将流传很广的“九儒十丐”的说法固定下来,①但这一现象未必就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儒士地位低下,必然导致儒家伦理道德淡化,尤其在金钱和权势的诱惑下,哪怕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也难保不蜕化变质,高洁的道德观被钱与权涤荡而败坏。元杂剧作家石君宝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感悟到了社会上的这一现象,于是在杂剧《秋胡戏妻》中着力塑造了罗梅英这一典型形象,通过女主人公的言行,揭露并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使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作者理想中的人文情怀在家庭伦理道德喜剧中得以宣扬。
杂剧《秋胡戏妻》写罗梅英与丈夫秋胡新婚才三日,秋胡即被勾去“当军”,一去十年,音讯杳无,家中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梅英肩上,她既要“种桑养蚕,择茧缫丝,担水买浆,洗衣刮裳”②,又要侍奉多病的婆母,日子实在艰苦难熬,这还不算,还要抗争豪强恶势李大户的逼婚欺压,丈夫荣归却遭戏弄,夫妻几乎要劳燕分飞,在婆母以死相逼的劝说下才得以大团圆的结局而告终。就在这一连串的矛盾冲突中,梅英从一个破落的大户人家的纯真少女逐渐磨炼成了勤劳善良,泼辣勇敢,不为金钱利诱,不被权势所欺,敢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具有鲜明个性的叛逆形象,她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主要是在其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一、信守诺言,对爱情坚贞如一
元杂剧中许多作品肯定的往往是以真挚热烈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情”是爱情元素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更多地落实到感情交融和精神契合上,“情”的因素,可以说是确定有无爱情和爱情深浅的重要尺度,是人类爱情生活的显著标志。③梅英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表现出坚贞如一的品质,这与她和丈夫有着真正的爱情是分不开的。
剧本第一折,梅英嫁到夫家的第二天就有媒婆恶意挑嗦,“姐姐,你当初只该拣取一个财主,好吃好穿,一生受用;似秋老娘家这等穷苦艰难,你嫁他怎的?”“如今秋胡又无钱,又无功名,姐姐,你别嫁一个有钱的,也还不迟哩。”④可见在世俗眼中,秋胡并不是人们理想的对象,无钱,无权,在夫荣妻贵的封建社会里,秋胡只是在下层社会中讨生活的劳苦人民中的一员,自己不发达,家人也只能跟着受穷。可是,梅英对这桩婚姻并无不满,“自从他那问亲时,一见了我心先顺”⑤,料定自己的丈夫腹内有“珍”,日后定是“黄阁臣”,即使享一世清贫,也心甘情愿。所以,婚后第三天,当秋胡被勾去当兵时,梅英只是表现出心中的不舍与对日后生活更加贫困的预料,并丝毫没有自己会被抛弃的担忧,梅英在“想着俺昨宵结发谐秦晋,向鸳鸯被不曾温,今日个亲亲送出旧柴门”的伤感中,牢记秋胡临别的嘱托:“你在家好生侍奉母亲,只要你十分孝顺者”⑥,这一切心理表现充分表明了梅英对自己的爱情充满了信心。十年后,秋胡荣归故里时的宾白正照应了这一点,“想当日哭啼啼远去从军,今日个笑吟吟荣转家门。捧着这赤资资黄金奉母,安慰了我那娇滴滴年少夫人”⑦。可见,当初梅英择婿的眼光不差,秋胡“通文达武”,“累立奇功”,终于做了“黄阁臣”。再者,秋胡从军离家时对家的恋恋不舍,十年中的荣迁,时刻魂牵梦绕着妻母,从未想过抛弃糟糠之妻,梅英和秋胡的婚姻是以彼此的信任作为基础的,他们心中都深藏着对方。
十年的光阴不算短,世事无常,村中的李大户凭着自己有财有势,谎称秋胡已死,打算强娶罗梅英,梅英的父母在金钱诱惑下充当了帮凶,就连相濡以沫的婆母也在强大的恶势力下低了头,竟然劝说梅英改嫁。在与李大户的矛盾冲突中,在与自己亲人的矛盾冲突中,梅英誓不低头,坚决抗争,她讥讽父亲见钱眼开,“怎使这洞房花烛拖刀计?”竟帮坏人施展阴谋,并对强权恶势的李大户以铜钱相诱时,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其实我便觑不上”。“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⑧她对铜钱肮脏本质的揭露多么深刻有力。她还以假想丈夫此时荣华富贵的排场与腹内无珍的李大户作了强烈的对比,言词的犀利尚不算,还怒气冲冲地推倒李大户,一个大胆泼辣、不屈淫威的农妇形象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初婚时柔顺羞涩的少妇缘何有如此大的抗争力量,源其动力不正是对丈夫坚贞的爱情吗?正是与秋胡的一见倾心,与短暂的恩爱,让爱情作了婚姻基础,她视富贵如粪土。哪怕安守十年的贫困,在金钱利诱面前也不会动摇对爱情的忠贞。这就把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不使得那些爱钱如命、追求荣华富贵、贪图享乐的人无地自容。
二、争取女权的民主意识
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尽管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地位依然低下、微不足道,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规定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妇女永远是男人的附属物,是逆来顺受,惟男子之命是从的奴仆。⑨元朝社会,虽然由草原向中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妇女的命运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与劳苦人民接触频繁的元杂剧作家们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许多劳动妇女在家庭中支持门楣、执掌情感枢纽、承担生活重负的现实,尽管当时的社会不予认可,但在剧作家们的笔下仍然塑造出了一批这样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用充满生气的民间伦理大胆地向传统的封建道德观挑战。石君宝笔下的罗梅英正是这众多妇女中的一位佼佼者。
罗梅英嫁给秋胡时,就做好了受贫穷的心理准备。十年间,梅英独立支撑门楣,做着家中的顶梁柱。长期艰苦的劳作凝聚了她勤劳、善良、淳朴的个性和自立自强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梅英才在婚姻家庭中享有绝对的发言权。
剧本第三折中,秋胡荣归故里时途经桑园,“一见了美貌娉婷,不由的我便动情”,先是以诗相挑,言语轻薄,遭到梅英严厉斥责,接着动手动脚,举止轻浮,又遭到梅英机智的抗争,并斥之为“不晓事的乔男女”,两计不成便拿出俸养老母亲的黄金加以引诱,在对爱情坚贞如一的梅英面前又一次无奈地败下阵来,梅英责之“富家郎,惯使珍珠,倚仗着囊中有钞多声势,岂不闻财上分明大丈夫?”并骂之为“沐猴冠冕,牛马襟裙”。恼羞成怒的秋胡最后用武力威胁,“你若不肯呵,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拼的打死你”⑩,此时的梅英面对强恶势力无比勇敢,毫不畏惧,痛快淋漓地怒骂:“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送;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了剐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坟墓,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谁着你桑园里,戏弄人家良人妇!便跳出你那七代先灵,也做不了主。”⑪在不屈淫威,敢于反抗,视金钱如粪土的农家妇女面前,跋扈的秋胡此时完全败下阵来。
十年的阻隔,让夫妻相见却变得陌生,于是上演了一出“戏妻”的悲喜剧。笔者认为,秋胡是有意试妻而非戏妻,剧本中有充分的依据证明这一观点。第三折秋胡上场的宾白中有“兀的不是我家桑园!这桑树都长成了也。我近前去,这桑园门怎么开着”的句子,既然认得自家桑园,也该猜到采桑的娘子便是自己的结发妻子,结尾也写到“到桑园糟糠相遇,强求欢假作痴迷;守贞烈端然无改,真堪与青史标题”⑫,可见是秋胡有意试妻。而淳朴善良的梅英却哪里知道阔别十年荣归故里的丈夫却在试探自己、考验自己。
当梅英认清了戏弄自己的竟是为之守贞十年,朝思暮盼的丈夫时,爱情底线一下子崩溃了,怒责丈夫“谁着你戏弄人家妻儿,迤逗人家婆娘!”“我怎生养活你母亲十年光景也?”“你可不辱没杀受贫穷堂上糟糠。我捱尽凄凉,熬尽情肠,怎知道为一夜的情肠,却教我受了那半世儿凄凉。”⑬对“五花官诰”“驷马高车”“夫人县君”毫不稀罕,只叫着“秋胡,将休书来!将休书来!”封建礼教中,从来只有丈夫休弃妻子,此时的梅英公然要休夫,在婚姻生活中要争取民主权。只是在婆母以死相逼的劝说下,夫妻才和好得以团圆,但她却宣称要整顿“妻纲”,公然与被列为“三纲”之一的“夫纲”分庭抗礼。罗梅英大胆争取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得到尊重的权利,在挑战封建传统礼教中显露出朴素的民主意识,这在封建社会中实属罕见,正是这样,罗梅英的形象在文学史上格外耀眼。
三、勤俭善良,深明大义
作为剧作家精心塑造的鲜明女性形象,罗梅英不仅具有朴素善良、勤俭孝顺的优良品质,还表现出超凡脱俗的深明大义。
梅英明知嫁给秋胡就要遭遇贫苦,却毫不动摇自己对爱情的坚贞。尤其秋胡从军离家后,信守诺言孝顺婆母,十年间,勤勉持家,维持生计,忍饥挨冻,艰难度日,还要与恶势力强逼婚作抗争,也不改自己对婚姻的承诺,对婆母的侍奉孝敬。这一切直感动得婆母“只愿的我死后,依旧做她媳妇,也似这般侍养她,方才报的她也。”⑭这里充分凸现了梅英勤劳善良,十年如一日敬奉婆母的美德。
第四折中梅英坚决向秋胡索要休书,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此时李大户率领人众前来抢亲,却不料被比他权势更大的秋胡摆平了,这无疑给罗梅英夫妻讲和提供了条件,加上相依为命十年的婆母以死相逼要求梅英原谅秋胡,善良的梅英怎忍心让相濡以沫的婆母横尸当前。再者,梅英和秋胡的结合原本就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十年的相隔相思,秋胡并未抛弃糟糠。桑园戏妻,其实是秋胡故意做出的试探,尽管梅英信以为真,但在当时的社会、家庭、个人看来并不是绝对不能原谅的行为。此时善良的梅英深明大义,为了婆母,她宽大为怀原谅了秋胡,并表明“则是俺那婆娘家不气长”,“非是我假乖张,做出这乔模样;也则要整顿我妻纲”。⑮如果说《陌上桑》中秦罗敷以夸夫打击豪权的压迫,那么罗梅英不但大胆提出了要“整顿妻纲”,争取女权,还用犀利辛辣的言词反抗封建伦理道德,这种叛逆精神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值得世人称道的。
有人认为结尾部分大团圆的结局削弱了罗梅英的反抗意识,其实不然,作者匠心独具的安排,正体现了罗梅英的宽容善良与深明大义的高尚品质。
“秋胡戏妻”的故事在流传嬗变过程中,元杂剧作家石君宝倾力刻画罗梅英的形象,将作者关注的人文情怀和道德情操借这一平凡而高尚的女性形象得以张扬,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①③ 苟人民:《金元俗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9页,第98页。
② 张大新:《石君宝杂剧对爱情婚姻题材的拓展与深化》,《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30—32页。
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 顾学颉,《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01—226页。
⑨ 奚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