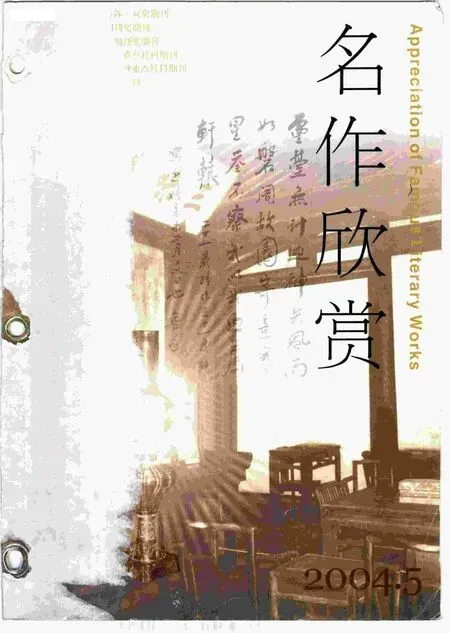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缅甸岁月》中的身体叙事
⊙邓云飞[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2]
作 者:邓云飞,硕士,西华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一、引言
高宣扬在研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系谱学后总结道:“福柯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出现和实际影响,都离不开身体这个最重要的场所。当权力试图控制和驾驭整个社会资源、人力和组织的时候,它首先所要征服的,就是身体。身体是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中介场域。是连接个人自我同整个社会的必要环节,也是把个人自身同知识论述、权力作用以及社会道德连接在一起的关键链条。”①
《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第一部小说。贯穿故事始终的主要线索之一,是木材商人弗洛里因遗传的身体特征——“胎记”在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被“妖魔化”和“他者化”,最终被除名的悲剧命运。
二、“胎记”名称的演变
小说中提到,弗洛里的“麻烦从娘胎里就开始了,老天让他脸上长了蓝色的胎记”②。事实上,胎记给弗洛里带来的困扰从他九岁时上学读书才开始的。那是他第一次进入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天生的身体特征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才继而对人的志趣、人格、价值观、人生观等产生影响的。学校的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教师的教育和规训,另一方面体现在伙伴之间的游戏、起外号甚至拉帮结派的活动中。弗洛里上学的第一天,几个男同学紧盯着他看,还给他取了“青脸儿”(Blue face)的外号。除此之外,学校里的小诗人作了一首诗侮辱他:
新来的弗洛里确实像怪物他那一张脸,活像个猴屁股
如果说“青脸儿”的外号首次从肤色的角度把弗洛里从白人群体里划分出来,这首诗更进一步把弗洛里“妖魔化”、“非人化”,为歧视、排挤乃至攻击他的行为变得理所当然。而且诗歌的形式更加朗朗上口,易于流传。这样,弗洛里的“胎记”就引起更多同伴的注意,也更容易受到群体的排挤。在这个团体里,设有一个“西班牙审判所”,每周星期六审判他们认为的“异端”,并实施一种叫“特别多哥”的酷刑:被一些孩子紧紧抓住被惩罚的孩子,另一些孩子则用拴在绳子上的七叶树果子打他。弗洛里因为脸上的胎记经常接受这一酷刑的惩罚,他的体会是:“其中疼痛只有先知才知道。”先是用言语进行“贬损”和“妖魔化”的精神摧残,然后是“酷刑”的肉体折磨。如此恶劣的环境无疑对幼小的弗洛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小说中提到弗洛里有踢足球的特长,赢得了小伙伴的尊敬,并很快摆脱了“猴屁股”的外号。
在缅甸殖民地,他的“胎记”再一次被提及,遭人议论,以至于造成他求婚失败而开枪自杀。每当弗洛里的言谈举止不符合“白人老爷”的标准的时候,人们就利用“胎记”作借口,把他“非英国化”和“非白人化”。英国沙文主义者埃利斯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为了攻击弗洛里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与东方人交往的生活方式,常常借题发挥,将原本“暗青色”的胎记看成是“黑色”,刻意把弗洛里打入另册。比如,他在欧洲人俱乐部散布针对弗洛里的谣言:“就我看来,他也有点太布尔什维克了。我可受不了谁成天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统,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脸上有一块黑斑的原因。花斑一块。而且瞧他那黑色的头发、柠檬色的皮肤,看起来就是个欧亚混血。”他甚至把弗洛里比作美国黑人教育领袖布克·华盛顿,蔑称其为“黑鬼的伙伴”,并“给他取了‘南希’的绰号——就是‘黑人养的小白脸’的简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把类似的话语叠加到“胎记”上来,甚至无论是出于善意的照顾还是恶意的谩骂,都源于“胎记”。就连与弗洛里年纪相仿的仆人柯斯拉对主人也怀有同情之心而非应有的敬畏,因为他觉得“胎记是个可怕的东西”。结果是,原本只是一个生理特征的“胎记”被殖民话语赋予了决定弗洛里命运的力量。
三、“胎记”的教化功能
弗洛里的悲剧在于,由于不断接受外部环境影响,他在自我评价中认同他人强加给他的评判,他人的眼光使他再次对自己的“胎记”敏感起来。小说在弗洛里一出场就提到他脸上的“胎记”:“人们看见弗洛里,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左脸上的那块“胎记”,大致呈月牙形,从眼睛一直拉到嘴角。从左侧看上去,他的脸一副受尽折磨、愁容不堪的样子,仿佛胎记是一块伤痕似的——这是由于它是暗青色的。由于面容上的缺陷,他自己十分清楚,因此无论何时,但凡有人在的时候,他总是不时侧转身子,就是他极力想让自己的胎记不被别人看到。”“胎记”在缅甸已经具有了教化功能,它使得弗洛里逐渐变得胆怯、懦弱、自卑:在与埃斯利为首的白人老爷们对抗时,他失去据理力争的勇气,因为脸上的“胎记清晰可感”;平日里口若悬河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不是违心地妥协就是消极地逃避;与土著情人马拉美发生性关系之后,他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也联想到脸上的“胎记”。在欧洲人圈子里,他离群索居,孤独苦闷,渴求“一个不在乎他的胎记的女孩儿”的拯救。当遇到巴黎来的白人女孩伊丽莎白,他立刻把她当成拯救自己的天使。尽管他发现伊丽莎白的浅薄和平庸,但“胎记”让他自惭形秽,他时常有意识地侧身,避免她看到有“胎记”的那边脸。他孤注一掷地设想“必须拥有她,只有娶她,他的生命才能得到救赎”。
不幸的是,伊丽莎白与其他欧洲人一样,有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观念。在她眼里缅甸男人黝黑的面庞、赤裸着上身,“像魔鬼一样丑陋”;缅甸女人是小怪物,长得“像一种荷兰娃娃”;欧亚混血儿在她心中激起的是厌恶之情,她把他们分类为南欧人,那种在许多电影里扮演无赖的墨西哥人和意大利人。她甚至相信一些种族主义者宣扬的“人种学说”——诸如:有色人种的额头是倾斜的,而额头倾斜的是罪恶型;欧亚混血儿长得堕落,因为他们遗传了父母双方的缺点。无疑,她难以理解弗洛里作为一个白人对土著文化的浓厚兴趣。因此,她无法接受“不愿做白人老爷的”弗洛里的爱情,与其说是因他地位低、收入少,不如说是因为他脸上的“胎记”带给他“非白人”的身份:“他的胎记使得俩人在观点上的差异更加明显。她瞅他的眼神甚至有些敌意,让人奇怪得冷酷。”
伊丽莎白与弗洛里分开后,她很快对有贵族头衔的宪兵军官维拉尔投怀送抱,而唯一记得起弗洛里的是“他脸上的胎记”。被维拉尔抛弃之后,她又回心转意,对弗洛里再次示好,也点燃了弗洛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使他在教堂第一次自信地将自己有“胎记”的那一半脸正对着伊丽莎白,心里憧憬着与伊丽莎白结合后的美好生活。当土著女孩马拉美受人支使,在教堂公开与弗洛里之间的关系时,她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居然跟这么一个灰头土脸、疯疯癫癫的东西是情人。”其实,伊丽莎白早已知道弗洛里与土著女人马拉美的关系,欧洲白人买当地女人做情妇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因为弗洛里在处理缅甸人暴乱中表现的勇敢,让她再次对他产生好感并原谅了他。让她最难以接受弗洛里的一是他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弗洛里脸上的“胎记”。当她隔着过道蔑视地看了弗洛里一眼,只见弗洛里“表情僵硬,面无血色,以至那块胎记就像一条蓝漆似的,在脸上异常扎眼”。“胎记”使弗洛里在伊丽莎白眼里蜕变成了一个“非白人”,和他结婚将会使她做白人太太的美梦化为泡影,因此,她“深感厌恶,简直就觉得恶心。比一切都更为糟糕的,便是他此刻的丑陋面容。他的脸如此惨白、僵硬、苍老,让她非常害怕。整个就是个骷髅,只有那块胎记尚有生命。她现在开始因为他的胎记而痛恨他了。直到此刻,她才知道,这是个多么丢人现眼、多么不可原谅的东西”。她终于下决心与身败名裂的弗洛里分手,最终导致弗洛里饮弹自尽。
弗洛里死后,“胎记”“也随即慢慢褪色,成了一块淡淡的灰斑”。如同寄生的毒瘤,它似乎也完成了它的使命,伴随它的宿主的死亡而消亡。
四、结语
弗洛里因脸上天生的“胎记”,最初在学校被同伴取“青脸儿”的绰号,这是社会从肤色的角度,第一次给弗洛里的脸归类和加注,把他划分为“有色人种”,这一事实“融入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种族意识”③。后来到了缅甸,他再次被同胞的殖民话语界定为“有色人种”。一个人天生的身体缺陷,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被“贬损”“降级”“他者化”“妖魔化”直至除名。弗洛里用身体甚至生命为代价,挑战“白人至上”的殖民话语权。他个人的悲剧是对英印殖民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强烈质疑以及对“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观的有力批判。
①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2页。
② [英]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译序》,李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文中引用原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 许淑芳:《弗洛里的“胎记”与殖民话语批判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第11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