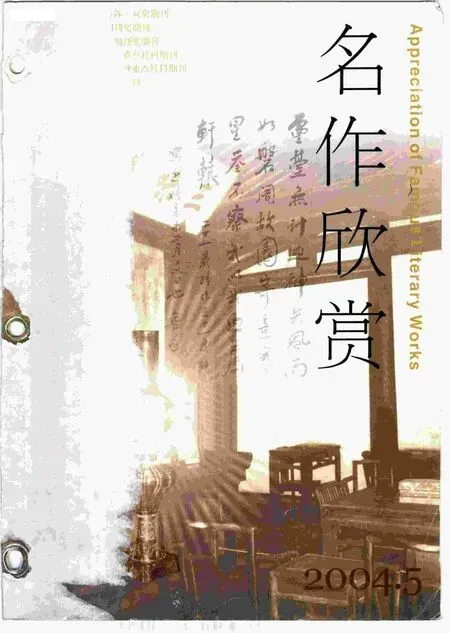荒诞外衣下的民间罪感文化——解读莫言《蛙》中万心的忏悔意识
⊙赵婉竹[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作 者:赵婉竹,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2级研究生。
一、忏悔——罪感意识的回归
万心罪感意识的复苏是在她退休的那天,是阴历的七月十五。她走在一片洼地里,“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只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而且,路边还不时有青蛙跳出,有的在姑姑面前排成阵势,试图拦截姑姑的去路,有的则从路边的草丛中猛然跳起来,对姑姑发起突然袭击。”姑姑被吓坏了,她的裙子都被偷袭的青蛙一条一条地撕去了,这个场面让姑姑发自内心的恐惧,坚信这是民间的“因果报应”,所以她晚年一直生活在对“蛙”的恐惧中。
其实这就是民间“罪感文化”的作用,讲究的是一种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在《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等多部小说中都有体现。作者通过果报模式,寄寓的是文化讽刺和人性讽刺。而讽刺的背后是对当时社会体制的荒谬的揭露。“因果报应”作为一种信仰,意在告诉人们:人的一切都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主宰着,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注视着。只要人心存恶念,只要人行不善,就会遭到报应,即,作恶者终会得到应有的惩处,邪不胜正,正义永远是胜利的一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姑姑晚年一直被“蛙”所困,被一个绿孩子和一群破碎的青蛙追着“讨债”,作者采取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用这些不合常理的荒诞事物,制造出奇异荒诞的幻觉,并将这些神奇怪异的现象与日常所见事物相结合,虚实交错,进而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
姑姑这种晚年的迟到的忏悔者形象与她年轻时雷厉风行、无所畏惧的钢铁般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姑姑年轻时可以称得上是“政治斗士”、“时代先锋”、“送子观音”、“夺命阎王”、“无谓地狱的叛神者”,从这些称号中不难看出姑姑年轻时叱咤风云、坚定执着的形象。在她执行“计划生育”这项任务时那种病态的强悍与偏执,让她无所畏惧,忠诚而又冷酷地履行那个时代赋予她的职责,她是那个时代的守护者。可是,当她退休了,卸去了时代、社会赋予她的职责的时候,她开始用民间的、大众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开始了忏悔。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也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姑姑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她的这种忏悔、这种转变是深受民间“罪感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罪感文化”不同于西方,它是民间的对中国传统政治观的一种补充。“是对这种人类罪性和有限性的洞察和理解。正是这种自我洞察和理解,标志着人类作为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①而这种文化源于自然崇拜时期的“万物有灵观”。原始人为了生存要猎杀动物,可是面对动物的灵魂有一种恐惧感,为了缓解心理的恐惧和压力,为了免除动物灵魂的复仇,原始人在猎杀动物时都要举行仪式向动物忏悔,这种“罪感”心态在原始人中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弗雷泽《金枝》中的记载:“科里亚特人将死熊带回家来的时候,妇女出来迎接,打着火把跳舞。熊皮连着熊头一起剥下来;有一个妇女披上熊皮跳舞,求熊不要生气,要对人们仁慈。同时,他们用一个木盘子向死熊献肉,说道‘吃吧,朋友。’而后举行仪式,送去死熊,或者说的准确一点,送走死熊的灵魂,让它回家去。”②这种原始的仪式的目的是要保护人们,防止死熊和它同族的愤怒,防止它们灵魂的复仇。而万心所受的精神上的折磨正是来源于死在她手上的孩子的“灵魂的复仇”,其实这些都是姑姑心造的幻影,是民间的“罪感文化”在起作用。正因为姑姑年轻时夺去了一些无辜孩子的生命,那时候有着“社会责任感”的庇佑,姑姑在精神上能够找到出口,并一直固执地坚守这个社会角色。可是一旦将这个“社会责任感”卸下之后,还原一个医生、一个人本来的身份和角色之后,对从前的所作所为的审视角度也随之改变,姑姑那深埋在骨子里的“罪感意识”就复苏了,这种意识不像是法律强制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精神的刑罚,对人的精神进行惩治。
二、警示——灵魂救赎的未完待续
这种因果报应信仰的心理震慑力主要是利用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在精神上给予约束,作为法律在心理上的补充,使人自我约束,抑恶扬善。万心深受民间“罪感意识”的影响,在心灵上忏悔,想要寻求精神上的救赎。所以她嫁给了捏泥娃娃的郝大手,通过口述记忆中的孩子的模样,让郝大手捏出不同的泥娃娃,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轻自己心中的罪恶。
因果报应对人们的心理有很强的威慑力。正如姑姑说:“是报应的时辰到了,那些讨债鬼们,到了跟我算总账的时候了。每当夜深人静时,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号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这些破碎的青蛙折磨、吞噬着姑姑,让她深深地陷入对过去的质疑和反思中,成了一个失眠的,需要各种方式来为心灵减压,寻找解脱的赎罪者。“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就像鲁迅笔下那个捐门槛的祥林嫂一样,要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出口。姑姑是一个清醒的人,越是清醒,面对自己的过错,就越是煎熬。所以,姑姑不想点破她虚妄的忏悔,用这种于事无补的方式给自己一点希望,让自己得到解脱,夜里不做噩梦,让自己能够像个无罪的人一样活下去。作者用魔幻的手法,借助幻想与隐喻,写实与夸张,把现实放到一种魔幻的氛围和环境中进行客观的、夸张的、虚实交错的描写。这是一种赎罪,是一种忏悔,是对罪性的自觉和人的生存悲剧性的自觉。“忏悔的最关键的内涵,就是对人类的可悲可怜的生存之自觉,对宇宙最高生命对我们的仁爱和救赎保持信心。”③
“忏悔意识”是源于人们对“因果报应”的恐惧,它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是一种信仰。人们对它有着敬畏之心,认为自己遭受的不幸或者是福报,都是源于过去自己的所为,从而使这种意识有了存在的价值,成了社会法律的辅助,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不足,也免除了法律强制性的特点,成为一种思想上的自觉,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指引、威慑、教育的作用,对社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作用,是除了法律之外人们要遵循的另一种秩序。莫言写万心的“忏悔意识”,是对生命本身的爱与敬畏,是对人的灵魂深处的自我的一种审视与反思,是人类罪感意识的回归,同时也是在警醒世人要有作为“人”的“忏悔意识”,正如莫言在《蛙》中所说:“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净重与悲悯。”
将民间的这种“罪感意识”、“忏悔意识”运用到作品中最典型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笔下的神、鬼、狐还有人总是能得到应有的报应,今生未报,来世仍然逃不出这因果循环,让善恶在时序上达到了一种公平、平衡,这也是蒲松龄笔下的“鬼狐世界”会吸引历代读者的原因。蒲松龄“对受报者进行戏谑性的惩罚,把丑恶的东西表现得更为丑恶,来深刻批判人性的弱点,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④。
蒲松龄和莫言通过“因果报应”模式,弥补人间惩治机构无法触及到的一面,对人的灵魂进行拷问,对人的精神进行威慑。人们读此类作品能够唤起道德自律,接受“罪感文化”,就会在头脑中自动形成“因果报应”体系,此体系“基于人类共同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有序性的心理期待”⑤,主张赏善罚恶,没有执法者,全由个人对因果律的信仰,避恶趋善,规范行动。
可是当用来忏悔的泥娃娃成为商品,“罪感意识”被贴上了价签,神圣的东西就变得荒诞可笑,意识上是真诚的赎罪,在行动上却成了虚妄的忏悔。这是莫言对人、对人性、对现实、对社会的讽刺、批判,这也是莫言为什么说“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的原因。作者借助万心这一形象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重新审视人的卑微的、脆弱的灵魂。
①③ 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中国文化》2007年第25、26期,第52页,第59页。
② 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④ 郑春元:《“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作品散论(续)》,《“聊斋志异”研究》2006年第2期,第19页。
⑤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09页。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