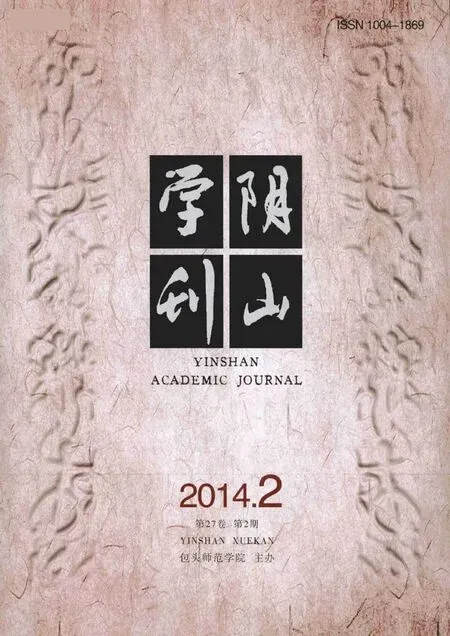刘永济《天问通笺》平议
常 威,周 建 忠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一、绍继前人,批判继承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曾评述刘氏《〈离骚〉〈九歌〉〈天问〉〈九章〉〈九辩〉通笺》云:“诸论大体以旧说为根基。若无新解,而思力至勤。要非空言无凭者所可同日而语。”[2](P258)诚然,观刘氏注骚,大体参依前人注解,因之求诸文义,发微探隐。至若前人注说于意未安者,则指摘得失,明其否当,而别立新说以释之。至于屈骚需要批判继承的原因,其在《笺屈馀义》中亦有明确的表达,曰:“屈子生于二千二百余年之前,尔时楚国文字尚有与秦汉文不同者,其作品当由秦汉人搜集流传,至汉代方写以篆隶,嗣后复由篆隶而行楷而草书,传至赵宋,始有雕本。……在此漫长之时代过程中,其文句之讹夺,音义之变化,篇章之移易,解说之纷歧,殊难指数。即其文中所用鸟兽草木之实,与夫山川县邑之名,亦已几经改更,难于稽考。……楚国史籍,如古所谓梼杌者,已无片字留存。……欲求明了楚国之社会经济情况,与其上层建筑之政治文化,亦无充分之资料,尤于屈子生平事迹,记载殊为缺略。”[3](P215)而正是由于文字舛谬与载籍缺失,遂滋生种种疵病,“一者,后世注家多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不知屈子所见之书,有出孔子删定之外者,于是对于屈赋中涉及史事者,往往不得其解,而曲为之说。……二者,不得客观资料,而欲自圆其说,则以主观想象补充之,甚且向壁虚造,逞意妄说。……五者,不知阙疑之义。……六者,不知存异之义。”[4](P216)因此,基于前人解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与不足,刘氏亦并非是“拘守先儒旧说,不敢作古人诤友”,从而人云亦云地对其全盘吸收,而显然是依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研究态度对其加以评骘和选择的。
具而言之,刘氏对前人《天问》注解的渊承与批判一方面表现为其对诸家释意高屋建瓴地审视与鸟瞰。如,释读“何启惟忧,能拘是达”曰:“王夫之曰:‘《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盖列国之史异说如此,启能忧勤以济难也。拘,囚禁也。达,逸出兴师也。’按诸家说此,皆以启伐有扈为言,惟姜斋据《竹书纪年》立说,言启益事,不用儒书。考此事见《晋书·束皙传》引《竹书》,今本无之。又与儒书所传异,故诸家不从。不知《天问》所述,自是古书传说出儒书之外者。王疑列国之异说如此,是也。”(案:刘氏于诸家之中,似乎对王夫之《通释》之说颇为倾心,故而其在参引诸家学说中,于王说亦每多称引和颂扬。)
又如,其论“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滨”更能体现刘氏在广阔学术视野下对前人旧说的熔铸与批评继承,其曰:“丁笺引《路史》,谓此文‘妻彼雒滨’,盖有洛氏之女。崧案又引陈本礼云,《竹书》‘帝芬十六年,雒伯用与河伯冯夷斗。河雒,二国名,伯其爵,嫔其妃耳。羿恃善射,杀河伯夺其国,又杀雒伯而淫其祀。’王氏《通释》则以雒滨为河伯之妻有雒氏,似本《路史》。按陈据《竹书》,但可证河雒为二国。杀河伯雒伯之妃事代为想像之词。刘盼遂又谓河伯斥伯封,洛嫔即伯封之母,后蘷之妻,名玄妻,又作眩妻,而浞所贪之纯狐也氏也。亦无塙据。要之,此问因上文而发。上言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何以自恃善射,肆其淫威?故下文又曰:‘后帝不若’,而卒召吞撥之祸。此数问相承,但直书其事,以见吉凶无门,惟人自召之意,亦《天问》文例之一也。”
而另一方面,刘氏对前人注解的承祧与批判则表现为其对某一家论说的深度剖析与体认。
如,刘盼遂校《天问》“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脋曼肤,鹿何膺之”曰:“协与平字当互倒,平又矛字误也。古文平与矛形甚似近。协脋者上文撰体脋鹿何膺之,盖谓肌理之美者。此二语上述王该以歌舞诱有易之女,下述有易女之容也。”[4]而刘永济虽然认为“刘氏《校笺》云‘此述王亥以歌舞诱有易之女事’是已”,但是却认为刘氏校“协与下文平字当互倒,平又矛字之误”则有未安,其论曰:“干协二字,义究难详,必有伪误。时,是也。是舞,上当言所舞者,特不必干矛耳。如刘说必与下句平字互易,又必证平为矛之误字,则曲折太多矣。”
又如,王夫之释“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曰:“言禹受舜禅与益受禹禅同,益以亡身,而禹无害,作革,言为启所革。播降,书所谓敷于四海也。”[5](P53)而刘永济虽谓“王说近是”,但又云其犹有未尽。其曰:“王说近是,而未尽瑩。此即承上为问,言益佐禹治水,皆躬就之事,劳身焦思,而无害厥躬,此禹益之所同也。今益则始即位而革,禹则子姓蕃衍隆昌,其相异如此,故以为问。”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刘氏对前代注解的承祧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自我的一己之见而流于人云亦云的尴尬境地,而其对前人持论的批评亦并非信口雌黄地任意指责。应该说,刘氏在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的结合中,不仅没有窘困于前人《天问》解读的窠臼,反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天问》研究注入了汩汩流淌的“活水”。对此,吴志达有详细的论述,其曰:“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学术思想,是刘、程两代大师学术研究的共同特色。这种治学观念,刘先生主要体现在《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论略》、《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唐宋词研究等具体的学术成果中,其特色就是既长于考据,又长于持论,但不作声张。……这种自觉的治学方法,使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创新精神。他的论著中既具有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缜密的考据之功,又有着鲜活的理论深度,善于从不同的侧面、新的角度找准新的切入点。他从不作缺乏过硬文献资料的空疏之论,也不作缺乏理论深度的烦琐考证,没有套话、空话,力求陈言之务去。”[6]
二、阙疑存异,务求适度
诚然,刘氏“从不作缺乏过硬文献资料的空疏之论”,故而其在《天问》研究中面对缺乏史料参佐的旷古疑难时,往往阙疑而不作空疏之论。如,释“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曰:“按诸家说此多用旧注,以为屈子呵壁时事,非也。王氏《通释》连下‘伏匿穴处’一问说之,谓似言舜纳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其德可以事上帝,不能得瞽瞍之心,至浚井而穴空以匿,此又何说?精诚可以格天,不能感玩嚣,孝子忠臣所以穷也。……郭焯莹《屈赋章句古微》即依此为说。大抵以雷电二字牵合为之,恐亦未的。疑古事之失考者耳。”又,释“伏匿穴处,爰何云”曰:“按诸家亦用叔师屈子自谓之说。惟蒋骥谓指楚先王熊绎及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事。言楚之先,虽僻陋,而世有贤君,其可称者何事?王闿运说同。传合难信。疑亦壁画故事之失考者。”
此外,刘氏对于诸家《天问》注解中含有精义者,亦以科学严谨之态度将之一并留存而不妄下断言。如,校读“苍鸟群飞,孰使萃之”曰:“旧注以苍鸟即《诗》‘时为鹰扬’之鹰。孙诒让又谓即苍雉。引《史记·齐世家》‘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索隐》曰:‘本作苍雉。’为证。谓萃之,即总尔众庶。叔师以比诸将帅也。按此说亦不免以文字牵合之失。此当说武王伐纣时祥异之事,如白鱼入舟之类,今不可考矣。蒋骥谓‘苍鸟群飞’即《汲冢周书》‘武王曰:自发生六十年,飞鸿满野,天不享殷。’扬子云《方言》曰:‘南楚谓鸿雁为苍鹅。’苍鹅即苍鸟也。‘孰使萃之’,指天事言,上文‘何践吾期’指人心言。与孙说并存之,亦俟考证。”
又,释校“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曰:“按此二句未详。丁笺申旧注,言中央之蛇,或干帝怒而杀之,而蠭蛾之微,亦肆其螫毒,羣聚于帝台,何大小之反常也?毛氏《补注》曰:‘中央共国国君,亦宠大矣,何以上帝有时覆怒之也乎?蠭蛾细物,其命甚微,何以其力反固能自全乎?言大者有时以失,餌细者有时以得,存亡祸福,旋转无已,不可知也。’戴氏《音义》曰:‘言居地之中,共牧斯民,列后何以相怒而争乎?蠭蛾之属,赋命甚微,乃亦有君长,各相竞斗,其力何坚乎?’三说不同如此。然叔师旧说当有所本。王薑斎谓当时稗官所记,是也。”
以上二例,皆可谓刘氏存异之论,而其在《笺屈馀义》中亦明确表达了存异的理念,其曰:“‘苍鸟群飞,孰使萃之?’有三说。……‘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有三说,皆宜并存,以待考实者。”[2]由上可知,刘氏对于《天问》解读中聚讼纷纭的历史疑难问题,或阙疑以俟之将来,或存异以启后人之思。可以说,刘氏《天问》研究中呈示的这一研究特色正是其解读务求适度客观,而非从主观出发,追逐怪迂新奇的过度之论的最好注脚。
三、审字定词,因时(地)制宜
刘氏《屈赋释词·凡例》:“古典文学因历世悠久,传本不同,或作者本人在其他文中复用原句,或经后人引用的缘故,往往致令此处此句此字与他处此句此字有所不同。此种不同的字,在校勘家不论虚实,概称之为‘异文’,而语法家则或称虚词异文为‘互文’,因其可以互用也。但实有虽可互用而用来究竟于语气与句义有未能恰合或使初学不易领会者。”其又云:“屈赋所用的词汇,其涵义亦有与今特殊者,或係古义,或本与今不异而为后人误说者,本书于此类词则详辨之。亦有即在屈赋各篇而取义不尽同者……又古人书字有假借之例,注家每以假借字义说本字,或以本字义说假借字而不说明此字是假借……其复用词中的联绵词,历来注家于二字同义之联绵词往往说成二义……至于二字不是一义者,间亦取其易误者释之。”[7](P240~241)诚如其论,古典文学字词中确实存在不能一概而论的诸多问题,因此,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显然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对其加以辩证审视与看待,而这一研究方法在刘氏的《天问》校释中亦不乏例证。
如,校释“并驱击翼,何以将之”,“将”字曰:“将亦行也。何以云云,盖有不宜行而行之意。”而其释《九歌》“穆将愉兮上皇”句“将”字时却云:“诸家皆以将为动词,训奉持也,皆失其义。此与下文‘盍将把兮瓊芳’,《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宫’句法一例。将,且也。”[8]是将字之意,于屈赋之中,有字虽同,而义实相殊者,诚不可一概而论。对此,其在《屈赋释词》中有详尽的总结,其曰:“《天问》‘并驱击翼,何以将之?’又‘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王逸于前文说为‘奋击其翼,独何以将帅(率)之?’于后文说为‘后稷……桀然有殊异将相之才’。盖因前有‘驱击’字,后有‘弓矢’字,故说为将帅,非也。今按屈赋用将字各句最多,大都是尚未如此而会要如此,原意如此,或方待如此之义,故王注或以为‘将然’,或以为‘方将’,或因是常语而不注,惟《天问》二将字皆说成名词,不知前文‘将之’与上文‘行之’之行,字异义同。‘将,行也,’见《诗·燕燕》‘远于将之’毛传。后文‘将之’则用也、以也,言后稷以何殊能而冯弓挟矢作司马也。由《九歌》‘穆将愉兮上皇’,‘盍将把兮瓊芳’,‘蹇将憺兮寿宫’,三将字皆且也,亦常语也。王注殊欠分明。”[7](P354)
又如,《楚辞》中出现逢字者还有《离骚》“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天问》“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下逢伊挚”、“云何而逢”、“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逢彼白雉”,《九章·惜诵》“纷逢尤以离谤兮”,《天问》“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等句,以上数句除“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之外,大多学者训“逢”为“遇”,而刘氏以为《天问》“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逢字之意显然与诸例不合,不当以常义释之,故而释曰:“冯训大,逢训遇,皆误。”其在《屈赋释词》中亦曰:“《天问》‘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王逸注‘何逢后世继嗣之长也’。洪氏《补注》‘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按王、洪二氏说此字皆不能通顺,此逢字当说为丰大义,非逢遇义。《书·洪范》‘子孙其逢’,《音义》‘逢,马云:“逢,大也”。上文有‘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义与此同。王注但云‘后嗣子孙长为诸侯’,不出逢字,或亦以为逢遇也,此亦古义之不明者。至‘逢尤’、‘逢殃’等词,则皆逢遇之义。”[11]
四、知人论世,了解同情
陈寅恪《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11](P1361)而在刘氏的《天问》研究中,其亦本着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释读字句或阐发文义时,时刻保持着“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期冀通过揣究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创作意图和对诗人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审知,达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理想状态,进而在此基础上洞明意旨。
如,释读“鸱龟曳衒,鲧何听焉”曰:“窃尝从鮌何圣焉一句问意,推究朱子之言,恍然知屈子此问之意与《离骚》女嬃之称鮌比原,及《九章》之屈子以鮌自拟之故,皆能贯通。……盖治水之事,古记传说,最多神异之事,惟此不见他书,故滋疑义,又后世儒书,多以治水之功归之大禹。古时别记,必不尽然。且以事理推之,亦非禹一人之力所能为。此屈子所以有纂前绪,成考功之言。……翫屈赋凡涉鮌事,皆有叹息之意。……屈子盖以为冤抑,而鮌之被放,坐婞直方命,亦正与屈子同故,故不觉其言之反复深切也。”案: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见于《天问》者曰:“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又云“鸱龟曳街,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鲧何所营?禹何所成?”由上而观,屈原对“鲧禹治水”中鲧所起作用以及对其评价似乎与世人颇异。要之,众人皆言“鲧疾修盈”,但是屈原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从《天问》中可知,诗人不仅对鲧治水无功不仅不加以贬斥,而且对其充满着不尽的同情,并且对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尤有不满。究其因,诗人或是因为治水虽然至禹始得功成,然鲧所作之贡献似乎并不能一笔抹杀,况禹为鲧子,则鲧治水方法之得失利害必为禹所耳濡目染矣,故禹方能以“变化”,“遂成考功”。《山海经·海内经》曰:“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10](P469)又,《国语·吴语》曰:“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11](P86)兹皆鲧、禹并称,是刘氏之论庶几与屈子意合。
又如,论“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曰:“考《楚世家》顷襄二年,怀王卒于秦。秦楚绝。六年,与秦平。七年,迎妇于秦,屡为好会。自顷襄立十八年,国未尝出一兵。故屈子悲之。王以文情论,张复证以史实,皆能得屈子之深意者。”这里刘氏谓是句关涉屈子与楚事可谓至为精确,李嘉言曰:“不管怎样,要可看出屈原作这篇文章,不是无所为而发,仍然是有其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屈原对于这些神话历史,大体对自己都有他自己的看法,都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是曲直莫辩,是非不分的。所以我们说《天问》有其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12](P84)这里李氏所言《天问》“是有其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可谓与刘氏所论一脉相承。
五、圆融通博,每多创获
程千帆先生曾经称颂刘永济曰:“(其)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沿革地理、名物制度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研治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13](P69)诚如其论,刘氏不仅精通小学,而且熟知诸子、群经,于版本、校勘之学亦有深刻钻研,而刘氏外露突显的这一研究特质在其《天问》研究中亦每多呈示。
如,校释“而交吞揆之”曰:“孙诒让曰:‘揆亦灭也。……此云交吞揆之,即谓与国人交接而破灭羿之家也。’按孙说是也。惟揆无破灭义,揆乃撥字之误。撥,败也。……《怀沙》曰:‘巧倕不斫兮,孰察其撥正。’《史记》作揆正,此揆撥易伪之证。癹又孳乳为拔。战国时伐绝人国曰举国。《齐策》‘三十日而举国。’《注》:‘举,拔也。’《史记·苏秦传》:‘五日而举国。’《注》:‘举犹拔也。’皆其证。交或反之误字。反吞撥者,上言羿善射,何以浞反吞撥之,问意显然。王念孙《墨子杂志》曰:‘隶书交字或作,与反相似而伪。’”案《天问》“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之意,诸家多以为《左传》所载浞杀羿之事,历来并无争议,然而对交字之解释,却胜义纷纭,莫衷一是,或以为浞交接国中而杀羿,或以为浞与眩妻(家众)交谋而杀羿,而刘氏擎举着乾嘉朴学的大纛,释“交”为“反”,或别有精义。是羿虽然善射,其力足以贯革,但是最终却为浞等所迷惑而残害,故释交为反,语义甚明,自可迥然备为一说。
又如,解读“而顾菟在腹”曰:“按朱子疑顾菟是已,而曰不晓其义。毛氏申旧注以为月中兔名,引简文袁庆诗为证,而下文又曰‘古人引事,各自为说,如“鷽斯”斯字本助辞,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螽”,“螽斯”又作螽名,以毛后说推之,顾亦语词,而顾连文,王引之《经传释词》曰:‘固,犹乃也,或作故,又作顾。’据此,则而顾,犹而乃也。……故乃即顾乃。而乃、顾乃、二顾,皆有与上文语气违反之意。……古人行文,习用双字,遇单明则加一虚字以足之,若‘有虞’、‘有夏’、‘终风’、‘斯文’、‘逎文逎武’、‘有邦’、‘有家’等词,皆是也。”这里刘氏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而顾犹而乃”并谓“古人行文,习用双字,遇单明则加一虚字以足之”可谓颇有见地,故其此论亦可给后人以启迪。
可以说,以上不管是训“交”为“反”,抑或是训“顾”为“乃”,二者皆殊途同归地展示了刘氏圆融通博的渊深学识和扎实深厚的小学功底。当然,亦正因为刘氏对自身学识的汲汲以求、深沟高垒以及对乾嘉治学精神与范式的深刻体认与精心研求,故其《天问》研究每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
综上可知,刘氏在批判继承前人《天问》研究的基础上,以圆融通博的学术积淀和阙疑存异的适度解读,以及知人论世、“了解同情”的研究态度与方法,为《天问》研究的持续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而言之,不管是对文字的训诂,还是对地理名物的周密研求,刘氏的《天问》研究成绩皆可圈可点,在《天问》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因此,对刘氏的《天问》研究加以钩深致远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1]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刘永济.笺屈馀义·屈赋通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刘盼遂.天问校笺[J].国学论丛,1929,(1).
[5]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吴志达.两代大师的风范——刘永济、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J].武汉大学学报,2003,(6).
[7]刘永济.屈赋释词[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刘永济.九歌通笺[J].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4,(1).
[9]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全集[M].台北:里仁书局,1979.
[10]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王云五总编.国语(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12]李嘉言.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分册)[M].开封:开封师范学院语文系编,1957.
[1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15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