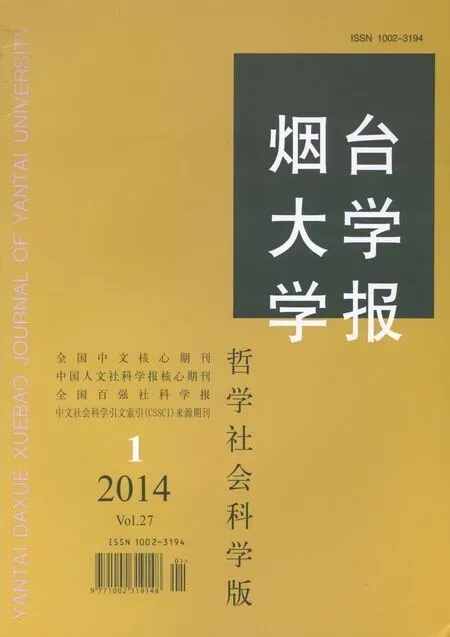孟子心学与宋明理学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宋明理学又称新儒学,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的新形态。如果说宋前儒家重五经的话,那么,宋明理学则重四书。这使《孟子》的地位骤然升高。宋明理学家对孟子推崇备至,其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孟学印记。本文拟以心这一范畴为切入点,探讨孟子心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思想继承性和一致性,再现儒学发展的心路历程。
一、孟子对心的重视和阐发
孟子认为,心与生俱来,对于人至关重要。为此,他宣称:“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①《孟子·公孙丑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67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有两种:一是“四端”,一是四肢;人生来就有“四端”,犹如生来就有四肢一样。对于人而言,“四端”与生俱来,是人人如此的。“四端”即“四心”,对于“四端”、“四心”究竟是什么,孟子做了如是回答: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孟子·公孙丑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267页。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③《孟子·告子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01页。
孟子的回答突出了两个要点:第一,“四端”也就是“四心”,“四心”具体包括恻隐之心(又称“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又称“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第二,心具有道德属性,内蕴善的萌芽,故而称“端”,这四种善的萌芽扩展为仁、义、礼、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38页。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四心”与生俱来,每个人都具有——没有“四心”,或者说,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心,人就不成其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一再宣称: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01页。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266-267页。
按照孟子的说法,“四心”与生俱来证明了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不仅生而具有,而且人人相同。这就是说,“四端”与四体一样与生俱来,从本原处看是上天赋予的。不仅如此,“四端”、“四心”与生俱来,因而是天然的,也是内在的。于是,他断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这里,孟子一面强调“四心”的先天性,让天为心存在的合理性做辩护;一面将心的具体内容界定为仁、义、礼、智,在使仁义道德成为人性基本内容的同时,强化了宇宙本体——上天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为了树立心的权威,阐明心的正当性、合理性,孟子始终强调心与上天之间的关联性,把心所标志的仁、义、礼、智之善端说成是上天赋予人的先天本性,把仁义忠信等道德说成是上天赋予人的最尊贵的爵位。对此,他一再说: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04页。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267页。
可见,在孟子那里,对道德的张扬是通过将仁、义、礼、智说成是“四心”,进而又将“四心”说成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完成的。由此可见,他对人性、“四心”的阐释可以视为对仁、义、礼、智之道德与宇宙本体上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说明和论证。在此过程中,孟子对心之存在状态的说明使心同时拥有了形上和形下的双重属性:第一,心是先天的,并为上天所庇护和尊崇。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具有形上属性。第二,心作为人的属性、本质而存在,具有某种形下属性。进而言之,心在孟子那里兼具形上形下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心的双重身份和存在的双重维度——既存在于天堂又存在于人间;就存在于人间而言,心是人先天而非后天、内在而非外在的东西。如此,他一面在上天那里为心寻找来源出处和身份证明,借助上天至高无上的权威宣布心的天然合理性;一面把心下放,心的形下性使之成为人生而固有的某种本性和本能,引领人的思想和行为,为其贯彻、实现奠定了基础。
对于人生而固有的心究竟具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孟子认为,心是思维器官,具有思维的作用和功能。耳目之官不会思考,往往被外物所蒙蔽。与耳目之官不同,心是思维器官,自然会思考——只要用心思考就可获得认识,正如不用心思考就不会有所认识一样;只要充分发挥心的作用尽心思考,就会“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循着这个逻辑,孟子相信,充分发挥心的思维作用即可通晓宇宙万物之理,进入“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
对于心的作用机制,孟子解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就是说,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不仅是一种行为本能,而且是一种认知本能。所谓的“良知”、“良能”都是针对心而言的,是心的作用机制;离开了心,“良知”、“良能”便无从谈起。在他看来,心之所以具有“良知”、“良能”,是因为心中之知不用思考,无须后天学习或训练,心的所知所能是作为先天的、潜在的本性和本能存在的。进而言之,由于心的这种知和能与生俱来、完全出自本能,因此,一旦有所感触,自然会流露出来。对此,孟子举例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266页。见孺子入井必然伸出援助之手,这一举动是在瞬间发出的,自然而然,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甚至不经过理性的权衡或选择。同样的例子:“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37页。这表明,由于“良知”、“良能”是一种根于本性的本能,只要良心未泯,便会乘机自然流出,无往而不胜。在这个意义上,心又被孟子称为“良知”、“良能”。
孟子对心的界定、阐释本身即流露出对这一范畴的重视和偏袒。这与心对上天与性、仁义道德的沟通作用有关,更与践履仁义道德、与上天合一的方式密切相关。孟子对心的道德内涵的凸显体现了儒家一贯的道德本位。在这方面,孟子的做法是将性、心合一,致使人性成了上天赋予人的先天的道德观念,而心则是性、德之表现。这在为仁义道德赢得合法性的同时,也使通过知性而知天成为可能。
总之,孟子对仁义道德与上天联系的突出是通过上天赋人以性完成的,证据是“仁义礼智根于心”。为此,他将内含仁、义、礼、智的“四端”、“四心”说成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天——心——性的逻辑结构注定了心的至关重要。不仅如此,通过对心的诠释和阐扬,孟子逐一解答了心的意蕴内容、身份来源、存在状态、功能作用和本能属性等根本问题。经过如此这番阐释,心横跨本体、认识、人性、伦理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奠定了通过心,以践履仁、义、礼、智与上天合一的理论前提。
二、心与孔孟哲学的差异
孟子的思想带有深深的儒学烙印,与孔子的思想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然而,根于仁义礼智的性善说拉开了孟子与孔子思想的距离,使继承孔学的孟学呈现出不同于孔学的新态势。孟子思想的独特之处和不同于以往——尤其是不同于孔子的新动向始于以心为桥梁,突出仁义道德与宇宙本体——上天之间的内在联系,聚焦于心、性、德的合一,最终表现为通过尽心而践履仁义道德达到天人合一。在这里,心不仅是作为联结仁义道德与上天的中介出现的,而且是人发扬本性(“四端”,即仁、义、礼、智之善端)、与上天合一的途径,故而显得至关重要。可以看到,在孟子对心的进一步阐释和界定中,心的出现不仅限于概念、范畴的侧重和使用,而且关涉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和理论走势。于是,他的本体哲学、认识哲学、道德哲学乃至人性哲学由于有了仁义道德与上天的密切相关和心的沟通作用而处处呈现出与孔子及以往哲学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两人在概念运用、理论侧重等方面的学术分野,而且彰显了孟子通过心、践履仁义道德,与上天合一的思维方式、理论走向和价值旨趣。
首先,在孟子的哲学中,心是作为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和本能存在的,从来源处看具有属天的形上性,从存在处看具有属人的形下性。心的形上与形下属性即属天性与属人性使心架起了宇宙本体——天与人之间的桥梁。正如仁、义、礼、智之“天爵”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一样,心与生俱来拥有形上属性;上天赋予人的四心具体展现为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作为上天对人的天赋之命,是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人显露本性的过程和结果即是与天合一。换言之,正如心的天赋性决定了心对于人是先天的而非后天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一样,对于人的先天固有和内在性使心作为人的本性和本能始终左右着人的行为。人把先天固有的、作为本性的“四心”显示出来即证明了心并非外在强制的“天爵”身份和形上品格。显然,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心的形上性、“天爵”身份决定了心对于人的先天性和内在性,强化了心的天然合理性,这是天本论和天命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心对于人的内在性和与生俱来的先天性反过来强化了尽心、存心的自觉性和必然性,并通过后天行为把先天善性显露无遗,使心的“天爵”身份得以最终贯彻落实。前者是基础,属于本体哲学;后者是升华,覆盖认识、道德和人性哲学等诸多领域。这两条路线和逻辑层次构成了孟子天人合一的主要内容。按照他的逻辑,人的心中固有仁、义、礼、智之善端,充满宇宙万物之理;只要把上天赋予人的并且存在于人心中的仁、义、礼、智之端完全、彻底、充分地展露出来,就可以与天合一。可见,通过心的形上化和“天爵”身份,孟子奠定了儒家以道德完善、践履上天赋予人的善端来参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一模式。孟子开创的这套散发着道德情调的天人合一模式有别于道家、墨家及法家,尤其在与道家保持天然本性的天人合一模式的对比中更显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同样,孟子的这一模式又因遵循尽心、养心、存心和“求放心”的内求路线而演绎为不同于孔学的思维走向和理论归宿。在践履仁义道德与上天合一的过程中,孟子对心非常推崇,提出了尽心、存心、养心、“求放心”等这些口号和思想。
其次,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与天合一是人的使命和价值。这不仅是孟子一个人的看法,而且是中国古代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追求天人合一是各家的共识,彼此的分歧主要聚集在天人合一的内涵诠释和具体方式上。与其他学派不同且开理论先河的是,孟子极力强调心的作用和功能,致使存心、尽心、养心和“求放心”成为天人合一的基本内容和行动方案。由于天人合一的步骤、方法都围绕心展开而归根结底离不开心,孟子试图通过尽心、存心、养心和“求放心”等方法来充分发挥先天良知、良能的作用而知性知天、安身立命,这是一条心学的认识路线和践履工夫:一方面,人与天合一具体化为尽心、存心、“求放心”和养心寡欲的过程,心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位置,致使人与天合一成为发挥人内心的善端,使先天固有的良知充分显露出来的过程。另一方面,天人合一的结果——“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更是把宇宙万物纳入人的心中,在先天善性的发扬光大中,参天地之化育。
需要提及的是,孟子关于心之为善(人性善)的价值判断奠定了夸大心之作用的理论前提,使尽心、存心、养心和“求放心”拥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可以看到,他的许多主张和观点都围绕心而展开,上面提到的存心、尽心、养心和“求放心”即是明显的例子。此外,还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03页。等等。在孟子那里,心的使用有显有隐,或概念,或口号,或命题,或主张,如此层层叠叠、环环相扣,编织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关节网,贯穿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其实,孟子之心以及以心为核心的命题、口号和主张不仅辐射到本体、认识、人生乃至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作为深层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模式左右着孟子思想的立言宗旨。正因为如此,他把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实现系于一心,开创了儒家道德至上的心学之路。
再次,被孟子寄予厚望、津津乐道的心具有与生俱来的双重性:一方面,心是思维器官,会思考,具有认识功能。这便是所谓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04页。另一方面,心有道德属性,是价值和实践理性。因此,他断言,心内含仁、义、礼、智之四端。不仅如此,对于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和本能,孟子如是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37页。在这里,良知、良能与其说是与生俱来的认识本能和行为本能,不如说是先天的道德本能和本性。所以,孟子对良知、良能的具体诠释是仁义之善而非纯粹的认知智力。心在孟子思想中集认知和道德为一身的双重规定和内涵直接决定了尽心、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双重内涵和意义——既可理解为认识过程和手段,也可理解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即使是他对“心之官则思”的思之内容和后果的界定也含有道德、伦理因素。例如,孟子对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说明是这样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404页。
显然,“心之官则思”的立论角度不是知识、技巧而是伦理道德,尤其是先立其大的宗旨是成为大人,“心之官则思”的作用和结果是为人而非为学在此一目了然。与此相关,尽心——知性——知命——知天既是认识过程和手段,也不失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同样,养心的方法不是益智而是进德,这与“心之官则思”的结果不是知识的扩大而是为人——成为大人如出一辙。其实,心的道德属性在表明心的实质内容为仁、义、礼、智的同时,也注定了孟子对待心的态度是存、尽、养、求,总之,都是在积极和鼓动的意义上使用和对待心的。与此类似的,还有恒心和“不动心”之说。他不仅认为有恒心是士的操守,而且宣称自己从四十岁开始就已经臻于“不动心”的境界。《孟子·公孙丑上》篇详细讲述了不动心的做法和内容,要点是以立志为先,“养浩然之气”。他坚信,通过立志,保养浩然之气而使之常守不失,便可以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成为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四书译注》,乌恩溥注译,第314页。
诚然,伦理本位不是孟子的首创,更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儒家都有伦理本位的思想倾向,孔子庞大的思想体系以伦理思想为核心即是伦理本位在其思想体系建构上的反映。所不同的是,孟子的伦理本位更鲜明、更彻底,并且与天人合一直接联系起来。为了伸张仁义道德的权威性,他到宇宙本体——上天那里寻找依据,在使心成为“天爵”而获得上天庇护的同时,为人通过道德践履与天合一埋下了伏笔。
三、孟子对宋明理学的引领作用
孟子将人性(四心)说成是上天赋予人的先天本性和本能,在赋予仁义道德形上性的同时,使践履仁、义、礼、智之善成为人的行为追求和神圣使命。孟子将仁义道德与宇宙本体——上天直接联系起来,引导人通过道德践履与上天合一的做法被宋明理学家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天人合一的模式被固定化和程式化:在强调宇宙本体与道德密切相关方面,宋明理学家认定仁义道德就是宇宙本体(天理、吾心等)。
首先,孟子推崇的“四端”(仁、义、礼、智)被宋明理学家奉为宇宙本体。沿着孟子请出上天为仁义道德的合法性、权威性辩护的思路,宋明理学家直接将仁、义、礼、智称为天理,奉为宇宙本体。众所周知,宋代以前,对宇宙本体的认定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天、道、气、无、玄道到阿赖耶识,这些本体各具特色,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仁义道德无涉。从理学开始,仁、义、礼、智被含纳于宇宙本体之中,或者说,宇宙本体的具体内容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二程明确提出“天者理也”,并且自诩体贴出了“天理”二字。朱熹干脆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奉为天理,作为其哲学的宇宙本体和第一范畴。对于作为宇宙本体的理究竟是什么,他明确声称:“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一,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由于心中包万理、万理具一心,视心为世界本原的陆王心学只是在换个说法的同时,巧妙地把朱熹所推崇的理从虚无缥缈的天国拉回到了人间,使其常驻心中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宣布心是本原的陆王心学实际上是把仁、义、礼、智安插进心中,等于宣布了心即仁、义、礼、智,这便是王守仁断言“心外无仁”、“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的真正意图。不仅如此,即使是以气为本原的张载和王夫之等人也千方百计地凸显气的道德属性。如果说孟子对心的阐释突出了儒家的道德诉求,为了伸张仁义道德的永恒性和神圣性不得不借用上天的权威、使之与宇宙本体相搭界的话,那么,宋明理学家则直接而明确地把仁、义、礼、智说成是宇宙本体——天理或吾心。这种做法极大地提升了仁义道德的地位,也是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和强化。当初,为了增强心的正当性、合理性,孟子搬来了宇宙本体——天来为心正名,使心具有了某种形上意蕴。由于心为仁、义、礼、智四心,心的形上性表明了仁义道德与宇宙本体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然而,就仁、义、礼、智与宇宙本体的关系而言,如果说孟子在承认上天为宇宙本体的前提下,借用上天的权威为心辩护——此时的天仍然是本体、仁义礼智只是沐浴其光环而受其庇护的话,那么,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则直接把仁义道德抬高为宇宙本体。在此,宋明理学所做的是由间接向直接的转换。这种转换意义重大:一方面体现了宋明理学与孟子心学血脉相连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把儒家的道德主义追求推向极致。
宋明理学家在将仁、义、礼、智奉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上,通过本体哲学——人性哲学——认识哲学的三位一体,将孟子开创的以道德主义为旨归的天人合一模式固定化。在宋明理学中,一方面,无论宇宙本体为何物,宋明理学家都用本体去说明、阐释人性,使人性奠基于本体哲学之上,这使其本体哲学与人性哲学呈现出合二为一的趋势;张载、朱熹等人对宇宙本体显现为人之性命的阐释既是人性哲学的内容,又不失为宇宙本体派生万物的过程。另一方面,本体哲学决定了认识哲学的价值目标,尽管宋明理学家对于宇宙本体的界定相差悬殊,却都在认识领域以穷尽宇宙本体为己任,把穷尽宇宙本体视为全部认识的最终目标。这使理学的本体哲学与认识哲学呈现出合二为一的趋势。例如,认为天理是本原的朱熹把认识的目标锁定为“穷天理”,推崇心(良知)为本原的陆王把认识的路线归结为“反省内求”、“自存本心”和“求理于吾心”、“致良知”。可见,宋明理学家的共同做法是,在本体领域奉什么为本体,认识领域便以穷尽此本体为目标。进而言之,由于人性是宇宙本体在人身上的具体显示和呈现,认识以宇宙本体为对象和目标,其中就包括对人性的认识。在这里,人性哲学与认识哲学,一个是宇宙本体的显现,一个是对宇宙本体的认识,在宇宙本体的沟通下呈现出合二为一之势。因为人性至善,认识要尽心、存心、致良知,认识的过程和结果本身就是人性的完善过程。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最典型的形态,天人合一的模式也从此被固定化和程式化。
其次,孟子发挥心之作用知性知天的致思方向被宋明理学家提升为道德践履工夫。尽管宋明理学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派别,尽管并非所有的流派都把心奉为宇宙本体和第一范畴,然而,禀承孟子的心学路线,心被宋明理学家一致推崇。除了尽心之外,张载极为重视“大心”,“大”与孟子所讲的尽、存、养和求一样是心的动词,并且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对“大心”的重视表现了他对心的推崇。不仅如此,对心的重视和推崇使张载以气为本的气学路线在认识和人性领域急剧向心学倾斜。朱熹强调“穷天理”必须格尽天下之物,遵循向外穷理的认识路线。尽管如此,他还是念念不忘格物必须先存心。心使朱熹最终偏离了以理为本原的理学路线,其认识哲学和人性哲学带有厚重的心学痕迹。陆九渊虽然承认理是本原,却利用“心即理”的命题把理由虚无缥缈的天堂拉回到人间、植入人的心中,以至于其哲学被归为心学一派。同时,“心即理”的命题把心与理的关系密切化,心中只有理——毫无人欲之杂。这种说法在纯化、净化心之内容的同时,用心消融了理,树立了心高于理的权威地位。王守仁哲学只剩下了心,心成为统辖一切的绝对,天理也概莫能外——“心外无理”、“心外无仁”和“心外无义”——总之,心外什么都没有,离开心,整个世界荡然无存。“求理于吾心”和“致良知”则使心集认识主体与客体为一身,认识被还原为从心出发、达到内心的“自存本心”。
再次,孟子的“四端”与四体对举在宋明理学中开显出双重人性论。孟子宣称:“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他对人性内容的阐释和探讨人性的思路影响了宋明理学家,“四端”、“四心”与“四体”对举的做法更是被宋明理学家演绎为善恶兼具的双重人性论。不需要太多留意即可发现,宋明理学家所讲的人性双重与孟子的“四端”、四体并举相呼应。孟子对人性内容的分析和判断开了将人性一分为二、分别对待的先河。事实上,他对四心与四体关系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孟子把人的“四端”与四体对举,承认它们具有相同之处:正如耳、目、口、鼻、四肢都有欲望,并且具有相同的嗜好一样,人心也有欲望,也有相同的嗜好——这就是同心即心之所同。这成为孟子论证人性善的逻辑前提和证据之一。第二,孟子强调四心与四体的差异。尽管耳目口鼻、四体与心、四心一样与生俱来,一样都有欲望、嗜好,他却对它们分别对待。孟子“道性善”,那是就“四心”而言的,人性之善中并不包括四体以及四体之各种欲望。与此同时,他贬低“四体”、耳目口鼻之欲,有蔑视四体之欲、斥之为恶之嫌。这表明,孟子人性学说中隐藏着把人性一分为二的思想要素:四心之善与四体之恶。
张载、朱熹的双重人性论与孟子对人的四体与四心之分息息相关。正是沿着孟子的思路,继张载把人性分为至善的天地之性与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两个部分之后,朱熹宣称人性包括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个部分。正是按照善恶有别的思路,张载和朱熹不约而同地宣布,作为气之全部的天地之性和作为天理体现的天命之性是至善的,作为气之局部或理气杂合的气质之性却有善有不善。与孟子对四心与四体的分别对待如出一辙,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路别无二致,为了人性的完美和统一,张载和朱熹共同主张变化气质。这套理论路径和价值取向可以视为孟子基于“四端”与四体的对举和分别,进而断言“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的翻版。
上述内容显示,宋明理学的主要范畴、基本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与孟子有关,在各个层面都显示出孟子思想的特征。具体地说,孟子引领了理学对概念、范畴的喜好和侧重,使心成为气学、理学和心学共用的范畴,同时影响了理学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建构。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