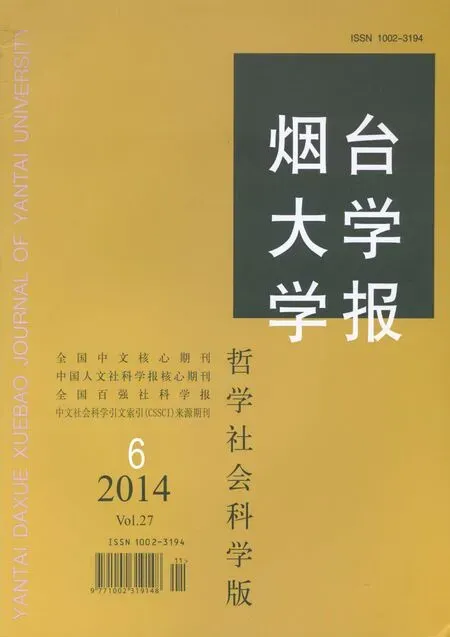朝鲜人眼中的日本近代城市
——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
张礼恒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1881年2月8日至3月1日,为了寻求修补《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中有关关税问题的对策,全面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形势,朝鲜国王李熙发布密令,选派一批朝廷重臣,组成大型赴日考察团,以私人出国游览的形式,出访日本。这支代表团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该团于5月7日踏上日本国土,8月25日回到朝鲜。在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朝士视察团”行迹遍及长崎、大阪、东京、横滨、神户、西京(京都)等地,对明治维新14年后日本的综合国势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清晰展现了东京、大阪、长崎、京都、横滨、神户等地的基本风貌,留下了一幅日本近代城市的写真图。这些记载对于研究近代日本城市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遗憾的是,对于朝鲜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外史学界研究很少。①韩国史学界主要有:许东贤:《1881年朝士视察团研究——以日本见闻报告书之内容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高丽大学历史系,1993年;崔震植:《韩国近代的稳健开化派研究——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之思想与活动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岭南大学历史系,1991年。日本史学界对此事件虽有涉及但不多,主要体现在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东京:宗高书房,昭和15年,第746-747页;《世外井上公传》,东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昭和9年,第449页。本文主要以“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中心,截取日本城市这一断面,全面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城市发展的概况。
一、城市建筑以传统为主,西洋为辅
城市建筑及其风格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近代化程度的一种标志,折射出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水准与基本走向。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的国家,其近代化进程是在仓促情况下启动的,且以爆发式的规模进行,这就使得日本近代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工业与农业相互交杂的景象。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城市建筑和风格也基本相同。那就是传统为主,西洋为辅。东京、大阪、横滨、神户、长崎、西京(京都)作为此期的日本城市代表,以其现实的存在,向“朝士视察团”展现了日本城市的基本风貌,彰显着日本近代化的演进趋向。
在“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之下,此期的日本城市表现出两大特征。
其一,蕴涵着东方传统城市的痕迹。
按照词义解释,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在东方国家的词义中,“城”的基本功能是防御,四周建有厚厚的城墙是其外在特征。《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内为之阔”。据此可知,所谓的“城”,就是周边被城墙环围的空阔地域,一般修建在交通要道、战略要地,军事职能优先考虑。“市”则是进行交易的场所,正如古书所云:“日中为市”。由此可见,东方国家“城市”的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均与近代的“城市”有着本质的差异。仅就此期日本的城市而言,东方传统城市的色彩极为浓厚,无论是东京、西京,还是大阪,位居城市中心的或者是天皇御所,或者是幕府所在地,整个城市都是以其为圆心向四周扩展而成。据“朝士视察团”成员闵种默记录,东京“北连沃野,冈阜回伏,王居在中,即德川旧府也。为城三重,揫以石壕,中高而外下,城各周濠,引玉川水灌之,门设不关,架桥梁以达内外,市衢宽广,夹植树木,疏风荫。……果是一大都会也。”*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45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朴定阳的记载则突出了东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和军事功能。他说:东京“城中以三重,筑之石,周可数十里。城内无闾家,内城最高处为日主所居,即前日关白之旧府也。内城以外三城以内,则皆官省公廨,多是前日藩臣之私室云。……城各有壕,壕中灌水,深流不绝,……城则有门而无关,壕则设桥而通路。……重城之外,闾阎扑地,台榭层叠,尽是雄都,周可七八十里。”*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6-158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相比之下,大阪作为关西重镇,旧都屏障,其城市布局的军事功能更多更加突出。据朴定阳、赵准永记载,“大阪即日本三大府之一也。……此地有陆军镇台,即六镇之一。而三重石城,城下有壕,壕深、城高比于东京之城,反为完固。此盖平秀吉之所筑云。”*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9-160页。“大阪城池之固,户口之繁,素称雄镇,富商大贾,多藏于此。”*赵准永:(60)《闻见事件》,第597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此种天子居于中,四夷守于外的城市布局,典型体现了“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东方传统,物化了君主的中心地位。君主居地之城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重功能,军事功能是其底色。
其二,建筑风格明显西化。
日本古代居住建筑样式大致经历了圆锥形竖穴式、竖坑式、高床式三个阶段,到平安时代(794-1185),形成了寝殿式建筑的住宅风格,确立了现代日本住宅的建筑风格。无论是民居,还是皇家贵族住所,皆为木材框架结构,房顶盖以茅草或丝柏树皮,门窗用纸遮糊。中国人罗森1854年2月21日,作为随员亲历了美国准将柏利逼迫日本开国的全过程,其在《日本日记》中,描述了日本房屋的建筑风格。他称:“予游横滨,见郊外只有龙神古庙,以木为之,内悬镜像,俨若兴云致雨之意。有店烧瓦,其瓦坚实,灰色而厚,不同中国之式。再行二三里,则有人居屋,亦或灰或草结盖屋,外多以纸符巾于门上。”*《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王晓秋、史鹏点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页。此种建筑的最大弊端就是易发火灾。
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激增,日本城市建筑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1873年东京神田町、福田町大火,损失惨重。1879年12月12日,东京桥箔屋町大火,烧掉了79个町、万余户住宅,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大的火灾。为了防范持续发生的火灾,东京府在东京人口稠密区实行大规模的建筑改造。这主要体现在建筑用料上。东京府强制规定,所有房屋必须依据新的标准建设,废弃板顶、草顶,一律换成瓦顶;废弃板壁,一律换成“炼瓦造、石造、藏造(夯土筑墙)”墙壁,且外层涂抹上厚厚的泥灰,目的在于增加房屋的防火能力,减少火灾的发生。此外,还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划定了若干个功能区,对城市统一规划。此次城市改造计划虽然未能全盘实施,但基本确立了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格局。当1881年“朝士视察团”到达日本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建筑风格日益西化、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整洁有序的近代化城市。姜文馨的描述最具代表性。他说:“凡公私宫室之制,本无温堗,只是重屋层楼,亦不施丹臒,多涂石灰,黑瓦粉壁,眩耀相杂,飞甍危栏,高低层出,远而望之,殆同罨画之境,近而视之,实失都料之法,柱细而长,檐高而短,风撼雨洒,频年修改,盖多仿西国新制,闾阎扑地,旗亭连队,庭无片隙,喜植花卉,盆松瓶梅,列置椅栏。至于公府官舍之大,不设外门,长廊围以木栏,或以铁扉前庭,后院多植松竹,树林荫翳,花香袭人,颇有幽趣。所过村落,或有茅庐、板屋,而京都府治,绝无仅有。城郭则只见于江户,周围七十里,四重四濠,深可容舟,雉堞不置谯楼,外城不设石门,未知缘何规模。而内城虽曰有门,亦非筑石虹蜺,只设板门、片铁,所见甚踈虞。”*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8-69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建筑材料、建筑风格、城市布局,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
二、城市规模较大,经济繁荣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殖产兴业”战略的推广,大批新兴产业如炼钢、造纸、造币、纺织、机器制造等产业在城市周边迅速崛起,促进了日本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转型,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了城市人口激增。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东京、西京(京都)、大阪、长崎、横滨、神户为代表的日本城市人口少则几十万,多则近百万。据朴定阳记载,东京是当时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凡二十四万九千五百十五户,男四十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余口,女四十七万四千四百九十余口。盖市户居多也。”*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6页。西京(京都),“户十九万零,人口八十一万四千余,有知事守之。屋宇之宏杰,人物之繁多,可与东京比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8页。但在闵种默的笔下,西京不足50万人口,两者差距较大。他说:“统户人口四十六万余。”*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35-137页。横滨近邻东京,是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户可十余万,人口为七十万余。”“大阪即日本三大府之一也。”“物华之盛,足称雄府。而户十五万七千零,人口五十七万八千零”。*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9页。神户既为通商要地,“现今户可数万,人口可十万余,人物之丛杂,物华之蕃多,亦一大都会。”*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1页。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对于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做过如下评说:“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城市人口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20年代,每4个日本居民中就有1个居住在城市。”*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日本在明治维新十多年之后,散布于全境中的主要城市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景象。据朴定阳记载:在东京,“各国商业之人,杂居其间,昼而继夜,互市不绝,夜以达晓,明灯不灭,道路净洁,污秽不触,川桥纡萦,舟楫相通。”*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8页。赵准永对东京的商业繁荣印象深刻。他说:“江户即东京,沿海方四十里之地,原野衍广,无险阻之势,通衢大路,肩磨毂击,民物富庶,屋宇华丽,灯火连街,夜行如昼”。*赵准永:(60)《闻见事件》,第597页。大阪向有皇都屏障之称,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东京的经济中心,“人烟稠密,商货辐辏,东北距京,为之屏蔽”。*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33页。朴定阳对其更是高度评价,称“大阪即日本三大府之一也。处在旷野之中,一面滨海,川江萦纡,桥梁交错,舟楫出入,商贾络绎,人物之蕃,物华之盛,足称雄府。”*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0页。西京作为故都,虽显保守,但商业繁荣丝毫不输东京。宋宪斌称其“屋宇宏伟,民物丰盛”,“街中车毂相击,人肩相磨,其繁华似胜于大阪矣”。*宋宪斌:(69)《东京日记》,第382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3篇,第14卷(下同略)。长崎是明治维新前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维新之后,成为日本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朴定阳称此地“设港最久,在前则物货凑集,商舶络绎,极为蕃富,近年以来,开港多处,其利分歧,比前虽残,市街之连络,物品之侈靡,亦足曰一大都会。而有造船所、打铁所、工匠分所,皆是火轮之机也。距此七十里,有曰古岛地,即石灰掘采之处,而其产冠于一国”。*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1-162页。由上可见,明治维新后,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城市均表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国际、国内贸易频繁往来,商业流通极为繁昌,统一的国内市场已基本形成,整个日本流溢着浓厚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业气息,对于前来经商贸易的17国商人,“日人不以殊俗而怪之,或以习闻见于长崎者寻常看做万里比邻,遐迩一体,穰穰利往,滔滔如水之就下”。*严世永:(51)《闻见事件》,第344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各主要城市在保持原有经济特色的前提下,根据地理位置和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调整,衍生出若干新兴产业,构成了一个功能各异,优势互补的城市经济网络,城市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
三、城市交通便捷,铁路、公路、海运四通八达
交通拉动经济,经济促进交通发展。便捷的交通运输业,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加速了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铁路、公路、海运将全国联为一体。这是“朝士视察团”感受最多的收获之一。自踏上日本国土开始,“朝士视察团”就充分领略了日本交通的便捷。据使团成员沈相学与姜文馨记载,5月7日中午,“朝士视察团”乘坐日本“安宁丸”号邮轮离开朝鲜,下午5点左右到达对马岛,行程480里。8日凌晨启航,下午1点左右到达长崎,行程570里。14日中午乘坐火车,从神户出发,下午1点左右到达大阪,行程92里。17日下午1点左右乘坐火车离开大阪,3点左右抵达西京,行程100里。24日换乘“广岛丸”号轮船,从神户出发,25日上午9点左右到达横滨,行程2530里。当天下午3点左右,乘坐火车抵达东京,行程73里。*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16-2178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52-54页。据此可知,随着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日本主要城市之间,大多可数小时抵达,即使相隔近3000里的神户与东京,也可一天之内到达。对此,使团成员李宪永惊叹道:“轮船之一日千里,轮车之一时百里,此岂人力可致哉?”*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5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2篇,第12卷(下同略)。从横滨到东京更是快捷无比,“横滨港在东京之东南七十里,以铁路通行,日人往来,便同邻家”。*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9页。使团随员宋宪斌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东京至大阪乘车观感。他说:“火轮车无数,往来一轮车之行,所连付者亦亘三十间,乘人处则有上中下三等之别。……黑烟一发,其行如飞,一时之间,即抵大阪。”*宋宪斌:(69)《东京日记》,第375页。
“朝士视察团”更是仔细考察了日本铁路的历史与现状。使团成员闵种默称,“铁路始于明治二年(1869),自东京至横滨,七十余里。”*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6页。相比之下,使团成员朴定阳的考察更为详实。他介绍道:“铁路者为其火轮车之行而设也。以铁打做片条,鳞续于大路或凿山而通道,或沿河而成桥,以便车轮之运用。此亦西制,而自已巳始设于东京横滨之间七十三里,至壬申讫功。自甲戍又设于神户、大阪之间九十里。丙子又设于大阪、西京之间一百二十里。其年又设于西京、大津之间四十八里,并已讫功。前后所费,合为一千一百万圆零,而火轮车数合为五百九十四辆也。……一时之间可行一百里,其用甚博,其行甚速。”*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88-189页。到1881年日本已修筑铁路“三百余里”,*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6页。确立了以东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铁路发展规划。
日本城市交通便捷不仅体现在城市之间,更体现在城市内部。马车、牛车、人力车、商船等是此时日本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据闵种默观察,在东京这个不足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就有各种车船四万多辆(艘)。在考察报告中,闵种默记载到:东京有“马车三百余辆,牛车、人力车、荷车共四万余辆;商船,蒸气、铁制、风帆共百余艘”。*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45页。车夫们多是家无恒产的贫穷之辈,“无恒之民,日趋于役车,阗街溢衖,无非车夫”。*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47页。记载显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城市的交通运输业还处于一种低端水平,马车、牛车、人力车充当着城市交通运输的绝对主力,机械力远未取代自然力,由数万人组成的运输大军,为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强劲动力。
四、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现代城市的建设、经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却以楼堂馆所、桥梁、道路为主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以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为主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前者是硬指标,后者是软实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城市的繁荣昌盛。“朝士视察团”笔下的此期日本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情况,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和带有社会福利性的特殊教育上。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是“朝士视察团”极为关注的对象,几乎每个使团成员都留下了与此相关的大量记载。记载显示,此期的日本学校教育一改传统教育模式,广泛采用西方近代教育体制。其一,在学校建制上,构建了由小学、中学、大学组成的完整的教育体制,实行专门学校与师范学校并举的教育模式,推行公立、私立两种办学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六七岁幼稚无不入就,而解字解音,日用之文,半是罗马,纵横之画,部洲之界,必称地球,东西之图。京外大学区有七,而其余中学、小学、公立、私立,可以千万计也。”其二,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儒家经典被边缘化,近代的声光电化等学科扮演主角。李宪永这样记载:“所谓学校也,圣贤经籍束在高阁,化理气数设而为场。”*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6页。朴定阳称:“戊辰以后专攻西学”,“其所传习者,曰物理学、兵学、技艺学、光学、化学、各国语学、医学、测算学等,许多名目,不可枚举。”*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8页。姜晋馨介绍说:“国内学校处处有之,皆非专经攻文之业。有语学、法律学、理学、化学、重学、光学、算学、矿学、画学、天文学、地理学、机器学、动物学、植物学、汉学、英学、商贾学等名色。”*姜晋馨:(68)《日东录》,第234-235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3篇,第14卷(下同略)。其三,重视女子教育。女性是民族之花,民族繁衍之母,其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民族的整体素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极为重视女子教育,专门设有女子师范学校,规定“上自公卿,下至平民,女子十岁便使入学”。学生在校期间,除学习一般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外,“凡系女红之针织、玩戏之书画,各歧就工”。正如李宪永所言:“公卿家女子亦为生徒,而能书能画”。其四,聘用西洋人担任教师。随着学校的增设,尤其是大学的急增,日本国内合格的师资极为短缺。为此,明治政府不惜重金投入,聘请西洋人担任教师,化解师资不足的难题。朴定阳记有:“诸学中或以西洋人聘以为师,日人之有识者颇为慨叹。”*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8页。其五,学校教育规模宏大,日见成效。据闵种默记载:“全国学校总数,至明治十二年,二万七千余,教员七万余,生徒二百四十万七千余。一年费金额五百三十六万圆,皆隶于文部省,即太学、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其课程皆有定则,暇由各给日时。”*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20页。
在现代社会,学校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文明得以承续传播的重要场所。学校所设置的每门具体课程,均体现了民族进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的精神内涵,折射出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取向、理性思维。声光电化等学科是对欧洲文明的高度凝缩和体认,反映了西洋文化的特质,它同日本传统教育制度在培养人才、陶冶情操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明治政府在教育上的举措表明,为了实现“脱亚入欧”的宏愿,日本已经将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了西洋,抛弃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将儒家典籍束之高阁,广泛开设近代声光电化等课程,大量聘请西洋教师登堂授课,表现出强烈的“求知识于世界”的进取心。
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现代城市的必有之物,在传播现代知识,陶冶市民情操,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朝士视察团”对明治时期日本图书馆的记载并不多,仅见于闵种默的考察报告之中。据闵种默记录:“图书馆在汤岛町,圣庙雄伟,题额昌平馆,左右廓庑,位设濂洛六君子影帧。我国信使金世濂志跋焉。间间层桌,经史图书之贮藏,充栋汗牛。而明治以后新贮书,其泰西之文十居八九。馆无生徒,但四五游学之时,时寓馆焉。近废尊享,或云要路之人叨行此举,不胜惭慨。”*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24-125页。
医院在保障全民健康,提升生命质量诸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卷帙浩瀚的“朝士视察团”考察报告中,介绍日本医院情况的仅有一份。但就是这份只有一百多字的文字记载,清晰地描述了明治时期日本医院的基本概况:每个城市均设有规模宏大的医院,医院建立了一整套职责明确、分工细致的规章制度,广泛引进西洋医疗器械,大量欧美医生被聘请为医院的医生。“(西京)病院亦在东区内,馆廨宏阔,院有长、看事员二十六,生徒三百名,统一年院外院内之来惠治病者,亦七千余名,治病之具,专以银铜为割剥鍼刺之具,各属为二万余钉,每钉又不知几百千个,罗列床桌,又置治病引伸便用之各种械器,而专试洋制水药,尚延泰西教师隶工焉。”*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39页。
明治时期日本以聋哑残疾人为对象的特殊教育更是“朝士视察团”津津乐道的话题。根据实地考察,“朝士视察团”发现,日本政府在对残疾人、孤儿的救助问题上,其救助措施、保障理念均脱出了东方传统的窠臼,带有鲜明的近代色彩。其一,随着近代化运动的全面启动,明治政府已经将聋哑、失亲儿童的扶养、教育纳入了国家管理层面,一改维新前残障儿童散居各个家庭或寄宿少数寺庙的分散、孤立的旧习,“(西京)设置盲哑院,杂聚男女盲哑者置师教之”,“又置救育院,幼儿之失父母、流离者,贫人之无室家丐乞者,收而养之,及其成长,使各授业,俾有归属”*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84-86页。,对全社会的慈善事业,作出统筹安排,残障、失亲儿童不再是被社会遗弃、嘲笑、自生自灭的弱势群体,而是国家法律保护下的享有同等接受教育、拥有一技之长的国家公民。其二,残疾人保障制度的理念由传统的施舍、恩赐变为保障权利、参与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东方国家传统的慈善事业主要是由慈善会、慈善堂承担,其活动主要有:为死去的贫苦者提供棺材,为无衣者施奉衣物,向无钱治病者馈赠医药,掩埋暴尸、照料鳏寡孤独者,收养育婴等。以这些活动为载体的慈善事业,是东方传统文化、道德的体现,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消极做法,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令“朝士视察团”赞叹不已的是,明治政府在大力学习西洋的同时,适时移植了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对包括聋哑、失亲儿童在内的社会特殊群体,采取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政策,变单纯的收容、收养做法为收容、收养同教化培训相结合的办法,根据残疾者的生理特征,传授其基本的生活技能、生存本领,教会他们赖以为生的专业技能,“盲者教地势、形便、道路远近及日本谚文,而地图刻以木板,分别高低,以手按摩,可验横直。谚文,口以授之,耳以听之,日课月考,致自然成诵。哑者,教书画、算数、雕刻等技,而口虽不言自之所见,手之所使,无不精通。初给料而劝课,末乃技熟而收税,虽或近于为利,亦使民无游食,免乎沟壑之意也”。“盖其身以疾废,才质未可同废云。”*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39-140页。使之成为足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尊严活着的城市市民。其三,体现了明治政府尊重人权的治国理念。残疾人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事业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与文明程度。其主旨在于弘扬受教育权也是一项天赋人权,并据此使残疾者在保障基本温饱性生存的基础上,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实现社会融入,共享人类社会的文明福祉,促进残疾人社会价值的自我实现。“朝士视察团”记载下的日本特殊教育,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展现了日本明治政府在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以西洋为师,全方位学习,既有器物层面上的照搬,也有制度层面上的效仿,更有意识、观念上的更新,昭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
五、城市治安规范有序
伴随着城市化过程而来的是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人情冷漠、治安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但“朝士视察团”在日本考察期间,看到的却是一个秩序井然,城市运作规范有序的日本社会。探及缘由,“朝士视察团”将其归之于三点。
其一,严密有序的城市治安管理机制,主要体现为日本警察制度的近代化。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原本就是法制社会的产物,最早出现于英国。1829年“近代警察之父”罗伯特·比尔爵士设计的近代警察制度在英国确立,并被迅速移植到欧洲大陆,为宪政建设提供了公共秩序的保障,将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纳入了法律的保护之下。1872年时任逻卒总长的川路利良,作为日本司法省派出的“西欧视察团”8人成员之一,远赴欧洲考察警察制度。1873年9月回国后,提出了以法国、普鲁士为榜样的警察制度改革方案。1875年,明治政府采纳了川路利良的建议,改革旧有的警务模式,以立法的形式颁布了《行政警察规则》,创建了一整套严密有序的城市治安管理机制。此法律的颁布实施,奠定了日本近代警察制度的基石。此后,日本警察地位大幅提高,权利急速扩张,隶属关系进一步厘清,指挥系统顺畅便捷,职责分工明确。内务省统管国家行政警察事务,司法省掌管国家司法警察事务,各道府县设有警察本部(又称“本店”),下辖若干派出机关(又称“支店”),负责各地治安保卫工作。基于东京都地位的重要性,“东京都警察本部”独称“警视厅”,归内务省直接监督管理,最高长官称为“警视总监”。最初的警察多由民风强悍的萨摩藩士族担任。*“人物之繁盛,江户、大阪为最。而文材以肥前、安艺、水户三县为最,武才以萨摩、长门为最,是以更张之初首唱者,萨摩之人十居五六矣。”见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38页。使团要员赵准永对此有过记载。他说:“东京及各府县置警视局,监全国。警察之政,预防人民之为害者也。区町之间,各设屯番之所,有巡查其状,似陆军武官。而如遇国家有事,授兵器为军队,以当一方,此可谓陆军部外一种之常备兵也。其数共一万五千八十余名,分掌里巷,游徼讥詗,有犯罪者执送法官。”*赵准永:(60)《闻见事件》,第607-608页。
其二,明治政府高度重视警察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警察人员的配置数量上。世界通用的警力与居民的配置最佳比例为1∶2000。尽管“朝士视察团”对日本警察数量的统计有较大出入,赵准永记载为“一万五千八十余名”,闵种默记载为“二万二千百余”,两者相差7000多人。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难以确认哪种记载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在此暂且估算日本警察总数为二万人。当时日本全国共有三千万人口,警察与国民之间的警力配置为1∶1500,高于国际通行的警力配置标准。如果再考虑沈相学、姜晋馨所记载的“每六十户,巡一人”,那么明治时期日本警力的配置比例就更高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警察国家”了。高配置的警力在日本社会全面转型、新旧矛盾突出的时代,为稳定城乡秩序,保障近代化事业有序推进,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
其三,划区设警,分片维稳举措,大显成效。开国之前,日本社会秩序良好,多为外人称赞。1854年2月,中国人罗森在游历日本之后,留下了如下记载:“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却(劫)之风,亦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王晓秋、史鹏点校,第38页。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利益的再分配,社会矛盾激化,秩序一度混乱。尤其是城市治安环境趋于恶化,每当地震发生之时,东京、大阪等城市火灾、抢劫、入室盗窃等恶性案件频繁上演。随着警察制度的确立和全国警察网络的建成,警力深入到城市、乡村,特别是划区设警,分片维稳举措的实施,混乱的状态被迅速扭转,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基层警察尤其是巡警,手持警棍,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全天候巡逻在辖区之内,处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盗窃、火灾、传染病报警、物品遗失、交通等事务,保一方之平安。据沈阳学记载,“江户每多地震,而又多火灾与窃发之患,统其六十户,有警卒一人,称以巡查,分布昼夜,缉捕告警,不违其时。”*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第239-240页。姜晋馨则称:“(东京)府内人家极为稠密,最忌失火,故使警视厅,以备不虞。每六十户,巡以一人,司警察者称曰巡使(如我国捕校),持三尺棒,无论风雨,每日巡行,计刻递代,夜深不散,火作则击钟而传警焉。”*姜晋馨:(68)《日东录》,第234页。良好的治安环境,尊法、守法的社会风气,让“朝士视察团”赞叹不已。沈相学就曾记载道:“街无哄斗、酗酒之杂类,刑法无拷杖之威,而分罪之轻重,或受罚金,每多征役,赫衣满狱。大抵立法细密且严,官一出法,民无违划。”*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第240页。
六、日本近代化的全记录
历史秘密时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披露。“朝士视察团”可能真的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国王李熙的旨令,“日人之朝廷议论、局势、形便、风俗、人物、交聘、通商等事之大略,一番更探甚好。卿须着意,混骑日人船只,往渡彼国,内务省所掌事务及外他多少闻见,勿拘年月久近,一一探来。后此别单,从容为之。”*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74页,见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国学资料院,2001年,第3篇,第13卷(下同略)。在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对明治维新14年后的日本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留下了上千万字的记载,为后世了解、研究此期的日本社会保存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史料。细细研读这些记载,完全可以说,“朝士视察团”的考察报告,实质上是一篇日本近代化的全记录。
“朝士视察团”考察报告中有关城市社会生活的记载,浓缩了1868-1881年间,明治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和“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生活方式等领域推行的近代化运动和业已取得的斐然成绩,全面展现了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生的巨变。此期的日本城市既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又是日本近代化的见证者、亲历者,它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佐证了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起步、迅跑。外延式建设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空间上的拓展,城市人口数量上的激增,以东京、西京、大阪、神户、长崎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城区面积急剧扩张,首都东京,“周可七八十里”,*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7页。城市人口,少则十万人,中则五十万至七十万人,多则八十万至近百万人,仅前四个城市的人口总和就达到了3175740人。*此人口统计,参考了考察团的记载。东京人口:“凡二十四万九千五百十五户,男四十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余口,女四十七万四千四百九十余口。”见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7页;西京“人口八十一万四千余”,见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8页;横滨“户可十余万,人口为七十万余。”见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9页;大阪“户十五万七千零,人口五十七万八千零。”见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0页;神户“现今户可数万,人口可十万余。”见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1页。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为三千万,*“人物总计一国为三千万口。”见赵准永:(60)《闻见事件》,第600页。据此可知,日本城市人口比例已高达12%,如果再算上长崎市人口,日本城市人口比例应当在14%左右。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统计,到19世纪后期,“就世界范围而言,已有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几乎是一个世纪前的三倍。”*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第167页。英国是此期城市居民最多的国家。“到1881年,英国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1/3。”*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第146页。同期相比,日本城市居民比例虽然远低于英国,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近3倍,无怪乎朴定阳就曾赞叹道:“盖市户居多也”。*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7页。这一数据足以显示日本在城市化、近代化运动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如果说,规模大小、人口比重高低,是城市化的硬性指标的话,那么,以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为表征的内涵式建设,则是城市化的命脉所在,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社会发展提高的一个标志。在“朝士视察团”的笔下,日本既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各类大、中、小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有便捷、快速的交通运输网络,铁路、公路、海运四通八达;又有传承文明、陶冶情操、救死扶伤的城市公共设施,博物馆、图书馆、西式医院、盲哑院、救育院随处可见;更有严密的警察制度,警察恪尽职守,化解社会矛盾,高效快捷地处理刑事民事案件,治安状况良好,社会秩序井然,街头巷尾绝无打架斗殴之事,绝无吸食鸦片之人。使团成员严世永为此记载:“所谓鸦烟之卖卖,设一厉禁,著为章程,绝不见其人其物也。”*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79页。闵种默更为此与中国进行比较,颂扬日本良好的社会风尚,鞭挞中国丑陋的社会恶习。他说:“丙子(1876年),江宁税务司李圭航亚米之路,过此叹曰:‘通商情形虽不及上海十之三四,然贩运洋药商人,如在中华之沙逊洋行(沙逊,英国巨商,专贩洋药)无有也’。日本烟禁极严,食者立治重法,国人皆不敢犯禁,虽齐之以刑,亦可见法而民从。惜我中华,不知何时乃能息此毒焰?”*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44页。
平实而论,“朝士视察团”各成员完成的是一项使命,记录下的却是一段日本近代高速发展的历史。掩卷遐思,抚今忆昔。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历史演进的方向,是东亚国家学习、模仿西方的成功范例,是落后国家由被迫开国到实现转型跨越的一个奇葩。如果将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同期的“非驴非马”的洋务运动进行比较,则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时至今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认识仍未到位,对明治维新的研究还需加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