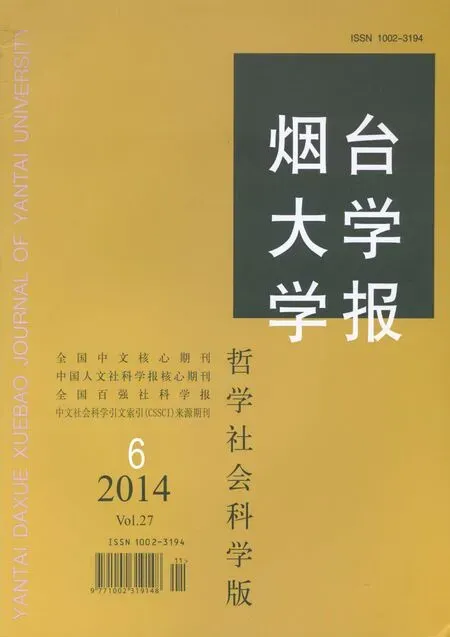“他者”之殇
——从《觉醒》和《双鱼星座》看女性他者地位的变与不变
李 昕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2.长春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他者”是个哲学范畴,与自我(the self)相对,意近客体、次要、从属。女性在社会中的“他者”属性,不是哪个国家的个别现象,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女性文学萌生的最初,“他者”便是一个相伴随的概念。正是在女性诗学发展的洪潮中,“他者”跨越了古老的哲学疆界,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对女性“他者”(the other)地位的论述,最早见于波伏娃的《第二性》。在这部被誉为“女性文学的圣经”的著作中,她对女性的他者属性(otherness)用一句话概括:“他是主体,是绝对的——她是他者。”①De Simon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Books USA, 2009, p.6.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勾画、印证了女性“他者”属性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觉醒》和《双鱼星座》虽然分属不同世纪、不同国别的文学,但对女性之为“他者”的摹画均有其毋庸置疑的典型性。
《觉醒》创作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讲述了一位年轻少妇妄图突破婚姻樊笼、赢取经济独立、实现自我追求但最终失败的故事;《双鱼星座》创作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叙述了一个年轻而富有创造力的女性人物在现代男权社会权、钱、欲的围剿中孤独的抗争、失败和逃离。两部作品在揭露各自社会男权本质的同时,体现了极为明显的本质相似及历史承继关系。
一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经济结构的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工厂制广泛建立并深刻地影响了生产关系②参见杨生茂、陆镜生: 《美国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促使女性的生活领域开始突破家庭的局限而向社会其他领域延伸。与此相关,女性意识的觉醒、伦理观念的变迁、女权运动的兴起,成了女性文学繁荣的历史语境。
《觉醒》作为此时女性文学的代表,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强烈的伦理冲突,揭露了传统父权社会女性之为“他者”的典型表现:经济依附、自我迷失以及隶属性的社会地位。
其一,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在派别林立的女性主义内部,经济因素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影响已经获得了包括伍尔夫、波伏娃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内的广泛认同。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父权社会,女性因生理上的弱势而在社会分工中占次要地位,丈夫参与社会生产,而“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71-21页。,她们“因没有拥有或赚取金钱的权利而毫无经济独立可言”*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39.。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让渡一定的个人权益,甚至沦为“毫无法律地位的‘非’人”②,以求得男性的庇护。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但职业女性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数据,1870年美国女性就业率为14.8%,1920年的就业率为24.2%。由此推之,1890年间,八成左右的美国妇女仍处在无业状态。参见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Women in Gainful Occupations, 1870-192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pp. 36, 40-45.。《觉醒》的女主人公艾德娜嫁给中产阶级商人。在家庭分工中,她不参与商业经营,只负责照料孩子、安排家事、宴友会客。经济上,她貌似富足安逸,实则毫无权力。家庭经济的真正控制者是她的丈夫庞德里耶先生:“他(庞德里耶先生)非常珍视自己的财产,主要因为它们是他的”。*Kate Chopin, The Awaken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p.73.为行文方便,本文引自该书的内容只在文中注明页码。在这种生活中,因为丈夫相对的慷慨体贴,艾德娜曾倍觉满足、幸福:“庞德里耶太太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她没有遇见过比他更好的丈夫”(p.10)。但随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夫妻间地位差异的体认,艾德娜终于认识到丈夫对她在经济上的“绑架”,并力图挣脱:她决定搬出和丈夫共有的家,用绘画、赌马所得,购置自己的房产,因为“那栋房子,还有维持它的钱,都不是我的” (p.115)。
艾德娜是勇敢的。在世人冷眼旁观中,她赢得了哪怕是短暂的经济独立。然而,和她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克里奥妇女,仍然在难以抗争的男权传统中固步自封,过着相夫教子、看似安稳、实则没有自我的生活
其二,女性自我在家庭责任中的磨失。“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被变为女人的。”*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p.293.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导致男性对女性形象的种种规约。这样的女性形象被伍尔芙定义为“房间中的天使”*Virginia Woolf, “Professions for Women,” The Death of Moth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p.236.,被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描述为“女性纯洁的永恒类型”*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这些女性,看似纯洁高尚,实则没有自我,丧失自由,只能在侍奉夫君、抚育子女的所谓的崇高中穷此一生。
在格蓝岛夏季的沙滩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女人,她们“宠爱自己的孩子,崇拜自己的丈夫,将抹煞自我、充当孩子和丈夫守护天使视为神圣的特权”(p.11)。阿黛尔·拉提诺夫人便是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她风姿绰约、妩媚优雅,恰似浪漫传奇的女主角、雍容华贵的皇后甚至万人瞻仰的圣母玛丽亚;她疼爱子女,几乎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并对他们悉心照顾;她崇拜丈夫,对他说的一切都怀有热切的兴趣;她热心于家事,连坚持练习钢琴也是为了调节家庭气氛。在众人的眼里,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女人,但艾德娜却觉得她可怜:“她的生活单调乏味。这种生活中她却一贯盲目地满足,从没有烦恼触动她的心灵,她也从没有品味过生活的狂喜”(p.82)。这不仅是她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女人的问题。她们被男性架到“天使”的神坛上,从此为了这个貌似神圣的称谓,丧失了自我,牺牲了人之为人的快乐。
可以想象,在不快乐的天使和快乐的人之间,很少有人会想成为前者。拉提诺夫人是“天使”女人的典范,但她是不快乐的。她日益羸弱的身体就是她身心备受摧残的证明。艾德娜曾奉阿黛尔为楷模。但格蓝岛海水的冲刷之下,在克里奥文化的熏染之下,在爱情的重塑中,她本就隐潜着的女性意识觉醒了。她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妈妈型的女人,她会爱孩子胜过爱自己,却不会为孩子放弃自我;她渐渐厌倦当个完美的女主人,废除了会客的惯例,对于家事也不再上心。她自己摒弃了“天使”般的地位,于是无可置疑地成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所论的第二类型的女性形象——怪物(monster)*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p.20.。按照庞德里耶先生的描述:“她行事不太正常,很古怪,不太像她原来的自己。”(p.96)艾德娜最终在看不见希望的迷茫和压抑中投身大海,是拒为天使的女性命运的缩影,是对父权话语强烈的控诉。
其三,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物的社会地位。根据西方创世神话,最早的人类是男人,女人来自于男人的肋骨。所以,“人就是指男人。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自身去定义女人,而把女人看作自身的相关物;她,不被当作自主的存在(autonomous being)”;而且,“女性的身体结构本身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思考自身,而没有男人,女人则无法考量自己”*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p.6.。于是,女人附着在男人身上,和房子、金钱、权位一样成了男人的所有物。
《觉醒》特别描述了这样的两性关系:艾德娜和罗伯特游泳归来,庞德里耶先生看着艾德娜晒黑的手臂,如同看着被破坏的财产,心疼地说:“你晒得不成样子了。”(p.3)这段的叙事角度和话语安排,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言外之意:丈夫把妻子视作自己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关心的表象之下暗含责备。由此透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不难发现丈夫的地位明显高于妻子。毋庸否认,综合作品的全部细节,庞德里耶先生谈不上一个跋扈的丈夫,他有他的胸怀、容忍和体贴。但是,这些表象不能掩盖夫妻间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当艾德娜疏于理家,庞先生非常气愤,指责艾德娜:“我以为,作为一名女主人、孩子的母亲,整天呆在画室里太有失体统了,你该用这些时间给家里做点儿什么。”(p.83)艾德娜痛恨这样的关系,她渐渐下定决心“除了自己之外她不再属于其他任何人” (p.116),即便面对她日思夜想的罗伯特,她也大声地宣布:“我已经不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之一。我自己会选择我想要的”。(p.156)然而,她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所触怒的,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还有她的父亲:“‘里昂,你太宽容,实在太宽容了’,上校说,‘需要强制,行使权威。行动要坚决、果断,这是唯一的驭妻之术。相信我的话。’”(p.104)这个时候,上校的身份并非是一个女儿的父亲,而是一个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一个曾用自己的霸权将妻子过早地送进坟墓的男权主义者,他所考虑的也并不是女儿的幸福,而是自古以来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的特权:女人,作为附属于男人的存在,是一定要听话的。
二
时光之河浩浩汤汤,裹挟而去的,不仅有艾德娜心有未甘的灵魂,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女性主义思潮萌生于18世纪末,历时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改善,艾德娜们所为之斗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已经成为女性的基本权利。不再从属于男性的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在各个领域追寻着自我的价值。然而,她们是不是已经摆脱了“他者”的地位、成为社会的主体了呢?
徐小斌是当代中国富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她这样阐述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当我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我才深感伍尔芙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女人境遇的透彻……令人震惊的是,伍尔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统治仍未有丝毫改变”*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她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双鱼星座》为我们解读当代社会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和女性“他者”地位提供了范本。
《双鱼星座》的副标题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讲述了出生于双鱼星座的电视台剧作家卜零耽于幻想、渴望被爱、抗拒低俗,最终在男权社会金钱(由卜零的丈夫韦代表)、权利(由卜零老板代表)、欲望(由石——韦的司机、卜零潜意识中的情人代表)的围剿中伤痕累累,只能在假想中实施完报复之后,前往佤族山寨,于原始社会形态中寻求慰籍的故事。她在家庭、社会中的种种遭遇与百年之前的艾德娜遥相呼应甚至更有过之。
首先,从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角色来看,卜零生活的年代,距离伍尔夫发出“杀死房间里的天使”的号召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七十年的时间足以把女性赶下天使的神坛,却不足以卸下女性身上沉重的家务负担。
韦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早出晚归”,家务自然是无暇负担的。“卜零努力做个好妻子。每天离丈夫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她就开始剥丈夫爱吃的豌豆,……指甲都染成了绿色”*徐小斌:《双鱼星座》,见雷达、赵学勇等编:《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篇小说卷(下)》,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31页。为行文方便,本文引自该书的内容此后只在文中注明页码。。卜零的辛苦似乎没有白费,韦把吃卜零炒的菜作为一种享受。于是,久而久之,做饭也就成了卜零的义务:“偶尔卜零没有按时做好饭,韦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②;连买一点儿菜,韦也认为是在承担卜零的工作:“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给你买了你还挑三拣四”②。有了固定的家务分工,卜零是不能偷懒的,正如艾德娜疏于理家会被丈夫责备一样,卜零因为玩游戏没有烧水,韦“忍无可忍地大吼一声:这日子没法过了!!呼啸着便上来抢游戏机。那个长方形的黑色机器最终被摔成了碎片”。②
卜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在法律上和丈夫韦无可置疑地享有同等的权利。较之百年以前的艾德娜,她的境遇理应强上许多。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家务仍然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她已然承担了自己的那份社会分工之后。卜零的遭遇并非个案。香港学者於嘉在参阅很多国内外数据之后得出结论:“在家务分工这一领域,男女的差距仍然很大,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即便在男女平等水平很高的福利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不及女性的一半”。*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社会》2014年第2期。对此,倪志娟曾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是从男性的利益出发的,认同所谓的贤妻良母,女性只能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性。当女性希望建立自己的事业、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时,她的主体性价值与她的社会性别价值就处于矛盾之中:她在事业上越成功,获得的主体独立性越大,她就越失去作为女性的价值——因为她的性别价值是依附于男性的。”*参见李丹:《女性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反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恩格斯曾经说过,“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大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9-160页。。卜零以及很多现代女性的遭遇告诉我们,“房间中的天使”仍然是架在很多女性身上的重轭,“妇女解放”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不但如此,因为今日女性承担着更为多元的社会角色,“妇女解放”也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其次,就经济地位而言,毫无疑问,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女性终于赢得了几乎等同于男性的工作机会。她们在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用自己的肩膀坚强地分担着家庭的经济负担。然而,社会上隐性的经济歧视不但是难以回避的事实,而且理论上已经自食其力的女性,在极端情况下,很有可能失去男性在经济上的同情和支持。
卜零和艾德娜有很多相似,其中一个就是她们都嫁作商人妇,而身为商人的丈夫在家庭经济上都拥有实际的掌控权。有所不同的是,庞德里耶先生生活在女性基本没有经济来源的十九世纪末,他有承担女性生活的自觉,并把这作为男人权利的体现。在这种观念之下,他愿意为妻子提供舒适的生活,买些礼物,给些零用钱。而韦生活在女性已经承担50%的社会分工的二十世纪末,男人承担妻子的费用在他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韦自从进入大公司以后不再把薪水如数交给老婆,只有在高兴的时候给老婆一点零花钱。”(p.625)卜零作为大老板的妻子,在别人眼里生活优渥,实则连乘火车都只能乘最慢的列车,“仅仅是因为它最便宜”①。最后,卜零无法迎合低俗丢了工作,韦大发雷霆地宣称:“告诉你,你要是想让我养门都没有!我没有这个义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p.643)女人赢得经济的独立是历史的进步,但由此而失去夫妻间在经济上的相互扶持是匪夷所思的。以女性独立为由拒斥夫妻互助,实则是维护男性话语权,其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要独立吗?好,我们不管你们了!
于此,卜零的状况或者并非普遍,但暴露出的两性关系的某些方面、或者男权思想的某种残留仍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女性的经济能力直接影响夫妻关系中她们的幸福指数,恰如吴帆所证,“女性的收入水平越高, 其在家庭中的平等状况及感受就越好”*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
再次,从两性情感的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女性不承担复杂的社会职责。料理家务、相夫教子,便是世俗标准下的贤妻良母,拥有社会舆论的支持。恰如《觉醒》中人们在评价起阿黛尔·拉提诺夫人时说,“要是她的先生还不懂得怜香惜玉,那真是禽兽不如”*Kate Chopin, The Awakening, p.11.。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物质文化、功利主义的渗透无所不在。置身其中的女人想在男权社会中获得认可,事夫理家自是其中之一,而社会角色扮演得成果与否,将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丈夫对妻子的定位。卜零是以文字为业的剧作家,在韦眼里,这一职业曾经分外神圣。然而,当他发现冷俊孤傲、不合世俗的卜零不能用文字换来任何实惠的时候,妻子在他眼里成了最为贫弱的女人,他对她的轻视,渐渐渗透到骨子里,觉得她远不如欢乐场里的轻薄女子,至少“她们懂得最简单的交换价值”(p.604)。从此,卜零生活在冷冰冰的房子里,丈夫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懒得看卜零一眼。在韦眼里,卜零完全化作了一团空气,连做爱,也像帝王临幸一般的,要在日历上记上记号。冷漠的生活里,卜零觉得自己成了一条冻僵的鱼。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思想独立如卜零可能为男性所不屑或顾虑,而如莲子(石的情人)般“无知无能”、“似水柔情”,只会乖乖地依偎在男人怀里说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p.638)的女人却能获得石的承诺。莲子所满足的,正是男性对女性的千载不变的控制欲;她所迎合的,正是男性在当代社会毋庸置疑的话语权。
第四,女性的社会角色。家庭内部的男性话语权,实为社会范围内男权话语本质的衍射。在今天的社会,虽然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劳动,但在社会分工之中并不占有同等的权利。数据显示,因比男性更多的受累于家庭,女性的就业空间相对狭小,在就业市场也受到较为普遍的歧视*据李丹在《女性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反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提供的数据,“在工业化国家,工薪部门中妇女所领工资平均为男子的77%,在发展中国家则为73%。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的行情仍然很普遍”。参见《福建论坛》2007年第2期,第127-131页。。而即便女性和男性同样获职于某单位,在同等条件下,男性也比女性有更大的升值空间。加之历史上的原因,职场上的领导多为男性,规则多出自于男性。由此,社会生活中,女性也处处处在男性的话语势力范围之下。
卜零的领导是一位中年男性,一开始对卜零颇为重视:“老板刚刚调到市台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卜零”,因为这个女人“从整个表情和体态充盈着一种生动和妩媚”(p.640)。但是,“在影视圈美女如云围绕着老板每天都给老板打饭、打水、清扫办公室乃至做各样的事情”(p.640)的形势下,卜零竟好像视老板为空气。她不但不迎合领导,还时常让领导“扫兴”、“下不来台”。当卜零被安排到一个六集戏里有三次强奸的剧集时,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这个剧的轻蔑;当老板扭曲事实嘲笑剧作家只为活跃会议气氛时,卜零竟公然指责老板“不顾事实”和“伤害别人”。于是,卜零被老谋深算的老板拉来当剧集被撤的替罪羊、被老板像“押送进屠宰场的一只小牲口”一样地拉着去献血、最后被开除公职的结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总结老板的形象,低俗、市侩、虚伪是最恰当的词汇。中年的、大腹便便、老谋深算的他,也成为了职场之上男权话语的代表。固然,并非所有的男性领导都如此般,但男权话语的强势和顽固,确是合了老板的形象。
三
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和西方女性文学作品及理论的译介密切相关。学界公认,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以二十世纪80年代朱虹在《世界文学》上对美国妇女文学的译介为起点*魏天无,魏天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历程及其问题》,《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而“90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熏陶和影响”*杨绍军,郭健斌:《论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徐小斌长期订阅《世界文学》杂志*宋伟杰:《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6期。,虽未有证据表明她读过《觉醒》或凯特·肖邦的其他作品,但她熟谙波伏娃和伍尔芙的女性主义观点的确是可以得到明证的*徐小斌对波伏娃和伍尔芙的观点都有明确的引用。参见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第45-48页。。所以,《觉醒》和《双鱼星座》有诸多契合时便不足为怪了。
从文学分期上看,《觉醒》创作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时期,手法写实,语言质朴;而《双鱼星座》创作的年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技法已为中国作家熟悉和借用了。所以,《双鱼星座》的情节设计和语言展现带有更多的超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发现二者之间诸多的相似。比如,就人物设置而言,两部作品都存在一个懦弱的、不敢承担的男性:罗伯特和石;就情节设计而言,两部作品都以第三者恋情影射女性爱情理想的幻灭;就人物命运而言,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深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压迫而选择逃离:艾德娜逃向死亡,卜零逃往佤寨;就艺术手法而言,两部作品都有明显的身体叙事和自然意象。但是,二者主题的承续性最具文学史的深意。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质上属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范畴。对女性“他者”地位的揭示,是女性文学所长期致力的,也是女性主义文学可直接贡献于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主题。对《觉醒》和《双鱼星座》中所描述的女性“他者”地位的比较,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历史视角的承续和变迁关系。
首先,当代社会环境下女性社会地位的“他者”本质更为隐性。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女性无工作、无收入,附属于男性,碌碌于家务,自我泯灭,生活枯燥。此时,男性强权话语对女性的统治和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社会,女性有工作、有收入,她们在名义上已经取得了与男性相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她们所面对的问题是:(1)从属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主要由男性制定的社会显、隐规则;(2)受制于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和一百年前的境遇比较,当代女性所受到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更趋隐性,更趋无形,更难把握。
其次,女性斗争的对象依然强大却不清晰。不论百年前的艾德娜还是百年后的卜零,为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权益都进行了斗争。一百年前艾德娜的斗争目标是明确的:经济独立,爱情自主,思想自由。然而,一百年后,似乎已经赢得了所有的这些的卜零仍然深陷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她想斗争,却几乎不知该如何斗争、和谁斗争。男性话语权对她的笼罩和制约似乎是无所不在的,但却那么模糊,那么不具体。所以,相比艾德娜,她的斗争消极而被动,她的结局也体现了更为彻底的迷茫、失落以及无助。
比较百年以来女性的境遇,我们首先得承认,由显性而隐性、由明确而迷茫,本身即是一种进步,至少说明女性主义运动已经实现了其有形的目标。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女性争取两性平等、和谐的努力依然任重道远。
余 论
乐黛云曾说,文学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划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和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女性主义文学,实属总体文学的一个分支,因其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而具有世界性。对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觉醒》和《双鱼星座》的比较阅读,使我们对女性“他者”地位的过去和现在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在实现比较文学互补、互证、互识的功能的同时,也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世界女性主义运动及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以期实现两性和谐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