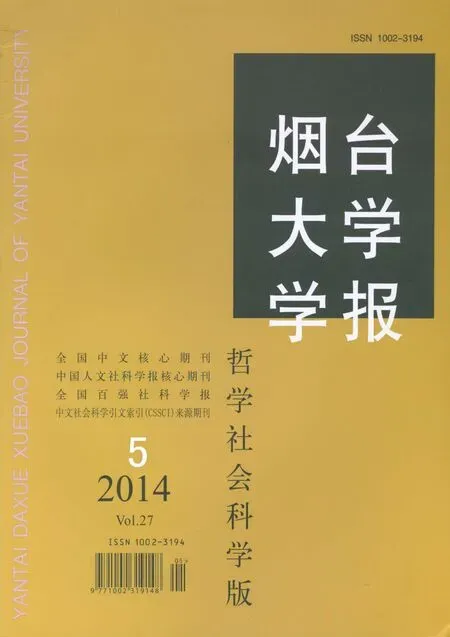论韩国中世纪小说中的梦
尹允镇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梦是中世纪小说中常见的一种文学现象。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中世纪梦小说很多,如《红楼梦》和《神曲》可谓是代表东西方中世纪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而这两部作品恰恰就是写梦的。在韩国中世纪小说中,以《九云梦》、《玉楼梦》为代表梦小说非常多,所以在韩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有关“梦字类小说”和“梦游录”的也不少。①孙慧欣、吴伊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参见孙惠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吴伊琼:《韩国汉文小说〈玉楼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受容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但是为什么韩国中世纪小说经常使用梦,它在小说中起到什么样的艺术作用,为什么中世纪作家经常以梦的形式写小说等关键性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文学,尤其是东方小说经常采用梦的形式?固然这里有众多原因,但笔者认为与中世纪作家对小说的理解和小说的本质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结合韩国的古典小说,阐述梦在中世纪小说中的作用。
一、梦与韩国中世纪小说
和梦有关的韩国中世纪小说有两种,一是“梦字类小说”,二是“梦游录小说”。所谓的“梦字类小说”指的是以梦的形式描写现实的小说,它整体框架是梦,框架内描写的是现实,其代表性的作品有金万重的《九云梦》、南永鲁的《玉楼梦》、李庭绰的《玉鳞梦》、宕菴的《玉仙梦》等;梦游录是以梦游的形式,描写梦中所见所闻的小说。梦游录在虚幻或梦形式的采用上和“梦字类小说”没什么两样,但“梦字类小说”写的是现实生活,梦游录写的是梦中的事,代表性的有沈义的《大观斋梦游录》、申光汉的《安凭梦游录》、林悌的《元生梦游录》、尹继善的《达川梦游录》、李渭辅的《何生梦游录》等。
“梦字类小说”和“梦游录小说”的区别,还表现在小说的结构上。一般地说,“梦字类小说”采用“入梦——梦中——觉梦”的格式,其核心内容在“梦中”部分;“梦游录小说”采用“入梦——坐定——讨论——诗宴——觉梦”的形式,核心内容是“讨论”和“诗宴”部分;“梦字类小说”采用“从理想界到梦幻中的现实界再回理想界”的循环结构;“梦游录”采取“从现实界到梦游中的理想界再到现实界”的循环结构。换言之,从作品主人公的角度讲,“梦字类小说”采用的是“现实界——理想界——现实界”,从读者的角度讲是“理想界——现实界——理想界”;“梦游录”则采用“现实界——理想界——现实界”的格式。但无论是“梦字类小说”还是“梦游录”写的都是梦,和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都采用梦的形式表现作者的某种理想,在这一点上可谓这两种小说都属于梦小说,可以从梦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韩国与梦有关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九云梦》。据传这是金万重于1687年在流放期间为母亲创作的。作品描写一个叫性真的佛门弟子做梦到现实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后觉梦,认为人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春梦,从此他真正皈依于佛教的故事。后来这部作品介绍到中国,以《九云楼》流行于清朝。据王文元的考证,《九云梦》传到中国后,对《红楼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梦小说’热滥觞于《九云梦》。如果说《九云梦》是朝鲜‘梦小说’的开始,《玉楼梦》、《玉莲梦》等则是受《九云梦》影响而创作出来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受到《九云梦》的很大的影响。”*参见金万重:《九云梦》序,王文元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可见,《九云梦》在韩国的梦字类小说乃至整个东方中世纪小说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它常被文学史家誉为韩国梦字类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在韩国文学史上这不是第一个写梦的作品,第一部描写梦的是《调信的一生》,这部作品收录在《三国遗事》中。讲述调信爱上了金昕公的女儿,经常到寺院祈求与她结良缘。但几年后这个女人却嫁了别人。调信“又往堂前怨大悲之不遂己,哀泣至日暮”,累了小憩一会儿,结果睡觉做了个梦。梦中调信和金昕公的女儿结婚,50年岁月生了五个孩子,但生活极为贫困,以至于大孩子饿死。调信最终忍受不了这种悲惨的生活,要与金昕公的女儿分手,但临分手时他的梦醒了。之后调信“及旦鬓发尽白,惘惘然殊无人世意,已厌劳生,如饫百年辛苦,贪婪之心,洒然冰释,于是惭对圣容,忏涤无己”。作品结尾处作者写道:“读此传,掩卷而追释之,何必信师之梦为然,今皆知其人世之为乐,欣欣然役役然,特未觉尔。”很显然,这是宣扬人生苦海、人生如梦等佛家思想的作品,和后来的类似作品在思想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综观这部作品很难说是小说,但它的情节结构、虚构的故事、细节描写、叙述方式等方面,已经接近了小说,具备了准小说形态。
与梦小说稍有不同,但具有梦游录形态的还有林悌的《元生梦游录》。作品描写一个叫元子虚的儒生梦见“死六臣”,讨论国家现实政治的故事*“死六臣”:1456年成三问等人反对李世祖篡权,掀起了端宗复位运动。但这个运动失败,成三问、朴彭年等六人送了断头台,这六人叫“死六臣”;金时习、南孝恩等六人虽然有罪,但没有死,这六人叫“生六臣”。李世祖,名瑈,字粹之,世宗的二儿子,他于1455年用武力篡侄子端宗的位,当了朝鲜朝第七代王。由于他篡的是侄子的位,深受朝野上下的反对。他为了巩固王位,实行暴力,残酷镇压反对派,“死六臣”就死于他手下。。在作品中,元子虚和“死六臣”谈论国家大事,认为国家动乱的原因在于李世祖的残暴和他的独裁政治。很显然,这部作品是为反对李世祖的暴政而写的。除此之外,李奎报的《梦验记》、金时习的《南炎浮州志》、南孝温的《睡乡记》、沈义的《大观斋梦游录》、尹继善的《达川梦游录》等作品中都有梦。这说明《九云梦》出现之前,韩国已经有过不少与梦有关的作品。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九云梦》就沿袭了这些作品,但应当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作品中的宝贵的艺术探讨,《九云梦》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九云梦》是韩国古典梦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作品,在梦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正因为有了《九云梦》,才有了后来梦小说的一度繁荣,出现了《玉楼梦》为代表的许多梦小说。
二、韩国梦小说和中国文学的关联
韩国中世纪梦小说,不仅和韩国小说史前时期的叙事文学中出现的梦有关,而且还和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梦也有关系。
中国文学中的梦由来已久。《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子梦蝶”就是非常著名的与梦有关的作品。到汉代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和谶纬迷信之说,为志怪小说和梦小说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春秋战国到汉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梦或者说是充满虚幻、梦幻的作品,尤其是到唐代出现了《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等与梦有关的作品,为后来的梦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传播也为志怪小说和梦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论这一时期的小说时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大家知道,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引起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成为他们奴化社会的精神工具。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纷纷崇佛奉法,同时大力建寺造像,百姓也跟随迷信佛法,争相出家。据统计,西晋时期仅在洛阳、长安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人;东晋时也立寺1768所,僧尼24000人。*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225-226页。佛教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给小说在内的文学也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小说在汉代的神仙方术和谶纬迷信之说的基础上,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宣扬人生如梦,人生不过是一场梦之类的佛教思想的作品。《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等就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佛教在中国占有如此巨大的市场,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平等观。佛教对人生的看法也给文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的人生如梦的看法对梦小说给予了重大的影响。从佛教的角度看,人生如梦,而梦是空的,虚无的,所以,人生也是空的,是虚无的。《维摩经方便品》说:“是身如梦,为虚妄见”,宣扬的就是这种观点。所以,佛教和佛经传到中国以后,与汉代以降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和谶纬迷信之说相结合形成了许多神乎其神的虚幻故事。唐代的梦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唐代以后,梦小说更是盛行。被誉为“临川四梦”的汤显祖的作品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俞达的《青楼梦》等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梦小说的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红楼梦》起于梦、止于梦,120回《红楼梦》共写了大大小小的梦32个,可谓是梦的集大成者。
但是,给韩国的梦小说给予重大影响的还是《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等唐传奇作品。《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等作品何时传到韩国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据《高丽史》记载,《文苑英华》和《太平御览》已在十一世纪前后传到了韩国。《高丽史》世家记载:“〔宣宗七年十二月壬辰〕宋赐《文苑英华》集”;卷十一世家、肃宗条也有这样的记载:“〔肃宗六年六月辛卯〕……帝赐王《太平御览》。”宣宗七年是公元1090年,肃宗六年为公元1101年,《文苑英华》和《太平御览》分别在982年和977年编撰,那么,可以断定《文苑英华》和《太平御览》至少是在它编撰不过100年,11—12世纪之交已经传到了韩国,《枕中记》是随着《文苑英华》传到韩国的。
《太平广记》何时传到韩国尚不清楚,但估计仍是在这个时候。在韩国首次出现《太平广记》这一书名的是《翰林别曲》。据《高丽史·志·乐二》记载:“《翰林别曲》……唐汉书、庄老子、韩柳文集、李杜集、《白乐天集》、《毛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太平广记》四百余卷,伟历览景如何……。”高丽后期韩国流行叫京畿体的一种新的民族诗歌形式。这是一种多个人围绕着一个主题,一人造一节,唱一节的具有游戏娱乐性质的诗歌,反映了贵族阶层的休闲娱乐生活。《翰林别曲》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和其他京畿体诗歌一样,它反映着当时贵族阶级的生活。作品列举了当时儒生主要攻读的各种书籍,诗歌中的“伟历览景如何”是韩文的助兴句。由此看来《太平广记》也是当时儒林中非常流行的一部书籍。从《高丽史·志·乐二》记载看这是高丽高宗时期(1214-1259)的事情。那么,这说明最晚这个时期《太平广记》已在韩国广泛流传。从《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传到韩国的情况看,《太平广记》也在11—12世纪之交已经传到韩国,成了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之一。*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传播情况参见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
不仅如此,到十五世纪成任(1421-1484)还编撰了《太平广记》节本,起名为《太平广记详节》。《太平广记详节》分143项,收录843篇作品。这是由于《太平广记》太庞大而缩编的,所以篇幅大约为《太平广记》的十分之一,但《太平广记》中的主要作品基本都收录在其中。而后成任仿造《太平广记》自己又编撰了一本韩国版《太平广记》,叫《太平通载》。《太平通载》是成任根据中国和韩国的许多古文献编撰的。据有些学者的推测,《太平通载》应是240卷,80余册,但现存的只有五卷2册。但从现存的五卷2册看,成任编《太平通载》时,借用的古籍不仅有《三国遗事》、《高丽史》、《新罗殊异传》等韩国的古文献,而且还有中国的《史记》、《晋书》、《元史》、《战国策》、《列异传》、《剪灯新话》、《东波文集》等,而其中就有《太平广记》、《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作品集。*《枕中记》收录在《文苑英华》中;《南柯太守传》收录在《太平广记》里。这一切充分证明韩国的梦小说,包括《九云梦》在其创作过程中,应受了中国梦小说的影响,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学家金万重想必读过这类小说。由此可以说,韩国的梦小说在其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了自己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吸收了中国的志怪、传奇、话本小说的丰富营养。
三、中世纪作家对小说的理解和作为艺术装置的梦
如前所述,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的梦小说都与佛家的空思想、人生如梦等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点王文元有精彩的阐述。他认为佛教总把人生比作梦的原因在于“梦是空的,人生也是空的,二者有惊人的一致性”。在谈论作家常用梦的原因时,他在叙述《弥兰王问经》中做梦的六种原因后,指出:“佛教认为,只有因前兆所产生的梦为真,其他皆是虚妄。虽然前兆之梦只占梦的六分之一。*指的是《弥兰王问经》中所说的六种梦,前兆是这六种梦当中的一个,所以他说这是六分之一。但总说明梦还存在有一丝真实的可能性,所以文人墨客就利用这一点,让自己的作品通过梦,来隐喻某种结果或结局,而且不至于让人攻讦为妄说。如果把梦理解为‘前兆’,那就不是梦语,而是真言,从而产生感染力。”*金万重:《九云梦》序,王文元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就是说,在文学作品中,梦从艺术表现方式来说是一种隐喻的手法;佛教或者是事件的前因后果来说是一种“前兆”,具有佛经上经常说的前因后果逻辑形式;其结果来看,梦可以转化为“真言”,产生艺术感染力。很明显,在这里王文元从多个方面解释文学中的梦,为进一步深入解释中世纪小说中的“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
但是,中世纪文学中的梦和它的作用不止于这里。换言之,中世纪小说中的梦,不仅有“隐喻”、“前兆”等功能,而且还和中世纪作家对小说的理解和小说作为特定的文学体裁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中世纪作家是如何理解小说的呢?韩国中世纪作家对小说的理解大体上和中国相同,那么他们是怎么理解小说的呢?
在中国“小说”一词首见于《庄子·外物篇》,但它和后来所说的小说略有不同。在中国开始谈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是桓谭和班固,其中班固的观点影响很大。他在《汉书·艺文志》中不仅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等微薄之词谈论小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诸子十家中,把小说家列为十家之末尾,认为可观的只有九家。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成为中国人的典型的小说观,小说一直属于“别乎大言”的“杂类”、“琐言”、“异闻”之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有甚者,把小说看作“诲淫劝杀”的东西加以排斥。清代著名的汉学家钱大昕说:“……演义盲词,日增月益,诲淫劝杀,为风俗人心之害,较之唐人小说,殆有甚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页。韩国也是这样。他们一直把小说看作是“杂类”,或者是“余技”加以排斥,更有甚者,把它看作“作奸诲淫”的东西。李德懋就说:“演义小说,作奸诲淫,不可接目,切禁子弟,勿使看之”。*李德懋:《小士节》。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不仅有小说性质的角度评价小说的,而且还有从小说的功能、表现技能等方面评价小说的观点。
在中国,汉代桓谭对小说的看法就是与众不同。他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新论》,转引自《文选》卷三十一。其实,这是小说的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其中的两点颇引人注目。一是“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二是“近取譬论”。前者是试图从“治身理家”的角度把握小说,想给小说赋予作为正统文学的应有地位;后者是从小说的艺术功能上解释小说的。前者符合以伦理道德为主要价值观念的中国社会现实,是迎合不折不扣地把伦理道德价值为最高艺术标准的社会的方式;后者是从“比喻”的角度,即小说的表现手法的角度谈论小说特点的。后来到宋代,洪迈称小说为“一代之奇”,*洪迈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洪迈:《容斋随笔》,参见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页。到明清时期李卓吾、袁宏道、金圣叹等人把小说推奉为正统的经史之上,由此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韩国,小说的地位从17—18世纪开始有了一定的变化。金春泽在评价金万重的《谢氏南征记》时,认为小说有可观之词;李颐淳也认为小说“语皆鄙俚”,但《谢氏南征记》、《感义录》等数篇,有感人之处;李养吾等人也留下了类似的话。*尹允镇:《朝鲜现代小说艺术模式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6-17页。尤其是李颐淳对小说的评论颇有精辟之处,他说:小说“虽出于架空构虚之说,便亦福善祸淫底理。”*晚窝翁:《一乐亭记序》。在这里,李颐淳把小说看作是“架空构虚之说”,很显然,这已经接近了小说的本质——虚构,就是想从虚构的角度,把握和理解小说。大家知道,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但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小说描写的不一定就是真事,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编造的故事。即使是写真人真事,也要虚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虚构是小说的根本,没有虚构就不是小说,有了虚构才是小说。西方把小说称为“fiction”,就是抓住了虚构这个小说的本质属性的。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也是从虚构的角度理解和解释小说的。班固所说的“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小说不是描写真人真事,小说里的故事是人们编造出来的。班固以后,也有人从“正史之馀”*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第12页。、“史之支流”、“稗官野史”*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第27页。等方面阐释小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小说写的不是真人真事,而是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故事。古典文人对小说的这种理解很重要。这一方面使他们把小说从记录真人真事的历史分辨出来;另一方面他们也探讨有别于这些记录真人真事的另一种记录方式。梦就在这样的艺术探讨中进入文学高雅之堂的。
古典作家也常寻求与历史、与真人真事不同的记录方法。他们也朦胧地意识到小说的根本在于虚构。如果说,虚构是编造故事的最好方法的话,那么他们认为梦也许就是编造故事的一种最佳形式。梦区别于现实,它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即使是梦里发生的事与现实中的事情毫无两样,但是这毕竟是梦里发生的事情,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就这样梦常被作家使用,逐步成为表现虚构故事的一种艺术装置。在中国这些观念与佛教的传播更加兴盛起来,出现了唐传奇为中心的大量的梦小说。在韩国,这种理解与作家理解的小说相吻合,出现了大量的梦小说。
总之,韩国的中世纪梦小说受自己的文学传统和中国文学的影响,再加上人们对小说的理解,梦作为小说艺术的一种艺术装置广泛使用的。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小说观念的流入,以及人们对小说艺术的深入理解,这种小说样式也随之消失,小说进入到与世界文学并轨携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