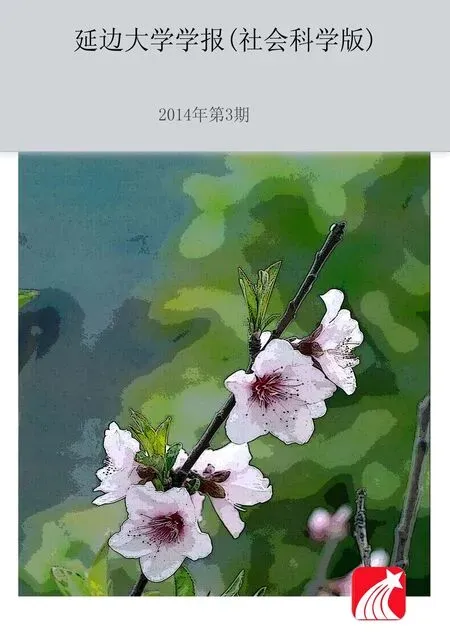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
张振亭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 133002)
“诗话”是肇端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论诗文体。狭义的诗话,是指诗歌的故事、随笔等,以条目的样式呈现,针对某一具体诗歌现象直接发表评论,内容长短不限,形式灵活而自由,如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韩国高丽时期李仁老的《破闲集》等;广义的诗话,是指诗歌鉴赏与诗歌批评的著作形式,如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韩国李朝时期徐居正的《东人诗话》等。中国特有的诗话批评样式萌芽于魏晋钟嵘的《诗品》,成熟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后又流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东方汉文化圈内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样式。
作为韩国古代文学批评最主要、亦是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的韩国古代诗话,它也是韩国古代美学思想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因此,探究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是追觅韩国古典美学与韩国传统文化特性的一条有效途径。从韩国历代诗家论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造、文学文本的构筑以及文学的鉴赏与批评等一系列批评话语中,我们都可以深切地感受与体验到激荡于其中的绵绵不尽的美学意蕴。
所谓美学意蕴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而是一个存在论的范畴。由于属于存在论范畴,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它在衍生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审美活动中的当下体验。可以说,美学意蕴的发生是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在凝视对象的刹那间形成的一种感性直观的印象,是主体与审美对象交互运动的结果,是主体的感悟与对象的诸种审美素质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感应关系后而衍生出来的综合性的审美效应,或者说,美学意蕴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总体审美效果。
我们说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是指韩国古代诗家在以诗话体式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偏重以自我的直观体悟为主,其话语的呈现往往留有诸多空白,这空白极大地拓展了接受者的想象空间,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审美张力。由此可见,美学意蕴的发生,是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的,进一步说,是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而言的。离开了人的主体性,离开了主体的生命体验,美学意蕴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的空谈。因此,我们在此究思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即是体验其中潺潺流淌着的脉脉的人文情怀。
韩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的文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韩国古代诗话的一个突出品格:就是以彰显人的主体性,特别是主体的活生生的直观生命体验为主。事实上,韩国古代诗话批评在展开的过程中,也时刻遵循人文一体、品诗如品人的理论传统。也就是说,韩国古代诗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习惯于把诗歌的生命当做诗人的生命来看待。由此,他们认为透过诗歌的生命体征就可以直接感知到诗人的生命体征。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本身就带有浓浓的生命的味道,呈示出某种生命的情调或人生境界,体现了某种蓬蓬勃勃的生命律动,给人以绵延不绝的美感体验。
综上所言,我们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悟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
一、生命情调或人生境界的诗意呈示
清代诗家刘熙载在《艺概》中鲜明地指出“诗品出于人品”,这不仅是中国古代诗家的一种普适价值,也可以说是整个东方诗学的一个传统。韩国古代诗家无疑也秉持了这样的理念,他们在进行诗歌批评时自然而然地将诗与诗人融为一体综合考虑。由于擅长透过诗歌的中介追觅作为主体的人的气息,因而使其诗歌批评浸透着某种生命的情调或揭示了某种人生境界。诗即其人,这也是韩国古代诗话的一个普遍的价值取向。这种情形在韩国古代诗家的诗话批评中随处可见。南孝温(1454—1492)在《秋江冷话》曾言:
得天地之正气者人,一人身之主宰者心,一人心之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精且清者诗。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商周之《颂》、桑间之《风》是也。然太古之时,四岳之气完,人物之性全。樵行而歌吟者,为《标枝》、《击壤》之歌;守闺而咏言者,为《汉广》、《摽梅》之诗;初不用功于诗,而诗自精全。自后人心讹漓,风气不完。《风》变而《骚》怨,《骚》变而五言支离,五言变而律诗拘束。汉而魏晋而唐,浸不如古矣。虽以太白、宗元为唐之诗伯,而所以为四言诗者,所以为《平淮雅》者,犹未免时习。视古之稚人妇子,亦且不逮远矣?是故士君子莫不于诗下功焉,如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子从“三上”觅之。而晚唐之士,积功夫或至二三十年,始与《风》、《雅》仿佛者,间或有之。夫岂偶然哉?[1]
“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表明南孝温把诗看做是人的本真心灵最真实的外化映射,由诗品可以直观人心的正与邪。这种以人为本、以人的品性为准的的伦理化诗歌批评趋向,使得韩国古代诗话批评到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人性论色彩。“得天地之正气者人,一人身之主宰者心,一人心之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精且清者诗”,意即由诗可察人言之精清否,由人言之精清可观人心之善恶,由人心之善恶可品人之德行高下,这让我们感觉到韩国古代诗家仿佛并不特别看重诗的文学性,而是把诗作为探讨人性、评判人心、追求理想人格的一种手段。因而,在韩国古代诗家的诗话批评中常常流露出某种人生的意绪。朝鲜朝诗家李德懋(1741—1793)在其《清脾录》中言:
读是诗者,净室洁席,焚香而玩,可得其趣。亦于古松、流水之侧,高吟朗诵,与松声、水音共具琤琮清冷之韵。甚至欲起舞,或恐舞而仍飞去也。[2]
有超世先生,万峰中雪屋灯明,研朱点《易》。古炉香烟,袅袅青立,空中结彩球状。静玩一、二刻,悟妙忽发笑。[2]
李德懋认为鉴赏诗歌前需先“净室”、“洁席”、“焚香”,即首先要营构一种怡神、益气的情绪氛围;如果在室外阅读,则主张应在“古松、流水之侧”,伴随着“松声”、“水音”高声吟诵,兴之所至,甚而手舞足蹈。只有这样,方可领悟诗歌之妙趣,才会“悟妙忽发笑”。这种欣赏诗歌的方式,既体现了鉴赏者的某种生命情调,它本身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种情调、这种境界并不是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是以隐喻的形式,需借助接受者自由想象和联想的心理机制,才能体悟到蕴藉于其中的意味。这样的诗歌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美感体验的召唤形式,蕴涵着绵绵不绝的美的意蕴。
韩国古代诗家在诗话批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蕴藉了某种生命的情调或某种人生的境界,使诗话批评与人生感悟有机融合,鉴赏诗歌虚幻之美的同时也在体悟着现实人生的某种意义,因而赋予诗话批评以无限的审美韵味。这是韩国古代诗话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悠远缥缈的美感
生命的情调与人生的境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性体悟,它本身就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动态境像,不可能言语道尽。因此,在诗歌批评的过程中,需要借助“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隐喻手法呈现出来。所谓的隐喻手法相当于古人常言的“含蓄”,韩国古代诗家洪万宗(1643-1725)认为,“凡为诗,意出言表,含蓄有余为佳。若语意呈露,直说无蕴,则虽其辞藻宏丽、侈靡,知诗者固不取矣”。[3]诗歌创作以“含蓄有余”为佳,切忌“直说无蕴”。诗歌批评亦然。许筠(1569—1618)在《惺所覆瓿稿》亦云:“诗之理,不在于详尽婉曲,而在于辞绝意续,旨近趣远,不涉理路、不乐言筌为最上。”[4]“辞绝意续,旨近趣远”强调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批评都要讲究含蓄蕴藉之美。
在诗歌批评的过程中,含蓄或隐喻手法的运用就会使得生命情调与人生境界的生成呈示为一个气韵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延长了人们感受和体验美的时间;境界情调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方式呈现,又造成了人们接受时的距离感。这种时间上的延宕感与空间上的距离感,就使得诗歌批评带有一种缥缈悠远的动态美感。这样的美感无疑是由其美学意蕴所带来的。这种状况在韩国古代诗话批评中也随处可见。徐居正(1420—1488)在《东人诗话》中曾言:
李相国诗:“轻衫小簟卧风棂,梦断啼莺三两声。密花翳花春后在,薄云漏日雨中明。”陈司谏澕诗:“小梅零落柳丝垂,闲踏清风步步迟。渔店闭门人语少,一江春雨碧丝丝。”两诗清新幻眇,闲远有味,品藻韵格如出一手,虽善论者未易伯仲也。[1]
徐居正面对这两首诗,鉴语简小,韵味无穷,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闲远”是就其状态而言,属于视觉范畴;“有味”指其审美效果,属于味觉范畴;“韵格”则指其音律,属于听觉范畴。短短数语,竟充分调动了视、听、味诸种感觉共同参与,最后才形成其总体印象:“清新幻眇”。这一方面体现了批评者高超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它也会有效地使接受者的诸种心理功能充分活跃起来,参与其中,对诗话文本进行二度创造。这样,整个鉴赏活动和接受活动都将具有一种无以释怀的生命张力,给人一种挥之不尽的、连绵杳渺的美感体味。在此,诗歌鉴赏的过程实际上已转化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方式,诗歌样式无疑成为了人之生命的某种隐喻,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文学具有了感化人心的巨大张力。
这种悠远缥缈的境界,其实现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其话语表现方式常常是“含蓄蕴藉”式的。因为批评话语的“含蓄”,能够将似乎无限的意味隐含或蕴蓄在有限的话语之中,使“小”中蓄“大”,让接受者在有限的话语形式之中体味无限的韵味;批评话语的“蕴藉”,将会造成话语活动中多重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不同的接受者都能从中体验到精神的愉悦与个体生命的高度自由。这在韩国古代诗话批评中也是极为常见的,如洪万宗在比较韩国古代诗人张维、李植、郑斗卿的不同诗风时,就使用了含蓄蕴藉的批评话语:
谿谷(张维)文浑厚流畅,如太湖漫漫,威风不动;泽堂(李植)精妙透彻,如秦台明镜,物莫遁形;东溟(郑斗卿)发越后壮,如白日青天,霹雳轰轰。[3]
这段批评话语中的“浑厚流畅”、“精妙透彻”、“发越后壮”作为对三位诗人不同诗文风格的概括而言,都属于模糊性的批评话语,但模糊并不等于不知所云,无从谈起,也不会使人陷入不可知的境地。相反,它为接受者留下了更多的空白,提供了可以使读者率性涂抹的广阔无垠的诗意空间。批评者虽然以“太湖漫漫,威风不动”阐释“浑厚流畅”,以“秦台明镜,物莫遁形”阐释“精妙透彻”,以“白日青天,霹雳轰轰”阐释“发越后壮”,但这种解释虽没有说明诗歌蕴涵的感官样貌,反而使这种模糊性本身更具某种生命的韵调。这即是韩国古代诗话批评美学意蕴的最为生动、鲜明的呈示。
韩国古代诗家在诗话批评过程中,模糊性批评话语的大量使用,极大地增强了诗话批评之含蓄蕴藉的色彩,因而赋予其整个批评具有一种缥缈悠远的美感效应。这在韩国古代诗话批评中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三、蓬蓬勃勃的生命律动
韩国哲学会编的《韩国哲学史》指出:
风流意味着古代韩国人的一切文化与精神……在接受外来思想影响之前,支配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原理,即是风流的信仰。作为信仰外化形式的风流,在韩民族原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所以,以信仰作为基础的风流孕育了韩民族的主体文化力量。[5]
把“风流”思想视为韩国精神的原型。新罗文人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有言: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6]
把风流思想视为韩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中国学者李苏平在《韩国儒学史》中有言:“笔者认为,在韩国文化中,‘风流’就是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人们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神人一体观念……通过风流,使形而上的神(自然)的世界与形而下的人的世界相连结。在风流中,人们体悟到人类‘生命的根基’,是通过祖上的连结,最终都处于无限的自然之中。风流使人体验到生命的无限性,这就是风流思想的生命观。”[7]论者亦将风流思想看做是韩国古代的一种生命哲学。
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源于新罗花郎道的风流理念,使得韩国传统文化习惯于将大自然的生命力视为人间化的运动,进而在一切人类活动中都极力凸显人的主观作用与人的主体价值。由于以主体精神为核心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可以称朝鲜民族文化为主体性的文化。
朝鲜民族文化的这种主体性特质,逐渐积淀成为传统朝鲜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以“生”为大。这也决定了他们在一切的人类活动中都能体悟到生命的某种真义,处处洋溢着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律动,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中展示得最为明显。朝鲜民族文化的这一性质,在韩国古代诗话批评中表现得也特别突出,如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中有云:
白云子弃儒冠,学浮屠氏教,包腰遍游名山。途中闻莺,感成一绝:“自矜绛觜黄衣丽,宜向红墙绿树鸣。何事荒村寥落地,隔林时送两三声。”吾友耆之失意游江南,闻莺亦作诗云:“田家椹熟麦将稠,绿树初闻黄栗留。似识洛阳花下客,殷勤百啭未曾休。”古今诗人托物寓意多类此。二公之今作,初不与之相期,吐词凄婉,若出一人之口。其有才不见用、流落天涯、羁游旅泊之状,了了然皆见于数字间。则所谓“诗源乎心”者,信哉![1]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云:“诗无达诂。”这说明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只有一个终极的阐释,但是任何一种解读却都标明一种确切而鲜明的态度。这两位诗人在诗中的意指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李仁老在此却从诗中窥视到了诗人“有才不见用、流落天涯、羁游旅泊之状”。将诗与诗的创造者——诗人的生命状态联系在一起进行剖析,那么,诗歌批评的过程也就转换为体悟生命的过程,这就赋予诗话批评以某种生命的张力,“诗源乎心”即诗源于生命,这种认知给人一种蓬勃盎然的生命律感。
我们说韩国古代诗话批评呈示出某种生命的律动,是指韩国古代诗家在进行诗歌批评的过程中,常常把自我的生命体悟浑然无间地融入批评话语之中,甚至看不出造作与斧凿的痕迹。这不仅表现在诗歌鉴赏实践中,即便是在阐释理念世界时,也能让我们聆听到生命之流的淙淙乐音。高丽文人崔滋(1188—1260)的《补闲集》在批评文体风格时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语:
文以豪迈壮逸为气,劲峻清驶为骨,正直精详为意,富赡宏肄为辞,简古倔强为体。若局生涩、琐弱、芜浅,是病。若诗,则新奇绝妙,逸越含蓄,险怪俊迈,豪壮富贵,雄深古雅,上也;精隽遒紧,爽豁清峭,飘逸劲直,宏赡和裕,炳焕激切,平淡高邈,优闲夷旷,清玩巧丽,次之;生拙野疏,蹇涩寒枯,浅俗芜杂,衰弱淫靡,病也。
夫评诗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一般意格中,其韵语或有胜劣,一联而兼得者尽寡。故所评之辞亦杂而不同。《诗格》曰:“句老而字不俗,理深而意不杂,才纵而气不怒,言简而事不晦,方入于《风》、《骚》。”此言可师。[1]
在这些阐释诗文理念的精美文字中,处处流溢出某种生命的机趣。“豪迈壮逸”既为文之气,也是人之为人的浩然之气;“劲峻清驶”不只是文之骨,也是人之修身必具的品格;“生涩、琐弱、芜浅”、“浅俗芜杂”等不但是文之病,也是人之患;“理深而意不杂,才纵而气不怒,言简而事不晦”不仅是为诗之道,更是为人的准的;评诗要以“气骨意格”为先,品人也要先品其是否有“骨气”。凡此种种,无不将评诗与品人融为一体,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互渗,密不可分。在诗歌批评的背后,处处奔涌着无意识的生命冲动,让人从中体验到无限的生命自由。在这里,原本属于艺术的符号由于被灌注了人的生气,这样,艺术的形式也就转化为人的生命形式。面对这种具有生命张力的生命形式,怎能不引发我们对自我生命的诗意诉求?这样,诗歌批评的话语也就自然生发出无穷的美的蕴味。
关于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还有许多未尽的话题,也有诸多切入的视点,如从韩国古代诗话范畴入手,探讨韩国古代诗话的美学意蕴,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研究课题,也有极大的阐释空间,这将是我们未来的研究重心。笔者在此只是从宏观的、整体的印象上来谈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1][韩]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一编)[M].汉城:太学社,1996.582,52,458,82.
[2][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四十八·清脾录序[Z].汉城:太学社,1996.583,374.
[3][韩]任廉.旸葩谈苑[M].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1.783,857.
[4][韩]许筠.惺所覆瓿稿(卷四)·宋五家诗抄序[M].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0.346.
[5]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上)[M].白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1987.132.
[6][韩]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兴王条[Z].汉城:瑞文文化社,1980.78.
[7]李苏平.韩国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