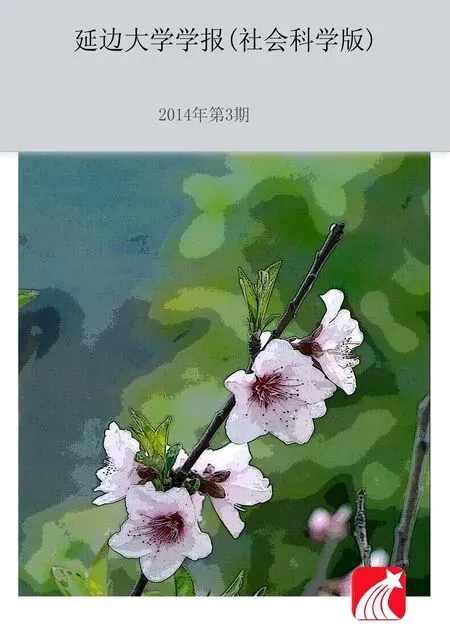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
——兼谈金富轼的女性观
金锦子,高 航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金富轼(1075-1151),高丽中期政治家、史学家和儒学者,字立之,号雷川,谥号文烈。1145年,由他主持编撰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国家现存的最早史书,该书在体例上借鉴了中国史书的编撰方法,分为本纪28卷、列传10卷、年表3卷和志9卷。在《三国史记》的10卷列传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宿将、忠臣、文臣、名儒以及逆臣等男性为中心来编撰的,但其中也出现了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女性形象。通过考察这些女性形象,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古代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女性的生活面貌,了解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同时也揭示出了这些三国时代女性所被赋予的特定典范特征,以及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对社会民众的教化意义。
一、《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
在《三国史记》列传中共出现10位女性,①但其中只有孝女知恩和薛氏女是直接以其名立传,其他则是在相应的列传中出现。尽管如此,这些女性却涵盖了上层贵族至下层庶民等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三国史记》列传中出现的女性可从孝女、贞信女和节妇等几个类型来加以分析。②
(一)孝女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行是为人子女所要遵守的基本准则。列传第八中所载孝女知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且她还是《三国史记》列传中唯一一个被单独立传且有姓名传世的女性。
关于孝女知恩的孝行,据《三国史记》记载,她出生在新罗韩歧部一个普通百姓之家,她的孝行体现在“性至孝,少丧父,独养其母。年三十二,犹不从人。定省不离左右,而无以为养,或佣作,或行乞,得食物以饲之”。[1]尽管每日佣作和行乞却也无力奉养老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知恩不得不瞒着自己的母亲“就富家请卖身为婢,得米十余石。穷日行役于其家,暮则作食归养之”。[1]为了奉养老母,知恩不仅舍弃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同时也舍弃了自己的人身和自由,其孝行可谓感人至深。正所谓母女连心,知恩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瞒过其母,当获知真相的母亲因为自己的拖累而“肝心若以刀刃刺之者……以我故使尔为婢,不如死之速也”。[1]正当母女二人为生计一筹莫展之时,恰好为出游的孝宗郎所见,遂“归请父母,输家粟百石及衣物予之。又偿买主以从良,郎徒几千人各出粟一石为赠”。[1]由此,知恩重新获得了自由。此后新罗真圣王也因其孝行“赐租五百石、家一区,复除征役”,标榜乡里,赐予“孝养坊”的美誉,同时还将此事报于唐朝。
可以说,知恩因其“性至孝”先苦后甜,不仅得到了衣食住所继续奉养老母,而且还获得了广为传诵的美名。
(二)贞信女
在《三国史记》列传描述的女性中,不仅有像知恩这样的孝女,还有超越孝的伦理忠于信义并坚守贞节的女性,可称之为贞信女。
1.薛氏女
薛氏女是《三国史记》列传中第二位被单独立传的女性。同样为人子女,薛氏女在尽孝的过程中与孝女知恩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薛氏女同样也是出身于新罗栗里的普通民家女子,品行可谓“虽寒门单族,而颜色端正,志行修整,见者无不音艳,而不敢犯”。[1]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突出了其品行的端正,以至别人尽管艳慕她的美貌却也不敢有所冒犯。作为女儿的薛氏女无疑是孝顺的,因“其父年老,番当防秋于正谷。女以父衰病,不忍远别,又恨女身不得侍行,徒自愁闷”,[1]此时恰好有一位沙梁部青年嘉实暗自喜欢薛氏女,自告奋勇要代替薛氏女之父服徭役。其父遂将女儿许配嘉实,面对父亲的安排,薛氏女还是应允了与嘉实的婚约,但却是“强与嘉实约”,似乎是略带有勉强的意味。面对与嘉实的婚期之约,薛氏女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婚姻,人之大伦,不可以仓猝。妾既以心许,有死无易。愿君赴防,交代而归。然后卜日成礼,未晚也”。[1]后来嘉实一去6年杳无音讯,薛氏女之父以3年约定之期已过为由要将其另嫁时,薛氏女以“弃信食言,岂人情乎”来反对父亲的决定。后“其父……欲强嫁之,潜约婚于里人,既定日引其人。薛氏固拒,密图遁去而未果。至厩见嘉实所留马,太息流泪”,[1]恰好嘉实归来,终成眷属。
从薛氏女为父担忧到听从父亲的安排应允与嘉实的婚约,再到反对其父食言抗婚的举动,可以看出在薛氏女眼中,作为子女孝行是应当的,但遵守信约,即遵守和实践父亲与嘉实的约定以及自己与嘉实的约定更为重要。通过薛氏女对信的坚持,不仅坚守了自己的节操,同时也使自己的父亲得以实践承诺,而不至于陷入不义,她的言行也正应了对其“颜色端正,志行修整”的评价。
2.平冈公主
薛氏女的故事发生在寒门单族之家,而平冈公主的故事则发生在高句丽王室。《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平冈王(亦称平原王,559-590年在位)的小女儿好哭,平冈王遂戏言要将其嫁给低贱的温达为妻。等到平冈公主到了适嫁年龄,国王要将其嫁到上部高氏的权门之家时,公主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君王就毫无条件地遵从其意愿,而是提出“大王常语,汝必为温达之妇,今何故改前言乎?匹夫犹不欲食言,况至尊乎?故曰:‘王者无戏言’。今大王之命谬矣,妾不敢只承”。[2]可见,她对平冈王的食言不是从父女关系而是上升到君臣关系层面进行反驳,执意违背王命(父命)要下嫁给贫贱的温达。从公主的言行中可以看到的是对信义的遵守。但面对温达的拒绝和温达母亲“吾息至陋,不足为贵人匹。吾家至窭,固不宜贵人居”的疑虑,公主则以“古人言:‘一斗粟,犹可舂;一尺布,犹可缝。’则苟为同心,何必富贵然后可共乎”,[2]表明了自己贫贱不能移的决心。
与温达结合后,平冈公主又以贤妻身份帮助自己的丈夫建功立业,“乃卖金钏,买得田宅、奴婢、牛马、器物,资用完具……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温达为先锋,疾斗,斩数十余级”,[2]并使温达获得了平冈王的“是吾女婿也”的认同,还获得了大兄的爵位。后来,温达在与新罗的阿旦城之战中战死,“欲葬,柩不肯动,公主来抚棺曰:‘死生决矣,于乎归矣!’遂举而窆”,[2]表现出了夫妻间笃厚的情谊。可以说,《温达传》虽以温达之名立传,但他的建功立业都得益于平冈公主对信义的遵守和执着。
在薛氏女和平冈公主的故事中,共同的一点就是对“信”的承诺。在“信”的缔结上,薛氏女与嘉实的婚约、平冈公主与温达的婚约都不是当事者双方缔结的,而是通过第三方,亦即薛氏女的父亲和平冈王缔结的。薛氏女和平冈公主故事的焦点也就发生在作为“信”的缔结者违背当初约定而产生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或臣子对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进行反抗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正是通过这种反抗坚守了自己的节操,也使“信”的缔结者最终信守了承诺。
(三)节妇
在《三国史记》列传中还有一类女性,她们或是能够不畏强暴坚守节操,或是遵从和支持丈夫的行动和信念,可将其称为节妇。
1.都弥妻
都弥妻是出现在《都弥传》中的人物,虽然不是专门为其立传,而且连名字也没有出现,但却可以说是撑起该列传的核心人物。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都弥是百济人,虽然也是属于普通的编户小民,但颇知义理。而都弥妻子的外貌品行则是“美丽,亦有节行,为时人所称”。[1]她的这种品行在反抗盖卤王的威逼利诱中得到了体现。盖卤王认为“凡妇人之德,虽以贞洁为先,若在幽昏无人知处,诱之以巧言,则能不动心者,鲜矣乎!”[1]为了考验都弥妻,盖卤王派一近臣穿着王的衣服乘着王的马车夜抵都弥家,都弥妻则以“国王无妄语,吾敢不顺。请大王先入室,吾更衣乃进”相敷衍,而后装扮一婢女进献。盖卤王知道被骗后,就降罪于都弥,弄瞎其双眼后放逐海岛,之后欲再次威逼都弥妻就范。都弥妻则以“今良人已失,单独一身,不能自持,况为王御,岂敢相违?今以月经,浑身污秽,请俟他日薰浴而后来”[1]相推脱并逃离百济,乘孤舟随波而下来到泉城岛,遇见了自己的丈夫,在高句丽人的帮助下,两人得以团聚。
在这里可以看到,都弥妻面对盖卤王的诱惑和强权毫不动摇,始终如一地同丈夫都弥生死与共,将至死不渝的贞洁表现到了极致。可以说,在《三国史记》列传中《都弥传》将女子的贞洁推向极致,蕴含着浓厚的训诫意义。同时,也应看到都弥与妻子之间的相互信任,即面对盖卤王对都弥妻品行的质疑,都弥却坚定地认为“人之情不可测也。而若臣之妻者,虽死无贰者也”,表现出了对妻子的充分信任。③
2.昔于老妻、智炤夫人、素那妻
昔于老是新罗助贲尼师今(230-246年)和沾解尼师今(247-261年)时的重臣。253年,在接待倭国使臣葛那古时因戏言“早晚以汝王为盐奴,王妃为爨妇”而招来倭国的征讨。昔于老抵倭国军营欲化解干戈,但却被倭人“积柴置其上,烧杀之,乃去”。到味邹尼师今(262-284年)时,倭国大臣来聘,昔于老妻“请于国王,私飨倭使臣,及其泥醉,使壮士曳下庭焚之,以报前怨”。[2]昔于老妻不忘丈夫的惨死,最终也同样以惨烈的方式为丈夫报仇,可以说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
智炤夫人是新罗大将金庾信之妻,太宗大王金春秋的第三女。在新罗与唐朝的石门之战中,新罗军队遭到惨败。当时金庾信次子元述为裨将,虽欲战死,却为晓川、义文等所阻。后其父金庾信认为“元述不惟辱王命,而亦负家训,可斩也”。虽然得到国王的赦免,但元述惭愧不敢见父亲。直到金庾信死后,求见母亲,但智炤夫人认为“妇人有三从之义。今既寡矣,宜从于子。若元述者,既不得为子于先君,吾焉得为其母乎?”[3]最终不肯见自己的儿子,元述也因不容于父母而抱恨终生。
素那妻,新罗加林郡良家女子。其夫素那是白城郡蛇山人,675年在阿达城与靺鞨的战斗中奋勇杀敌,中箭而亡。对于丈夫战死沙场,素那妻的态度是“吾夫常曰:‘丈夫固当兵死,岂可卧床席死家人之手乎!’其平昔之言如此,今死如其志也。”[4]尽管素那妻也为丈夫的死感到悲伤,但却认为丈夫死得其所,实现了大丈夫战死沙场的人生追求。
在这些节妇中,都弥妻是节义型的,正如列传中对她的评价“美丽亦有节行”。昔于老妻则属于为夫报仇型,尽管丈夫死去多年,但一直不忘为夫报仇,最终火焚倭国使臣。而智炤夫人和素那妻则属于秉承丈夫意愿型。这些女性身为人妻,用自己的言行坚持了操守,体现了对丈夫的忠贞。
二、《三国史记》列传中女性形象的社会教化意义
史书的编撰是有其时代要求的,为了凸显其时代要求,就要树立各种楷模。《三国史记》列传中出现的女性也同样具有这种社会教化意义。
(一)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典范
关于《三国史记》的编撰目的,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提到“惟此海东三国,历年长久,宜其事实,著在方策……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况惟新罗氏、高句丽氏、百济氏,开基鼎峙,能以礼通于中国。故范晔汉书,宋祁唐书,皆有列传,而详内略外,不以具载。又其古记,文字芜拙,事迹阙亡。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5]可见,金富轼憾于高丽以前的历史在中国史书中“详内略外,不以具载”,而本国所撰古记又“文字芜拙,事迹阙亡”,以至于“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失去了“以垂劝戒”的作用。为了达到劝诫的目的,在编撰《三国史记》的过程中,无论在事件、人物,还是史料的选择上,金富轼都遵循了这一原则,而其进行褒贬的准绳则是以儒家道德规范为标准的。
考察《三国史记》的编撰目的,也不能忽略高丽中期社会出现的重大变化。金富轼以70岁高龄编撰《三国史记》,其动因皆在于当时高丽处于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加剧、动乱屡生的时期。在他从政生涯中经历了两次对高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即1126年的李资谦叛乱④和1135年的妙清叛乱,⑤在此过程中,高丽王权衰落,贵族官僚体制趋于瓦解,成为高丽中期社会动荡的开始。
经过两乱的高丽王朝,更加强调以儒排佛和强化国家王权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为了从“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的历史中吸取鉴戒以垂训后世,就必须以儒家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判。所谓列传,就是“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即为具有历史鉴戒作用的人物立传,因此对人物的选择也必然有其目的性。可以说,列传中出现的这些女性是高丽社会所崇尚的女性形象。知恩的孝行、薛氏女和平冈公主的贞信、都弥妻的节义以及智炤夫人和素那妻的忠贞、知恩母亲和温达母亲的慈爱、明事理都是按照当时高丽人的要求而被典型化了的形象,其所反映的已经“不是三国人的主体历史,而是以高丽的视角被他化的历史”,[6]用三国时期的女性来对高丽社会的女性,以及社会道德提供借鉴,这些女性在金富轼笔下也就实现了其所具有的社会教化作用。
(二)重建高丽社会儒家道德理念的诉求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金富轼重视儒家道德的重建。列传中女性的言行也都体现了忠、孝、礼、信等儒家思想理念。孝女知恩的“性至孝”、薛氏女的“颜色端正,志行修整”、都弥妻的“美丽亦有节行”,以及智炤夫人的“妇人有三从之义”等品行,在金富轼看来都是作为女性应具有的美德。尽管如此,金富轼更重视信的践约,正如薛氏女所言“弃信食言,岂人情乎”,守信是人情的根本,是为人道德的底线,即如前文所述,知恩的孝行固然值得提倡,但当子女的孝与信发生矛盾时,如薛氏女与父亲、平冈公主与平冈王之间,为人子女首先应坚守信。如果为了实现对父亲的孝顺而违背信义,实则将父亲陷于违背信义的境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父亲坚守承诺,避免其“失信”,这才是作为子女真正孝行的体现。
此外,在列传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对这些女性家庭出身的记载,即大多都出身于平民,如孝女知恩是“韩歧部百姓连权之女”,薛氏女是“寒门单族”的“栗里民家女子也”,都弥妻也是百济“编户小民”家的妻子。尽管出身寒微,但她们或是“性至孝,少丧父,独养其母”,或是“颜色端正,志行修整”,亦或是“美丽,亦有节行,为时人所称”。由此,可以看出金富轼在编撰列传时所体现的独具匠心之处,即作为平民女性所体现出的这些美德,不仅对普通百姓,而且对整个高丽社会同样都具有社会典范和教化意义。
三、金富轼的女性观
如前所述,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是以儒家道德为基准的,列传中对女性形象的记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儒家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了其对女性的深刻认识。
(一)男尊女卑思想
尽管金富轼在列传中记述了众多女性形象,但其女性观中最根本的思想仍未摆脱男尊女卑的固习。这一点可以从其关于善德女王的史论中窥见一斑,即“臣闻之,古有女娲氏,非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至若吕雉、武瞾,值幼弱之主,临朝称制,史书不得公然称王,但书高皇后吕氏,则天皇后武氏者。以天言之,则阳刚而阴柔,以人言之,则男尊而女卑。岂可许姥妪出闺房,断国家之政事乎?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位,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书云“牝鸡之晨”,易云“羸豕孚蹢躅”,其可不为之戒哉。[7]由此金富轼明确阐明了“男尊而女卑”的观点,女性不应“出闺房”而应局限于家内,更不可染指国家政事,因此对新罗女王继位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另外,从列传的结构安排来看,列传第八是为具有孝行、重名节以及具有杰出才艺者所著的。有意思的是,金富轼把具有孝行但却是男性的向德和圣觉放在最前,而同样以孝行闻名的孝女知恩则被置于书法和绘画才能突出的金生、率居之后,此前还列有重节守义的实兮、勿稽子、百结先生、剑君等人。所以如此安排,或许就因为知恩是女性的缘故。
可以说,列传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是符合金富轼的儒家道德规范而被凸显出来的形象,并被作为三国时代的女性楷模而载入史册,而且“往往从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出发来解释一些现象和进行说教。即便他对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纯真爱情和深挚的母女之爱表示了肯定和赞许的态度,也是把她们纳入封建道德的框框之内”。[8]
(二)女性应充分发挥其在家庭中的角色作用
在古代社会,女性作为被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而局限于家庭生活的群体,在家庭中承担着为人女、为人妻或为人母的角色。在《三国史记》列传中也可以看到她们所承担的这些角色。为人女者如孝女知恩、薛氏女、平冈公主,为人妻者如都弥妻、昔于老妻、素那妻、智炤夫人等,为人母者如温达母亲、知恩母亲。
根据前述对列传的分析,可以看到金富轼比较重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作用。为人女者应尽孝道,而且要通过自己对信的坚守来完成孝的实践,如薛氏女和平冈公主,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不仅践约了父亲的信,进而达成了对父亲真正的孝。为人妻者应恪守对丈夫的信任和忠贞,如都弥妻的节义、智炤夫人的“三从之义”等。为人母者应慈爱、明事理,如知恩母亲对女儿的爱怜、温达母亲的明事理成全了温达与平冈公主。这些女性能够在家庭中发挥其角色作用,最终也会帮助男性充分发挥其社会角色作用。
(三)女性的言行应合乎儒家道德而不偏激
《北史·列女传》记载:“盖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人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是以《诗》、《书》所记,风俗所存,图像丹青,流生竹索,莫不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也。”由此可见,古代对女性要求标准是“温柔和贞烈”。但在《三国史记》列传中出现的这些女性似乎“温柔”有余而“贞烈”不足。
《三国史记》列传中出现的女性,尽管遭受各种磨难,但却没有一个采取自杀或殉夫等极端行为。薛氏女面对父亲的逼婚,采取的是“秘图遁去”的方式。都弥妻面对暴君盖卤王的再三威逼,也没有以死抗争,而是以计谋敷衍,最终出逃并和丈夫重逢。平冈公主与温达情深意厚,温达在阿旦城中流矢而亡,欲葬而柩不动,公主抚棺告之“死生决矣”才得以入葬。此外,列传中出现昔于老妻、素那妻等,也都没有与丈夫共同赴死。这与后世所推崇的要求绝对服从,甚至以死保全名节的烈女、烈妇有很大不同。
另外,对于昔于老之妻焚倭国使者为夫报仇的举动,金富轼在其史论中也表明了批判态度,即“(昔于老)然以一言之悖,以自取死,又令两国交兵。其妻能抱怨,亦变而非正也。若不尔者,其功业亦可录也”。[2]
(四)赞扬女性追求忠贞爱情的浪漫情怀
作为文人的金富轼在列传中也展现了其浪漫情怀。平冈公主贵为一国公主,为了寻找自己憧憬的恋人,义无反顾地抛弃荣华富贵,自愿成为乞丐温达的妻子,并协助丈夫温达成就一番功名,展现了真挚而美丽的爱情。“温达和平冈公主之间的爱情,同司马长卿和卓文君的爱情一道,实际上都是东方鲜见的超凡脱俗的恋爱。他们摆脱了所有人为的束缚,只为了纯真圣洁的爱情而活,连他们周围的环境,也要净化方才甘心。故事以当时政治大势为背景,以公主的恋爱和温达的功名为经纬,编织得美丽而又动人。”[9]另外,从薛氏女和都弥妻身上也能看到这种浪漫情怀。
总之,作为封建时代的儒学者,其女性观中难免会存在重男轻女,以及将女性局限在家庭中并要遵从封建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三国史记》列传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金富轼重建儒家道德规范的诉求。在高丽中期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这些三国时期的女性被赋予了用于教化民众的典范意义,同时也体现了金富轼不同于后世性理学对女性诸多限制和禁锢而略显“开放”的女性观。
注释:
①根据《三国史记》列传的记载,可以找到有言行记载的女性主要有智炤夫人、孝女知恩、知恩母亲、薛氏女、平冈公主、温达母亲、都弥妻、昔于老妻、朴堤上妻、素那妻。
②关于《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类型,笔者认为可以依据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分为女儿、妻子、母亲等,也可依据其品行分为孝女、贞信女和节妇。《三国史记》的编撰体现的是儒家道德史观,故而采用后一种划分方法。
③韩国学者郑出宪认为,虽然《都弥传》中更引人注目的是都弥之妻,但列传却是以都弥之名而立,是因为相对于都弥之妻的节义,金富轼更侧重于都弥对妻子的信任。但作为男性却被置于女性之后,是因为都弥是百济人的缘故(参见《解读三国女性的两个“男性”的视角——以〈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中心》,载《古典文学研究》,1996年,第11辑)。
④李资谦是高丽睿宗(1106-1122)和仁宗(1123-1146)时期的权臣,睿宗纳其二女为妃,此后权倾朝野,历任参知政事、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进开府仪同三司等。1122年,立其外孙即位,是为仁宗,封中书令、尚书都省领事、判兵部等职。李资谦后又强迫仁宗纳其三女、四女为妃,权势日盛。1126年,仁宗为剪除李资谦势力诛杀其党羽,李资谦、拓俊京等人遂发动叛乱围攻王宫,并掌握了朝政。后仁宗利用拓俊京与李资谦的矛盾铲除了李资谦一门及势力,叛乱得以平定。李资谦叛乱标志着高丽贵族官僚政治开始瓦解,成为高句丽社会趋于动乱的开始。
⑤妙清是高丽中期的僧侣,一号净心。李资谦和拓俊京叛乱被平定后,西京官僚试图掌握朝政,郑知常、妙清等人以风水图谶说称西京王气已尽,要求迁都西京,并于1128年在西京修建了大华宫,但迁都的主张遭到开京贵族的反对。1135年,妙清在西京发动叛乱,自立国号为“大为”,年号“天开”,称“天遣忠义军”。仁宗命金富轼率军讨伐西京叛军,西京叛军赵匡杀妙清求降未果。1136年2月,西京被攻破,赵匡自焚而死,叛乱遂平。妙清叛乱是开京门阀贵族与西京新兴官僚争权夺利的统治内部的斗争,进一步加深了高丽贵族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1]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十八·列传第八[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545,545,545,545,546,546,546,546,523,523,523.
[2]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十五·列传第五[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523,523,523,523,519,519.
[3]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十三·列传第三·金庾信(下)[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499.
[4]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十七·列传第七·素那[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532.
[5] 金富轼.三国史记·进三国史记表[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6] [韩]郑出宪.解读三国女性的两个“男性”的视角——以《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中心[J].古典文学研究,1996,(11):295.
[7]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64.
[8] 韦旭昇.韩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3.
[9] [韩]金台俊.朝鲜小说史[M].全华民,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