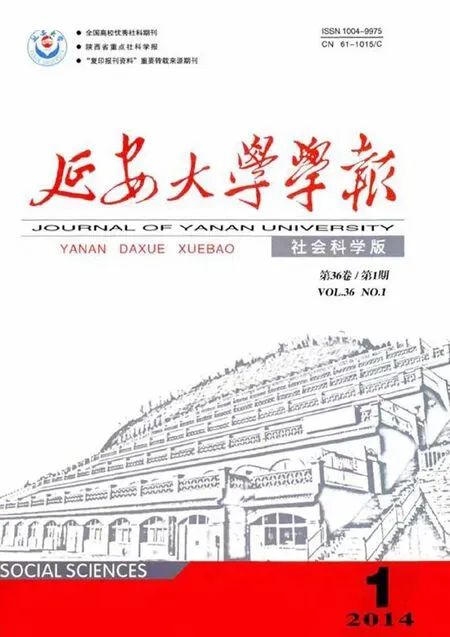论莫言作品中文化景观的审美诉求
赵 婷,郭 婷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022)
Sauer C.O.于1974年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它形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并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是人类和自然双重作用的结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在1992年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它具有广泛的内涵,是某一地域环境下各种文化要素的整体体现,文化景观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人文性特征。[1]文化景观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物质文化景观主要涉及土地、生存区域和建筑等;非物质文化景观是一种内在体现,包括思想、语言、风俗、艺术、文学、信仰等。[2]审美诉求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是一种旨在探索事物中美的本质、关系和规律的审美活动。
本文通过审美诉求引导下的美学实践活动,针对文化景观的非物质层面,以莫言作品中的七种人文现象作为审美对象,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沧桑和复杂现实,探求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审美品质,进而发现莫言艺术创作中的豪放性和纪实性风格,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
一、多样性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不仅指传统意义上人与自然的亲和状态,而且还突出“生存整体观”,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自身的精神生态纳入生态文化的研究范围。[3]生态文化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促使人们形成一种追求生态整体利益的思维模式。对莫言作品生态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生态地域环境。莫言作品以高密东北乡为创作原型,描绘了浓郁的乡土文化,将天南海北的景观、事物、植物等融入到这片充满原生态的地域环境中。王衍提到高密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等生态地域特征构成了莫言民间创作的素材。[4]孟文彬指出齐文化作为生态地域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对莫言的民间世界的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创造了神秘美好的民间世界、自由奔放的人物形象以及豪放不羁的写作风格。[5]其次,原生态写作。莫言运用山东方言,描写民间社会风貌和普通民众生活,展现底层文化形态,反映特定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为小说增添了浓浓的乡土味。姬凤霞从句式的角度,指出了莫言小说的民间口语化特征,小说中短句、插入语、省略句等都展现了口语特点和民间特色。[6]
莫言一方面刻画了乡土视野下自然与人类保持着诗意般的祥和状态,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人类在物质和利益的驱使下所产生的物种退化、人类异化和社会畸形等生存危机。莫言向读者表达了崇尚天人合一和对自由原始状态的向往,同时也对自然、人类生存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进行了抨击。笔者将莫言作品中多样性的生态文化归纳为自由性、异化性和收缩性。(一)自由性。莫言作品中生命的世界涌动着充满自由性与和谐感的生态之美,虽然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大都处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但他们英勇抗争,始终保持着强劲、自由和永不止息的生命力。莫言通过展现特定生态环境下人类和环境的冲突问题,传达出一种自由的生命意识。《红高粱》中“我”奶奶戴凤莲不受传统纲常礼教的束缚,发出作为独立女性的爱情和幸福宣言,这种性爱自由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不甘于命运的折磨,希望通过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过上正常生活,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渴望通过冲破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美好愿望。《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全民入社时期坚持单干,从他的身上折射出一种不畏强权的自由精神。(二)异化性。莫言作品中生态文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心态的异化性。心态的异化主要针对人类的精神生态层面,这种失衡的产生是以自然和生态的失衡为前提的,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和人性的扭曲变形。[7]《枯河》中外部的压抑力量使人的生存状态变得混沌不堪,同时精神也呈现出异化和扭曲的形式。《筑路》中的来书因为天降横财而变得神经敏感,而财宝的不翼而飞彻底打破了他的精神底线。《倒立》展现了一个深受官本位思想浸染的社会,人们失去了人格和自我,迷失在权力和欲望的深渊之中,这种畸形的价值观表现出人性的堕落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三)收缩性。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在繁衍和能力上却呈现出退化的趋势。莫言作品中生态文化的第三种形式为物种的收缩性,它的产生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环境的压迫以及人类自身的劣根性导致了生存状态的失衡,人类种的退化和非人能力的展现是物种收缩性的主要体现形式,非常理的想象展示了人类具有某些动物的特征,这种由人向动物的转变过程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红高粱》中爷爷的英勇杀敌,父亲的大战狗群再到我的安于现状,能力的退化让不肖子孙们认识到了伟大的消逝和自身的无能。《生蹼的祖先们》中手脚生蹼膜的孩子是人类倒退的表现,这种近似动物的特征是物种退化的鲜明标志。《翱翔》中的新娘燕燕为了躲避无爱婚姻的束缚竟然像鸟儿一样飞翔。《嗅味族》中长鼻人只要嗅一下食物的香味就能吃饱。这些超越常人的奇异本领说明在特殊环境下动物比人更能适应环境,从而反映了人类退化的趋势。可见,莫言作品中的生态文化在生命、心态和物种三个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分别以自由性、异化性和收缩性的方式展现出既和谐又病态的现状。
二、批判性的夸诞文化
齐国之地,地理位置优越,濒临大海,交通便利,因此造就了当地信息的快速流通。见多识广的特点让齐人具有敏捷的思维和反应能力,加之神仙巫术的影响,当地人就形成了夸诞不羁的风格特色。[8]《说文解字》中认为:“夸,奢也,从大于声”,意思就是超过本来状态,夸张声势,而“诞”指的是“从言延声”,[9]意思为拖长和拓展声势,也就是虚张声势,因此夸诞结合了夸张和荒诞的双重含义。对莫言小说中夸诞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荒诞与现实的游离。荒诞带有违背常理和逻辑、无意义和不可调和的意味。在哲学领域,荒诞指的是一种尴尬与不和谐的生存处境,作者通过变形和扭曲的情节折射社会现实,从而批判和讽刺社会的不合理性。刘广远认为莫言小说中的节日和暴饮暴食场景与荒诞现实主义密切相关,将虚构的话语世界与现实的生存世界进行对比,揭示了社会的残酷性和病态特征。[10]第二,夸张描写。夸张的写作手法能够突出情节和人物的特性,从而反映故事背后体现的社会问题和生存困境。程艳芳认为夸大黑孩的感觉细胞,目的是反映现实社会的残酷以及小人物的无奈和悲哀,对于他们来说只能通过幻想的方式挣脱现实。第三,荒诞叙事。莫言的一些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这种无结构的编排实际上是作者有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揭示现实的荒诞无稽和剖析人性的弊病。针对莫言作品中魔幻的氛围、残忍的杀戮、屎尿横飞的场景,周梦娜、肖薇提出这些违反常规和逻辑的情节反映了一个真实和荒诞的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劣根性。[11]
莫言作品中的夸诞文化主要利用那些离奇、夸张、戏谑和变形的故事情节,表达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讽刺和评判。莫言将自己放在平民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带着同情和理解的心理去警示世人。他用时而荒诞、时而夸张变形、时而又幽默的故事情节,揭示其悲剧性的目的。[12]在莫言的作品中,这种批判性的夸诞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一)生存的幻城。通过荒诞和夸张的叙事再现人类压抑和畸形的生存现状。《幽默与趣味》中的王三在压力和烦躁的作用下竟然变形为一只猴子,这种变形反映了人类缺乏生活的自由和满足感,内心的空洞使得人们希望通过变形达到一种逃离的目的,但是暂时性的摆脱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存现状。《铁孩》中有一个靠吃铁来充饥的小男孩,这种并不存在的现实写照讽刺了那个缺少关爱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物质资源的匮乏让生存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二)历史的尘埃。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特定阶段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会带给人累累的伤痕。人们在反思中回忆,在痛苦中成长,滚滚烟尘是那个时代沧桑的见证。《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定格在“文革”动荡时期,荒诞的政治让那些头脑发热的革命分子失去理智,混淆是非的可笑行径是对历史的嘲弄和讽刺。个人是社会中的一员,政治和历史的后退必然导致个体生命的践踏和蹂躏。《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只因地主的阶级身份,就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本性善良的他勤恳持家、乐善好施,西门闹的悲惨命运与土改这段历史密不可分,荒谬的社会现实是个人悲剧的主要原因。《挂像》中也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闹剧:个人领袖的价值超越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狂躁不堪的人们丧失了理性和认知。历史的戏剧化导致了一场场荒谬夸张的闹剧。(三)情节的飘零。莫言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地设计了一些杂乱无序、缺乏条理的故事情节,通过看似飘零的故事和空洞的内容,希望读者能从夸张和荒诞中体会到作者所要传达的深层含义。《二姑随后就到》中描写了惨无人道的兄弟俩为二姑复仇的情节,然而主人公二姑却始终没有出场。这种离奇的故事、暴力的刻画、荒诞的杀戮和主角的缺失让读者更能感受到二姑的神秘和非凡。作者用夸诞的写作形式对社会、历史、政治和人性等问题进行批判,揭示荒诞无稽的外界环境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夸张和离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讽刺与抨击。
三、深邃性的宿命文化
依照中国的宿命文化,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凡人无法预知和掌控这种超自然力量。宿命常常与悲剧和苦难相联系,是中国文化中比较封建和保守的思想内容。关于莫言作品中宿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女性悲惨命运。旧社会中女性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物,封建礼法对女性进行压制,使得她们难以逃脱被压迫的生活。彭在钦和段晓磊分析了《丰乳肥臀》中女性的悲苦命运,上官家的女人们没有选择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而是男权的牺牲品。[13]第二,人类的苦难之旅。人类会受到历史、社会、政治等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其中某些消极力量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同时也是未知的。赤裸裸的丑恶现象会使人们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从而导致人类的悲剧。李晓亮以《蛙》为例分析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社会、家庭和人类悲剧。无数的婴儿失去了生命,以及政策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创伤。[14]第三,儿童生存悲剧。在莫言小说中,儿童作为弱势群体时常受到成人世界的排挤和压迫。他们顽强地挣扎,却始终摆脱不了悲剧化的命运。郭群和姚新勇展现了莫言小说中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状态,以及社会、家庭、文化等因素对他们幼小身心的沉重打击,最终这些年幼的生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龙阳分析了莫言作品中的黑孩和赵小甲形象,他们忍受着生活的艰辛、人生的无奈和社会的冷漠,缺少关爱的童年注定了人生的悲惨和痛苦。[15]
莫言作品中的主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思想、道德等各个领域的悲剧性因素,将人性的弱点和客观的外界环境相联系,表现出中国宿命文化的深邃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陈旧思想的毒化,同时也揭示出作者正经历一次充满消极性和血腥性的精神苦旅。在莫言的作品中,深邃的宿命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情困致死。人世间玄妙的爱情,让深陷其中的男女无所畏惧,甚至生死相随。《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上尉在外界和家庭的压力下只能与心爱的人在天堂中相聚。《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为了使自己的发妻不受皮肉的惩罚,独自承担所有的罪过,最后被判处死刑。《天花乱坠》中的丑皮匠为了自己心爱的财主小姐,苦苦地等待,为她耗尽了最后一滴血。莫言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带有虐心的成分,从相知相识到生离死别,始终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痛苦和痴迷反映了男女内心中无法磨灭的情感创伤,而这一切都归结于天数的左右,强大的命运之轮预示着深远和无尽的苦难之路。(二)苦命相随。凄惨悲苦的人物命运验证着天命难违的可怕预言。《红耳朵》中王十千的命运从一出生就已经被预言,虽然他也经历了大富大贵、轰轰烈烈的生活,可是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沦为乞丐的命运。《司令的女人》中的女知青小唐本以为考上大学会和司令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但是命运的悲剧始终没有放过她,最终还是被人残忍地杀害。《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代表了封建社会里那些没有地位和尊严的女人们,她们的命运从出生就已经被定格,因此只能用凄惨的生命吟唱悲哀的挽歌。莫言笔下的苦命之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抗争来获得幸福生活,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佛教认为命运早有定数,而莫言也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这种思想的根源难以动摇,其带来的影响也是深邃和复杂的。(三)梦中之泪。莫言描绘了很多离奇和杂乱的梦境,这些梦境充满了苦涩的滋味。《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描写了这样的一段梦境:支队长与高司令赛马,其赌注就是彼此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人生从来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战友重逢》中作者通过梦境与牺牲的战友钱英豪相遇,有心报国却无法实现的苦楚让人感到心酸和苦闷。《马驹横穿沼泽》中讲述了一个奇异的梦境:一个小男孩与由红马驹变成的美丽女子相爱,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可怕的魔咒还是未能放过这对苦命鸳鸯。莫言笔下的这类人物受到情感纠葛、命运之轮和梦境幻化的困扰,终究未能逃脱宿命的魔爪,最后成了苦难的牺牲品。这种宿命文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腐朽的历史画卷,其传递出一种深邃的悲剧力量和一段无言的内心独白。
四、迷离的传奇文化
莫言建构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奇色彩的高密东北乡,而这片大地更多地受到齐鲁文化中齐文化的影响。齐文化传承了夷人风俗,另外还受到方术道教和民间巫术的熏陶,因此那里的百姓具有开放、机智和灵活的性格特点。高密的地域特色造就了充满魔幻、神秘和灵异色彩的传奇文化。学者对莫言小说中传奇色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奇叙事。传奇主要讲述不合常理、神奇怪异的民间故事,对象可以是神妖鬼怪,也可以是奇人异事。张鹏飞基于莫言小说中的传奇叙事,揭示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美学意蕴,以及虚构与写实情节中的神秘情愫。[16]第二,神秘超体验。莫言的小说充满灵性,其原因之一便是他对奇异和神秘感受的描写,敏感的感官能力将生命体验详细而深入地刻画出来。陈少萍认为异于常人的体验和生命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曾利君指出莫言小说中的感觉描写为文本增添了魔幻性特色。[17]第三,魔幻叙事。这种写作手法基于社会现实,利用夸张和魔幻手法展现事实,主要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和时空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在虚与实的结合中创造神奇和荒诞的艺术效果。薛茂红指出了莫言小说魔幻特色的产生原因,以及莫言笔下故事情节、人物和高密东北乡等具有的真实与虚幻的文化氛围。郑恩兵和李琳提出莫言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多声部特色,同时阐明了这种多重变奏对揭示人物心理和感悟生命的积极效果。[18]
莫言用想象勾勒出一幅幅充满鬼怪、灵魂和神魔的离奇画卷,时而真实,时而虚幻的情节让莫言作品中的传奇因子变得迷离和神幻。这种迷离的传奇文化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魔幻的灵物。《藏宝图》中虎须能够看到人前世的本相,《白狗秋千架》中那条白狗能够洞察人类心理,《野骡子》中的鲁西大黄牛能够报复杀牛人,还有《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中那条不远千里从长白山来复仇的狼,《木匠和狗》中为木匠挖好坟墓的狗,以及《老枪》中那把始终不放过大锁家人的枪等。这些通灵的动物和物品时常具有人类的思维,而且甚至拥有超越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第二,怪异的行为。莫言作品中的某些人物行为与常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他们有着古怪、神秘甚至是奇异的行为模式。《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沉默不语、时常发呆、饱受压抑,并且无法传达情感,《小说九段》中那个把什么东西都要翻过来的儿子,《球状闪电》中那个浑身粘满羽毛飞来飞去的鸟老头以及《生蹼的祖先们》中那个性情残忍、通灵入玄,能够洞悉他人心理的儿子青狗等都具有怪异的行为。莫言用大胆的想象创造了许多充满怪异色彩的人物形象,他们超凡脱俗、一反常态,虽然神秘,却没有恐怖之感。第三,离奇的巧遇。莫言描写了奇特和迷离的见闻轶事,巧遇之中充满了魔幻因子,作者通过幻想勾勒了一个既现实又虚无的世界。例如,《奇遇》中作古的赵三大爷让探亲回家的“我”转交给父亲一个玛瑙烟袋嘴。《白杨林里的战斗》中的“我”与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相遇,并且文中的黑衣人还让“我”经历了一次无痛的炮烙。《夜渔》中讲述了那个曾经帮“我”捉螃蟹的奇怪女人,竟然像预言所说的那样,25年之后又一次与“我”相遇。《嗅味族》中的“我”在井下认识了一些通过闻食物的气味就能吃饱的长鼻人。莫言描写人、鬼、神和灵物的亲密交流以及亦真亦幻的巧遇过程,展现了其作品神幻化和灵异性的创作特色。第四,神秘的鬼魅。莫言擅长用想象建构一个人与鬼神共存的世界,在这片领域内,生死只是一个界限,而灵魂与肉体也可以独立存在。正如阿城评价的那样:莫言所描绘的鬼神并非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具有一种浪漫、神秘和柔和的情调,因此这种精神的飞跃带给人们的是灵魂的释然和超脱。[19]《战友重逢》中死去的战友们在烈士陵园里竟然组成了一个阴兵团,他们有着正规的编制和严格的纪律。《生蹼的祖先们》中老爷的灵魂竟然能与活着的人对话,而且亲自给后人交代送葬事宜。《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下岗的老师傅在经营幽会小屋时遇到了一对苦命的鬼鸳鸯,让本已心怀愧疚的他变得更加不安。莫言的小说将传统的鬼神引入写作当中,这种带有神秘和异样色彩的传奇性故事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迷离的精神体验,其中包含着飘移不定、万物有灵、机缘巧合、魔幻怪异的感觉因子。
五、英勇的侠义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侠义文化格外推崇,很多小说也描绘了身怀绝技、为国为民、舍己为人、充满正义的侠客英雄。在莫言看来,侠客英雄并非仅仅指那些“为国为民”的大侠,他认为侠客英雄指的是那种蔑视法规、敢作敢为、勇敢无畏的人,而至真至善至美的侠客和英雄只是人们心中的理想人物。因此英勇的侠义文化展现了侠客英雄事迹,莫言将这种侠义文化诠释为:成败并不是关注焦点,而真正的焦点是对人类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力量,侠义文化是一种超越世俗、勇敢无畏、言而有信、自由洒脱的文化概念。[20]对莫言作品中侠义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反传统英雄。这一类英雄打破了英雄神话的概念,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完美形象,是美丑参半的结合体。英雄是美丽和邪恶的并存体,《红高粱家族》描写了他们不平凡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反映了反传统英雄在人性方面暴露的缺陷。[21]朱永富提出杂种英雄的概念,这一类人物是不完美的,在承认其辉煌历史的同时,还要正确对待他们的不足。第二,传奇英雄。这一类英雄形象具有崇高的品质、敢爱敢恨的性格、豪放洒脱的风度等,他们创造了非凡的事迹,是真正的本色英雄。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出自于民间,充满传奇色彩,他们虽出身卑微,却创造着历史,具有非凡的社会价值和人格魅力。他们的忠义本色与传统的齐鲁文化和精神一脉相承。[22]第三,苦难英雄。莫言笔下的英雄虽然具有卓越的功绩,但也同样与苦难和痛苦相随,悲惨的命运是他们难以逃避的。朱永富认为英雄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命运紧密相关的,因此个人的悲剧也反映了社会和民族的悲剧。[23]
莫言作品中的侠义文化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英雄女性。这一类女性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拥有火热的心灵和坚韧顽强的意志。传统的封建礼教不能约束她们的行为,豪放的性格展示了女英雄们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天马行空的个性特点。这些女性是社会的叛逆者,个性的解放让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坐标。《二姑随后就到》中刻画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二姑形象,她拥有盖世绝伦的武艺和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她的出场要以血腥和死亡来铺垫,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闪烁着刀光剑影的女侠形象。《扫帚星》中的祖母英勇地与恶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而且能够大度地将自己的接生事业转交给新人,祖母的身上具有勇敢、沉着和豁达的优秀品质。《梦境与杂种》中的小女孩树叶无私、勇敢、谦让。莫言作品中的英雄女性具有大度、勇敢、坚强、反叛等优秀品质,她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演绎了一幕幕历史的传奇,作者用朴实的语言展现了女性人生的壮丽之美。第二,热血男儿。莫言作品中还刻画了一群热血沸腾、英勇顽强的男儿形象。《岛上的风》中为了保护战友,自己却牺牲在台风和海啸中的副班长李丹;《黑沙滩》中为抢救国家粮食而被处分的无辜场长,他为了国家利益宁可被他人栽赃陷害;《野种》中的代理连长余豆官用机智和胆识谱写了一段光辉的传奇。莫言笔下的男儿形象具有刚强不屈的优秀品质,他们是正义的化身,血性之美尽展男儿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本色。第三,凡人英雄。英雄并不一定都要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默默的平凡人同样也能书写英雄的佳话。[24]《大风》中那个扛起家庭重担的爷爷,用真诚和无悔的行动为家人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秋水》中那个有着一副好心肠并拯救饥饿女子的男人;《售棉大路》中那些心中充满爱意、热心帮助他人的平凡英雄;《弃婴》中那个收养弃婴女孩的主人公;《放鸭》中拾金不昧的李老壮。这些善良的普通人用自己不平凡的善举书写着英雄的史诗,他们的爱心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莫言作品中的凡人英雄具有朴实之美的特性,他们用真挚的情感和无私的帮助谱写着一曲曲赞歌。在莫言的笔下,这种侠义文化所指代的对象包括冲破传统束缚的女性、勇敢无畏和豪情满怀的硬汉,以及平凡善良的好心人。正如宋剑华和张翼所说的那样:他们发展和传承了绵延久远的侠义文化,将民族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为读者揭示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英雄情结。[25]
六、冷艳的死亡文化
生与死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始终不能回避的两个问题,一般来说生的过程具有色彩和活力,而死亡的瞬间充满恐惧和阴暗。针对莫言的死亡命题,许多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第一,死亡叙事。莫言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描写死亡的场景,作者对死亡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字里行间都弥漫着阴郁和恐怖的气氛,揭示了生命的脆弱、人类的暴力和生活的苦难。白玉总结出莫言小说中死亡现象的特点和死亡叙事的产生机制和原因。[26]第二,死亡之美。一方面死亡带有悲剧性和残酷性,另一方面它也代表着灵魂的解脱、坚贞顽强的意志,具有飘逸、空灵和潇洒的特点。王禹丹指出了莫言死亡叙事的狂欢化风格,这种语言的自由运用使得死亡也充满了快感,死亡只是代表着灵魂的解放和对痛苦的解脱。王睿识认为莫言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之死带有壮丽的色彩,而且自杀式的死亡也反映了精神的拯救和解脱。[27]《檀香刑》中的孙丙虽是受刑而死,却展现了正义的力量,悲剧的背后是民族不屈的真实体现。第三,死亡叙事的相异性。针对死亡命题,许多学者将莫言和其他作家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了彼此的写作特色和风格。王禹丹对比了莫言和阎连科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方言书写,莫言描写了一波三折的生死传奇,阎连科的死亡书写却具有沉痛冷峻、一针见血的特点。[28]温伟针对莫言和福克纳小说中的死亡主题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他们小说的相似之处,即死亡是小人物生命解脱的方式,也是脱离苦难的途径。[29]
莫言认为死亡也是一种美,包括很多种类:有的充满暴力和血腥,有的让人感到压抑和混沌,还有的似乎是一种灵魂的超脱。[27]莫言的死亡观深受中国死亡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佛教文化认为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人死之后会六道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儒家文化认为人应顺天命,要死得其所,注重人生修养。道家思想认为人不应惧怕死亡,而应保持一个乐观和平和的心态,因为死亡是回归自然的最佳途径,是人类超脱和进入逍遥仙境的开端。因此在莫言的行文中,死亡时而带有惊悚之美,时而带有混沌和无声之美,时而又充满了神幻化的仙境之美。莫言作品中这种冷艳的死亡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血腥的杀戮。莫言非常擅长对杀戮的细节描写,他将血腥和暴力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将死亡的惊心动魄和极端残忍真真切切地描述出来,这种恣意的快感让人的各种感官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檀香刑》中对凌迟之刑和檀香刑的详细刻画让我们看到古代酷刑的残忍、嗜血和变态。《红高粱》中对罗汉大爷剥皮的描写,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二姑随后就到》中麻奶奶、大奶奶、七老爷爷、十四叔以及三伯的悲惨死亡带有施刑者的嗜血无情。(二)混沌的死亡。面对着残酷的世界,人类的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个人无法与外部力量相抗衡时,人就会变得消极和萎靡,最终用生命的终结作为无助的妥协。沉默和压抑的外在表现使得这类人物之死变得扑朔迷离,呈现出一种混沌和模糊的状态,旁观者无法说明他们死亡的真实情况和具体原因。《冰雪美人》中的孟喜喜,在他人的偏见和嘲讽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本性善良的她最终变得逆来顺受,在充满冷漠和指责的世界中无声地死去。《白棉花》中被男友抛弃的方碧玉,感情的创伤让她变得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最终棉花机里那个血肉模糊、死相凄惨的她不知是有意的自杀还是无意的操作。《梦境与杂种》中的混血女孩树叶,在他人鄙夷和有色的眼光中坚强地成长,但自信和乐观的她最终却不明原因地溺水身亡。这种无声的死亡过程体现了一种黑色、凄冷和孤独的美学特征,揭示了悲观主义的价值原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抑的厌世情愫和悲剧思想。(三)灵魂幻化。莫言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种死亡过程:幻觉和现实交错,真实和虚构杂糅,死亡最终带给人的是灵魂的超脱和对真相的回避。人世间的残酷让人感到痛苦和无奈,而此时死亡却能够带给人永远的安逸和舒适。当灵魂摆脱肉体飞向远方时,在无拘无束的神话世界中享受自由和欢乐。死亡对于《复仇记》中因偷吃东西而被枪毙的小毛孩来说,只是灵魂的腾空飞起,轻缓舒适的感觉让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欢乐。《拇指铐》中的阿义受到路人的百般折磨之后,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中飞向那条鲜花盛开、月光满地的天堂之路,并获得了永恒的欢乐和满足。《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中枪之后,感到自己就如小鸟一样在这片高粱地上飞翔,在五彩霞光的照耀下奶奶的灵魂从苦海中得到了幻化。莫言作品中的死亡文化充满了冷艳的色彩,这种基调是建立在杀人、自杀、莫名死亡和灵魂幻化等基础之上的,种种的死亡迹象表明命运也充满了终结之美。
七、悠远的乡情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莫言生在高密东北乡这片神秘和富饶的土地上,他用充满民间特色的语言描绘了家乡秀美的景色、淳朴的乡俗、悠悠的乡语以及睿智的乡识,并站在农民的视角上将高密的图景勾勒出来,[30]突出了其独特的地域和乡土色彩。关于莫言乡情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乡土生活。这一主题突出了地方色彩的刻画,描写了当地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乡间生活,展现了自然的原始生态。涂登宏对莫言小说的乡土特征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小说的乡土特征主要来自于作者的民间立场和乡土生活经历。[31]第二,乡村意识。乡村意识的形成是与长期的乡间生活分不开的,另外也受到历史文化和风俗传统的影响。在这种意识的左右下,作者会从农民的视角看待问题和进行艺术创作,展现乡村生活及风俗,揭示深刻的社会现实。王衍认为莫言的小说传承弘扬民间文化和民风民俗,从农民的感觉视角对故乡的生活进行描写,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农村生活经验。[4]第三,民间文化立场。民间文化立场意味着作为老百姓的代言人,以人民的姿态创作文学作品,反映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从而展示民间文化的审美特色。漆福刚以《檀香刑》为例,提出莫言以平民的姿态审视历史、社会、情爱和刑罚,用民间的立场展示民族的悲剧和人性的恶劣,表达作者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以及对民间自由生命的渴望。[32]
莫言认为民间写作就要突出个性化和自我意识,因此他笔下的乡情文化具有浓浓的中国民间色彩和地方特色,尤其是刻画了高密东北乡那充满生机和原始性的土地,这里是真实和虚幻的结合体,很多事物虽然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但是仍然保留着真实的痕迹,人文和生态的生动再现让莫言作品富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莫言作品中的乡情文化:(一)一川风月,即山河的美丽景致。莫言勾勒出高密东北乡特有的风光和韵致,这里到处都充满景色之美:《放鸭》中青草湖的水清澈见底,湖边鲜花盛开;《秋水》中漫山遍野的红高粱和玉米;《民间音乐》中槐花盛开、香气扑鼻的八隆河堤;《夜渔》中秋风习习、洒满月光的小河沟;《流水》中那片油汪汪的麦垄等都展现出具有清净自然和意蕴宁融的美丽世界。作者描绘家乡美景,表达了他内心真挚的乡情,高密东北乡成为作者写作的源泉,是他灵魂的栖息地,这种乡恋情节反映了作者的思乡之情。(二)奇风异俗。习俗是对当地文化和历史的反映,是民风的具体体现,奇特和迥异的民俗展现了独特的地域风情,同时也反映了某一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征。洪子诚认为:风俗将个人、社会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应了时代的特征,是地域性文化的完整体现。[33]莫言作品中的风俗景观体现在三个方面:1.高密特有民俗。《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和《金发婴儿》等作品中描写了野合的场景,野合指的是高密当地男女在田野中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红高粱家族》中也对“高粱殡”有过详细的阐释,指的是在高粱地旁为死者举行殡葬的风俗。2.普通生活民俗。《弃婴》中的童养媳,《翱翔》中的换亲,《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阴亲,这些都是落后农村非正常、非人性的联姻现象。《丰乳肥臀》中还描写了孩子要在土中出生的习俗,《五个饽饽》中展现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上供和接神的生活场景等。3.农村劳动习俗。《月光斩》中描写了打铁这一劳动过程,《售棉大路》中也对棉花的收购程序进行了逼真的刻画,《透明的红萝卜》反映了生产合作社时期人们的劳动模式,这些劳动方式是农村生活和生产状况的一个缩影。(三)悠悠乡语。口语、方言和具有乡土特色的语言与修辞让莫言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泥土气息,让人似乎置身于乡村之中,融化在这片充满原生态的民间世界里,呈现朴实之美。首先,莫言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民间和乡土特色的修辞表达。《生蹼的祖先们》中将烧得半熟的黄鼬比做黑丝瓜,将刺猬比喻成黑倭瓜,以及把行动缓慢的老婆比做老母鸡等。莫言利用农村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将对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这体现出莫言本身具有农民的思维模式,而且修辞手法的乡土化让作品充满了淳朴的生活气息。其次,莫言还运用了大量的谚语、歇后语和地方说唱形式来表现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檀香刑》中谚语和歇后语的运用,如“死知府比不上活老鼠”,“老鼠舔弄猫腚眼——大了胆了”等,[34]以及《生死疲劳》中顽童嘴中的顺口溜,《金发婴儿》中黄毛所唱的民谣,《天堂蒜薹之歌》中张扣的快板,《红高粱》中的茂腔等都展现了特有的乡土文化和地方特色。最后,莫言的作品具有口语化、通俗化和方言化的语言特色。《儿子的敌人》中“扎着小抓鬏”,[35]《石磨》中“噌噌地纳鞋底子”[36]和《红蝗》中到城里气(去)了”[37]等都反映了作者具有的乡村生活背景和民间生活经验。充满泥土气息的口语和方言表明了作者的农民身份,字里行间渗透着乡土文化的痕迹,同时莫言还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运用到作品当中,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对家乡和民间的热爱和赞美。(四)先人之明。在岁月的长河中,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莫言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前人的至理名言,它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饱含着生活的常识和智慧,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先人身上所散发的睿智之美。《麻风女的情人》中提到一句老俗话:“破茧出俊蛾”,[36]意思是丑陋的蚕茧中能生出美丽的蝴蝶,这里指的是麻风病夫妻虽然相貌吓人但他们的孩子却很健康、漂亮,古人留下的常识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红蝗》中提到一句古训“休了前妻废后程”,[37]本意是糟糠之妻不可弃,不然会得到报应,这里指的是四老爷休了四老妈使得全村人招致了灾祸。另外,先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大风》中爷爷向孙子提到的“灰云主雨,黑云主风”就是典型的例子,[36]天上有灰色的云彩,代表着天即将下雨,而如果是黑色的云彩,那么一般只会刮风。可见前人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智慧财富。这片充满悠远乡情的土地具有宜人的景色、传统的习俗、淳朴的乡语和睿智的乡识。它不仅展示了大自然的造物之美,也反映了文化和历史的内在精髓,莫言让读者置身于这片充满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的土地之上,一草一物和一情一景都让人徜徉其中,心醉不已。
莫言用豪放潇洒的文笔描写了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景观,以高密东北乡为创作原型,展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沧桑和生活原貌。从美学角度出发,我们发现莫言作品中的文化景观主要有七类:生态文化在生命、心态和物种三个方面呈现出自由性、异化性和收缩性的特征,展现出既和谐又病态的状态;畸形的生存和戏剧化的历史揭示了批判性的夸诞文化;宿命文化的深邃性通过苦情、苦命和苦泪来展现;魔幻的灵物、怪异的行为、离奇的巧遇和神秘的鬼魅则展示了迷离性的传奇文化;侠义文化涵盖了英雄女性、热血男儿及凡人英雄形象;血腥杀戮、混沌死亡和灵魂幻化使得死亡文化充满冷艳色彩;乡景、乡俗、乡语和乡识则传承着那份悠远的乡情文化。
[1] 李和平,肖竞.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中国园林,2009,(2):90-94.
[2] 肖笃宁,李团胜.试论景观与文化[J].大自然探索,1997,(4):68-71.
[3] 鲁枢元.生态文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46.
[4] 王衍.莫言写作与民间文化[J].安徽文学,2009,(7):322-323,322-323.
[5] 孟文彬.齐文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J].文学与艺术研究,2012,(8):66-72.
[6] 姬凤霞.从句式看莫言小说语言的民间口语化[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29-132.
[7] 王立,沈传河,岳庆云.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作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8] 乔力,李少群.山东文学通史(下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581.
[9] 高数藩.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89.298.
[10] 刘光远.莫言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7,(2):42-44.
[11] 周梦娜,肖薇.论莫言小说中的荒诞叙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113-116.
[12] 崔玉香.从苦难主题看余华对传统宿命观的承袭[J].山东社会科学,2006,(6):122-124.
[13] 彭在钦,段晓磊.深陷“围城”的女人——浅论《丰乳肥臀》与《无字》中女性的悲苦命运[J].剑南文学,2013,(1):42-45.
[14] 李晓亮.远未终了的悲剧——论莫言《蛙》[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4):56-58.
[15] 龙阳.莫言作品的人物分析——黑孩与赵小甲的奇幻世界[J].安徽文学,2007,(8):18-19.
[16] 张鹏飞.论莫言文学传奇话语的审美情趣[J].电影文学,2008,(18):134-135.
[17] 曾利君.论莫言的感觉与魔幻[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3):16-19.
[18] 郑恩兵,李琳.多重变奏下的魔幻现实——莫言小说的声音叙事[J].河北学刊,2013,(4):76-80.
[19] 杨杨.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39.
[20] 莫言.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45.
[21] 隋华臣.“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历史[J].名作欣赏,2013,(1):109-111.
[22] 巴俊玲.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主义情结[J].文学界,2011,(2):47-48.
[23] 朱永富.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中英雄形象为中心的考察[J].甘肃社会科学,2013,(2):50-53.
[24] 现代市民文化之诗意建构——以张爱玲、池莉和王安忆的作品为例[J].创作与评论,2013,(6):19-23.
[25] 宋剑华,张翼.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文学史意义[J].湖南大学学报,2006,(5):92-97.
[26] 白玉.论莫言小说死亡书写的表征及其形成原因[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91-95.
[27] 王睿识.三岛由纪夫与莫言的死亡意识比较[J].青年文学家,2011,(5):191-192,191-192.
[28] 王禹丹.镇魂曲的两种旋律——莫言与阎连科死亡叙事的方言书写[J].青年文学家,2013,(9):39.
[29] 温伟.论莫言和福克纳的死亡主题小说[J].名作欣赏,2007,(5):126-128.
[30] 张闳.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1999,(5):58-64.
[31] 涂登宏.莫言小说的乡土特征探讨[J].北方文学,2010,(3):33-34.
[32] 漆福刚.从《檀香刑》看莫言式的民间立场[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6):17-19.
[3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4.
[34] 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1-32.
[35] 莫言.与大师约会[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260.
[36] 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0,496,153.
[37] 莫言.食草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