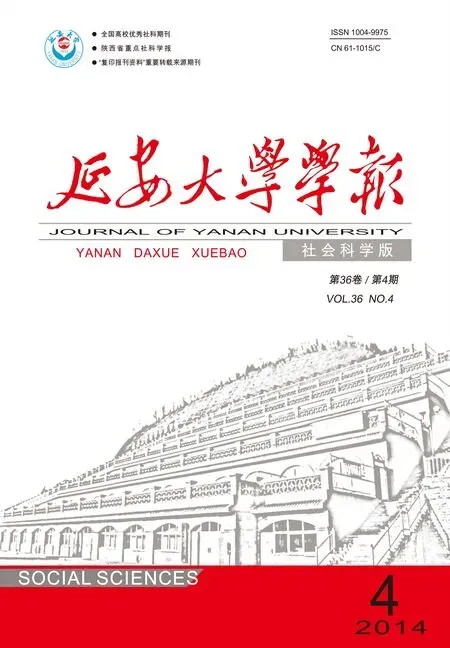论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的对外扩张
张鹤玲
(中国政法大学 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论智力,也许罗马人不及希腊人;论体力,也许罗马人不及高卢人;论经济能力,也许罗马人不及迦太基人。罗马人为何成就了“伟大属于罗马”的辉煌?本文从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权对外扩张中出发,希望看到古罗马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冰山一角”。
古罗马的公民权的对外扩张,是一个对“公民权”内容分割、分别授予的过程,这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智慧成功地起到了对异族的同化作用,在同化的基础上,罗马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继而推动了罗马社会的交流融合。
一、古罗马公民权概述
(一)公民权的含义
公民权反映了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具体而言,意味着个人在罗马城邦中的地位,即拥有公民权,就能够成为古罗马城邦中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享有包括公权利和私权利在内的一系列市民权。
公民权类似于现代社会“国籍”的概念,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权是一种特权,在罗马城邦元老院阶层、骑士阶层、公民、行省民、解放奴隶、奴隶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公民阶层拥有一定特权。也就是说,公民权“不只虚荣问题,其间有最实在、最宝贵的利益。凡非罗马公民不被认为丈夫、父亲;亦不能为合法的产主或继承人。非公民就在法外,有了这种资格,就进到正式社会。这就是罗马公民权的价值。于是这种资格遂成为人民极兴奋的欲望”[1]。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日益强盛,代表一定特权的公民权成为了颇有价值的财富,甚至存在意大利人将子女卖给罗马人,希望其子女可以成为罗马公民,可见,罗马公民权在当时的吸引力。当然,罗马人视公民权为珍宝,并非始终“大方”的对外授予,只是,罗马人智慧的通过分割公民权,达到其向世界性大国发展的目的。
(二)公民权的产生
古罗马公民权的产生与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不同于古代中国拥有广袤而肥沃的河流冲积平原,古罗马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其开展如古代中国那样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其农业生产水平也远不能和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相比。但正是因为农业生产难以满足古罗马的发展,罗马人才“另寻出路”,利用其处于台伯河商业要道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了当时的贸易枢纽。高度发展的商业吸引了周边的移民。罗马积极扩张,争取更多的土地,也吸收来自异族的融入者。对于其他部族的加入,罗马人展示了“友好”而非“敌对”的态度,授予其罗马的公民权,而不是设法奴役这些来自其他部族的“新成员”,这种最初产生的开放的公民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罗马公民权的对外扩张。
公民权的授予给了其他部族成员参与统治的机会,时刻扩大罗马城邦的规模,为日后罗马的强盛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公民权的内容
在古罗马,公民权与服兵役的义务以及拥有土地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三者构成了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公民权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了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法律权利(诉讼权),经济权利(参与公有土地分配权、税收上的优惠权、以及享有相关的社会福利),家庭身份权利(婚姻权、遗嘱权)等等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多项权利。
公民权广泛的内涵,尤其其公权利领域所包含的参与政治统治的权利,促使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的对外扩张中,在授予公民权时并非笼统的全面授予,而是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公民权的内容进行分层,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充分利用了公民权价值。
二、公民权对外扩张的原因
(一)古罗马的共和体制
古罗马的共和制政体构成公民权对外扩张的基础。
同样是古代文明的典范,罗马和希腊对待公民权态度却大相径庭。希腊是由多个城邦国家建立的,姑且以最为强盛的雅典为例,雅典观念中“公民”的资格是有严格的限制的。苏格拉底双亲都是雅典人,他拥有雅典的公民权;而亚里士多德出身马其顿,尽管他对雅典做出了杰出贡献,仍旧没有雅典的公民权。雅典社会为何如此封闭呢?因为雅典采用了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建立的基础就是有权者的平等,而一旦其他部族的人也可以平等参与雅典的统治,就会引发既存的雅典公民的不满,也会产生剧烈的利益分化,便会导致社会不安,所以,雅典采取了“闭国”策略。再对比古代中国,农业生产高度发达、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得普通民众无法享有可以同古代罗马相比的“公民权”。
罗马的共和政体则大不相同,和谐有序的权力制约机制——民众大会、元老院、执法官三者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元老院在古罗马统治中核心地位实质上表明罗马社会是贵族统治社会,这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会的民主。尽管罗马公民并非始终积极主动对外授予公民权,这其中推动力包括外国人的斗争,但是,罗马人无须担心“公民权”授予其他部族会引发剧烈的社会震动。反之,授予公民权,摒除了血缘纽带建立的封闭社会,代之以共同守护罗马意志的公民组成的的政治国家,罗马统治基础因此扩大,伴随着公民权的享有,承担服兵役义务的人数量有所增加。所以,在公民权问题上罗马人“最终超越了希腊人创造的城邦狭隘性的政治框架和希腊人意识的局限性。”[2]
(二)古罗马巩固统治的需求
随着古罗马的对外扩张,对广大的领域进行治理日益关系到古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巩固统治成为公民权对外扩张的动力。
古罗马共和国的强盛导致罗马公民权成了一种颇具价值的财产,其经济利益、政治利益都被外族人觊觎。其他部族人民、非公民和奴隶对罗马公民权的渴望,远远胜过现代社会外国人对美国绿卡的渴望。
在罗马征服地区,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被征服人民的归属感、对被征服地区的有效统治、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基础,分化原有敌对同盟等等问题的解决,罗马公民权成了有效的武器,通过在一定条件下授予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公民权,极大程度上达到了“分而治之”,同化异族的目的。在对外扩张中,打破原有被征服地的社会秩序,用公民与非公民的划分代替了敌与我的划分,成功地实现罗马统治的巩固。
(三)古罗马的宗教传统
在古典城邦时期,宗教传统对政治的影响极为显著,有相同的神灵信仰的部族,有着天然内在的认同感,基于这种信仰上的认同,“公民权”授予就存在宗教传统上的思想基础。
“罗马最初信奉的主神有三位:天神朱庇特、战神马尔斯、奎里努斯神。马尔斯是罗马人的部落神,奎里努斯神是萨宾人的部落神,两神在天帝之下共治,反映了罗马人和萨宾人的部落联盟关系。这促使罗马人在公共信仰方面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不仅纳入伊达拉里亚诸神,还大量纳入希腊诸神。罗马人在伊达拉里亚统治下,接受伊达拉里亚人信奉的三位主神为国家崇拜之神,天帝袭用了朱庇特之名,两女神朱诺为家庭和婚姻之神,米涅瓦为工艺与智慧之神。”[3]
由此可见,罗马人以开放的意识纳入了外来的神,可以说,罗马人的宗教认同感打破了异族之间差异的“栅栏”,对于信仰宗教的罗马人来说,授予相同信仰的人民公民权并非难事。
(四)无公民权居民的斗争
公元前493年,罗马人与拉丁同盟签订了“卡西安条约”*卡西安条约,也译为“卡西乌斯条约”。,这个条约确立了以平等权利为基础的同盟集团,条约中没有对统领地位的规定,但是,实质上罗马取得了军事统帅权,于是,平等的条约逐渐在罗马人的统领下变得不平等。罗马公民与拉丁同盟的人民权利义务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平等,拥有公民权代表着更多的权利。这种实质利益的不平等引发了拉丁同盟的不满,战争随即爆发,拉丁战争之后,拉丁同盟归属罗马,这就带来了罗马公民权的首次大规模的扩张。之后还有多次战争引发的公民权对外扩张。
可见,罗马公民权的对外扩张,并非完全积极主动的,尽管罗马人成功运用了扩张公民权的智慧,但是,并不代表罗马人一开始就愿意将公民权与其他部族共享。
综上所述,共和政体构成了公民权扩张的体制基础,巩固统治的需要是公民权对外扩张的强劲动力,而宗教传统则在思想上起到了促进作用,无公民权居民的斗争则构成公民权对外扩张的引力,四者共同作用,推进了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的公民权的对外扩张。
三、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对外扩张概况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成功的达到了对拉丁诸城和意大利人的实际控制,公民权也随即扩张。
古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城市分而治之,有效的分化了同盟,使得其利益起点有所不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具体而言,罗马人将拉丁同盟分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授予完全的罗马公民权、第二等级授予不完全的罗马公民权,这些被授权的同盟人民被称为“半罗马人”;第三等级是一般盟友,没有授予罗马公民权。
罗马公民权对外扩张的结果是,以公民权的享有为标准,对罗马境内的人进行了一下三个类别的划分:
首先,罗马市民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是享有市民法规定的各项权利的自由人,这种公民权通过出生取得和解放奴隶、奖赏、恩赐等其他途径取得。
第二类是拉丁人,拉丁人是一种法律身份上的概念,拉丁人根据享有罗马公民权的内容不同存在区别。第一,古拉丁人,这类人和罗马人在心理、文化、宗教、地理上最为“亲近“,故享有仅次于罗马公民的公民权,除不享有荣誉权之外,享有广泛的罗马公民权。第二,殖民地拉丁人,这类人不享有公民权中的公权利,即排除了其直接参与统治的机会;同时私权也受到了限制,例如,不被允许罗马市民通婚等,所以,殖民地拉丁人享有相对广泛的罗马公民权。第三,优尼亚拉丁人,在拉丁人中优尼亚拉丁人享有最少的罗马公民权,即同殖民地拉丁人一样,不享有公权利。同时,私权受到比殖民地拉丁人更为严格的限制,除受到殖民地拉丁人同样的限制外,最重要的限制是财产权不包括被继承权,因而,优尼亚拉丁人被称为“生而自由、死而为奴”的一类人。
第三类人是外国人,这类外国人更准确的称谓是“友邦人民”,外国人通过万民法规范,不享有罗马公民权,与敌国人相对立。
以上严格的公民权内容和层次的划分,体现了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理念。公民权的对外扩张不是积极主动的,而是一种被动扩张之后“吝啬”的智慧。
四、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扩张的作用
古罗马的公民权政策对共和国的兴盛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作用可以概括为同化作用、稳定作用和交融作用。
(一)同化作用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通过公民权的对外扩张,对异族人进行同化,使他们成为罗马的一部分,拥有守护罗马的意志,这种同化作用对于罗马发展成为世界性大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对于被征服者而言,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使之产生这样的一种效果,如克劳狄帝所言,“只要这些人的子孙还活着,他们对罗马的爱丝毫不比我们差”,即使这是帝国大帝的理念,但是在共和国时期同样适用。罗马征服过后,即使战败,罗马人依旧以政治家长远的眼光,接纳他们成为罗马的公民,而对于被征服的人民而言,从战败者到参与统治者的身份改变,使其很快同化进入罗马社会,并且积极参与社会的建设,“罗马共和国正以自己的宽厚政策为荣,常常得到她的养子的效忠和侍奉”[4]。究其原因,从同盟战争中外国人战争口号中可见一斑,“得到公民权,成为合作者,而不是被统治者”,可见,罗马市民之外的同盟者在内的其他部族的人对罗马公民权的渴望,他们希望得到进入罗马并参与统治的“门票”。
第二,公民权的对外授予,解决了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一旦获得罗马公民权,意味着,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人民,接受罗马的统治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其中缘由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加入某国国籍意味着接受该国宪法、遵守该国的法律制度,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承担该国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个国家对入籍者合法的统治。接受被授予的罗马公民权,意味着有资格进入并且已经进入罗马共和国先进有序的执政体制中,接受罗马的统治,既然是罗马公民,那么罗马的统治当然合法。
第三,授予公民权,人造了一种联系,这是先进的政治国家理念。公民权不是血缘纽带、不是地域联系、不是宗教认同、也不是种族归属,公民权是一种政治纽带联系,冲破血缘、地域、宗教、种族的限制,通过权利义务的授予,使得被征服地区人民成为古罗马的一员,臣服的意识迅速转化为稳定当地的重要因素,而后,这种稳定促进臣服的意识进一步发展为对罗马的效忠,心理上的同化较之古代中国战争之后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身份同化,更为持久。忠诚于罗马——这一心理认同感,使得政治国家较之血缘纽带的氏族群落稳定而和谐。征服后授予公民权,使得罗马统治者免于奔波在广大的领域上治理社会,只需利用当地的资源,同化其人民成为罗马公民,即可达到统治的目的。
(二)稳定作用
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的对外扩张,不仅仅达到了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同化作用,同时也稳定了罗马的统治。同化作用是达到稳定的基础,而稳定又进一步促进了公民权的对外扩张,逐步形成了“扩张——同化——稳定——再扩张”的良性循环,使得罗马向前发展的脚步铿锵有力。
第一,对外授予公民权,扩大了罗马的统治基础。首先,罗马公民人数急剧增加。拉丁同盟战争后,罗马公民人数从公元前339年的165000人扩大到公元前319年的250000人。据不完全统计,后来意大利人的加入,罗马公民的人数从公元前86年的463000人达到了公元前69年的90万人。还有,罗马的统治稳定的基石更为深厚。这些“新”的公民,是以一种政治统治参与者的姿态加入罗马的,不同于简单的被征服地区人民,“罗马公民”——这一身份上的认同使得公民自觉地守护罗马的意志。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战场上骁勇强悍,而繁荣国祚不及罗马绵长,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没有将以往的敌人和公民的关系加以稳定,而是区别对待,这种不稳定的基础使得统治的根基不及罗马深厚。因此,横向而言,罗马对外公民权的授予使得公民人数增多;纵向而言,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使得统治深入根源。
第二,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使社会分层的流动性增强,罗马社会进一步稳定。通过授予公民权,参与罗马社会阶层流动的人员基础扩大。罗马的社会分层流动性相对于希腊,相当高。古罗马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据说很多元老院其祖先便是解放奴隶出身,根据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高度流动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现代中国社会,也借鉴古罗马的智慧,提高公民意识、提高社会流动性,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三,罗马公民权对外扩张,不是笼统的授予,而是经过了精致的分层,并非全部授予完全的公民权,而是根据与罗马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授予不同层级的公民权。这种对外“分而治之”的理念,一方面摧毁了原有的敌对同盟,使其利益出发点有所不同,难以形成统一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排除了短时间大规模享有平等公民权的公民数量激增,由此带来的对现有小城邦基础上建立的共和制的冲击。所以,罗马公民权对外扩张的过程,也是对被征服地区进行“分而治之”的过程,体现了罗马人的统治智慧。
(三)交融作用
通过授予公民权,罗马人将“你们”与“我们”的界限模糊,代之以平等的“公民”概念,促进了罗马社会的交流融合
首先,授予罗马公民权无疑会使罗马吸引大量的人才。罗马公民权对那些非罗马公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即成为这座城的属民,“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公民权受到更大的关注和敬仰的了。罗马不像人类有记录的任何社会一样,把社会简单地分割开。罗马,你广泛地授予公民权,建立亲密的关系。世界的有智之士,有勇之士都承认你的领导权,聚集在你的联盟之下。无论广阔的海洋,还是崎岖的大地都无法阻止公民权的扩展。无论是亚细亚还是欧罗巴,他们在你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整体。在你的统治下,路路相通,在你的统治下,没有一个有才能,有品德的外邦人被排斥在外。世界性的公民社区被创建起来,我们都被融合在统一的社区之中,享受着我们应得权益。”[5]这种公民权的吸引力,类似于今天美国绿卡对部分精英阶层的吸引力,吸引力源自于罗马社会或者美国社会在同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但二者的性质却存在根本性差异。大量人才的进入,无疑对罗马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了贡献,这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又进而吸引了更多人才,这个良性的循环就是公民权对外扩张的交流作用。
另外,罗马公民权的对外扩张,促进了文化的交融。授予公民权,不仅仅是身份上的改变,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内心对罗马社会政治文化的认同,当他们自称“罗马人”的时候,罗马的征服真正胜利了。新的公民对拉丁文化的认同,对罗马政治体制的认同,对罗马市政规划的认同,促使一批类似于罗马的城市的建立,推动了拉丁文化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拉丁文化吸收了更多的其他部族的文化,这种交流成了文化发展繁荣的催化剂。
总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共和国公民权的扩张是罗马人摸索和探寻的过程。公民权对外扩张的同化作用是其首要目的,也正是在同化的基础上,才保障了罗马社会的稳定,继而加深了交流,促进了罗马的繁荣。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的对外扩张推动了城邦罗马向大国罗马的发展。罗马的公民政策是重要的国家政策,公民权,对罗马国家而言是一种管理政策,对于罗马人民而言是一种权利认同。公民权的对外扩张表面上是罗马公民人数的激增,实质上是罗马政治文化思想的渗透,是罗马共和国统治者实现对被征服地区同化、稳定和交融目的的重要动力,是理解罗马发达政治文明的一个角度。
所以,罗马人的智力、体力、经济能力也许都不是一流的,但是,发达的政治智慧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伟大属于罗马”。
参考文献:
[1]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316.
[2]徐新.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1.
[3]王振霞,田德全.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J].北方论丛,2005(4):89.
[4]爱德华,吉朋,席代岳.罗马帝国衰亡史[M].台湾:联经出版社,2004:33.
[5]Nicolet C.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trans[J].PS Fall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Timothy J Lukes,198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