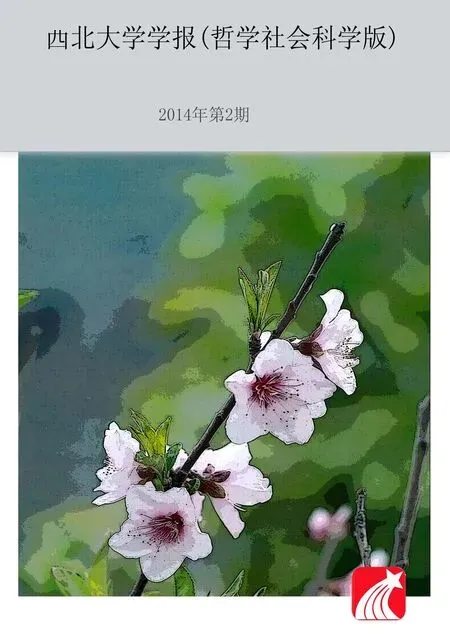中美就业反向歧视的存在基础比较及借鉴
杨云霞
(西北工业大学 法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72)
对于反向歧视一词,界定众多,根据《美国传统英语词典》,反向歧视是对占主导地位或多数人群体的一种歧视,尤其指产生于为纠正对少数族裔群体或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歧视而制定的政策中的歧视[1]。美国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以下简称Title VII)的初衷旨在消除职场对特定群体如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歧视,在其实施后的数年中,雇主们相继采取了法院授权的肯定性行动、自愿性肯定性行动或非自愿性肯定性行动,给予少数族裔群体优惠待遇以消除歧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起,白人男性基于此提起了第一例就业反向歧视的诉讼,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至今已有大量的诉讼案件出现,相当一部分反向歧视的诉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而在中国,尽管也有反向歧视的媒体报道,但真正的反向歧视案件并未出现。究其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基础及社会条件存在差异。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关注肯定性行动这一问题,反向歧视被作为肯定性行动的一个结果加以研究。而对于作为一种独立问题存在的反向歧视来讲,对其存在基础的研究是纠正就业歧视的根本所在。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比较分析,试图对我国纠正就业歧视、完善反歧视立法提供一点思路。
一、美国司法中认可反向歧视的基础
(一)法律基础
1.法律并不认为肯定性行动是必然合法的目前,美国对于《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11号公约)等均没有加入,这些公约中所包含的暂行特别措施自然不是美国的法律渊源之一。而且,从美国政府或雇主现已采取的肯定性行动措施来看,无论是政府合同还是雇主实施的法院授权的肯定性行动、自愿的或非自愿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有很多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的,如1941年罗斯福的8802号行政命令、1961年肯尼迪的10925号行政命令、1967年约翰逊总统的11375号行政命令等,而非根据国际公约或国内成文法或判例法授权的。所以,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对于因为采取肯定性行动计划等平权措施而产生的反向歧视之诉,自然无法借法律授权或合法性依据之名义来驳回其诉讼。
2.民权法等法律提供了认可反向歧视的空间在某些法案下,不存在认可反向歧视的可能,如1990年的《身心障碍法案》或称《美国残疾人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简称ADA),因为对于普通人,无法证明自己因为非残疾而受到反向歧视。但在Title VII和1967年《反对就业年龄歧视法》(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以下简称ADEA)下则存在认可反向歧视的法律空间。Title VII旨在保护所有的人免受歧视,无论其种族、性别,这其中包含的意思必然是白人男性同样受到反歧视的保护。在法院审理McDonald v. Santa Fe Trail Transportation Company案时,就是援引了Title VII而认定雇主构成反向歧视。继该案之后,任何人基于种族或性别而遭受歧视均可依据Title VII主张其权利。在ADEA中,规定了受保护的群体是40岁及以上的人。但在各州的成文法中则不尽然,有大约29个州的立法中没有界定受保护的年龄,或界定为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或18岁及以上。所以,在这些成文法下,反向歧视的主张极有可能成立,事实上,有些原告的确胜诉了[2]。
3.大量的司法判例确认了反向歧视的违法性由于美国各个法院对反向歧视的界定不完全相同,所以使得就业反向歧视案件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第一类是由于雇主或国家采取了肯定性行动,从而导致原有的多数人群体认为被反向歧视,大多数的案件属此类;第二类是由于原有的多数人群体没有被纳入到反歧视立法保护范围中,所以认为被反向歧视,这其中不存在肯定性行动[3],如McDonald v. Santa Fe Trail Transportation Company案中,白人认为自己被解雇而黑人受到Title VII的保护没有被解雇,法院认可了反向歧视的存在;第三类是认为由于雇主的宗教信仰而导致非同一教派的雇员遭受歧视,由于这不同于传统的由于雇员的宗教信仰而被雇主歧视,所以也被称为反向歧视,如Noyes v. Kelly Services案中,原告诉称公司的主管只提拔和主管自己属于同一个宗教组织的同事,而不提拔她,所以她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反向歧视[4]。本文主要研究与肯定性行动有关的就业反向歧视案件。
从美国已有司法判例来看,与肯定性行动相关的反向歧视案件出现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一是白人(或男性)雇员或应聘人诉称:少数族裔(或女性)雇员或应聘人依照自愿的肯定性行动基于其种族或性别得到了优惠待遇,而自己因此被歧视;二是白人(或男性)雇员对非自愿的肯定性行动提出质疑:对于司法上证明了的歧视,法院授权的救济导致了用优惠待遇来补偿少数族裔(或女性)雇员。这在就业中是很典型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雇主基于种族或性别而作出决策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说,反向歧视的诉求很多时候是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一大挑战。第三种情况是,提出申诉的白人(或男性)雇员诉称:只有少数族裔(或女性)获得优惠待遇,并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甚至“良性”动议都是没有必要的[5]。
在上述几种类型案件的司法判决中,已认定了多起反向歧视原告胜诉,这些判例的存在,使得反向歧视具有了判例法意义上的法律依据。根据美国劳工部(DOL)的报告显示,1990—1994年间,在3 000例以上的就业歧视案件中,有约100例反向歧视诉讼[6],尽管这一数字很小,但很多案件的判决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如从已有的案件及裁判结果来看,目前法院已认定了反向种族歧视、反向性别歧视,而对于反向年龄歧视仍存在争议。
(二)理论基础
在美国,反向歧视诉讼之所以被认可并频繁出现,其理论的支撑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歧视的肤色色盲理论(Colorblindness Theory)。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1883年,在Pless v. Ferguso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力排众议,在这一著名的民权案件中,写下了美国宪法史上的一句名言:“美国宪法是色盲,它既不知道也不容忍在公民中划分等级。在享有民权方面,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卑贱者和高尚者都一视同仁。当涉及由国家最高法律保障的民权时,法律只论人而不考虑他的背景或肤色。”[7]今天,肤色色盲理论日臻完善,它的含义源自公平概念,它很少甚至根本不涉及历史或社会条件。在该理论下,Title VII被认为是“完全地禁止就业中的种族歧视,当雇主在作就业决策时,禁止其考虑种族因素,无论是白人或黑人。”事实上,在严格的肤色色盲假设下,偏袒传统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种族——少数族裔的法律也将被视为不公平。该理论认为,对白人男性的歧视和对少数族裔以及妇女的歧视一样严重。所以,该理论禁止采取任何形式的肯定性行动,相应的,它完全认可反向歧视的存在。
当然,并非所有理论都支持反向歧视,被保护阶层理论(Protected Class Theory)则与肤色色盲理论针锋相对。该理论的含义源自歧视的现实世界的状况(包括历史的和现代的),源自相关法规的历史承接性。例如,该理论认为Title VII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雇佣机会的均等并减少歧视性的实践及策略,因为这导致了职业环境的种族分层,对少数族裔产生了不利。”该理论认为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比对白人男性的歧视更严重。所以它完全认可肯定性行动而排斥绝大多数的反向歧视诉求[8]。
事实上,这两个相对立的理论并非仅仅是针对反向歧视而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理论目标的不同,即是让某些目标群体获得结果的平等还是形式上的平等,是实现社会领域中各群体之间长期的动态的平等还是短期的静态的平等。
(三)社会基础
在美国,就业中的反向歧视案件之所以数量较多,与其历史环境及社会现实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漫长的种族歧视历史,造成了种族间的极度不平等以及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而且造就了社会多数人群体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分层。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政府最早倡导实施肯定性行动。20世纪30年代,美国首次使用了肯定性行动,对早期的工会成员、工会领导者、退伍老兵和残疾人长期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进行干预,把他们优先安排纳入劳动力市场。尽管如此,对于缺乏福利国家价值观念的美国,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和形式上平等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范围实施纠正种族歧视的肯定性行动,但由于多数人群体已经习惯了固有的优势地位及获取优势资源,而肯定性行动本身就是对这一优势地位观念的颠覆与重建,因而在实施肯定性行动不久后的20世纪70年代便出现了第一例反向歧视诉讼,进而出现了反对纠正种族歧视的浪潮。如1996年底加州政府通过公投,决定政府不再基于种族、性别等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团体;1997年,加州大学公开宣布废除肯定性行动政策;2006年,密西根州也通过了“全面废除肯定性行动”的提案。这实质上是政治化的种族、性别问题在法律领域的反映。
二、中国不存在反向歧视的基础
在中国,有着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意识传统和立法理念:认可并强调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在法律领域注重弱者保护,在反歧视立法中强调形式平等,逐步开始运用暂行措施调整就业制度层面的不平等。目前,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反向歧视都仍缺乏存在基础。
第一,法律确认了特殊措施的合法性,导致基于特殊措施的行为很难被认定为反向歧视。这里的特殊措施包括两类:一类是暂行特别措施,另一类是特殊保护措施。首先来分析暂行特别措施的合法性。目前,我国已加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妇女歧视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就业政策公约》等,这些公约中或多或少都对暂行特别措施作了规定:一方面,公约规定了对所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不得视为歧视;另一方面,国际公约作为我国的法律渊源之一,为暂行特别措施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我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暂行特别措施也都是以国内法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基于此,暂行特别措施的实施不会引发反向歧视的诉讼。其次分析特殊保护措施的合法性。基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理念,我国分别针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法。此外,在《劳动法》中对于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专门作了特殊保护规定。所以说,就业中特殊保护制度在中国的合法化,使得基于特殊保护而提出的反向歧视的诉求难以成立。
第二,暂行特别措施的实施很有限。在《就业促进法》中,第17、18条规定对于安置残疾人的企业、残疾人自办的企业、失业人员自办企业等给予税收优惠、经营场地等方面的照顾,并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第28条规定就业中“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第52条提出了对就业困难人员“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办法,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等途径,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但对基于性别、民族、种族等的就业歧视,无论是政府或企业所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仍很少。即使是实施上述措施,也只是在很小的领域中惠及极少数的群体,尚未在意识层面构成对原有强势群体反向歧视的冲击。目前对女性、农民工等群体的歧视仍是就业歧视的主流,基于此社会现状不可能提出反向歧视诉讼。此外,就业歧视案件进入诉讼的障碍也是反向歧视案件尚未出现的重要原因。
三、研究反向歧视对于中国本土的借鉴
尽管中国尚欠缺反向歧视的存在基础,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立法实践层面,都有着借鉴价值。
(一)纠正理论研究中的偏差
目前,国际上对反向歧视的定性尚不统一,如有人认为只是一种偏见,有人认为已构成歧视。在反向歧视与肯定性行动的关系中,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肯定性行动的结果造成了反向歧视,也有人认为肯定性行动和其他优惠措施本身就对多数人群体构成了反向歧视,还有人认为肯定性行动并不产生反向歧视,而是一种补偿性正义(compensatory justice)。而且,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于推进不歧视的方式在名称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即使在同一国家,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其名称的使用上也存在争议。在英文名称中就有很多,如Compensatory justice(补偿性正义)、Differential treatment(不同待遇)、Employment equity(公平就业)、Positive action(积极行动)、Positive discrimination(积极歧视)、Positive measures(积极措施)、Preferential policies(优惠政策)、Reverse discrimination(反向歧视)、Special measures(特别措施)、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暂行特别措施)、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动)等[9](P51)。在诸多名称中,如何选择使用,笔者认为,应使用符合本国语言习惯以及语境的词汇,从积极的正面制定及实施反歧视制度,这样更有利于纠正歧视而非制造新的歧视或产生歧义。此外,当前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界定错误,如有人提出了应“建立反向歧视法律制度以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消除歧视”,显然是将间接歧视与反向歧视混为一谈。所以,对反向歧视的研究对于纠正理论研究上的偏差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为合理的暂行特别措施的出台提供反向借鉴
暂行特别措施之所以从起始之初就不断遭到反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缺乏一套完整的评定机制,如怎样合理地判断和证明弱势群体、措施实施的社会效果、措施应终止的时间节点等。即使从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也缺乏统一的标准。所以,反向歧视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完善暂行特别措施的契机。
在美国,法院通过对反向歧视案件的研究以及司法实践,逐渐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完善肯定性行动或自愿性计划的指导方针,如在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v. Weber案中,法院创设了私营部门的自愿性计划的指导方针:(1)计划必须反映成文法的目的,即计划必须给少数族裔开启就业机会,以打破种族隔离的旧有模式;(2)计划不能不必要地妨碍其他雇员的利益;(3)计划必须是暂时性的,它应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即一个劳动力市场大体上实现了多数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种族平衡时。在Johnson v. Transportation案中,法院进一步对肯定性行动提出了指导方针:(1)肯定性计划的设计,旨在减少机构中因传统职业种族隔离而导致的劳动力不平衡;(2)计划不能妨碍男性雇员的权利或给他们的就业设置绝对的障碍;(3)不能侵犯一个工作的“绝对的授权或法定期待”;(4)肯定性计划的目的是达到劳动力的平衡,而不是维持这一平衡[10]。此外,在对自愿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审查中,司法中形成了两种标准:一是宪法标准,采用严格审查制(strict scrutiny);二是Title VII标准,采用中间审查制(intermediate scrutiny)。这些指导方针及审查制度,比《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所规定的“此等措施的后果不致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个别行使的权利,且此等措施不得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和“不得因此导致维持不平等的标准或另立标准;这些措施应在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的目的达到之后,停止使用”更为具体,也更有可操作性。
当然,美国救济歧视的措施中也有一些反面的教训是值得借鉴的。如肯定性行动中的配额制,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违宪的质疑,在Bakke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苛刻的僵化的种族配额制(strict and rigid racial quota)是违宪的[11];而临时的“量身定做”的配额制(temporary and “narrowly tailored” quota systems)则是允许的,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Paradise案中,美国阿拉巴马州警衔晋升中的“每提升一名白人警官也相应地提升一名黑人警官”的配额制则被判定是合法的。
目前,我国针对特殊群体所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还较少,但是,这并不是说反向歧视问题的研究在我国没有必要或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政府在履行其国际公约义务的过程中,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时推出一些措施救济歧视。这就必然涉及到其合理性问题,以及是否存在引发反向歧视的不恰当因素,所以上述肯定性计划的指导性原则或标准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暂行特别措施以纠正歧视,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为就业平等权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对就业反向歧视的认可或反对实际上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平等就业权中的平等,它是一种起点的平等、规则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如果认可反向歧视,在群体层面上,实际上就是对历史上本已处于弱势地位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因为修正已有歧视的暂行特别措施必然带有差别待遇的成分以补偿历史上对这一群体的“亏欠”,对反向歧视的认可必然引发对暂行特别措施的干预与调整。如果不认可反向歧视,承认暂行特别措施的合法性,在个体层面上,则必然面临着强势群体中的个体的平等权受侵犯的问题,正如反向歧视的支持者所强调的“不能以牺牲现实世界的个体的平等权为代价来弥补历史上的不平等,这无疑会制造新的不平等;由现实生活中的并未歧视他人的白人个体来偿还历史上对黑人群体的欠债,这对白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基于这一两难困境,对平等就业权的合理解释则极为必要。本文认为,平等不是绝对化的平等,应是抽象平等与具体平等的统一,是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的统一,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12],是历史平等与现实平等的统一,是动态平等与静态平等的统一。只有基于这一思路,才能彻底纠正业已存在的就业歧视,并真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一点对于我国反对就业歧视制度的建立及其实施极为必要。
参考文献:
[1] EDITORS.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4th e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00.
[2]WILLIAM C.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s 2003 Term: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Disparate Impact and Reverse Age Discrimination [J].Labor Law Journal,2004,(2).
[3]ARRINGTON P L. Not always protected: Reverse ag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General Dynamics Land Systems, Inc. v. Cline [J].UMKC Law Review, 2005,73(3).
[4]ZACHARY M K. Reverse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J]. Supervision, 2008,69(4).
[5] BELL M P, HARRISON D A,ACLAUGHLIN M E. McLaughlin. Forming, Changing, and Acting on Attitude Toward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in Employment: A Theory-Driven Approach[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0,85(5).
[6]ROBERT L. Brady,Reverse Discrimination: Lawsuits Are Rare [J]. HR Focus,1995,72(19).
[7]KEITH E. Sealing, The Myth of A Color-Blind Constitution [J].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1998(54).
[8]DAVID S. Schwartz, The Case of the Vanishing Protected Class: Reflections on Reverse Discrimination, Affirmative Action, and Racial Balancing [J].Wis. L. REV. 2000(11).
[9李薇薇,Lisa Stearns.禁止就业歧视: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 GULLETT C R. Reverse Discrimination and Remedial Affirmative Action in Employment: Dealing with the Paradox of Non-Discrimination [J].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2000,29(1).
[11]MONROE S. Does Affirmative Action Help or Hurt? [J]. Time,1991,137(21).
[12] 蒋先福,彭中礼,王亮.“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法理学思考——以平等理论为视角[J].时代法学,2006,(3).